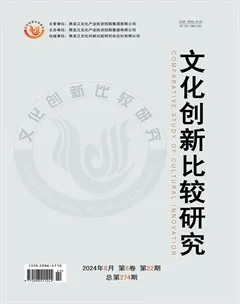亚瑟·韦利《论语》翻译的跨文化互释
摘要:海外典籍译者是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力量,他们凭借对中国文化的热爱和严谨的学术精神,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海外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英国20世纪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亚瑟·韦利是20世纪上半期蜚声世界汉学界的中国典籍译者,一生致力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介绍,1938年出版的《论语》译本是其中国哲学典籍翻译的代表译作。该译本注重历史文化背景考证、呈现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形象、挖掘儒学核心术语意义,译本出版后深受西方读者欢迎,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该研究聚焦于韦利《论语》英译本的深入剖析,旨在通过对其翻译策略与阐释精神的系统分析,为中西文明交流互鉴有所助益。
关键词:《论语》;亚瑟·韦利;典籍英译;阐释;儒学术语;孔子
中图分类号:H315.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a)-0152-05
Cross-Cultural Interpretation of Arthur Waley's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bstract: Overseas translators of Chinese classics are an important force in the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nd they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ut of their love for Chinese culture and rigorous academic spirit. Arthur Waley, a distinguished Sinologist and translator of Britain in the 20th century Britain, was a leading figure in translating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century. He dedicated his life to promoting and introducing Chinese culture and his translation of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in 1938 stands as a representative example of his work in translating Chinese philosophical classics, which is characterized by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 the presentation of the real image of Confucius in the history of China, and the exploration of the meaning of the key terms of Confucianism, has significant implications for the dissemin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This paper is aimed to provide examples and references for the exchanges and mutual learning among civilization by means of the systematic analysis of its translation strategy and interpretation.
Key words: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rthur Waley; English translations of Chinese classics; Interpretation; Confucian terms; Confucius
中国哲学典籍蕴含着丰富的古代人民对于生活的思考与智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通过梳理中国典籍走向世界的历程,发掘世界上重要的中国典籍译者的成就,梳理中国文化在世界各国传播的历史与轨迹,已经成为当前学术要务。英国翻译家亚瑟·韦利的《论语》译本1938年出版后就在英语世界大受欢迎,被誉为自理雅各译本之后最成功的译本。在文明互鉴的背景下,发掘韦利译本中的翻译策略和阐释精神对于中国文化传播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1 韦利翻译成就介绍
亚瑟·韦利(1889—1966)是20世纪蜚声世界的中国典籍译者和汉学家,其将《道德经》《诗经》及《论语》译成英语并出版,题目分别为The Way and Its Power(1934年),The Book of Songs(1937年)及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1938年)。此外,他还著有《中国古代思想的三种方式》(Three Ways of Thoughts in Ancient China,1939年)先秦思想史研究专著,深度剖析中国思想面貌。韦利还投身于中国古典诗歌及小说翻译工作,作品有《汉诗一百首》(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1918年)及《西游记》(Monkey: Folk Novel of China,1942年)的摘译,其作品考据严谨,语言精准且通俗易懂,文本丰富,极大地促进了中西文化的交流,深受学者赞誉。美国当代知名哲学家、汉学家、中国典籍译者美国乔治城大学教授艾文贺(Philip Ivanhoe)指出“在母语为英语的译者当中,韦利(Arthur Waley)在一些方面树立了高标准,因为他对古汉语有着很好的理解力,同时又是个非常优秀的英语作家”[1],不仅肯定了韦利的汉语功底,而且对其翻译的影响力予以了高度认可。
2 韦利《论语》译本的翻译策略与诠释精神
韦利的《论语》译本于1938年由伦敦乔治艾伦·昂温出版社出版,译本中韦利承袭了英国上一代汉学家理雅各、苏慧廉、翟林奈等译介结合、释证相济的翻译模式,不仅注重译介结合,还融入了释证相济的方法,并创新性地提出了《论语》成书的“历代层累说”,并且能够针对注疏不一致的地方,依据语境给出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具有重要的突破性和创新性。这一做法为之后的汉学家雷蒙·道森(Raymond Dawson)、大卫·辛顿(David Hinton)等所仿效,成为欧洲汉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文献资料。在此基础上,韦利打破了之前译者将《论语》视为神圣的儒家经典的传统做法,而将其视为特定历史条件记录中国历史与文化的文本。韦利在导言中明确提出其塑造孔子形象的依据——国学大师顾颉刚(Ku Chieh-kang)提出的“一个时期一位孔子”(One Confucius at a time)的原则,尽可能在译本中还原了孔子在《论语》中的形象[2]。译本中采用了清代考据学的诠释方法,并参考了清代儒学大家的注疏、民国学术研究的实证性进路,旨在恢复最初《论语》编纂者的意图,呈现成书时的社会形态,迎合了英语世界读者了解中国社会的需要,得到了中外评论家的一致好评。评论家西门·华德(Walter Simon)就指出“(《论语》译本)可能是他(韦利)所有贡献中最为成功的贡献,可能今天,甚至出版后30年,从各个方面来说,都是汉学最好的入门著作”[3],这一评价对韦利《论语》译本的质量表达了充分赞誉。
2.1 注重历史文化背景考证
韦利强调“思想源于环境”,重视文本考证。他认为《论语》翻译需要全面分析中国早期社会及对于外界刺激的反应,但受限于资料匮乏及当时的考古困境,他仅能根据零散信息安排内容,不能保证连贯逻辑,但在翻译中他结合了当时中国的最新考古发现,深入介绍了《论语》的成书背景。
韦利的译本由导言(Introduction,67页)、正文与注释(151页),附录(30页)三部分构成。附录中对一部分译文细节的处理进行了说明,包括“前言”“解释”和“纪年法”等。导言中韦利对孔子的生活背景、推崇的古人、同时代的人物、孔门弟子、《论语》的成书及版本问题进行了详细介绍,并选取其中的一些关键儒学术语进行了介绍。该书附录的第一部分对《论语》的注疏传统和《论语》开创的语录体的写作传统进行了回溯,并附有孔子年表、译文注释、索引等。同时,韦利对《论语》涉及的中国古代相关的书写传统、古代礼仪、服饰、丧仪、艺术等内容进行了梳理。这种做法不仅有利于读者了解儒家思想的演变,也使读者对诞生这种思想的中国的社会历史有了深入的体会。众所周知,理雅各的《论语》译本以“厚翻译”著称,使用了较长篇幅对《论语》的成书和注疏传统进行了介绍,重在呈现历代学者的不同见解,适合对中国文化背景具有一定程度了解的西方读者。然而,理译本对于《论语》的成书背景着墨不多,仅用9页进行了介绍。同时,理氏译文中对人物背景的介绍较少,更多注重字词的训诂解释。相较起来,韦利对于《论语》的背景介绍所用的篇幅较多,附录中对中国古代的文化传统进行了全面呈现,更适合初步学习中文和对中国缺乏了解的普通读者。整体上看,韦利的《论语》翻译参考了大量的中国古典文献,文字的训诂和历史考证是该书的重要特点。通过查阅译文中的注释,可以发现韦利参考到的文献不仅有儒学典籍中的《诗经》《孟子》《礼记》《书经》《荀子》《易经》《中庸》《孔子家语》等,还参阅了《韩非子》《墨子》《淮南子》《道德经》《庄子》《列子》等其他诸子文献。同时,还涉及其他历史典籍,如《后汉书》《周礼》《国语》等。不仅如此,对于历代《论语》的注疏,韦利则涉猎汉宋,主采唐清两代注解,据朱峰考证,“韦利参考的文献涵盖了18世纪和19世纪的清儒,选择性地吸取朱注,对宋学敬而远之,而对汉唐清主张求实的学者则极为青睐。他的中文底本主要是《集解》,一些章节的语义辅以《义疏》和《集注》,另一些章节的词义参考唐朝和清朝的训诂学著作”[4]。
在翻译中,韦利“采取了‘历史性翻译’的方法,努力进入到文本产生时的社会历史语境中,增加对该时期历史的认识,其语境构建具有明显的内部视角特征”[5]。这是因为在韦利看来,历史背景的介绍有助于读者深入理解《论语》文本。在韦利的《论语》译本中,无论是“哀公”“伯夷”“叔齐”这一类古代君主与贤士,还是“尹文子”“季康子”等重要的历史人物,韦利都在脚注中对他们的身份与背景都做出了详细注解。这种做法极大地提升了读者的阅读体验,使他们能够跨越时空阻碍,进一步领略《论语》所承载的中国古代的历史与文化。
以《论语·宪问》中的一句为例,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高)后于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韦利通过对比分析历史文本,考证出第一句中的“为”并非常见的介词用法,而是历史上一个重要人物臧武仲的弟弟臧为,韦利进一步考证出这一事件的历史背景,即公元前550年,臧武仲因涉及谋反罪而被鲁国流放。在流亡途中,他成功夺下名为“防”城这一城池作为据点。随后,臧武仲向当时鲁国的国君鲁襄公传话,表示如果鲁襄公同意其弟臧为接管“防”地,他将主动放弃该地,并继续前往流放之地,随后鲁襄公接受了这一提议。
在此基础上,韦利给出以下译文:“The Master said, Tsang Wu Chung occupied the field of Fang and then demanded from (the Duke of)Lu that (his brother) Wei should be allowed to take the field over from him. It is said that he applied no pressure upon his prince; but I do not believe it”。这一考证符合真实的历史,之前的译者理雅各虽然注重中国注疏,但是对于这一史实的解读出现了错误,理氏的译文为:The Master said, "Tsang Wu-chung, keeping possession of Fang, asked of the duke of Lii to appoint a successor to him in his family. Although it may be said that he was not using force with his sovereign, I believe he was"[6]。理氏误将“为”做虚词“为了”理解,将其译为“to appoint”,未能体现“将防地交给臧为”这一事实,出现了明显的漏译。
民国时期的《论语》译者辜鸿铭对该句的译文处理如下:Confucius, speaking of a powerful noble of his native State, remarked, "He took possession of an important military town when sending a message to the prince to beg him to appoint a successor to his own family estate. Although it is said that on that occasion he did not use intimidation with the prince, his master I do not believe it"[7]。对于细节的处理也出现了明显的误译。韦利的这种严谨的考据精神获得了Raymond Dawson、许渊冲等人的赞许,他们在各自的《论语》译本中也采纳了韦利的译法,瓦尔特·西蒙认为对《论语》文本考证性的研读彰显了韦利的学者身份。
再如,《论语》的8.3章: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夫,小子!”韦利的译文是:“When Master Tseng was ill he summoned his disciples and said, Free my feet, free my hands. The Song says:...But I feel now that whatever may betide I have got through safely, my little ones”。这里较为关键的是“启”字,韦利将其译为“free”,表达“解开”之意,理雅各根据朱熹注疏,译为“uncover”,意为“打开”。韦利通过考证《礼记》和《后汉书》中有关“启”字的用法,指出《礼记》有“人之将死,需有四人将其手脚抓住”的传统,《后汉书》也提出“人死后要将其手、脚松开”,韦利同时引用了人类学家詹姆斯·乔治·弗雷泽《原始宗教中的死亡恐惧》一文的说法,认为在古代人们之所以抓住将死之人的手脚,是由于担心死者的灵魂会复活。同时,也援引了高延在《中国的宗教体系》中提到的中国远古社会也有人死前会被捆住手脚这一习俗,只是到后来才逐渐演变为在人死后才会被捆住手脚的这一传统。此处,韦利认为《论语》这一段话中的“启”解释为“松开”,是因为“曾子为避免在临死之时手脚被人抓住而失了体面……因此希望在其真正面临死亡的时候能够被平静对待,不希望弟子再抓着自己的手脚”,由此可见,韦利能够引用中西方的相关历史文献对于中国古代的习俗进行考证,如实再现中国历史文化。
2.2 呈现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形象
韦利从事中国典籍翻译的时代,正处于英国汉学从传教士汉学到学院派汉学的过渡时期。英国的第一代专业汉学家理雅各出于传教的需要,利用基督教对中国的儒家思想进行批判,认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孔子过于复古和保守,对于当时的政治制度和社会现实缺乏足够的认识,是一个“异教的领袖”和造成中国落后的根源。理雅各之后的英国第二代汉学多为曾经在中国充当外交官的典籍译者,这一类的译者有《论语》的译者苏慧廉和翟林奈等。翟林奈根据自己的理解,将《论语》中主题相近的章节归入同一个主题之下进行了重构。然而,即便如此,他们对儒家思想的评判也都未能跳脱宗教的禁锢,对儒家思想的认知包含了批评。
韦利对《论语》的翻译摆脱了传教士和外交官译者的文化偏见与局限,其译本不仅参考了《论语》的历代注疏,还积极吸纳了民国时期“疑古”学派的最新研究成果。在《论语》译本导言中,kqk/r8eOxq/f/DYrKhL71A==韦利深刻剖析了孔子形象的历史变迁,他指出自汉代起,孔子被逐渐神圣化,塑造成为一位全知全能且道德无瑕的圣人典范形象,尽管这种塑造或许并未全然贴近孔子真实面貌,但是《论语》文本本身却是理解孔子最为直接的材料。韦利在导论就明确表示,他所探讨的孔子具有重要的学术前提,即基于杰出学者顾颉刚所倡导的“一个时代一个孔子”的重要原则,而且他所建构的孔子形象乃是基于《论语》内容塑造出来的——“一位四处游历失落的精神导师,最终成为一名成功的外交官和政治家”。韦利指出,尽管人们可以依据传说等构建一系列的孔子形象,但是通过对儒家思想中关键词的演变、《论语》成书的情境和各个《论语》版本的考证,在他看来,孔子不再是一名道德之师,打破了之前西方流传的孔子的“智者”“复杂问题的解答者”“先知”“巫师”等形象。依据韦利的说法,在《论语》中人们可以看到孔子这名失落四处游历的“导师”不仅劳心于自己国家事务,而且对邻国事务也同样关心。尽管在游历的过程中,孔子推行“仁”的主张难以得到各国统治阶层的认同,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孔子积极践行,他是一名有关“道”的知识的传播者,而不是理雅各所构建的“创造者”的形象。韦利在前言中指出,“孔子是一名私人教师,他对出身于士人阶层中的后辈展开针对他们出身的德行的教育。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孔子对自己的位置并不满意,更渴望得到一个面向公众的教师职位。”在韦利的笔下,孔子不再是一名落后的宗教领袖,而是一个步下圣坛的民间教师形象。
综上所述,在对《论语》的翻译中,韦利以《论语》为史料,梳理孔子的生平轨迹,从而使这位古代帝王眼中的圣人与儒家弟子心目中的至圣先师,以一种鲜明的平民形象走向西方读者,“他笔下的孔子,是一位理性、务实、谦和、睿智、具有饱满人格的‘先师’”[8]。
2.3 挖掘儒学核心术语意义
“《论语》的翻译传播路径可以简单概括为儒家哲学意义的不断重新阐释”[9]。为了呈现《论语》在创生之时的原初含义,韦利十分注重挖掘儒家核心术语意义。在译文正文的前面,韦利专门撰写了一章内容对儒学术语的含义的演变进行了介绍,其中涉及“仁”“道”“德”“士”“君子”“孝”“文”“信”“思”等。此外,韦利还特别注重《论语》文本内的相互佐证和《论语》同一时代典籍之间的旁证,并结合西方文化中相似的语言现象加以印证。韦利“力图突破以往那种针对不同语境而对相同概念采用不同翻译的方式,取而代之以一个词对应另一个词,一个概念对应另一个概念的诠释方法”[10]。韦利对“仁”的翻译采取的是统一的译文,这是由于他对“仁”的考据采取的是归纳与演绎相结合的方法,这种方法很大程度上受到清代学者王念孙和王引之的解释方法的影响,一般情况下,对于字的含义考据主要依托《说文》《尔雅》这类权威训诂著作,然后结合需要诠释的文本进行“本证”,并结合该著作同时代的其他典籍予以“旁证”,这种方法被现代著名学者周光庆先生命名为“归纳演绎法”。在这种方法的关照下,韦利首先从词源出发,选取了《说文》和《诗经》进行考证,并指出在《道德经》译本中,“仁”的本义是“族人”,族人之间的亲近感由此生发出“相人亲”的本义,并采用《说文》来将“仁”理解为“亲”的含义,该义与“民”相对。韦利结合英国文化,将“人是某一宗族的一分子”视为对人的最高赞誉,并结合《诗经》中的“美与仁”进行说明。韦利结合《论语》中与“仁”相关的篇章,如“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克己复礼为仁”“仁者不忧”“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等,对“仁”含义的演变进行了梳理。
众所周知,先秦时期,“仁”为众德之一;在孔子的儒学中,“仁”既可指众德之一,也可用作统帅诸德的“全德”,指的是人生最高道德原则和人生理想;宋明理学中,“仁”指的是宇宙本体论中的最高范畴和人的根本存在,又可用作绝对的道德理性或道德本体;清代重视考据考证,恢复“仁”的原义,指的是众德之一。韦利结合中国的历代典籍,指出“仁”具有一定的抽象性,难以用确定的词来传译,但最终结合通篇的考虑,选取了可以涵盖多种美好品质的首字母大写的“Good”来表示,以区别于用小写的“good”表示的“善”。这种考据方法与韦利的“客观求真”、恢复文本本意的原则基本上是一致的,这样做有助于将中国的古代文化真实有效地呈现在西方读者面前,从而使西方读者能够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和中华文明。
3 结束语
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典籍英译也是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历程,梳理典籍翻译历史不仅有助于洞察西方对于中国文化了解的过程,也是实现全球共同进步的重要途径。亚瑟·韦利的《论语》翻译就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缩影,该译本注重历史文化背景考证,呈现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形象,重视核心术语意义考证,促进了20世纪上半叶中国文化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并为中西文明的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本研究通过深入分析跨文化背景下韦利《论语》英译本的翻译策略与阐释精神,旨在发现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进路,期待其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范例,并为中华文明传播和中外文明交流互鉴服务。
参考文献
[1] 吕剑兰.中国哲学典籍的翻译与传播:美国汉学家艾文贺访谈录[J].中国翻译,2022,43(5):102-107.
[2] ARTHUR W.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London: George Allen &Unwin[M].New York:Macmillan Company,1938:14.
[3]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J].Fiftieth Anniversary Volume,1967(1):268-271.
[4] 朱峰.西方汉学家17个《论语》英译本之底本探析(1828—2007)[J].国际汉学,2020(3):101-112,203-204.
[5] 吴冰,朱健平.阿瑟·韦利英译《道德经》中的历史文化语境重构[J].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2019(2):91-97.
[6] 理雅各.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第一卷)[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195.
[7] 辜鸿铭.辜鸿铭论语心得:精编典藏版[M].重庆:重庆出版社,2015:55.
[8] 李冰梅.冲突与融合:阿瑟·韦利的文化身份与《论语》翻译研究[D]. 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09:189.
[9] 范敏.新时代《论语》翻译策略及其传播路径创新[J].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9,27(3):94-98.
[10]高志强.“去圣”与“一词一译”:阿瑟·韦利的《论语》导论研究[J].中国文化研究,2013(1):3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