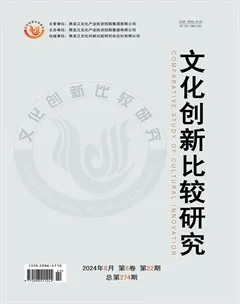连动结构“S.+V1+NP+V2+(NP)”中V1功能转换现象考察
摘要:该文运用原型范畴的理论及先行研究成果,探讨汉语语法中连动结构“S.+V1+NP+V2+(NP)”中V1的功能与介词功能发生转换的现象。基于现代汉语基本句法结构关系,先对连动结构“S.+V1+NP+V2+(NP)”的内涵与范围进行界定。从形态句法层面上看,连动结构“S.+V1+NP+V2+(NP)”中“V1”“V2”出现的顺序,与话语中事件发生的时空排列顺序相关,使得介词义取代“V1”的原型义成为可能。从话语功能层面上看,连动结构“S.+V1+NP+V2+(NP)”中“V1”的功能与介词发生转换受到话语层面隐喻过程的影响,使得“V1”原型义不再稳定而呈现“V1”去范畴化的现象。从语义角色、话语层面对“V1”功能变化现象的成因进行分析,可以进一步论证认知中话语的倾向性与语言中动词和介词转换现象有密切关联。
关键词:动词;连动结构;原型理论;范畴化;去范畴化;话语功能
中图分类号:H1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8(a)-0032-05
An Examination of the Phenomenon of V1 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the Linkage Structure "S.+V1+NP+V2+(NP)"
Abstract: Applying the theory of prototypical categories and the results of prior research,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phenomenon that the function of V1 in Chinese grammar the linking structure S.+V1+NP+V2+(NP) is transformed with the function of prepositions. Based on the basic syntactic structural relations of modern Chinese, the connotation and scope of the linking structure S.+V1+NP+V2+(NP) are first defined. From the morphosyntactic level, the order in which V1 and V2 appear in the linking structure S.+V1+NP+V2+(NP) is related to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arrangement of events in the discourse, which makes it possible for the prepositional meaning to replace the prototypical meaning of V1. From the discourse functional level, the function of V1 in the linking structure S.+V1+NP+V2+(NP) is influenced by the metaphorical process at the discourse level, which makes the prototypical meaning of V1 unstable and presents the phenomenon of V1 de-categorization. The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roles and the discourse level of the causes of the phenomenon of the change of the function of V1 can further argue that the tendency of the discourse in cognition is closely related to the phenomenon of the conversion of verbs and prepositions in the language.
Key words: Verbs; Linking structures; Prototype theory; Categorization; De-categorization; Discourse functions
陆俭明在《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1997)中指出,“研究语法形式的时候要找到语法意义上的根据,而研究语法意义时要有语法形式上的表现”[1]。
Lord和Carol(1973)对西非语言位置动词为什么会经历语法范畴的变化进行讨论,得出序列结构中位置动词短语在语义上不如其他动词短语重要,并且它在语法上失去了动词的地位,只剩下一个虚词。Li和Thompson(1974)从次动词角度,对汉语中连动结构中的次动词就是介词进行论证分析。Hopper和Thompson(1984)从形态句法层面分析了动词进入连动结构后,当它不能在结构中起着报道一个动作行为的功能,而表达的是抽象的愿望或者对未来的预测,它就无法发挥自己原型功能。
Hopper(1991)提出了“去范畴化”的概念:“去范畴化,即经历过语法化的形式,趋向于丢失或抵消包括形态标记和名词、动词的独特句法特征等,承担起形容词、分词、介词等次范畴的属性特征。”[2]简单来说,就是范畴化将动词或名词本身的原型意义归为一类,成为一个整体,去范畴化是使它们在原型义的基础上丢失掉一些功能,但范畴化与去范畴化也还是局限在表达词类的外在形态句法特征。
综合以上研究成果,发现Lord和Carol(1973)是从西非语言入手,并未涉及汉语例子的证据;而Li和Thompson(1974)是先将连动结构中第一个先出现的动词V1界定为次动词,再通过现代汉语和古代汉语的例子来证明,连动结构中的次动词就是介词。Hopper和Thompson(1984)及Hopper(1991)仅从形态句法层面对不同语言中连动结构的动词的形态句法特征进行简要对比分析,并没有将其引入话语层面进行进一步的分析。由此,连动结构“S.+V1+NP+V2+(NP)”中的V1就是介词,是因为在交际过程中,受到人们意识活动的影响,逐渐由一个对行为动作的报告原型义,转变为表达一些抽象的选择、指示义,因此变得不再像动词,而成为一个介词。
要对连动结构“S.+V1+NP+V2+(NP)”中动词与介词转换方面进行形式与意义的考察,需对其研究范围进行限定。首先,“连动结构是指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性词语,包括动词语素、动词及动词短语的连续排列,中间没有停顿,没有关联词语连接,并且按照动作发生的时间先后项序或事理逻辑顺序排列,在连续排列的动词性词语之间形成一定的句法语义关系或逻辑语义关系 ”[3]。其次,对共时层面的连动结构中V1范畴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当按照一定的原则进入连动结构的V1发生变化时,比如“你叫食堂少做点饭”中的动词遵循时间顺序原则依次呈现在序列结构中,但由于语义重心的变化或者受到人的意识活动的影响,“叫”的动词原型义逐渐虚化成了介词。
1 连动结构中的动词
朱德熙《语法讲义》(1982)“连谓结构”中的“谓”主要指的是谓词,但谓词又包含着动词和形容词。本文讨论范围仅是在连动结构中动词性词语的使用,不包含形容词性词语。连动结构中语素排列有明显的时间先后顺序和逻辑顺序,这同时也是其结构最本质的特征。先通过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进行简要了解,比如,“递给我一杯水喝”中,当说话人对听话人传达自己的意愿时,要是先发出“喝水”的动作,再出现“传递”意愿,那么这个行为就不太符合事理逻辑,并且,当“喝水”与“传递”意愿颠倒时,不仅不符合汉语SVO语序的语法,也颠倒了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在此,本文主要讨论的是连动结构中两个动词之间的关系,所以,将连动结构描写为“S.+V1+NP+V2+(NP)”,把位于其前面的动词记为V1,位于后面的动词记为V2。
1.1 连动结构中具有动词原型义的V1
1.1.1 在序列结构中遵循时间顺序原则
时间的流动性与运动变化是同时进行的,要想充分揭示连动结构中动词介词转换现象的动因,首先关心的是动词是如何在结构中表现它的时间特性的,尤其是在连动结构中的表现上。戴浩一(1988)对汉语的“时间顺序和语序问题”做出了深刻分析,首先,论证了汉语语序内部成分的排列遵循了“时间顺序原则”(The principle of temporal sequence,即PTS);其次,指出“当两个汉语句子由时间连接词连结起来时,第一个句子中事件发生的时间总是在第二个句子之前”[4]。 这个原则同样也可以用到连动结构中V1和V2先后关系的验证。动词在结构中出现的先后顺序,虽然仅从例句表面很难看出明显的时间顺序,但通过事件发生的先后顺序,以及起始动作附带的伴随动作,也是可以看出连动结构中的动词本身出现的顺序遵循着“时间顺序原则”的。例如:
例1:她对着镜子理头发。
例2:把帽子往下拉一拉。
例1和例2中,当“理发、下拉帽子”等动作行为在序列结构中位于前边时,那么整个结构的语义中心也会发生偏移。动词的任务是报道事件发生的行为动作,如果序列结构中V1和V2位置出现了颠倒状况,一方面不符汉语SVO的语法逻辑,另一方面动作行为会出现不连贯的情况,也就不符合事理逻辑了。
1.1.2 在序列结构中标记空间关系
事件的发生有先后也有伴随,但要基于一定的空间里才得以实现,限定了动词出现的空间范围,对其出现在连动结构中的特性也就能够更精准地定位。崔希亮 (2001)从共时和历时层面对“汉语的空间关系”进行了深刻分析,指出“在现代汉语中,空间方位关系的表达有介词和方位词两种手段”[5]。在对连动结构进行考察时,发现“S.+V1+NP+V2+(NP)”中,V1倾向于为V2引出事件发生的空间位置。例如:
例3:你叫食堂多做点饭。
例4: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
例5:在礼堂开会。
例3中,当V1表施事时,包含“使令”义的动词“叫”引出其后的“食堂”,此时的“食堂”既是V2的施事,也是做饭所发生的具体地点。所以,当动词进入连动结构中时,除了在表层形式上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动词无停顿地连续出现,以及动词或动语素在句法语义逻辑上的关联,还有从空间视角分析时不可忽视的时空紧密联系程度。在限定好的“S.+V1+NP+V2+(NP)”结构中,有“使令”义的动词“叫”一定要开始在“做饭”之前,并且要持续到“做饭”这个动作完成之后,同时,“叫”所对应的事件发生地点与“做饭”行为发生的地点是同样的,至此,“你叫食堂多做点饭”这个连续发生的行为才算真正完成。例4中“留”取其动词原型义“保留,留下”,为后半部的“能有柴来烧”提供了“青山”的地点作为参考。例5中在“开会”后并未衔接更多的补充,通过V1“在”的指引得知开会所发生的空间位置。
1.2 连动结构中失去动词原型义的V1
Hockett(1945)首次对次动词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次动词在句子中用来标记名词指称物,包括:(1)将后面的名词指称物与前面的指称标记相连;(2)暗示名词指称物与句子其余部分的关系。”[6]丁声树在《现代汉语语法讲话》(1961)中对次动词的语法功能做了简要阐释:“首先,次动词大都不做谓语里的主要成分;其次,次动词后面总要带宾语,而且一般是体词性宾语。”[7]Li和Thompson(1974)也进一步阐明连动结构中的次动词在语义上更接近介词,并通过汉英对照翻译证明连动结构中的次动词是真正的介词。
连动结构“S.+V1+NP+V2+(NP)”中,当V1不同时,就有可能会出现不同的语义解释,对V1真正成为介词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例如:
例6:a.他跪下来求我;
b.他跑过来求我;
c.他走过来求我。
同样是做出“求”的行为,展示自己目的意愿的行为可能会出现(a)句,出现持续性或者暂时性的动作行为可能会出现(b)句,当选择权在自己身上,就有可能会出现“跪”“跑”“走”等动作。
动词最根本的语义特征是不稳定性,当它在结构中不能通过自己的原型语义表述当前发生了什么的时候,就会丧失掉自己词汇的原型特征,只剩下表达信息的功能。例如:
例7:a.她在卧室里;
b.她在厨房里;
c.她在客厅里。
例8:a.她在卧室里吃饭;
b.她在厨房里吃饭;
c.她在客厅里吃饭。
同样是“在”,例7中“在”用的是动词的原型义表示“存在”,传达的是一个动作行为,但例8中“在”由于后面出现了“吃饭”这个动作,即当前动作已经由“吃饭”这个动词传达出来了,那么V1“在”就不需要重复使用其动词的原型义,而是出现了原型义虚化的现象,并仅用作描述当前发生的信息,表示事件发生的场所。
2 连动结构中V1与介词的语义差异
2.1 “S.+V1+NP+V2+(NP)”中的“真”“假”V1
在“S.+V1+NP+V2+(NP)”结构中,V1和其后NP的关系影响着V1演化为一个真介词,首先将能够进入连动结构中的NP分为具体和抽象两类,对于NP指代事物的不同,V1也产生了不同的含义。引出了具体事物的V1在连动结构中属“真”,而引出了抽象事物的V1在连动结构中则变为介词,属“假”。例如:
NP描述具体事物:
例9:挨着工厂修路。(挨:靠近,紧接着)
例10:按下这件事不说。(按:按下,搁下)
例11:当客人看待。(当:作为,当作)
例 12:给根烟儿抽抽[8]。(给:给予)
NP描述抽象事物:
例13:挨着次序放好书包。(挨:顺着次序)
例14:按制度办事。(按:依照)
例15:当着大家面说清楚。(当:面对着,向着)
例16:他爹给人抬着送回来。(给:当“被”字用)
通过例9—例16的对比,发现,连动结构“S.+V1+NP+V2+(NP)”中V1和其后的NP在语义上有着紧密关联。当NP描述的是一个具体的事物,比如“工厂、客人”,那么V1需要一个具体的含义对行为动作做出一个报告,此时的V1就发挥着动词的原型功能。当NP描述一种抽象的事物,比如“次序、制度”这种倾向于虚幻的、摸不着的东西,那么V1则会更向介词含义靠拢,会更多地呈现“选择”“指示”等抽象义。
除了V1与其后NP的具体和抽象关系,还有当NP具备时空义时,V1的含义也出现伴随变化,此时的V1则出现了介词含义。例如:
例17:朝学校走去。(朝:表示动作的方向)
例18:从窗缝里往外望。(从:表示经过,用在表示处所的词语前面)
r7uecxf9UOxUKZbOLqLXiA==例19:从北门进入校园。(从:从……或者拿……作起点)
例20:我起北京来。(起:放在时间或处所词的前面,表示始点,相当于“从”“自”“由”)
例21:水顺着山沟流。(顺:沿,依)
例22:消防员和村民们同森林火灾进行了长时间的对抗。(同:引进比较的事物,跟“跟”相同)
对比例17—例22,还发现,当连动结构中V1后的NP具备时空义的特征时,此时的NP仅在其中作时间或者地点的指称物出现。因为话语真正传递的语义中心已经发生了偏移,真正表示动作的只剩下V2,例如“走去、往外望”等,此时的V1已经从有实在意义的动词含义,变成了表示引进、指向、动作方向等虚化了的介词含义。
2.2 “S.+V1+NP+V2+(NP)”中“真”V1与介词的语义角色
通过表层形式的区分,很难在连动结构中准确识别出“真”V1与介词,所以,将关注的中心转移至连动结构“S.+V1+NP+V2+(NP)”中NP和V2之间的语义关系上。一方面,V1的语义角色影响着NP和V2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NP在连动结构中充当的语义角色对于V1真正转变为介词也有着重要影响。如前文例3“你叫食堂多做点饭”,例句中的“叫”具有使令义,在结构中的语义角色为施事,为动词。但当以下例句的语义角色出现时,V1在结构中的原型义更容易遭到削弱,从而转变为介词。例如:
例23:有事要跟群众商量。
例23中,“群众”是“跟”的受事,此处“跟”又用来引出动作的对象,成为一个介词。
例24:用那把刀切菜。
例24中,“刀”具有了工具义,而其工具义的出现,正好又是工具介词“用”所引出的。当“S.+V1+NP+V2+(NP)”中的NP是具有时空义的词语或者表示空间义的专有名词时,V1的含义则发生了虚化现象。例如:
例25:上北京开会;
例25中“北京”和“开会”为空间上的联系,那么“上”则由本身的原型动词义转变为指向抽象的处所。
3 连动结构中V1和介词转换现象的话语因素
上文对动词和介词进入连动结构中形态句法上的表现进行分析,并从它们在连动结构中充当的语义角色角度进一步区分,但单从形态句法层面的考虑还是不足以支撑该现象的真正成因,所以,继续将其引入话语层面进一步的阐明。
首先,Lord和Carol(1973)指出:“人们倾向于根据事件发生的地点、导致事件发生的手段、发生的方式及接受者或受益者来理解事件。这反映人们在交流中使用的结构,正是这些语义格关系最有可能在序列结构中表达出来——然后,最有可能由一个新的范畴——介词来表示”[9]。比如,例19中“从北门进入校园”,和例23中“有事要跟群众商量”,以及例8中的“她在卧室里吃饭”。从话语层面来分析,当说话人采取的话语是听者取向时,如例19,说话人想要主动让听话人从话语中了解到“从哪里进入校园”时,那么便不会用具有原型义的动词来描述,而是用带有指向性的介词来引入指称物。
其次,Hopper和Thompson(1980)对于形态句法层面的语法和语义事实的各种体貌特征,引入了话语层面的理解:“说话者根据他们对听者情况的评估做出的决定有关,关于如何表达他们必须说的话”[10]。词类层面的转化与话语层面的变化紧密联系,没有话语层面的隐喻过程,将抽象处理成具体再进行输出,动词所谓的范畴性就很难存在在形态句法的概念中。比如,例13“挨着次序放好书包”和例14“按制度办事”中,假设说话人说出这两句带“命令”形式的话语时,要想让听者能准确定位自己话语中的主要信息,说话人说出的话语就会带有重心,那么此时的动词“挨”和“按”受到说话人主体意识的影响,倾向于表示接下来话语中动作行为的趋向,而不是用它们的动词原型义单纯地报道事件。
因此,这也与Hopper和Thompson(1984)中提到的观点类似,“话语越不需要一个语言元素来报道一个事件或引入一个实体以进行潜在的话语操纵,它就越不容易被标记为语言普遍指定承担这一功能的范畴的成员”[11]。通过与连动结构中动词介词转换现象相关联,可以发现,当连动结构“S.+V1+NP+V2+(NP)”中V1并不需要通过本身的动词原型义来操控外在对话语的理解时,它本身的原型义也就没有用处了,那么,此时也就正好符合Hopper和Thompson(1984)提到的“范畴性假说”,即不再属于自己的原型范畴一类,可以自由地变化外在形态。
4 结束语
连动结构“S.+V1+NP+V2+(NP)”中涉及的动词,在描述动作发生时遵循实际事件发生的历程及逻辑上的先后顺序,是连动结构“S.+V1+NP+V2+(NP)”中的V1和介词之间产生变化的首要条件。连动结构“S.+V1+NP+V2+(NP)”中V1和NP语义关系关联紧密是V1保持动词原型义的必要条件,当NP描述的是抽象事物时,V1则不再发挥其原型功能,产生去范畴化的现象,转而变为一个具有虚化义、指向义的介词。连动结构“S.+V1+NP+V2+(NP)”中V1功能和介词发生转变的现象是交际过程中认知变化的结果,在语言使用者表达其话语内涵完整性不受损害的前提下,NP的语义重心在语境中发生偏离也会动摇V1在句子中的语法地位。所以,当连动结构“S.+V1+NP+V2+(NP)”中的V1受听者取向的影响,且V1所涉及的NP仅涵盖了整个事件中的某个层面,那么V1后的NP便可能未得到说话者在认知上足够的重视和认同,相较于那些语义重心位置上的事件,它们在说话人的主观意识中显得并不那么至关重要。那么V1在连动结构“S.+V1+NP+V2+(NP)”中所占据的语法地位就会发生相应的转变,它原有的动词原型范畴或将被取代或者丢失,从而被介词的功能特性所取代。
参考文献
[1] 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61-62.
[2] HOPPER P J. On some principles of Grammaticalization[C]//ELIZABETH C T,BERND H.Approaches to Grammaticalization. Vol 1.Benjiamin: John Benjamin Publishing Company,1991.
[3] 洪淼.现代汉语连动结构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4.
[4] 戴浩一,黄河.时间顺序和汉语的语序[J].国外语言学, 1988(1):10-20.
[5] 崔希亮.语言的认知与理解[M].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209-219.
[6] 丁声树.现代汉语语法讲话[M].北京:商务印书馆, 1961:95-96.
[7] LI C N,THOMPSON S A. Co-verbs in Mandarin Chinese: Verbsor prepositions? [J].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1974, 2(3):257-278.
[8] 朱德熙.语法讲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160-173.
[9] LORD C. Serial Verbs in Transition[J].Studies in African Linguistics,1973(4):269-97.
[10]HOPPER P J,SANDRA A T.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J].Language,1980,56(2):251-299.
[11]HOPPER P J,SANDRA A T. The Discourse Basis for Lexical Categories in Universal Grammar[J].Language,1984, 60(4):703-7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