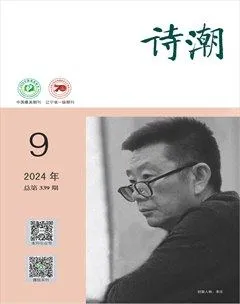生命的时代属性与现代性表达
一
如果要全面了解一个诗人的创作,而不只是获得粗浅的印象,就应该把他的作品放在时间的链条上考察,而不是以某个时间段的单一文本作为依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避免那种单向性的风格确认,从而更细致地看到他的“变”与“不变”,在“变”中发现他的思想脉络,在“不变”中把握他的艺术风格。这一点在杨克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作为第三代诗人中的代表诗人,他的诗歌创作和编辑生涯都是引人注目的。他主编的《中国新诗年鉴》系列,曾参与并见证了新时期“民间诗人”与“知识分子”的诗学之争,影响和风光一时无二。在这里,我无意梳理那场诗学论战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那是当代诗歌史研究者的工作;我想说的是诗人的诗歌创作。阅读杨克从20世纪80年代到当下的诗歌,我读出了诗人创作的时代属性和现代性表达。
诗人与时代的关系,不是那种被动地卷入,而是始终有一种主动拥抱并与之同步的热情和内驱力——自觉地融入时代,而不是游离于它之外;自觉地为时代歌唱,而不是拒斥它;自觉地表达对时代的关注和疑虑,而不是刻意修饰或屏蔽它。在这种生命与语言自觉的敞开中,诗人写出了生命在线性时间中的曲线律动,写出了他与时代互见互证的亲缘关系,写出了一个诗人在历史发展变化中的个体感受与民族性回应。
杨克的诗歌有鲜明的物质性,而这一点,恰恰和改革开放以后整个民族心理发生重大改变的现实产生了同频共振。20世纪80年代,他赞美热火朝天的工地,赞美在工地上“三名小憩的女工”(《蝶舞:往事之三》);他赞美“水与火两种绝对不相容的元素/在事物的核心完美结合”的石油,说“石油是新时代的马匹、柴、布、喷泉/金苹果,是黑暗的也是最灿烂的/今天石油的运动就是人的运动”(《石油》)。他赞美的都不再是远离生存基本元素的政治符号,而是具体可感的物质和物质创造。这是诗人以诗歌的方式传递那个时代的精神取向,是诗人以情感的流淌印证那个时代的激情四射。可以这样说,这样的诗歌创作不再是单纯的诗歌活动,而是那个时代的哲学和心理学,是那个时代用物质的指标重新解读社会与经济、生命与理想的文化表达。
诗人见证的广州,是物质的前沿,他笔下的天河城广场,是物质的集散地——“而溽热多雨的广州,经济植被疯长/这个曾经貌似庄严的词/所命名的只不过是一间挺大的商厦/多层建筑。九点六万平米/进入广场的都是些慵散平和的人/没大出息的人,像我一样/生活惬意或者囊中羞涩/但他(她)的到来不是被动的/渴望与欲念朝着具体的指向/他们眼睛盯着的全是实在的东西/哪怕挑选一枚发夹,也注意细节”“假若脖子再加上一条围巾/就成了五四时候的革命青年/这是今天的广场/与过去和遥远北方的唯一联系”(《天河城广场》)。把广场从宏大叙事的政治话语中解放出来,让它回到商业性和消费性共存的生活现场,让它以本来的嘈杂与喧嚣替代政治赋予它的严肃与整饬,让人间烟火的琐碎与柔软替换政治言说的庄重与锋利。这不仅仅是那个年代的生活实录,更是诗人对人世版图物质化和生活化的确认。
90年代初,为了实现与时代精神高度吻合,诗人甚至唱出了“生命本身也是一种消费/无数活动的人形/在光洁均匀的物体表面奔跑”“现代伊甸园 拜物的/神殿 我愿望的安慰之所/聆听福音 感谢生活的赐予/我的道路是必由的道路/我由此返回物质 回到人类的根/从另一个意义上重新进入人生/怀着虔诚和敬畏 祈祷/为新世纪加冕/黄金的雨水中 灵魂再度受洗”(《在商品中散步》)。今天看来,这样的声音是偏执的。我们当然清楚,拜物教是一种异化的“宗教”,只是,这种认知并不是和历史并行的认知,它似乎永远滞后于历史的发展。当我们开始批判它的时候,它前期的合理性和荣耀被遮蔽了。要理解这种情绪,我们必须回到诗人曾经经历的时代现场,以历史考察历史,而不是后知后觉地质疑与否定。在这首诗里,诗人描述的场景和心理都曾经是时代的潮流与风尚。它有不可置疑的前提——在政治正确性压倒一切的年代,人们合理的物质追求和生理欲望被诋毁、被污蔑、被碾压,而一旦有了欲望合法的出口,人们自然会重新观察世界和自己,重新审视正常而又合法的物质诉求和灵魂动向。这不是释放人性的潘多拉盒子,而是时代拨乱反正的自觉选择。而诗人,正是站在时代的船头,忠实地记录着身体和精神的激动与喜悦——“以纯银的触觉抚摸城市的高度”。这是顺应历史的姿态,是那个时代普遍的热情与普遍的情感。亚里士多德说“诗人的职责不在于描述已发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发生的事,即按照可然率或必然率可能发生的事。……因此写诗这种活动比写历史更富于哲学意味,因为诗所描述的事带有普遍性,历史则叙述个别的事”(《诗学》)。可以这样说,杨克笔下的物质礼赞并不是个案,而是那个时代的集体诉求与生命写照。
二
当然,我们也必须看到,诗人在表达对时代变革热情欢呼的同时,并没有放弃知识分子的怀疑精神与批判立场。即使是在忘我的赞美中,他的怀疑与批判也会如惊鸿一瞥,在瞬间闪出一道冷光,让人不得不反观自我与时代——“大自然在一滴石油里山穷水尽/灵魂陷落,油井解不了人心的渴意/游走奔腾的石油难以界定”(《石油》)。诗人礼赞物质之光,但分明又有一丝隐约的担忧,因为,在那种光芒里,有世界不可预知的方向和速度。这是对现代文明双刃剑属性的敏锐预见,是具有前瞻的生态意识。“银色的线条如此炫目/空气中辐射着绝不消失的洋溢的美/诉说生存的万丈光芒”“欲望的花朵 这个季节里看不见的花朵/被最后的激情吹向高处/我们的灵魂在它的枝叶上飞/当晦暗渐近 万物沉沦/心灵的风景中/黑色的剪影 意味着一切”(《逆光中的那一棵木棉》)。在一棵树上,诗人既看到了欲望之花绚烂的一面,也看到了它残酷的一面,生命的矛盾性在一棵树上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是一种向外的打量,更是一种深刻的内向观照,在这个双向敞开与奔赴的过程中,诗人不仅获得了一种物质意义上的审美感,更获得了一种灵魂意义上的追问感。在双重生命机制的运行下,生命不再呈现时间的直线特征,而是既有内在的冲突,又有外在的磋商;既有物质丰富带来的满足,又有灵魂自省带来的隐忧。
1986年4月,中央有关部门发出“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夏时制的通知”,具体做法是:每年从4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时间),将时钟拨快一小时,夏令时开始;到九月中旬第一个星期日的凌晨2时整(北京夏令时),再将时钟拨回一小时,夏令时结束。这绝对是那个时代独特的“发明”,这个发明的初衷是和时间赛跑,是最大限度地利用时间来生产物资。然而,诗人却看到了这种貌似积极的举措违背生命自然伦理的荒诞——“火车提前开走/少女提前成熟/插在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提前吹灭”“老地点老时间赴约会的小伙/从此遇上另一个女孩/躺在火葬场的死者/享年徒有虚名”,也看到了自然伦理的强大基因与运行法则——“只是孵房的小鸡拒绝出壳/只是入夜时分/月光不白”(《夏时制》);而在后来城市化的进程中,诗人更是沉痛地看到“厂房的脚趾缝/矮脚稻/拼命抱住最后一些土//它的根锚/疲惫地张着//愤怒的手 想从泥水里/抠出鸟声和虫叫……我竟然遇见一小块稻田/青黄的稻穗/一直晃在/欣喜和悲痛的瞬间”(《在东莞遇见一小块稻田》)。这同样是对物质文明的反思,是对自然诗意的挽留。
物质文明依赖科技,科技反过来又促进物质文明,这是常识。但诗人并没有因为对物质的信赖而在科技面前彻底交出自我,诗人始终坚持怀疑主义和批评精神,以此衡量科技时代的“日新月异”。在去医院的路上,诗人在手机信号的消长中发现了科技之于生命的干预与虚拟,也发现了生命本体的自足性:“是的,我也会像那朵浮云虚无缥缈/澹澹的,淡淡的,没有边际/也许,那儿再无信号,我不在服务区/世间再无我的音信”“只一眼就洞悉了宇宙内存的奥秘/生命只是一条微不足道的信息/携带它的密码/被复制到这个世界/随后被删除,转发至另一个时空”(《死亡短信》)。在所谓的大数据时代,生命的指标和意义都可以数字的方式呈现,生命活动与科技文明息息相关,甚至有被其裹挟而加速异化的可能。一方面,我们享受着科技带来的便捷;另一方面,却又不得不承受它的加速度带来的眩晕与无所适从。古老的生命节奏被打乱,生活被严重娱乐化,生命被强行消费化,在这个心神俱疲的现代和后现代的语境中,生命不再完整。对此,诗人是清醒的,他坚决捍卫自己对生命本质的确认,所以才会坚定地从那种科技文明的魅影中走出来,说出对它的深度认知和忧虑。
三
面对时代的合理性进程和结伴而生的不和谐因子,诗人并没有选择二元对立的非此即彼,而是二者兼顾,在时代的大前提下思考生命的意义。在诗人心中,生命绝非过去的唯精神存在,也不是当下的唯物质存在,它应该是二者的完美融合,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相互成就。因而,诗人心中的理想国,注定不是钢筋水泥的丛林,更不是人迹罕至的荒原,而是生命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互相支撑与双向生长——“这才真正是我的家园/心平气和像冰层下的湖泊/浸在古井里纹丝不动的黄昏/浑然博大的沉默/深入我的骨髓/生命既成为又不成为这片风景”(《北方田野》);是必须整体性理解的生命形态——“摇摇晃晃的企鹅,一分为二胸和背泾渭分明/生命是一个整体”(《热爱》)。
精神无法取代物质,同样,物质也无法完全对标精神,生命有可以用物质量化的部分,也有超验的空间,正如诗人在《谁告诉我石峁的邮编》写到的——“我到了陕西神木,却一直/到不了她的石峁。地理上的起伏/暗示心理上的连绵/至于信寄与不寄/石峁本就在那儿,而她也许只在梦中”。在诗人看来,传说也是愿景,愿景也可以化为传说,在这种虚与实的互证互现中,过滤掉的是人生的嗔、怒、怨、嫉、恨,留下的是寄托,是希望和慰藉,甚至是创造和审美。正因如此,人类的历史才不仅是王朝更迭的暗影和成王败寇的世故,而是多了些充满善意的时光凝视与感怀叙事。山海里有生命,事物中有期待的因果,它们不提供杀戮的武器,只会提供抚慰人心的叙说;它们不一定有光鲜亮丽的外壳,但一定有温润如玉的质地和纹理。
“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我的祖国/硕大而饱满的天地之果/它怀抱着亲密无间的子民/裸露的肌肤护着水晶的心/亿万儿女手牵着手/在枝头上酸酸甜甜微笑”(《我在一颗石榴里看见了我的祖国》)。这个祖国既是政治意义上的祖国和地缘意义上的祖国,也是生命意义上的祖国和人类意义上的祖国。在这个国度里,人与人之间没有职业、身份、阶层等附加意义上的高低贵贱之分,而是亲密无间的人类集合体,它们按照自然的伦理有序地排列在一起,共享自然的恩赐。当然,诗人没有过度美化这种天然的秩序,在歌咏的同时,他也看到了“靠着背阴的西部”,看到了“石榴的一道裂口/那些风餐露宿的兄弟”,看到了“他们土黄色的坚硬背脊/忍受着龟裂土地的艰辛/每一根青筋都代表他们的苦/我发现他们的手掌非常耐看/我发现手掌的沟壑是无声的叫喊”。这是诗人对生命秩序中隐含的缺憾的洞察,是对生命苦难的体认。但诗人并没有因此而彻底否定这种源自自然伦理与区域划分的生命秩序,而是赋予这种苦难以尊严,赋予它被同情和被关怀的社会性和主动性——无须刻意掩饰,而是让它呈现于太阳之下,让那个高高在上的造物主看到个体生命的挣扎、坚韧和倔强,看到整体生命“生生不息”的力量和保持“拳拳之心”的理由。“凝视每一棵朝向天空的石榴树/如同一个公民谦卑地弯腰/掏出一颗拳拳的心/丰韵的身子挂着满树的微笑”,在这个自外而内的观察与体认中,诗人与万物站在一起,领受并回应着天地的呼吸与体温。
美国批评家马泰·卡林内斯库在《现代性的五副面孔》一书中分析了大量政治的、历史的、艺术的发展规律后,总结出现代性的五种特性,即现代主义、先锋派、颓废、媚俗艺术、后现代主义。在他看来,这五种面孔并非独立存在,而是互相包含并相互衍生的关系。在对生命现代性的表达上,杨克拒绝形式上的媚俗和先锋,他没有选择夸张、变形、拼贴等现代方式,而是遵循生命的现代性反应和现代性感受,自然而又舒缓、浓烈而又不失节制地表达它。因而,他的诗歌鲜有那种凌空外逸的灵魂高蹈,少有那种曾经流行一时的箴言式抒情,更多的是日常的话语方式和正常的修辞表意,这一点,在《被车灯救赎的同一条暗路——致尼古拉·马兹洛夫》一诗中有充分的体现。这首诗既是写给异国的同行,同时也是诗人的灵魂自况,在这种设置潜在对话者的“独白”中,诗人选择与生命日常状态平行的节奏和语调,看似漫不经心,但对世界、现实和文学的观点和态度却是深刻的现代性反应。在这种透亮而又自在的陈述中,生命的细节俯拾皆是,对时代航线的真知灼见不时闪现,他始终如一地贴近生命,忠实于内心的声音,为生命在时代中的轨迹留痕,为生命对现代性的反应取证。
2024年5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