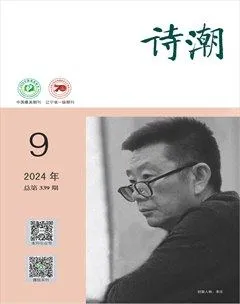近作十四首

乌贼骨
那时,父亲患有胃病
母亲在剖乌贼的盆子里
捞出了乌贼骨
说:这个可以止胃酸,止血
她在水嘴下冲干净
把乌贼骨晾在窗台上
院子里飘着乌贼的腥气
夕阳西下,晚霞血红
那时,我还不知道世界
正在大面积胃出血,转瞬
凝结成黑夜
妈妈,你俩如研细的乌贼骨粉末
消失在世界的口腔里,咸涩
但胃病无法治愈
它的消化物日趋复杂
重金属,玻璃,激素,农药
塑料,建筑垃圾和各种分类垃圾
以及一本散发着油墨香气的
名为《乌贼骨》的诗集
妈妈,那无法下咽的
我咽了下去——乌贼汁依旧漆黑
乌贼骨依旧洁白,柔软,易碎
理 解
我除了偶尔去湖边散步
几乎足不出户
在人群中我有窒息感
在梦中却常常回到年轻时
拥挤的异乡街头
在他人亲切的方言中迷路
想起多年前的古玩城门口
有个人坐在ba622ad33f3613492c76ddb84a23412db7b1f68078ed122b25848cfe9243288e有滑轮的木板上
左手打落了别人递过来的
吃剩的半个盒饭
右手举着一元钱
排队买刚出炉的烧饼
他无脚的踝骨裸露在细雨中
古玩城工商所的老陈说:脚
是他自己剁下来的
脑子有毛病
再也不能满世界收旧货啦
当时我看那张脸:表情正常
只是有些焦躁,有些疲惫
现在我想:是厌倦,他厌倦了
在大地上行走,却让双脚
去虚无中流浪
颤抖,微笑,剃须刀
我总是向虚无那边眺望
但没有一个人回来——我的父母、妻子
如果去那边打探消息
必须用一次性的钥匙——才能打开
那扇看不见的,牢固的,一次性开闭的门
根据二手的经验:无法保证归来
2002年夏天——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年
母亲去世的第二十一年
我带妻子、女儿去了青海湖
白天在湖边看水鸟翻飞
心里却浮动着一幅幅父亲年轻时
在青海湖畔骑骆驼的照片
照片里的风依旧像吹起父亲的头发一样
吹起我们的头发
那时他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他是否望着起伏的湖水想起他还在山东
生活的妻子儿女
但他无法想到多年后
我会站在湖边想起年轻的他
并用娃哈哈的空瓶盛满湛蓝的湖水
夜宿西宁,我用父亲留下的飞利浦
电动剃须刀剃须——打开刀网
我呀了一声
父亲遗留的和我新剃的胡须
黑白分明
却又那么亲密
我将它们永远封闭在剃须刀中
妻子用那块母亲用过的蓝色手帕
将剃须刀包好
她的手一直在颤抖
她小声问,把它放哪儿好呢
我沉默,我不知她说的是她的颤抖
还是父亲和我的剃须刀
2008年初春,她的手在我的手中
停止颤抖。她留在白色枕头上的浅浅
枕窝,盛满了无底的寂静
两根弯曲的头发
有着夜晚的颜色
我透过病房的窗户望去:德州明月湖
正风和日丽,十八年前
我俩在湖上,她听我谈起母亲
而十几分钟前,我还对她说
记住,你欠我一个来世的拥抱
过去后,代我向父母问好
告诉父亲,我欠他一个道歉
请他下次打我时,下手重些
告诉母亲,我欠她两个热吻
亲她右脸时,请准备好左脸
妻子微笑,像母亲、女儿一样微笑
我说,如果你回来,我就给你
做一辈子饭菜,好吗
她将微笑凝固在嘴角
在三月五日下午两点钟,拒绝了
我的请求
看来,我只能亲自过去
什么时候呢?哦,我会等待女儿慢慢
长大,我会尽量将这半杯酒品得长一些
将这一次性约会等待的时间
从容地分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美好的瞬间
我一定会带上一瓶青海湖明月湖的水
带上,那只飞利浦剃须刀
蚂 蚁
皮鞋,汽车,压路机
甚至死亡也没有碾碎
这只卑微的蚂蚁
但蚂蚁要死在诗里
死在命运之书的第一页和最后一页
必有一根手指,轻轻
掀开
蚂蚁就复活,就钻进你的骨头
咬你
预 感
站在龙年初二的锦绣川桥上
凝视冰雪融化后温柔的春水
这几乎要流尽我一生的水
我已不再诅咒,也不赞美
可以再流一回吗,为我,为所有人
你兀自在阳光下荡漾,荡漾
而我用一首酒后寒冷的诗将你永久
冰封。谁可以听见我心中
冻到冰炸的迸裂声而为之战栗
谁就是我流着鼻涕的小伙伴
在冰上抽着飞旋的陀螺
而少年时的雪又将落下,落下
却掩盖不住大地弯曲而深刻的车辙
这倒悬在命运之上残暴循环的河流
猫
它太好奇了
在门缝看着我俩
慢慢挤进来
你把它抱出去
我知道在关闭的门外
它凝听着
室内发生的一切
出门时它已不在那里
就像时光有着缓慢而迅疾的软蹄
悄无声息地隐入记忆幽暗的深处
只余双瞳
发光
祈 祷
我没有告诉爱猫的女人们
流浪猫每年生育的后代
和猫捕杀的鸟儿以及其他小动物的数量
是一个天文数字
这个数字因她们手中猫粮分量的变化
而增加或减少
当然,地球的重量不会因此而改变
她们的视频中又传来母猫
生了几只小猫的消息
我在心里祈祷:上帝
请保佑捧着猫粮的手温润如玉,请保佑
麻雀们叽叽喳喳的叫声清脆和猫爪一探
捕猎前轻巧的沉默
安眠或等待
你练成了缩身术
缩小
如蜗牛
缩入自身
不管外面风雨雷电
你安眠于一个僵硬的永不愈合的
伤口
等待着一只红色运动鞋的踩踏——
咔嚓
保 留
亲爱的,我身体的任何部位
都可以与你交换
左臂不行——
我最小的女儿小米
每晚都枕着它安眠
错乱的场景
你刚才说的是灰喜鹊,不是灰鹦鹉
是的,当我要说灰鹦鹉时
想起那年冬天,我挽着你在天津海河边
你突然说,咦,鸽子
我说不是鸽子,是灰喜鹊
就脱口把灰鹦鹉说成灰喜鹊了
此刻三种鸟在我心里乱飞
而你是第四种
早已轻盈地飞离了我的臂弯
我的左臂像一根枯枝仍在微微地颤抖
他给这些树起了名字
第1棵树是一个地名
第2棵树叫7月
第3棵树叫诗歌之夜
第4棵树叫52度
第5棵树本来就叫合欢
第6棵树身有1块疤
是一个人很深的名字
他有时会走过去拍拍它
它偶尔会落下一片叶子
他荡起涟漪的心就恰好
押韵了它一圈圈的年轮
拆线及其他
岳母脊椎手术后拆线
医生说刀口愈合得不错
这九组黑线辅助任务已完成
再不拆就捆绑皮肉啦
我说里面的六个钢钉
什么时候拆下
医生微笑着说,永久性的
已与脊椎骨融合,这是一种
必要的禁锢
黑线被咔嗒一声剪开
镊子夹住线头一甩
死蚊子一样,次第落入垃圾桶
我记住了拆线画面
却无法在脑海里打捞出看不见的
钢钉
空 位
东营火车站是一个单线小站
那是几年前的一个清冷早晨
候车室里旅客稀少
除了我和书恺因为谈诗,还有
一对夫妇谈着家事坐在了一起
我俩与他俩之间礼貌地隔着一个空位
其余的十几个人彼此之间都隔着一个
空位,仿佛遵守着某种契约
人们互相打量之后低头看着手机
今夜,隔着这么多的夜晚我突然想起
候车室里的那两排光洁的铝合金长椅
有序的空位
哦,其实空位上坐满了看不见的孤独
人们已不能紧挨着坐下
汝州风穴寺送别海因兄
这两天,三点水的汝州下雨
如佛般端坐,语调平缓的海因兄
时而会停下谈话,手里轻数着念珠
眼中似乎也有盈盈水气
上午在喜 堂讨论诗歌
听冯新伟之子冯蝶说起童年的困厄
海因兄终于落下两滴泪来
使我的目光更加潮湿
他递给我一瓶农夫山泉
谈完平顶山诗群和《阵地》的缘起
流变,前景,他悄然起身
我吱呀一声打开木门
两人看着两边雨后的青山
闲谈了几句,至风穴寺门口
他跨入车中回首:写好诗啊李庄
我拱手,目送车子远去
我抬头,此时天空又飘下细雨
代替了尘世的哽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