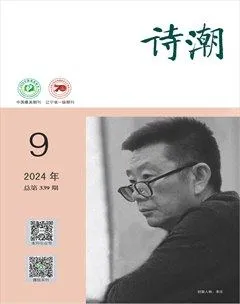抒情言志与社会实践
戈鲁作品

崖丽娟:碧薇你好,以我平时对你的“一知半解”开门见山就提问了:你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摇滚、民谣、电影、摄影等艺术是否与你的诗歌写作形成某种对位关系?现在有不少诗人已经有意识地把诗歌与音乐、戏剧、绘画、书法、摄影等艺术进行跨界融合。或许某种意义上,“诗人”身份于你而言,恐怕指代的是一个更为综合的艺术活动者身份。对于诗歌纯粹文本性的深掘与综合艺术互相渗透而呈现出多元跨媒介融合趋势,你有什么深切体会?
杨碧薇:谢谢丽娟老师。您从跨学科的角度开启话题,正好契合我的特质。钱钟书先生曾以“出位之思”来讨论诗画问题;不同艺术之间的通约性,就是诗性,正如海德格尔之见,“一切艺术本质上都是诗”。与诗的紧密关系,也让我与其他艺术更加亲近。我中学时代喜欢上摇滚,大学玩过三年乐队,这段经历没让我变成职业音乐人,但对我更多地了解音乐,以及摸索建立自己的批评坐标,都颇有助益。电影方面,高中阶段我开始系统地阅片,长此以往,积攒了比一般人略多的阅片量。后来,我去北大做博士后,从事的也是电影学研究。摄影则是我身边的事物,我父亲喜欢摄影,家中常备几台相机,我也比大多数人更早地接触到数码相机。我的母校昭通一中曾开设兴趣班,我选修了摄影课。手机摄影尚未普及的年代,我的青春是在挎着单反走南闯北里度过的。
但我深知自身精力与才华有限,不可能在每个领域成为行家。文艺给了我独特的视角,亦带给我必然的局限。离开文艺,我什么都不是,既不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也不能让一首诗去阻止坦克。对此我在诗里说“我知道我一生的孔雀,不过是美和无用”(《因此我不能……》),可我必须与这局限性共存,它塑造了我。
回到诗歌上。别的艺术与我的创作并没有形成严谨的“对位关系”,“对话关系”倒是有的。邦吉梅朵评论我的诗歌时谈到,这是一种艺术的“位移”。在从事批评与研究时,我也有意识地往跨学科的方向靠,在“位移”中建立独属于我的学术坐标。我的博导敬文东先生是先于我本人,最早发现我这一特质的人,八九年前,他便说,希望我能成为苏珊·桑塔格那样的批评家。我写过一些以诗歌为轴心,对摇滚、民谣、电影、摄影等进行观察与讨论的文章,有一部分已结集为2020年的《碧漪或南红:诗与艺术的互阐》。
能进行新诗的跨学科创作的仍然是少数。只对写作感兴趣的诗人大有人在,其他艺术不在他们关注的范围。我们的教育重在培养人的应试能力,培养通才不是应试教育的目标。而学科的纵深发展必然导致分化,带来交流的壁垒,造成知识与生存的内卷,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埋首于一个专业。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人是典型的单子式个体,社会分工的格子间与信息茧房就是我们的生存现实。
我喜欢的芬兰导演阿基·考里斯马基的电影里,就有这样的人,他们没什么爱好,生活单一、重复、孤独。《火柴厂女工》《薄暮之光》都揭示出当代人类境遇的普遍性。结合当下的汉语语境,“诗人”这一指称在约定俗成的意义中,尚不是“更为综合的艺术活动者的身份”,我也不是;一般情况下,诗人只是诗人,不能代表画家、导演、摄影家。在我的判断里,汉语新诗发展到现阶段,还不具备广泛深入的跨界能力。仅仅是汉语面临的现实、新诗本身的问题,已为诗人带来巨大的考验。对于自我要求高的诗人来说,“纯粹文本性的深掘”就需要付出十分艰苦的努力。我的朋友刘义就总结过他面临的写作困境:母语修养的问题,触及本质的能力,新技艺的发明之难。新诗写作尚且如此之难,“纯粹文本性的深掘”与“综合艺术的互相渗透”就更难在同一名汉语诗人身上共存。我还没见到过诗歌上写成当代杜甫、吉他上也成为Jimi Hendrix的。或许是我要求太高了,但真正的创作者都明白,要在某个领域突破极小的一步都很难,更别提跨界。
我爱好多,但我常常提醒自己:在精力的使用上还是要有侧重。我们期待优秀的跨界作品出现,更要尊重在自身领域脚踏实地钻研的人。这些人身上的专业精神,是浮躁时代的稀缺品。至于汉语新诗的高质量跨界、与其他艺术及媒介的更多结合,只能交给时间。
崖丽娟:诗歌一直是人类表达丰富情感的重要载体,在这个喧嚣浮躁的年代,诗歌之于青年,或青年之于诗歌究竟意味着什么?情诗问题也是中国新诗史中的一个学术问题,爱情诗是否更容易得到年轻诗人的青睐?请就此谈谈你的见解。
杨碧薇:我觉得这年头喜欢诗歌的青年并不多。在当下,诗歌并没有对广泛的青年群体产生影响。我挺喜欢和诗歌以外的人交流,他们为我展示了另外的世界,让我放下幻想,充分认识到:热爱诗歌的人并不多;在社会结构中,诗歌是非常小众也无比边缘的一部分。有了这个认识,我反而坦然了,不被虚无的崇高感绑架了。虽然我心中依然充满神圣的诗歌信念,但我深知诗人更应该学会和诗之外的世界相处——这个看似与诗相反的世界恰恰是培育诗的土壤;也只有在它的映照下,诗的神圣性才得以确立。
情诗在汉语新诗里的出现并不特殊,因为抒情是人的本能,中国文学有源远流长的抒情传统。说到汉语新诗史与情诗,就绕不开徐志摩。他为“新诗”这一文体的型构提供了独特且重要的东西,他对爱与美的关注,化为浓情投注到新诗里。直到今天,人们提到新诗,常常会联想到抒情、浪漫、新鲜……这些质素早就经徐志摩发扬光大。典型的现代情诗是穆旦的《诗八首》,是昌耀的《冰湖坼裂·圣山·圣火——给S·Y》……
“爱情诗是否更容易得到年轻诗人的青睐”,我不好说,我只是一个个体的写作者,不是某个群体的官方代言人。年轻人写情诗不奇怪,难的是人不再年轻后,还能保持爱情的纯粹,还有情诗的创作力。
崖丽娟:你在《碧漪或南红》中概述新诗阐释有“四难”:“大众对新诗的理解之难”“专业读者对新诗的阐释之难”“诗人对新诗的阐释之难”“新诗自身的阐释之难”。你身兼诗人、批评家,那么,诗人与批评家处于哪种状态才可以被称为互相“懂得”?当你作为诗人,从批评中收获到哪些反哺?当你作为批评家,开展诗歌批评坚持什么原则?
杨碧薇:金庸写过一个很有趣的人物,周伯通,他有一项绝技:左右手互搏。一个既写诗又做批评的人,应该是擅长左右手互搏的,其创作思维与批评思维正如左手与右手,是相互协调、相互锻炼、相互挑逗并愉悦对方的。
而新诗批评至今仍是一个尴尬的常识,很多时候仍需要自证。只写诗、不读批评乃至轻视批评的诗人不在少数,在他们看来,诗人会创作就够了,至于理论和批评方面的学习,只有坏处。我没有深究过这种看法的由来,但它一定与天才论有关,可能还逡寻着反智主义的身影。
新诗的诞生背景是现代性的兴起,比别的文体更强调现代式的个体性,因而是一种很容易激起人的自恋的文体。但事实是,大部分诗人既非天才,亦非智者。本来,后天的理论学习可以弥补天赋的不足,让人突破局限,写得更好,遗憾的是,很多人在理论和批评的大门前止步了。
读研之前,我也常常听到这样的论断,“中文系培养不了作家,只能培养学者”“搞理论和批评会害了写诗(作)”。事实证明,我能在两种思维间切换自如,创作与学术彼此激发、互相反哺,这个过程给我极大的享受,让我体验到非同寻常的乐趣。新诗里的诗人批评家不少。赵目珍就有一个“批评家诗人”的群,其中有40后的徐敬亚等前辈,也有90后的李海鹏等友人,咱俩也都在群里。这说明诗人从事批评、批评家从事写作的情况并不罕见,同一个人身上创作与批评并进的传统并没有在新诗里断层。
诗歌是一个很特别的文类,诗歌批评家往往自身就是诗人。优秀的诗歌批评难度极大,它要求批评家具备敏锐的感知力、扎实的学养、宏大的视野、深刻的洞见、前瞻的眼光、灵巧的辩论力、强大的说服力、精美的语言、老辣的修辞……还要有充满共情力的体察、对人类境遇的密切关注与悲悯、异于常人的想象力;他(她)最好还是文体学家,能建构自己的批评话语体系,打造独属一家的批评文风。以上种种,对诗歌批评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用胡亮的话来说,就是“侥幸的批评家”。
诗人批评家要坚持的原则,即诗的原则,不妨称之为诗的伦理,紧扣文本是最重要的一点。批评家要做的是深入了解文本,吃透研究对象,并在宏大视野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各种研究方法对研究对象进行有效的批评。至于批评的出发点,是不尽相同的。就我个人经验而言,有两点比较常见,一是兴趣,二是问题意识。首先,我对研究对象抱有兴趣;其次,我得先有一个或几个疑问。诗歌批评的落脚点也有千千万,因为每一篇文章研究的内容都是不一样的,达到的效果也都不一样,我认为至少要做到让剖析的问题清晰化,而不是让读者一无所获,更不是把批评家自己也绕进去。
崖丽娟:新诗的窘境还在于,一些圈内人纷纷赞誉的好诗,读者却觉得晦涩难懂,不知所云。提高“写作难度”与降低“阅读难度”是不是一个伪命题?口语入诗是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之一呢?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最根本区别何在?写作中如何保持对语言的激情和敏感?
杨碧薇:一路写过来的人都有切身体会:写作是逐渐进阶的过程。一开始简单稚嫩,后来就越来越难。关于写作难度,我想起敬文东先生在分析杨政诗作《苍蝇》时提出的一个概念,“表达之难”。“表达之难根本上是一个现代性事件”。表达之难敦促着新诗走向复杂。在持续的写作中,提高写作难度是必然的,身为诗人就应该有这样的抱负。
提高写作难度与降低阅读难度并没有必然的关系。提高写作难度,并不意味着在给读者设置阅读障碍。有的诗可能乍一看朴实无华,但包含着不小的写作难度,张执浩的《咏春调》,泉子的《真实》等小诗都有非一日可达的内力。而有的诗看上去繁复夸张,却是不折不扣的纸老虎,是表达的病症,是功力欠佳、火候不准的产物。诗人要关注的是写作本身,为不同的题材寻找最贴切的表达方式,而不是被观念绑架,也不是为了迎合读者,刻意去降低写作难度。从读者方面来说,不能坐等作者的写作降维,而是要通过持续深入的阅读来提高自己的理解能力。
口语并非万能药,在一些题材和语境中,口语能激发成倍的活力,但未必适用于所有写作,我的看法还是要对症下药,硬用一个标准去套所有诗歌,无异于美学的暴政。很多人对学院诗人有僵化的认识,其实,学院出身的诗人也各有不同。比如我,属于思维更民主的那拨,我用偏口语的形式写过《妓》《松绑》等诗。学院背景的诗人里,也有不斥口语的。我在鲁院课堂上就听臧棣讲过轩辕轼轲、尚仲敏的诗,我的同龄人袁永苹、杜鹏也都创作过口语诗。臧棣在《诗,必须写得足够骄傲》中提到,作为诗人,他要求自己具有开放的心态:“开放意味着在诗的表达方面,我只看重诗的活力。口语也好,修辞也罢,只要有助于强化和深化当代汉语诗性的表现力的方式、方法、手段、措施,我都愿意吸收过来。”这也是我的态度,如果所有人的诗都写成一个样,就不好玩了;不仅不好玩,一定是文化的灾难。
诗歌语言与日常语言最根本的区别,首要的是陌生化。诗歌语言就是要发现日常用语中被忽视的东西,重新刺激其活力,释放其潜力;就是要发明新的感受。至于保持对语言的激情和敏感,对我来说也是个难题,我没有感觉就暂时放一放写作,前提是心里有一根线在提着,提醒自己:我最终要回到创作上来,要自觉地恢复对语言的感觉。神奇的是,只要我这么想,就能做到,激情和敏感会再次回到我身上。对此,我的解释只能是,所谓功夫在诗外,可能语言也在语言之外。
崖丽娟:作为年轻一代诗人、批评家、学者,你拥有完整的高等教育背景,体现出良好的综合素养,现任教于鲁迅文学院,从事文学教育工作。很多综合性大学的中文系、文学院开设创意写作课,写诗是依靠天赋别才,还是需要经过严格的后天训练?大学课堂可以培养出作家、诗人吗?
杨碧薇:我不是创意写作专业出身的,而是选择了纯学术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从事文学的学术研究。我认识不少同龄人,也有很强的创作能力,也和我一样选择了学术之路。也有一些朋友上过创意写作专业,大多是有着较为良好的创作基础的,其中一些人的创作成果已经十分突出。与学术型的硕博相比,他们在论文上的科研压力要小得多。
我做博士后期间,给学生教过写作课。北大的学生学习态度积极主动,懂得怎样学习,擅长提问,促使我思考。来鲁院工作后,我接触的写作者就更多了。我阅读大量的学员诗歌,逐渐摸索出一些门道,发现大部分人在写作初期存在的问题是相似的。这么来看,在基本层面上,写作是可教的,有一些普遍规律可循。我将教学中的经验与心得整理成了一本关于新诗教育的书,期冀有合适的出版机会。我也做过相关的网课,在腾讯视频上。而“大学课堂可以培养出作家、诗人吗”就是一个不成问题的问题,从大学里,尤其是从中文系走出来的诗人、作家并不少。
写诗又确实需要天赋。如果大家都经过了严格的后天训练,学习积累在同一个层面,那么要拼的就是“别才”了。从这个角度说,写作又太“偶然”了,各样因素合在一起,才能造就一名优秀的诗人,别忘了,还需要运气。
崖丽娟:随着自媒体的兴起和社会文化语境的变迁,诗歌写作及传播方式的改变给当代诗歌带来重要影响。你在自媒体平台相对活跃,自己也做过相关网课投放在腾讯视频上。借助网络宣传推广及线下分享活动等是否有助于诗歌的繁荣发展?
杨碧薇:我写过一些文章,谈过相关问题,有一篇讨论的是新媒体下的新诗与民谣。一方面,民谣在向新诗学习,从新诗中汲取可用的文学资源,或者牢牢抓住“诗意”来做文章。另一方面,新诗对语言的要求越来越高,对语言本体的追求有时盖过诗意,成为写作的首要目标。音乐性在新诗里越来越边缘化,甚至被新诗残酷地抛弃。新诗对民谣的态度并不积极,这既与新诗自身的文体特性、规律有关,又暴露出新诗在当下社会发展中的封闭性。
新诗对新媒体的反应,可归入迟钝的行列。我只是呈现客观事实,不代表我在批评新诗。作为长期浸泡在新诗现场的写作者和研究者,我十分清楚新诗具有其他任何事物无法取代的独特性,它既不属于大众流行文化的范畴,也很难被商品化。在普遍情况下,新诗的诞生需要创作者沉寂下来,而不是陷入喧哗。如此一来又有一个悖论:沉寂显然不利于新诗的传播推广。
无论我们对新诗抱有怎样的希望,都要以认清它的文体特性为前提。《星星·诗歌理论》曾邀请我和李壮、李啸洋等人,就新诗破圈传播的问题展开讨论。我认为:“新诗在创作上没有必要刻意迎合读图时代。自媒体时代,众声喧哗……人们的爱好越来越多样化,有壁是正常的。对新诗来说,存在即合理,首先还是要有扎实的文本,其次,也可试着拓展一下关注和表达的边界。”结合你的提问,宣传的手段也可以“拓展边界”,在尊重新诗文体特性的前提下,宣传活动有助于新诗的推广。至于是否有助于传播意义上的“诗歌大繁荣”,我的态度是顺其自然。在大众文化占据主导、娱乐多样化、娱乐分层的当下,新诗基本不可能成为大众关注的重心(除非有某些极为特殊又极为偶然的条件催化),我们也不必为此焦虑。
我个人的实践就是最好的例子。2016年,我开通了个人公众号“杨碧薇Brier”,主要分享我和朋友们的文艺创作及批评研究,也会发布文学活动资讯。这些尝试有一定的宣传效果,但是这种以专业为主的自媒体平台很难破圈,受众是精准的、少数的——而这正是我对自己公号的定位,我不需要喧哗。公众号开通至今我没接过广告(尽管后台常常会收到邀请),也不发软文和心灵鸡汤。
崖丽娟:在我有限的阅读视野里,有不少诗歌选本以代际为划分依据。倘若从“20世纪60年代出生的诗人”(简称“60后诗人”)开始,对诗人群体以十年为代际进行划分的话,60后诗人到00后诗人这五代诗人中,你们80后正好处于承上启下中轴阶段。你是否赞成做这样的代际划分?作为80后,你更关注前20年的成熟诗人,还是后20年的青年诗人?为什么?
杨碧薇:代际划分并不严谨。我也免不了使用代际划分,因为在当下的语境里,它已经约定俗成。这样提主要是为了研究和讨论的便利;如果把时间线稍微拉长一点,代际划分确有其相对的合理性。你看,00后的诗与50后的诗有肉眼可见的差异。在一定程度上、在特定的时间范围内,代际,或时代的变更,是可辨识的,也是值得研究的。我的朋友陈丙杰就出版过诗学专著《内心的火焰:中国80后诗歌研究》,这是首部以80后诗人为研究对象的书。朋友子禾也出版了非虚构文集《异乡人:我在北京这十年》。他属于85前,我属于85后,读他的书,我都常常有陌生感。他写到了各种城中村,而我2015年来北京时,那些村子基本已被拆迁改造了。子禾那一代人在北京的生活是不可复制的,如果他不写,这些故事很可能就此湮没在历史的洪流里了。
但代际划分的边界必然是松动的、可疑的。出生于1969年的人,写的诗与1970年的人有天壤之别吗?他们其实是同时代人,分享的是同一个语境。从长远来看,时间单位如此小、间隔如此密集的代际划分就站不住脚。电影学界也曾以代际来划分导演,但第六代之后,就很少再用了。更何况代际划分背后往往隐含着一种进化观,似乎后面的就比前面的好,但你能说今人的小说就一定胜过了《红楼梦》吗?不加思考地承认并使用代际划分,是在给思维设限,让自己陷入思维的惰性。
我阅读时并没有基于80后的身份来进行选择。我对任何一代人都没有偏见。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不只是诗人,还是专业的诗歌批评者和研究者,还需要面对与自己的审美口味差异极大的文本。我必须广泛阅读,对当代汉语新诗有更全面的把握,这样我的批评才能更有底气。
这是我的阅读期望,而在实际中,我又明显地感知到自己的局限性。我们在写作中隐含着这样的愿望:向经典看齐。每一代人对前代人的关注是“天生注定”;对我来说,阅读成熟诗人正是这样一种必然。后来我逐渐意识到,在前代(成熟)诗人之外,还应该关注同时代人以及比我年轻的诗人。近年来我也在做关于同代人的批评,如《诗性、克制和无我——简论新一代藏族青年诗人》《新诗小传统下的青年诗歌》等。2022年12月,我受北京大学文学讲习所邀请,要讲一堂诗歌课,选择的研究对象是冯娜、张慧君等青年女诗人。课后,我将授课心得整理成一篇小文章《一堂关于“女性”的诗歌课》。
崖丽娟:你是云南昭通人,你的家乡蓝天白云,好山好水,有很好的诗歌写作土壤,出了不少好诗人。你上大学正好去的是我的家乡广西,后来在海南海口读硕士,又赴北京读博士、博士后,请谈谈“地域”对创作的影响。
杨碧薇:2019年,我参加了首都师范大学“写作困境与突破路径:女性诗歌写作的主体自觉”的学术研讨会,会后,我把发言整理成了随笔《我的故乡与诗歌》。这篇文章浅表地谈到了地域和写作的关系,还有许多东西,现在借这个契机,正好来谈。
在生活中,我的云南身份是常被关注的一点,但在新诗语境中,“云南”与我身份形象的绑定并不密切。与我绑得更紧的是“摇滚”“旅行”“女性”等,它们已成为我摆脱不了的标签。将我的文本与“云南”或“昭通”结合起来谈的,只有霍俊明、朱必松等少数几位批评家。
这种印象的成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既有评论者们对标签的渲染,有读者的“偷懒”,也有我自己的原因。当我开始严肃地写诗时,地方性、地域写作等早已是那个阶段新诗里的“显学”,很多人都在写,都在谈。云南题材,大家都写得不错,我还能写什么?我更想写的是与我自身贴合得更紧的经验,是更能凸显我本人特质的事物,其中就包含摇滚和旅行。
写作者“反地域”的同时,也在受地域影响。其实,在不同地方的生活,都给我留下了独特的经验和难以磨灭的记忆,这些东西也转化到了我的诗歌里,吴辰就说,“杨碧薇把沿途的风景都装进了心里,她的诗里同时具有山和海两种气质:山的沉郁,海的张扬”。每个诗人都是自身经验的集合,这里面必然包含地域经验。
这几年,我反而对云南题材产生了兴趣。没离开故乡时,我对其认知只是一个内视角;现在,我的视角与身份都更加立体多层了。在处理云南题材时,我觉得自己有了更大的自由度:“内”身份,“外”旁观。更重要的是,乡愁开始召唤我,我自觉有了足够的底气,去触碰、寻找并建构另一个文学原乡。我写下了和昭通有关的长诗《小镇》和《辛亥新春》。
崖丽娟:你刚才主要是讲故乡云南,其实关于海南、海洋,你的诗歌也不少,诗集《下南洋》里就有不少海南和海洋方面的诗。姜涛说:“《下南洋》是一部诗体的‘游记’,具有当代抒情诗难得的整体感。……‘南方本位’作为一种文化意识,不仅体现于自然与历史的展现上,更是充溢在浓郁的语言感性中。”胡亮亦说,“我不愿过多谈论杨碧薇的‘南洋想象’或‘南方想象’,这是因为,她无论置身何处都能娴熟于这样的左右互搏”。你在广西、海南生活了7年,这段经历对创作有什么具体影响,为什么想到如此集中地书写海洋,以及南洋?
杨碧薇:华南生活带给我的创作影响,主要聚焦于诗歌观念上。经历与阅读,都会影响并塑造诗歌观念,而我对海洋/南洋的书写,和经历、阅读都分不开。
假若我一直待在华南,也不会写下这些诗。写作背后的推力,是异质性的北方。来到北方生活后,我更直观深入地感受到地域差异性之大,进一步体会到不同文化在面对相异文化时可能会持有的傲慢与偏见。不可否认,地域差异在汉语语境中依然广泛地存在,它是一把双刃剑,你可以默认它对你的拘囿,也可以将它改造为另一个出口,一旦找到这个口,闯出去,写作就别有洞天。我的选择是“闯出去”,书写与故乡完全不同的海洋。
阅读与研究,也在影响我的诗歌观念。在研究中我发现,古典汉诗对海洋的书写很有限,很多时候还是概念化的。我想这与古代的交通条件有关。很多古人对海洋的认识只能从道听途说中、从书本中来。《红楼梦》里,大观园众儿女都羡慕薛宝琴,因为宝琴小时候便走南闯北,还写过关于交趾的诗。同时,古人的海洋意识也与现代人有差别,我们不能以现代人的意识去要求古人。新诗显然更看重海洋书写,郭沫若在《浴海》中写“无限的太平洋鼓奏着男性的音调”。在他笔下,自我命运、社会命运与海洋是拴在一起的。可以说,海洋是带着现代中国的诏谕,参与到汉语新诗里的。海洋,既是一道风景,又是一种观念。
新诗对海洋的书写还没有充分展开,至于南洋,写的人就更少了。这让我反思:新诗贵在“新”,但新诗书写中,或许仍隐藏着看不见的套路,影响着我们的思维,限制了我们放开手脚去开疆拓土。海洋与南洋,为我留出了巨大的书写余地。南洋与中华文明有着这样那样的勾连,与我们又有极大的差异。正是种种相似、不同、似曾相识与陌生感的交织,勾起了我的好奇,让我决定用诗的方式去探究、表现。我在随笔《南洋观看,中国想象,世界梦想》中说:“《下南洋》是一次漫长的行程。这组诗得益于我多年的东南亚游历经验,在创作过程中,我亲自走访,并查阅了大量资料。……从北往南,从过去到当代,南洋地区的华人群体经历了什么,中华文明在遥远的海上如何演变、生存并发展?”这只是一个简要的缘起,因为“随着写作的推进,我的构思原点一次次位移:对东南亚本土历史和现状的观照,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区域关系,也必然地进入了我的视线”。
例如,《 檀晚钟》以老挝的历史为背景。我在万象游览时,得知西萨格寺曾在万象王国最后一位国王阿努冯的手下得以重建。阿努冯致力于谋求民族独立,无奈一直受到暹罗摆布。后来,暹罗以万象拒嫁公主为由,进攻万象,将其夷为平地。这段介绍引起了我的兴趣。因拒嫁公主,便进攻万象王国,显然只是暹罗的托词。但由此推测,这位末代公主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她是谁,结局如何?我无从获取她更多的资料,只能让她在诗里复活。我虚构了暹罗部队兵临城下,万象王国即将毁灭的最后时刻:公主登上了西萨格寺,以自杀的方式殉国。在叙述时,我以公主的口吻说话,也把自身情志寄托其中。我在想,中国历史上,历代士人遭遇乱世,会有怎样的选择?儒家的追求是舍生取义,我诗里的万象公主也做出了一个儒家的选择。所以,《下南洋》也在写我们自身,写这个后现代现实下共同的人类境遇。对此我亦有陈述:“从2017年至今,《下南洋》写了四年半,目前仍在继续。其间经历的疫情,让我切实地体会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于我而言,在全球转型的大背景下,用汉语写作有了更重要的意义,也有更严肃的使命。汉语是我生存的现实,借用这一伟大的语言,我思考着以下问题:中国当代知识分子该如何定位自身,该用何种眼光看待当今的中国与世界,我们应致力于构建一个怎样的未来。”
写海洋和南洋,是我自身经历与阅读研究的双向选择;这个选择恰好容纳了安静书斋,又有着广阔天地,让我一次次体验到诗的冒险、乐趣与意义。
崖丽娟:接着上面问题,我们从地域边疆跨越到汉语疆界来谈你的具体写作吧。诗集《下南洋》《去火星旅行》,一看书名就有行走特征,旅游的视角让你的诗歌天马行空,独具魅力,在汉语诗歌的疆界方面你做了哪些尝试和拓展?
杨碧薇:“疆界”可以有多重理解,我就讲两方面。首先,这些年我比较关注新诗里的异域书写和边疆书写。2017年我开始写《下南洋》,2021年出版了诗集《下南洋》。“下南洋”一词,本身就包含着丰富的意义:地理、时间、历史、政治、文化……在边疆方面,2021年我写了一组新疆题材的诗。再往前,2018年,我在朋友秦晓宇的工作室看了王丽娜的电影《第一次的离别》,讲述的是维吾尔族儿童的生活。我写了一篇影评,发表在《电影评介》上。2020年7月20日,它成为疫情以来电影院开放后公映的首部影片。2022年,我又写了论文《当代汉语新诗的新疆经验》,以沈苇、蒋浩、李之平、苏仁聪等人的诗为例,发表在2023年8月的《中国文艺评论》。这些研究从不同角度打开了我的视野,让我对新疆有了更多的了解,也帮助了我的创作。
云南是我想写的另一个边疆。我“重写”云南,还意味着写作方式上的变化:以前我零星地写云南,是依赖自身体验,而现在对于云南,我应该补充自身经验之外的养料。朋友孙骁的专著《废坏与整饬——雍乾时期云南吏治变迁研究(1726—1799)》向我展示了一个特定历史时空下的云南(这个“云南”于我而言也是陌生的),重洗了我关于“边疆”的认识。书中提到,改土归流是云南与内地政治一体化的开端,“雍乾时期云南地区作为文化边疆区域的属性实际上已逐步减退”;清代云南频发的疆臣贪腐案,恰恰证明了这种一体化——雍乾以来,“云南逐渐成为一处‘被想象的边疆’”。从政治一体化出发,孙骁更多地看到的是云南与内地的“同”,这明显有异于我们在文学领域对云南的“不同”(也即异质性)的期待视野与表现手段。这次阅读再次提醒我:从不同的角度、用不同的方法、带着不同的期待视野去理解同一个事物,会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诗也如此,需要我们对它有“全面的发现”,哪怕最终我们选择写下的只是“片面的生动”。
其次,我关注技术的发展。科学/科技受到了汉语诗歌的冷遇,可它的确是我们今天生存的现实。以科技为背景,我写过《漂亮男孩》《雪后初霁》《孤独星球》《梦回帕米尔》等诗。《英雄美人》是颇受欢迎的一首,我想重点探讨的是未来的两性权力。我读过一则报道,科学家认为未来男性会消失。这首诗就是以这一观点为入口,以女性崛起为大背景,我构造了一个未来的女性世界。另一首《帕米尔高原》是将新疆题材与科幻元素相结合,我虚构了这样一种可能:在未来,人类与地外文明建立了联系;人们还可以把记忆存入银行,需要时能随时取出来。
北野武在随笔集《北野武的小酒馆》里感叹,现代人享受着科技的便利,而大部分是不懂科技的。我深有同感,我并不懂技术本身。我关注科技,也是集中在伦理学、社会学等层面。人文社科看似与科技不搭边,却有很深的联系,是殊途同归的。金观涛在《消失的真实》里提到,20世纪的科学革命深刻地改变了人类生活,尤其是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出现,遗憾的是哲学家们并不太关心科技发展,对其知之甚少。人文精神衰落了,科技却在日新月异地发展,这就引发了一系列问题。我阅读的另一位哲学家韩炳哲,也很关注这些问题,多次谈到当下的技术/社会变革。2023年春节,有关ChatGPT的新闻风起云涌,大有要将世界重新洗牌之势。我也写了《AI、稀有金属或终极之诗》,以李南为例,在新一轮技术焦虑的背景下来谈新诗。
在这次访谈交流中,我逐渐意识到,我的诗歌不完全是个体情志的表达,还始终与我对世界的思考连在一起。对我来说,诗歌不只是抒情言志的第一通道,还是社会实践的重要方式。这是我这次访谈的重要收获,谢谢丽娟老师。
2023年7月24日
崖丽娟

壮族,现居上海。诗人,兼诗歌批评,《世纪》杂志副主编。出版诗集《未竟之旅》《无尽之河》《会思考的鱼》。《会思考的鱼》荣获上海市作家协会会员优秀作品奖。
杨碧薇

中央民族大学文学博士,北京大学艺术学博士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学术研究涉及文学、摇滚、民谣、电影、摄影、装置等领域。出版《下南洋》《去火星旅行》等诗集、散文集、学术批评集六部。网课《由浅入深读懂汉语新诗》入驻腾讯视频。获《十月》诗歌奖、《钟山》之星·年度青年佳作奖、《诗刊》陈子昂诗歌奖·年度青年批评家奖、《扬子江诗刊》年度青年诗人奖·评论奖等。2021年入选《钟山》与《扬子江文学评论》“新世纪文学二十年·青年诗人20家”榜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