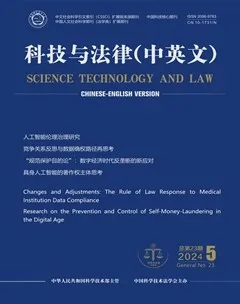“规范保护目的论”: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的新应对
摘 要: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面临的挑战需要探究新的应对策略。面对反垄断文本模糊引致规范准确适用难题、文本竞合造成规范选择适用障碍的双重挑战,“规范保护目的论”因其发展轨迹及外在功能,可为解决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的挑战提供有益借鉴。出于尊重差异、预防滥用的考量,“规范保护目的论”适用于反垄断领域应遵循类型化的基本要求。依循数字经济时代垄断纠纷与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之间的关系,可得出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领域“规范保护目的论”的三种场景化适用路径:文本明确时补强适用、文本模糊时解释适用、文本竞合时选择适用。
关键词:数字经济反垄断;“规范保护目的论”;规范文本;类型化
中图分类号:F 83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6-9783(2024)05⁃0056⁃08
当前,数字经济已成为重要的时代特征,为促进整体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了强大动力。与此同时,数据、算法等新技术的出现也使得传统垄断行为愈加复杂。在此背景下,《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以下简称《反垄断法》)的修改及相关部门规章、指南的出台对此作出积极回应,为开展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工作提供了法治保障。然而,文本模糊、文本竞合等立法不周延问题所带来的反垄断规范准确适用难题和选择适用障碍,仍给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工作带来较大挑战。在当前启动反垄断法修法不具备现实可行性的前提下,借鉴刑法学领域研究较多的“规范保护目的论”,进而促进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完善和实施,便成为一种新的应对选择。
一、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面临的挑战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我国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虽然通过立新、改旧的方式作出及时回应,以应对数字经济时代垄断行为的挑战。然而,作为“书本上的法”,文本无法自觉执行法律规范,欲实现反垄断法的使命,必须将其适用于经济生活进而转化为“行动中的法”。梳理发现,现行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在应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垄断问题时仍显蹩脚,主要表现为文本模糊、文本竞合情形下引发的适用难题。文本之于使命,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
(一)文本模糊:引致反垄断规范准确适用难题
为应对数字经济时代日趋复杂的垄断问题,我国修改后的《反垄断法》,相关部门规章及出台的《关于平台经济领域的反垄断指南》(以下简称《反垄断指南》)增设了数字经济领域垄断行为的禁止性规定,对于数据、算法的挑战已给出相应的立法回应,一定程度上消弭了规则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为维护市场竞争秩序提供了制度依据。然而,作为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仍在逐步走向深化应用的新阶段,这也给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具体适用提出了新的要求。面对主体更加多元、形式复杂、方式愈发隐蔽的新型垄断行为,现行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依然相对简单,具有较强的模糊性和技术上的规范弹性。
具言之,规制垄断行为时,我国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在立法表达上往往采用“列举+兜底”的模式。立法者在列举典型的垄断行为类型后,再通过含有“其他”“等”语词将具有同性质的类似情形纳入反垄断法规制范围内,前者为列举情形,后者为兜底情形,二者紧密联系。列举事项为兜底情形的适用提供了样板和参照,是预见兜底情形之内涵和意义的重要线索;兜底情形则能够弥补列举事项的有限性,为数字经济时代纷繁复杂的垄断行为认定提供“灵活转身”的规范空间。然而,兜底情形对所涉规范的构成要件缺乏较为具体的指引,法律适用过程中仅依据兜底情形通常难以对新型垄断行为作出精确定性[1]。如果缺乏对兜底情形的限制或明确,可能会产生两大问题:第一,兜底情形成为象征性立法,仅是形式意义上的存在,不会产生实质性法律规范的效果,难以体现兜底情形所被赋予的意义,难以规制列举情形之外的其他新型垄断行为;第二,兜底情形因其特有的模糊性和概括性,可能造成国家对市场竞争自由的过度干预、恣意干预。
以纵向垄断协议为例,《反垄断法》第十八条作出相关规定,其中,“禁止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达成下列垄断协议”系规范文本的主干,“(一)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系明确列举的所禁止的特定行为,同时还包括没有明确列举的;“(三)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中所指代的行为。《反垄断指南》第七条也明确平台经济领域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可能通过一些方式达成固定转售价格、限定最低转售价格等纵向垄断协议。显然,与反垄断法明确列举的显性文本不同,“其他”“等”未列举的情形属于反垄断法中的隐性文本,从法律的字面意思尚无法得出数字领域某一垄断行为是否在条文的文义之内。若缺乏相应的解释方法和基准,反垄断法文本的模糊性往往导致法律规范适用的不确定,即面对同一市场垄断行为,如何进行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适用尚缺乏唯一正确的答案。因此,文本模糊下如何准确适用反垄断法律规范仍是需要进一步明确的问题。
(二)文本竞合:造成反垄断规范选择适用障碍
面对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出现的新业态、新模式、新行为,我国市场规制领域的相关法律通过修订、新设等方式做出适时回应,集中表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以下简称《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以下简称《电子商务法》)、《反垄断法》三部法律之中。2017年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增设第十二条,对经营者利用技术手段从事不正当竞争行为作出规定;2019年实施的《电子商务法》针对电子商务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作出规定;2022年《反垄断法》修订也在总则及具体垄断行为的规则中明确经营者不得利用数据和算法从事垄断行为。表面上看,上述条款针对数字经济领域市场行为的规制更为全面,但由于不同法律所建构的理论逻辑不同,这些条款也导致法律适用上的竞合[2]。法条竞合是指“很多法条的构成要件彼此会全部或部分重合,同一案件事实可以被多数法条指涉”[3]。尽管反垄断法和相关法律的关系并非新话题,在传统经济时代已有相应讨论[4],但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行为的复杂性、隐蔽性等特征更是加剧了行为违法性认定及法律规范选择的难度,文本竞合下的选择适用难题仍需高度重视,既包括内部竞合难题,也包括内外竞合难题。
内部竞合是从反垄断法内部视角来看。针对数字经济垄断行为的法律规制,反垄断法内部易出现规范文本竞合的情形。这主要是由于立法往往较为抽象,而数字经济时代的市场竞争动态性较强,行为方式具有复杂性,加之缺乏对法条关系的周密考量,因此,不同规范文本之间对同一行为的判断可能产生竞合。如在反垄断法内部,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电商平台通过与平台内经营者签订协议的方式实施“二选一”行为时,可能同时违反《反垄断法》中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条款与纵向垄断协议条款。可见,同一部法律中出现法条竞合时,如何选择规范文本成为数字经济时代规制复杂垄断行为所面临的挑战。
内外竞合是从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规范间的关系来看。由于规范间界限的模糊性及数字经济时代垄断行为的复杂性,部分行为的法律规制缺乏明确的依据,可能落入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不同法律规范之中,此时就会产生反垄断法与其他法律规范间选择适用的问题。尤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新型垄断行为层出不穷,手段新颖、行为隐蔽,更是提高了这些垄断行为的认定难度。属性不明的市场行为往往容易引发法律规范的竞合,进而产生规范文本的选择适用难题。比如某一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电商平台,通过技术不兼容的手段破坏其他经营者的正常经营,可能同时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和《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当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电商平台在与平台内经营者进行交易时,附加不合理的交易条件,则可能同时违反《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与《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从行为方式上看,上述行为超出了正常竞争手段的范畴,既是以不正当的方式追求不法利益,破坏了市场的公平竞争,亦可能限制或排除了相关市场的自由竞争。行为效果的不确定造成行为定性的困难,进而容易引发法律规范间选择适用的难题。
二、“规范保护目的论”引入反垄断领域的理据分析
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面临的挑战,可以尝试引入刑法学领域研究较多的“规范保护目的论”。不论从发展轨迹来看,还是从外在功能观之,“规范保护目的论”均能为解决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挑战提供有益借鉴。
(一)从发展轨迹来看:“规范保护目的论”可应用于反垄断领域
“规范保护目的论”在我国的适用逐步由部门法领域扩展到法律解释层面,成为法律解释的理论模型。长期以来,刑法学界将规范保护目的解释为客观归责理论中的一个下位规则。客观归责论主要借助规范保护目的为刑法的限缩适用提供合理理由,即不在注意规范保护目的范围之内的结果不具有可归责性。一定程度上,规范保护目的对于刑法领域的责任认定起到了重要的制约意义。然而,有学者认识到仅将规范保护目的作为客观归责理论的子概念予以把握存在局限,应当从一般理论层面建构全新的规范保护目的理论,即将法律规范视为立法者实现某种目的的手段,应受目的的制约[5]。无疑,“规范保护目的论”在部门法中的适用具有重要的理论贡献,然而从功能论层面而言,规范保护目的的适用场域不应局限于归责问题,而应从属于法律解释的方法论范畴[6]。随着解释技术的普遍应用,规范保护目的作为具有“自在优势”的解释方法的定位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共识。
“规范保护目的论”是目的解释的一种方法,是立法者进行利益分配的基准和法律评价的立场,要求规范文本的适用应考察文本背后的规范保护目的。所谓规范保护目的,就是制定规范的目的[7],具体可从规范的整体目的及个别规定、个别制度的规范目的两种意义进行理解[8],前者如整体规范的立法意旨,往往能够产生宏观指导的作用,后者是具体规范中针对个别事项的规定,往往具有具象性和直接的应用性[9]。
当然,任何法律规范都是规范文本与规范保护目的的统一[5],反垄断法也不例外。反垄断法中规范文本明确了法条的文字、语句,具有显性的特征,而规范保护目的则隐藏在文本背后,服从特定目的与目标、立法者、法政策学的形成意志[10],是反垄断法律规范的价值内核,二者分别构成了反垄断法律规范建构的外在体系和内在体系。反垄断立法和法律适用均为文本建构与现实秩序之间的一种调适。立法者作为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创造者,出于一定的目的对经营者等主体的行为模式及法律效果进行设定,进而表现为法律语言、规范性语句等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以期通过规范文本的适用实现对市场竞争秩序的有效规制。可以说,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是实现规范“目的”的手段,受“目的”的制约。反垄断执法者和司法者通过适用规范文本成为现实秩序的建构者,在连接反垄断案件事实与规范文本时,就需要规范保护目的的指引。尤其在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不周延时,诉诸于文本背后的规范保护目的才能更加明确文本的文义射程,进而通过反垄断法律规范的适用实现对市场竞争秩序的合理、合法建构。
(二)从外在功能来看:“规范保护目的论”可克服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面临的挑战
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律规范的适用有别于文本建构下的规范主义制度逻辑。面对数字经济时代的现实挑战,反垄断法的适用需打破规则闭塞的固有窠臼,引入“规范保护目的论”以解决文本模糊和文本竞合下的适用难题,加强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与外界的互动。
一方面,“规范保护目的论”的引入有助于明确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之文义射程,进而提高规范适用的准确性。诉诸反垄断法文本之规范保护目的是一种基于规范保护目的来确定文本文义范围的解释方法。要想准确、恰当地判断行为的违法性,必须从规范保护目的的角度来说明[5]。规范保护目的作为规范的应然层面,无法为规范文本表达这一实然层面所包容,而“目的”是反垄断法规范之当为的范畴,也是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在制定与适用中应该体现的价值。可以说,反垄断法中所有规定了垄断行为违法性认定要件的条文都有自己特定的规范保护目的。当规范文本存在多种解释,反垄断实施机构必须更加努力、更深层次地考量文本背后的规范目的、立法历史、结构规范等[11]。只有在考量立法历史、目的、先例、代理观点、信赖利益和公共价值之后,才宣布“该规范有明确的含义”[12]。正如有学者指出,规范目的是一切解释的重要目标,任何解释都应当有助于实现规范内容所追求的规范目的,其他解释标准是解释者认识规范目的的工具[10]。因此,在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相对不明确时,“规范保护目的论”能够为确定文本的文义范围、提高违法行为认定的妥当性提供一种方案[13],进而有助于减少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模糊性。
另一方面,“规范保护目的论”可克服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竞合下的选择适用障碍。每一法律制度都有既定目标,即规范保护目的。规范保护目的先于规范文本表达,所有反垄断法律条文均基于目的的指引而建立,在规范保护目的下垄断行为的违法性认定要素得以成立,对具体违法性认定要素的理解必然受到规范保护目的的制约。而规范保护目的对于法律结构、行为性质、责任承担及追究模式能够产生决定性影响[14]。这就意味着当同一行为引发不同法律制度之间的竞合时,可基于法律制度的目标定位,即规范保护目的对行为进行定性。欧洲法院曾在2000年“CMB案”判决中明确指出,法律规范间可能存在交叉关系,即同一行为可能同时违反两个法条时,可根据两个法条所追求的不同目标做出规范选择1。此外,出于“目的—手段”关系协调的考量,化解规范冲突必须考虑具体法概念、法规范的保护目的[6]。法概念、法规范与规范保护目的之间呈现出一种手段与目的的关系,手段符合目的是法律适用中唯一正当的方法[15],故而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选择适用更为深层次的意义是规范保护目的的识别与选择。因此,面对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文本竞合的现实挑战,“规范保护目的论”可发挥重要的指引功能,应予以高度重视。
三、“规范保护目的论”适用于反垄断领域的基本要求:类型化
作为一种理论模型,“规范保护目的论”引入反垄断领域具有重要意义,但也存在适用差异的内在诉求,同时伴随“滥用”的可能。尤其在数字经济反垄断领域,法律关系的复杂性、垄断行为的新颖性、行为主体的多元性,均对“规范保护目的论”的具体适用提出置疑。在此背景下,将类型化作为“规范保护目的论”适用的基本要求,有利于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工作的顺利开展。
(一)类型化:尊重“规范保护目的论”适用差异的基本要求
在反垄断领域,即便将“规范保护目的论”作为统一的理论指引,也应尊重其在适用场景及适用要求方面的差异,基于不同情形对“规范保护目的论”进行类型化适用。
囿于具体功能的差异,“规范保护目的论”存在不同的适用场景和适用要求。在适用场景层面,“规范保护目的论”的适用离不开与其相统一的规范文本。在规范文本明确、规范文本模糊、规范文本竞合等不同场域,规范保护目的均存在适用空间。而每种适用场景之下,“规范保护目的论”的适用要求均存在差异。文本明确时“规范保护目的论”的适用要求低于文本模糊时的适用要求,前者仅需补强规范文本适用时的说理,后者则需对规范文本进行重新解释进而判断规范文本的可适用性,而文本竞合时“规范保护目的论”的适用要求更高,既涉及不同规范保护目的间的关系,又要准确回归规范文本的适用。由此可见,“规范保护目的论”有着独特的适用场景和适用要求。在不同案件中,“规范保护目的论”的具体适用都会产生更为精确、更有指向性的结论[16]。
贯彻类型化的基本要求恰能满足“规范保护目的论”适用差异的诉求。类型化与“规范保护目的论”紧密联系。类型的建构凸显的是规范的目的,依据一定的规范目的,个案事实在被适度抽象化后即有可能被某一类型观点整合成特定的法律行为类型[17]。法律类型由在法律上有“同等意义”的现象建构而成[18],体现了同类事物应作相同处理,不同事物应作差异化处理的法理基础[19]。同时,类型化以平等主义为准则,适用于反垄断领域能够实现“同等情形同等对待”。只有类型化区分适用“规范保护目的论”,方可符合平等的价值要求,确保个案的公平正义。就此而言,面对纷繁复杂的垄断行为,在尊重“规范保护目的论”适用差异的基础上,贯彻类型化的基本要求不仅有助于实现数字经济时代垄断纠纷的个案正义与比例正义[17],还能在事前发挥归类处理的功能,事后发挥验证法律裁决的作用。
(二)类型化:预防“规范保护目的论”滥用的基本要求
诚然,“规范保护目的论”能够克服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面临的挑战,但也伴随着滥用的可能性。标准宽泛、范围模糊、指导性较差,成为当前“规范保护目的论”面临最多的质疑。正如拉伦茨所言,“法规目的说的意义被其支持者高估了”,实际上法规目的说的提出标准过于宽泛[20]。在法律实施过程中,采用规范保护目的不同的适用标准,往往得出迥乎不同的结果,而规范保护目的的确定暗含法律适用者的自由心证,可能产生主观性、恣意性的判断。
类型化恰是预防“规范保护目的论”滥用的一条可行路径。在借助抽象、普遍的概念及其逻辑体系尚难以清楚把握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行为时,首先想到的应是求助于“类型”的思维方式[21]。类型化研究是理论发展的必然现象[22],其本质是建立认知模型[23]。作为连接抽象与具体之间的中介,类型化是反垄断法律规范保护目的与数字经济时代垄断行为之间的中间点。“规范保护目的论”具有抽象的特征,而类型化的基本思路恰能够为数字经济时代垄断案件的适用提供更为具体的方法,进而减少反垄断法律规范适用的恣意性,提高数字经济反垄断案件结论的可预测性和正义性。面对纷繁复杂的数字经济垄断案件,借助类型化立场能够更好地明晰反垄断法律概念、辨析垄断行为、判定竞争关系、参考指导性案例[24],有助于维系反垄断法律规范适用的安定性。由此可见,贯彻类型化的基本要求,一定程度上能够防止“规范保护目的论”的滥用与虚化,为规避法律适用者的恣意起到必要的保障作用。
四、“规范保护目的论”在反垄断领域的场景化适用
法律适用的过程是生活事实与法律规范互动、彼此开放的过程[25]。立足于类型化的基本要求,结合反垄断法律规范本身进行分析,可得出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领域“规范保护目的论”在不同场景的适用路径。具言之,依照数字经济时代垄断纠纷与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之间的关系,可将“规范保护目的论”在反垄断领域的具体适用解构为以下三种场景:存在一个明确可适用的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存在一个模糊的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存在两个以上可能适用的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在此基础上可归纳出“规范保护目的论”在反垄断领域的三种场景化适用路径,即文本明确时补强适用、文本模糊时解释适用、文本竞合时选择适用。
(一)文本明确时:补强适用
针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纠纷,当存在一个明确可适用的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适用该规范文本符合规范保护目的时,实施主体须援引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作为判断依据,同时可适用“规范保护目的论”以加强文书说理、强化法律论证,实现补强法律规范文本适用的效果。
法律实施中适用“规范保护目的论”补强规范文本充分体现了经济法的基本特征,即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平衡[26]。反垄断法作为重要的经济法分支,也呈现出这一特征。一方面,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作为形式理性的彰显[27],在法律适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也不能因此忽略实质正义的重要性和制约性。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不仅为维护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秩序、保护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提供了可遵守的规则和依据,还确认了国家干预的有限性,赋予了反垄断法限制市场竞争自由的正当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目标始终是规则及规则实施的重要约束因素[28]。规范文本的优先适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目标的妥当实现,要受到实质正义的制约。因此,聚焦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工作,引入规范保护目的一定程度上能够避免任意性,约束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适用。
另一方面,尽管适用已有的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已基本能够解决问题,得出结论,但从“规范保护目的论”的角度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纠纷进行深入分析和论证,有助于提高规范文本适用的合理性和正义性。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竞争的动态性特征导致反垄断法的适用具有较强的变动性,这就要求反垄断法的实施只有进行充分说理,才能保障法律适用的妥当性和合理性。然而,出于法律适用的效率、相关主体自我防卫的考量,法律实施中说理程度有待提高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此背景下,反垄断法律实施者可以在直接引用法律规范文本的基础上,通过运用“规范保护目的论”来解释规则适用情况,充分考量相关主体在数字经济时代市场竞争中的行为,从而达到补强文书说理的效果。而目的导向的法律推理往往包含着对实质合理性的追求和对实质正义的关注[29],“规范保护目的论”的适用正凸显了反垄断法所追求的实质正义。
反垄断法中规范文本与“规范保护目的论”的结合,有利于市场主体深入了解法律规范文本及其背后的保护目的,形成合理的法律适用预期。同时,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适用接受“规范保护目的论”的检视,也有助于约束执法者和司法者的权力。需要说明的是,补强型适用路径中,规范保护目的处于从属地位,发挥辅助性功能,不能代替正式的裁判依据和处罚依据。基于“规范保护目的论”在补强型适用路径的辅助性地位,反垄断法律实施者仅需对规范保护目的的阐释承担低级说理义务,即可实现补充说理的法律效果。
(二)文本模糊时:解释适用
在规范文本模糊时,通过“解释—构建”的路径能够提取和识别法律规范文本背后的正确“意义”[30]。针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纠纷,当存在一个可能适用的反垄断法律规范,但因该规范文本模糊、不明确,无法直接适用时,需援引“规范保护目的论”对其进行重新解释,以明确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真正意涵,并进一步确定涉案垄断纠纷能否适用该规范。
对反垄断法中的模糊文本进行解释的目的就是要把模糊的东西说清楚。反垄断法作为规则体系,具有较强的抽象性和模糊性。运用“规范保护目的论”对模糊的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进行解释必须依据反垄断法进行,解释的直接目标在于明确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的内涵,最终目标在于实现反垄断法的立法宗旨[31]。就此而言,文本模糊时解释适用的场景化应用有助于实现反垄断法解释的目标定位,借助规范文本所隐含的规范保护目的去判断兜底情形等模糊文本的文义范围,以实现具体法条之目的的内部协调。
具言之,在对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中的未列举情形进行解释时,首先要探寻条文中列举内容所表明的规范保护目的,并以此为内在基准,明确兜底情形的规范保护目的,进而得出兜底情形应涵摄的行为类型。只有符合该条文整体的规范保护目的,才可将欲评价的数字经济时代垄断行为视为与列举内容具有同质性的行为,进而将该行为纳入兜底情形的涵摄之内。以纵向垄断协议为例,“国务院反垄断执法机构认定的其他垄断协议”中“其他垄断协议”、《反垄断指南》第七条中“等”情形如何认定,应立足于规范保护目的,将兜底情形与其他列举内容进行比较。只有基于经营者与交易相对人之间的纵向关系,忽略不同行为之间的形式差异,并将“经营者能否实质性提高竞争对手成本并最终获得垄断定价能力”作为适用的重要参照[32],才能恰当适用纵向垄断协议的兜底条款,进而将实践中符合规范保护目的的垄断行为纳入规制范围。在反垄断法相关法律规范尚未明确纵向垄断协议兜底情形的分析标准和认定因素时,“规范保护目的论”的确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需要注意的是,在判断垄断行为是否属于兜底情形的涵摄类型时,立基于“规范保护目的论”,可采用类比推理的方法,借助列举内容与兜底情形之间的关系进行识别,但要防止扩大反垄断法的规制范围,超出国家干预市场的限度。
(三)文本竞合时:选择适用
针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垄断纠纷,当存在两个以上潜在可用的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但多个法律规范间存在竞合的关系,通过适用“规范保护目的论”方可选择一个最优规范文本,以做出较为妥当的个案认定。“规范保护目的论”对于垄断行为的违法性判断起着制约和指引的作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决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适用中面临的内部竞合与内外竞合的挑战。
在文本竞合时,如何适用“规范保护目的论”进行文本选择,需依循下述四个步骤:
步骤一:法律规范文本识别。实践中,同一垄断行为可能在不同的法语境下存在不同的规范语言表达,进而落入不同的法律调整范围,出现法条竞合的情形。这往往是由于数字经济时代垄断行为纷繁复杂而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间存在边界模糊、语义交叉等问题。因此针对涉案垄断纠纷,首先要辨别出该行为可能适用的法律规范文本。
步骤二:规范保护目的识别。针对法律规范文本竞合的情形,反垄断法律适用者应当运用一定的技术和方法,建立起彼此协调的适用秩序。由于法规范文本是规范保护目的的表征,解决反垄断法律规范文义方面的竞合需要探求其规范保护目的,寻求规范适用背后的合目的性。此步骤要求从法律规范文本之中识别出规范保护目的。本文所称的规范保护目的不单指主观目的,即反垄断相关法律规范的制定者在起草法律规范文本时所欲实现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尽管主观目的在适用时具有优先性,但不具有绝对性。在新的价值诉求出现、经济关系发生变化或利益状态发生改变时,可考虑对主观目的予以修正,以探寻法规范所追求的客观保护目的。
步骤三:确定规范保护目的间的关系。法秩序由不同位阶的法律规范组成,是一种等级秩序[33]。与此相对应,规范保护目的间也存在高低之分、抽象与具体之别,但这一划分仅具有相对性。其中,规范保护目的的确定以具体规范保护目的优于抽象规范保护目的为原则。确定规范保护目的间的关系主要在于判断具体规范保护目的是否相一致,如若不一致,则所涉法律规范文本可以同时并用;如若一致,则所涉法律规范文本存在竞合,相互排斥,不能同时适用。
步骤四:法律规范文本的回归,即根据步骤三所确定的规范保护目的间的关系进而确定所适用的法律规范文本。规范保护目的内嵌于规范语言表达之中,在对规范文本的选择适用进行指引后仍需回归规范文本本身。解决垄断纠纷时,反垄断执法和司法者也最终要将法律规范文本作为处罚和裁判依据。
在明确适用“规范保护目的论”进行文本选择的四个步骤之后,其思维流程如何展开,不妨以数字经济时代典型的电商平台“二选一”为例,展现“规范保护目的论”的具体适用过程。电商平台“二选一”主要指电商平台经营者要求平台内经营者只能在该平台提供商品或服务,禁止或变相禁止该平台在其他平台开展相关经营活动。从行为外观来看,电商平台“二选一”可适用的法律规范文本涉及多部法律法规,包括《反垄断法》第二十二条第(四)项“限定交易”条款、《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第(三)项“恶意不兼容”条款及《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不合理限制”条款。上述法律规范文本间存在文义上的交叉,难以直接适用以判断行为的违法性,需要反垄断法律实施者进一步探寻上述法规范文本的保护目的。从《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关系来看,二者的抽象保护目的一致,均为市场竞争秩序,但在具体规范保护目的方面却存在差异。《反垄断法》通过规范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目的在于维护整个市场的竞争自由,保护竞争;《反不正当竞争法》通过规制特殊的不公平竞争行为,保护单个竞争者的利益[34]。二者具体规范保护目的间的差异决定了两规范的适用范围不同。在具体适用方面,电商平台“二选一”行为达到《反垄断法》的适用门槛,应优先依照该法予以评价;反之,不构成垄断行为并不必然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调整,仅对于不公平且影响市场竞争秩序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才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35]。从《反不正当竞争法》与《电子商务法》之间的关系来看,二者的规范保护目的具有一致性。《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的起草过程揭示出该条款旨在禁止平台经营者实施滥用优势地位的行为,以维护市场竞争秩序[36]。可以说《电子商务法》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品性。因此,从“规范保护目的论”的角度观之,相较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二条,《电子商务法》第三十五条更有针对性、更为详尽。
五、结语
法律实施过程中,任何放弃探求立法规范目标的人,都意味着其有意识地选择了方法上的“盲目飞行”[10]。我国数字经济时代反垄断法的实施有必要适用“规范保护目的论”作为指引,以应对当下反垄断法律规范文本模糊、竞合所带来的准确适用、选择适用挑战。“规范保护目的论”的具体适用应遵循类型化的基本要求,结合个案情形,明确不同场景的具体适用路径,即文本明确时补强适用、文本模糊时解释适用、文本竞合时选择适用。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规范保护目的论”可以适用于反垄断领域,但并不是解决数字经济时代垄断问题的万能良药,更不意味着法律规范文本不再受重视。相反,规范文本仍在反垄断法律适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于“规范保护目的论”的适用应理性看待,既要反对“万能论”,也要摒弃“虚无论”。明确“规范保护目的论”所提供的仅是一种解决垄断问题的方法,面对数字经济时代的反垄断疑难案件时,往往需要综合多种方法以寻得“最优”结论。
参考文献:
[1] 丁茂中. 纵向垄断协议兜底条款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J].竞争政策研究,2019(2):5⁃14.
[2] 李剑. 被规避的反垄断法[J]. 当代法学,2021,35(3):55⁃67.
[3]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陈爱娥,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146.
[4] 李胜利. 反不正当竞争法与反垄断法的关系:突然现状与应然选择[J]. 社会科学辑刊,2019(3):164⁃169.
[5] 姜涛. 规范保护目的:学理诠释与解释实践[J]. 法学评论,2015,33(5):107⁃117.
[6] 于改之. 法域协调视角下规范保护目的理论之重构[J]. 中国法学,2021(2):207⁃227.
[7] 李波. 过失犯中规范保护目的理论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7.
[8] 王海桥. 刑法解释的基本原理——理念、方法及其运作规则[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180.
[9] 陈兴良. 刑法教义学中的目的解释[J]. 现代法学,2023,45(3):150⁃169.
[10] 伯恩·魏德士. 法理学[M]. 丁晓春,等译.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3:307⁃404.
[11] SCHACTER J S. Metademocracy: the changing structure of legitimacy in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J]. Harvard Law Review, 1995, 108(3): 594⁃595.
[12] ESKRIDGE W N. The new textualism and normative canons[J]. Columbia Law Review, 2013, 113(2): 586.
[13] 李波. 规范保护目的理论[J]. 中国刑事法杂志,2015(1):21⁃37.
[14] 焦海涛. 不正当竞争行为认定中的实用主义批判[J]. 中国法学,2017(1):150⁃169.
[15] WELLMAN V A. Practical reasoning and judicial justification:toward and adequate theory[J]. University of Colorado Law Review, 1985, 57(1): 45⁃47.
[16] ASAF R. A purpose-based theory of corporate law[J]. Villanova Law Review, 2020, 65(3): 523⁃584.
[17] 李可. 类型思维及其法学方法论意义——以传统抽象思维作为参照[J]. 金陵法律评论,2003(2):105⁃118.
[18] 李勰.再论诚实信用原则的类型化——以传统抽象概念思维为参照[J].西南政法大学学报,2013,15(5):68⁃81.
[19] 潘子怡. 我国民法诚信原则的类型化适用[J]. 法学,2023(9):125⁃141.
[20] 叶金强. 相当因果关系理论的展开[J]. 中国法学,2008(1):34⁃51.
[21] 卡尔·拉伦茨. 法学方法论[M]. 黄家镇,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577.
[22] 许玉秀. 当代刑法思潮[M].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05:565.
[23] 蒋舸.《反不正当竞争法》网络条款的反思与解释——以类型化原理为中心[J]. 中外法学,2019,31(1):180⁃202.
[24] 张斌峰,陈西茜. 试论类型化思维及其法律适用价值[J]. 政法论丛,2017(3):118⁃125.
[25] 亚图·考夫曼. 类推与“事物本质”——兼论类型理论[M]. 吴从周,译. 台北: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9:6.
[26] 李昌麒. 经济法理念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9:27.
[27] 岳彩申. 论经济法的形式理性[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25⁃52.
[28] 岳彩申. 论经济法形式理性的优先性[J]. 社会科学研究,2003(5):78⁃83.
[29] 叶明. 经济法实质化研究[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67.
[30] FARINACCI-FERNOS J M. New originalism' and statutory interpretation[J]. Revista Juridica de la Universidad Interamericana de Puerto Rico, 2020, 55(3): 695.
[31] 金善明. 反垄断法实施的逻辑前提:解释及其反思[J]. 法学评论,2013,31(5):16⁃24.
[32] 田辰. 《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三)项法律适用问题探讨与澄清[J]. 竞争政策研究,2018(5):72⁃81.
[33] 凯尔森. 纯粹法学[M]. 张书友,译.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8:88.
[34] 袁波. 电子商务领域“二选一”行为竞争法规制的困境及出路[J]. 法学,2020(8):176⁃191.
[35] 孔祥俊. 网络恶意不兼容的法律构造与规制逻辑——基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互联网专条的展开[J]. 现代法学,2021,43(5):124⁃144.
[36]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电子商务法起草组. 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条文释义[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110⁃111.
"The Theory of Normative Protection Purposes": A New Response of Anti-Monopol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Ye Ming, Jia Hailing
(School of Economic Law,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The challenges facing anti-monopoly in the era of digital economy require the exploration of new coping strategies. In the face of the dual challenges of accurate application of norms due to the ambiguity of anti-monopoly texts and the obstacle of selective application of norms due to textual competition, "the theory of normative protection purposes", due to its developmental trajectory and extrinsic functions, can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solving the challenges of anti-monopol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In order to respect differences and prevent abuses,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normative protection purposes", to the anti-monopoly field should follow the basic requirement of typology. Follow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onopoly disputes and anti-monopoly legal normative text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ree scenarios of th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y of normative protection purposes" in the field of anti-monopol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can be derived: complementary application when the text is clear, interpretative application when the text is ambiguous, and selective application in case of textual competition.
Keywords: anti-monopoly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theory of normative protection purposes"; normative texts; typology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字经济时代竞争政策定位与反垄断问题研究”(23&ZD076);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个人信息的竞争法保护疑难问题研究”(23BFX186);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回应性监管理论视域下反垄断行政约谈制度研究”(CYB23181)
作者简介:叶 明(1972—),男,四川绵阳人,教授,研究方向:经济法;
贾海玲(1997—),女,山西忻州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经济法。
1 Joined cases C-395/96 P and C-396/96 P,CMBT and others v Commission, [2000] ECR I-01365, paras. P33-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