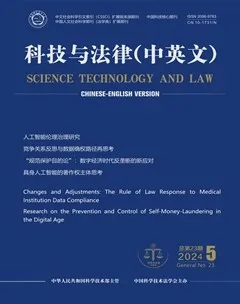赋权思路下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的完善路径
摘 要: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以赋权为思路,在模式上参考了美国《拜杜法》的同时也对其有所超越,将科技成果权属适用范围扩大至所有智力成果类知识产权,更符合中国国情和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需要。但中美两国由于国情不同,赋权于特定主体的具体含义也有所不同。在中国,赋权特定主体应当是构建一种多元权属制度模式,允许单位将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转让给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与市场有紧密联系的主体。在未来,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立法需要在赋权思路下构建统一完备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首先,构建多元的权属模式,允许单位将科技成果转让给科研人员,并允许二者在项目立项之初就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进行协商。其次,还应及时修改《科技成果转化法》等科技法律,使其与新修订的《科技进步法》相配合,构建完备的科技立法体系适应科技改革新动向。最后,立法需要对政府介入权进行明确定位,使其成为监管科技成果使用、保护公共利益以及防止关键技术流失的保障性制度。
关键词:科技成果权属;《拜杜法》;科技成果转化;知识产权
中图分类号:D 912.1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 2096-9783(2024)05⁃0013⁃12
一、问题的提出
科技成果转化要求将科技创新的成果运用到具体的生产和产业链中。实现技术有效运用和转化是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目的之一1,也是发展“新质生产力”对知识产权制度的要求[1],更是知识产权制度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在当今社会,科技的复杂性随着其发展日益增加,技术越来越多地由政府资助,通过多种渠道分散到学校、企业或者其他的科研机构之中,国家干预性成为科技成果转化的一个重要属性[2]。在这样的背景下,本文研究的科技成果转化是指大学或其他科研机构在政府财政支持下对其科研成果的商业化推广和应用2。
统计数据显示,2023年中国由高校、科研机构以及事业单位产生的发明专利占全体发明专利的25%以上3,而这些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则不到20%,显著低于企业49.3%的转化率[3]。高校与科研机构的研究经费有很多来自于政府财政支持,较低的科技成果转化率不仅不符合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不利于科技的发展,更会浪费国家的财政投入。造成此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涉及的权属规定并不完备,不完备的权属规定使得科技成果无法落到有能力转化它们的人手中,因此无法实现有效的转化4。
通过完善权属规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并不是一个新的议题,国内对此有着丰富且深入的研究。国内对科技成果权属的研究集中于职务发明权属问题,多数学者认为,应当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同时强调,科技立法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相协调[4-5]。同时,也有研究旨在厘清科技立法的体系逻辑,并依此对科技成果转化权属制度运行的全过程提出完善建议[6];还有学者从行政法的角度对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整体进行研究[7]。此外,有学者通过比较分析,吸纳外国立法实践经验对完善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权属制度提出思路[8]。尽管采用的视角并不相同,但是这些研究提供的方案不约而同地指向了“赋权”。
学术研究为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的赋权路径,进行了一定探索,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价值。但是,中国目前仍然缺乏明确且完备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赋权”的含义也有待进一步厘清。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不妨再次考察作为赋权思路的开创与典范,并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所借鉴的《拜杜法》(Bayh-Dole Act)[9],通过对“赋权”进行“溯源”,并结合中国实际探寻赋权思路在中国语境中的正确含义,并为中国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提供合理的路径,适应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
二、赋权思路下的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
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是在赋权的思路下展开的。最初1993年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以下简称《科技进步法》)中并没有科技成果权属的规定,但随后国务院与科技部发布了多项行政法规,我国开始逐步借鉴美国《拜杜法》中“放权让利”的做法进行改革[10]。同时,该由什么法律规定科技成果权属也曾出现过争议,2006年我国的《专利法修正案(草案)》中就曾有过科技成果权属的内容,但是后来仍然将该部分规定从《专利法》中移除并放置于《科技进步法》中。2007年《科技进步法》修改首次在我国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实践的基础上引入美国《拜杜法》中的核心内容,将政府资助形成的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授予项目承担者,同时将适用范围由《拜杜法》中的专利权扩张至发明专利权、计算机软件著作权、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和植物新品种权5,并且还规定了政府介入以及相应的知识产权运用规则以促进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2007年《科技进步法》的修订旨在通过将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从国家手中“下放”的方式促进其转化和应用。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以下简称《科技成果转化法》)延续了《科技进步法》的修改路径,进一步明确了专利法中政府资助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单位的规定,并赋予相应的大学或科研机构自主转化科研技术成果的权利。经过不断探索和改革,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的初步框架已经成型。通过对这一过程的审视不难发现,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最初就是以赋权为思路,并且在不断探索中为科技成果的运用和转化创造制度条件,为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实现提供更多的自由。
2021年修订的《科技进步法》代表了赋权思路下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的最新成果,它仍然坚持了赋权的思路。此次修改系统性地围绕“创新体系建设”这一主题调整了整部法律的结构,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自2012年以来科技成果权属改革试点的成果[11]:与科技成果权属最相关的第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对原先《科技进步法》第二十条和二十一条进行了的完善。第三十二条将原来第二十条的范围扩大至所有知识产权领域,并增加了科技成果的具体使用方式,明确项目承担者可以处分知识产权。第三十三条的增加则指明了未来科技成果权属制度的发展方向,即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探索赋予科学技术人员职务科技成果的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此外,此次修改对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利用方式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包括自行转化、向他人转让、联合他人共同实施转化等。此次修改不仅扩大了知识产权对科技成果的保护范围,同时还尝试与专利法进行衔接[12]。2021年《科技进步法》的修改仍然是按照赋权的思路进行:不仅科技成果权属制度的适用范围得到了扩大,法律还允许探索更多元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所有方式,同时《科技进步法》也与专利法进行互动,探索构建完整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框架。
因此,中国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在总体思路上是按照赋权的思路进行的:它参考美国《拜杜法》将专利权赋予高校和科研机构等的做法,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完善,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中国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对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成效仍然有限。如果赋权的改革思路被全球其他国家的实践验证[10],那么其在中国也应当具有发挥相应积极作用的潜力。为了探求赋权在中国语境中的应用方式,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界定其内涵,这就要我们回到科技成果赋权思路起源——美国《拜杜法》。
三、赋权思路的起源与典范:美国《拜杜法》
《拜杜法》能够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解决了科技成果专利权归属的争议,将专利权赋予大学和科研机构等私主体。这也是《拜杜法》留给其他国家最有价值的理论指引。但是我们也应当注意到,各个国家引入《拜杜法》中权属规定的尝试并不总是成功的,机械地模仿《拜杜法》规则显然是不可取的[13]。我们分析《拜杜法》的具体内容旨在透过具体规则探究具有参考价值的原理,全面了解《拜杜法》的价值及局限,吸纳其价值并克服局限,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改革提供理论支持和经验。
(一)以赋权为核心:《拜杜法》中的权属规则
《拜杜法》的核心内容在于赋权:它赋予了作为承担者的私主体选择权。承担实际研究工作的大学、科研机构或者小型企业有权利选择是否享有专利权,只要符合一些形式上的要求,小型企业就可以获得专利权[14]。承担者可以决定放弃申请专利,此时专利申请权则由联邦机构获得,并且联邦机构还享有对科技成果进行转化的权利。当政府也放弃专利权时则由实际发明人享有有关的权利[13]。在权利的获得上,小企业对发明享有优先获得专利权的权利。
当然出于国家安全与公共利益的考虑,法律对私主体拥有知识产权的情况也做出了一定的限制。在适用对象上,首先是外国企业无法获得专利权;其次是联邦机构出于实现法律目的的考虑可以限制或消除承担者的专利权;再次是被法律或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授权在国外进行情报或反情报工作的政府机关有权力出于工作的需要限制或消除承担者的专利权;最后是有关核安全事项能源部可以要求承担者不享有专利权6。此外,对于非营利机构的专利申请《拜杜法》做出了特殊的规定,包括只能将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收入用于科研或教育等。
从权利归属的角度来看,美国《拜杜法》赋予大学等科研机构选择是否获得科技成果专利权的做法,实际上是将专利权益从政府让渡给了私主体。私主体在不阻碍科技成果有效转化以及不损害国家利益和公共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处分专利权以促进其有效转化。这背后的价值考虑在于,权属确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前提,《拜杜法》的目的正是通过确定联邦资助的科研成果的权属来促进科技成果的商业化使用。因为只有将发明的专利权放到那些可以真正发挥其作用的人手中,政府在科研上投入的资金才能够得到最多回报[15]。而私主体相较政府来说有着更强的灵活性,并且与市场联系更加紧密7,将科技成果交给他们能够让这些成果放置到市场之中促进其转化。这种“赋权”的思路正是《拜杜法》成功的关键[16]。
(二)不充分的赋权:《拜杜法》的局限
尽管《拜杜法》确立了赋权的思路,但这种赋权是“不充分”的。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定位的局限决定了《拜杜法》赋权范围和内容的局限。其次,介入权的失位使得《拜杜法》中的赋权缺乏制约机制,从而无法平衡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与政府资助的目的相悖。
1.定位的局限
《拜杜法》仅仅是专利法的一部分,而非一部专门的科技法,它在定位上只是为了实现促进科技成果的商业化,而非引领科技的发展。从《拜杜法》的文本表述来看,“商业化”(commercialization)一词多次出现,且该法律大部分的文本内容都在说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目的,并没有直接提及促进科技进步,因此从《拜杜法》对于自身的定位来说,其仅仅旨在解决成果转化的问题,而并没有承担促进科技进步这样的宏伟目的8。
《拜杜法》对适用范围进行了明确的限制,其仅适用于受国家资助的专利产品,且适用对象仅仅是包括大学在内的非营利科研机构和小型企业。因此,《拜杜法》是专利法下一个解决科技成果转化这一具体问题的法律,而不是真正意义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性法律[9]。《拜杜法》的适用方式也仅限于专利,小企业和科研机构只有选择是否进行专利保护以及选择哪一个科研成果进行专利保护的权利[17],而无法选择如商业秘密等其他方式9。
此外,《拜杜法》功能的实现需要其他法律规则的配合。比如《史蒂文森法》(Stevenson-Wydler Technology Innovation Act),该法在适用上优先于《拜杜法》。《史蒂文森法》赋予联邦机构对完全由其完成的科研成果享有专利权,并且可以按照《拜杜法》的规则行使这些专利权,即联邦机构可以将专利权进行全部或部分的许可和转让。因此,《拜杜法》与《史蒂文森法》实际上形成了一套联邦机构内外合力共同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专利法系统,在外部授权联邦机构资助的主体可以获得专利权,在内部联邦机构亦可以获得自己研究成果的专利权并将其投入产业进行实际运用[17]。因此《拜杜法》无法单独实现促进科技进步的最终目的,需要与其他的专门法律法规配合才能共同实现。从这方面来说,《拜杜法》的功能是有限的。
《拜杜法》仅仅旨在解决科技成果转化问题,是专利法体系下的一个特殊法,与其他法律共同构成了美国专利法体系。在适用范围上,《拜杜法》具有排他性,对符合条件的申请人想获得专利权只能适用《拜杜法》而不能适用其他知识产权法律。当然,《拜杜法》也受到专利法一般规则的制约。通过对《拜杜法》与其他法律之间关系的分析,我们更加能够确信上文提出的观点——《拜杜法》仅仅是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这一目的的单独立法,而并不是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专门法。因此,从功能定位上来说,《拜杜法》“通过赋权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进而实现科技进步”的功能是有限的。
2.政府介入权的失位
政府介入权是一种基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需求或公共利益而由政府介入将专利强制许可给第三方使用的规定。《拜杜法》中规定政府在小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没有使用或合理使用其通过《拜杜法》获得的专利时,政府有权介入该专利的使用并将其授予第三方主体[18]。
政府介入权的内容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政府有权基于合理的理由和程序要求承担者、受托人(assignee)以及对专利享有排他性授权的权利人授予适格的申请人排他、部分排他和非排他的专利使用权。同时政府在有限的、特殊的情况下可以依职权进行上述授权行为,这些特殊的情况包括:承担者或者受托人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或者没有在合理的时间内采取有效措施促进有关专利的实践运用;出于对健康或安全的需要,且承担者或受托人无法满足这种需要;承担者、受托人以及被授权人无法有效满足联邦规定对公众使用科技成果的要求;上述私主体没有达成或者放弃了满足“美国产业优先”(preference for American industry)规定10的资助协议,或者没有履行协议中的有关义务 ⑪。政府只能出于转化或国家需要、公共利益等有限的四种情况下行使介入权,且介入权条款不存在基于一些基本原则而设立的兜底性内容,这介入权的适用情境受到了很大限制。
《拜杜法》中对介入权的规定一方面体现了政府在公共利益和私主体权益之间的权衡,政府既需要在专利得不到合理使用的情形下通过行政手段促进专利的使用,另一方面又要出于公共利益的考虑防止专利权被滥用以回应公众对于政府投资应当用于公众利益的期待[19]。因此,无论从背后的价值考量还是从规则的具体设计来看,政府介入权都与专利法中的强制许可类似。我们可以认为政府介入是一种特殊的强制许可;那么其定位应当与强制许可类似,即为了防止专利权滥用以及促进技术进步而采取的一种保障措施[20],实现其保障功能的方法则是对专利权进行限制。
显然《拜杜法》中的政府介入权并没有起到保障性的作用。尽管保障性规则的定位要求政府介入权的实施必须满足一定的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实施的条件应当过于严苛。《拜杜法》为政府行使介入权设定了过高的条件,政府如果要自行授予专利权利则需要证明自己处于上述四种情况之一才能够行使介入权。此外在程序上,《拜杜法》为专利权利人设立了申诉权,使得政府介入专利行使更加困难[21]。实际上的实施情况也说明了政府介入权难以得到实施,截至2020年,尽管有数起要求政府行使介入权的案件,但是政府的介入权一次都没有被激活过[22]。一个没有被真正实施过的规定显然无法构成有效的威慑,也无法起到良好的保障作用。
(三)《拜杜法》的综合分析:局限与价值
从规则角度分析,《拜杜法》是一个在目的和功能上都极为有限的法律,并且其本身也不完备。在立法目的上,《拜杜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促进专利的有效利用和商业化,而非促进科技进步。《拜杜法》的支持者通常也仅仅是主张《拜杜法》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而不是主张《拜杜法》能够促进科技进步[23],这使得《拜杜法》从目的上来说更像是一种政策而非法律;当然,不可否认《拜杜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促进科技发展并且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美国科技的发展,但这并不是其最主要的目的。在价值取向上,《拜杜法》有着明显的促进科研成果商业化的倾向,政府介入权并没有起到其设计之初的保障作用,在规则设计和实施层面都没能实现科技成果转化与公共利益的平衡。最后,《拜杜法》的调整范围也是有限的,该法律仅仅适用于专利权,并且调整对象仅仅包括小型企业或大学等非营利机构。因此,《拜杜法》是有局限性的,它仅仅是美国专利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也使得单纯模仿《拜杜法》的规则毫无意义,因为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文化、政治环境以及法律体系,单纯地模仿《拜杜法》让大学或科研机构成为专利权人的做法并不能保证为模仿国带来利益[13]。
实际上,《拜杜法》为其他国家真正带来的启示性价值在于规则背后的“赋权”理论。在英美法语境中,成文法的只言片语是法律理论和普通法的凝练,因此规则背后的理论和价值取向才是真正可能具有普适性和借鉴意义的。在此意义上,美国《拜杜法》及其实践告诉我们的应当是如何处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只有交给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人才能够充分发挥其价值,充分实现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这才应当是“赋权”这一思路在科技成果权属制度中的正确含义。在美国,赋权的对象之所以是大学和科研机构等是因为他们是市场的参与者,能够与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能够灵活地依据市场的需求处分自己的知识产权。但是中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等与美国的定位是不同的,这种定位上的不同使得中国机械地参考美国《拜杜法》制定出来的法律规则必然无法产生其在美国的效果。
四、再探赋权思路下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从《拜杜法》背后的赋权思路切入
当我们通过探究《拜杜法》了解了科技成果权属制度中赋权思路的含义后,我们有必要再次检视中国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选择了和美国《拜杜法》一样将科研项目成果的知识产权赋予项目承担者的模式。但二者基本的经济制度不同,仅仅只是模式上的借鉴。不过,中国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在某些规则上实现了对美国《拜杜法》的超越。我们用《拜杜法》背后的赋权思路分析中国的改革,能为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的完善指明方向。
(一)中国科技成果赋权要满足科技法的特殊定位
1.从科技法出发的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
《拜杜法》与《科技进步法》的定位是不同的。美国并没有统一的促进科技进步与发展的法律,而是将科技发展法律规则分散在各个领域的法律之中,《拜杜法》仅仅是在功能上与促进科技发展的规则有所重合。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拜杜法》无论从立法过程、法律文本表述,还是法律制度设计上来说都只是专利法的一个组成部分,不能将其看作一部单独的法律[9]。而《科技进步法》第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一开始就属于科技法的一部分,承担着促进科技进步、知识成果转化等多方面的作用。尽管该条款在功能上与知识产权法律规则重合并且需要与知识产权体系契合,但其作为科技法的一部分,有着超越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公法目的。
定位的不同决定了二者调整范围的不同。作为专利法的一部分《拜杜法》的调整范围仅限于专利领域;但作为《科技进步法》作为科技法的一部分,其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则应当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应当适用于更广阔的知识产权领域而不能仅仅聚焦于专利。所以,从体系定位的角度来看,《科技进步法》第三十二条和三十三条将适用范围扩张至整个知识产权领域从法理上来说是合理的,这是《科技进步法》定位和目的的要求。
当然,尽管扩大科技成果权属制度的适用范围是《科技进步法》作为科技法之“基本法”这一定位提出的应然层面要求,但是我们仍然应当注意扩大该项规则适用范围的可行性问题。综合来看,在《拜杜法》的基础上扩大科技成果转化中权属制度的适用范围是可行的。
首先,《科技进步法》将科技成果权属的范围从专利扩大到知识产权符合当今科技成果转化实践。科技成果的载体是多样的,除了专利以外,计算机软件著作权、植物新品种、集成电路布图等都可以成为科技成果的载体,并且与知识产权密切相关[24]。而正如上文所示,赋权本质上在于赋予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主体知识产权以实现科技成果的有效转化和利用,而其中的主要手段便是包括转让和许可在内的知识产权交易。所以,知识产权交易对象的多样性意味着科技成果转化方式同样牵涉多种知识产权。因此,当下科技成果的载体是多样的,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容也是多样的,这意味着在当今社会科技立法若仅将科技成果转化的范围限定在专利领域显然是不够的。
此外,《科技进步法》将《拜杜法》中的专利权扩张至整个知识产权领域与目前的立法趋势并不冲突。知识产权有关的法律呈现出强调智力成果应用的趋势。首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对技术合同的内容进行了较大篇幅的修改,不仅在立法目的上强调了技术合同应当保护知识产权,并促进科技成果的“研发、转化、应用和推广”[24];还在制度设计上强调了技术合同与知识产权的互动,使得原本的“技术—合同”二元互动转化为现在的“技术—知识产权—合同”的三元互动[25],将技术合同与知识产权链接旨在促进通过技术合同将知识产权实际运用;在制度涵盖范围上,《民法典》关于技术合同的规定几乎概括了所有的知识产权种类[25]。作为调整知识产权的基础规范[26],《民法典》的立法趋势反映了知识产权法律的发展动向,因此从《民法典》的变化来看,知识产权法的发展有强调对知识产权具体应用的趋势。此外,从知识产权制度本身的发展趋势来看,知识产权也在逐渐强调科技成果转化,即知识产权的应用本就是知识产权法基本原则的内涵之一[27],是所有类型的知识产权在立法和法律适用时都应当遵循的原则;国务院发布的《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年)》也指出要“健全运行高效顺畅、价值充分实现的运用机制”,这旨在强调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地位[28]。在整个知识产权领域立法强调将智力成果投入实际应用的趋势之下,《科技进步法》将赋予项目承担者知识产权的规定扩大至整个知识产权领域符合当今的立法趋势。
因此,《科技进步法》中对于科技成果转化权属制度在适用范围上的扩大不仅在理论上合理,在规则衔接上可行,更是基于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实践而做出的必然选择;就适用范围而言,中国《科技进步法》这一点改动是对美国《拜杜法》的超越。
2.科技法定位对知识产权法的进一步要求
当然,将科技成果权属制度作为科技法的一部分在理论上固然是符合目前中国实践的合理调整,但是这也对知识产权法律规则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美国《拜杜法》对接的主要是专利法内部的法律,而中国《科技进步法》涉及的是整个知识产权领域的法律,这对知识产权法与科技法的衔接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知识产权法需要为科技成果权属的规定提供足够充分的法律依据。
从目前中国知识产权法律规则的内容来看,中国的知识产权法还没有能够完全衔接科技法。无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以下简称《专利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还是《民法典》等其他法律法规在职务科技成果的权属问题上都规定相应的知识产权原则上应当由单位享有;当然,职务作品的著作权原则上由作者享有,但是主要利用法人或非法人组织条件创作并由其承担责任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单位所有。在科研项目上个人通常没有能力和资源组织科研项目,大多数情况下需要利用单位的资源,因此可以认为由政府资助产出的科技成果属于著作权由单位享有的情况 ⑫。这显然与赋权的理念不符。而《科技进步法》第三十三条旨在探索解决这一问题,赋予科研人员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但现有的知识产权法律大多没有为这条规定提供法律依据,在这种情况下科技法无法与现行的知识产权法律规定衔接。当然也有法律在进行与《科技进步法》衔接的努力,《专利法》在第四次修改后已经允许单位处分专利权,这就是《专利法》尝试与《科技进步法》衔接的体现[4]。但其他知识产权法律并没有类似的规定,与《科技进步法》的衔接仍然不够充分。
(二)中国科技成果赋权要满足中国实际
中国的实际情况注定其在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中不能直接参考美国的做法。尽管中美两国在科技成果的归属上都采取了赋权的思路,规定由项目承担者享有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但二者本质上是不同的,这主要是因为两国在财产权属制度上存在根本上的不同。《拜杜法》旨在解决国家和私人机构“谁应当拥有和利用科研成果,谁应当享受科研成果带来的果实”的问题[16],其所应用的对象并非联邦机构。赋予科研机构科技成果的专利权实际上是将对该科研成果占有、使用、收益以及处分的权益划分给了私主体,私主体可以以更加灵活的方式对专利进行处置,从而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而我国的高校和科研机构大多为事业单位,《科技进步法》将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划分给他们本质上并没有将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划分给私主体,因而实际上并没有遵循赋权的思路。
但倘若按照《拜杜法》赋权私主体的思路将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让渡给私主体则应当由法律规定将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优先赋予科研人员或者相关的企业等私主体,这也是不合理的。对于由事业单位承担的科研项目,法律不能将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直接赋予私主体。在我国大多数科研成果属于国有资产[29],具有较强的公益属性,出于维护公共利益的需要,不能任意地将科技成果交由私主体处置。此外,中国《专利法》仍然将职务发明的专利权认定为归单位所有[30],也是出于促进成果转化的考虑,为了避免给科研团队内部设置障碍⑬ 。诚然科技成果转化十分重要,但是考虑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带有一定的公益性,且对于属于国有财产的知识产权而言优先将其授予私主体会造成国有资产尤其是那些重要的科研成果流失的问题,法律不应当在单位作为承担者的情况下,直接将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出成果的知识产权赋予科研项目完成人或参与人。至于单位为何能对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拥有处分权,则是因为在单位是高校等事业单位时,它们从性质上来说就应当具有公益性,并且国家机关或事业单位的管理规定保障其公益性,因此出于知识产权转化的需要而赋予单位处分权与优先将知识产权授予个人是不同的。当然,目前《科技进步法》并没有将私人企业排除在政府资助的对象范围之外,当承担者是私人企业时,企业直接与政府部门对接,政府部门可以通过行政审批的方式保障科技成果的公益性;而与科研人员直接对接的通常是高校或者科研机构,保障科技成果公益性的责任很多时候需要他们实现,直接通过法律将单位的知识产权授予科研项目完成人则意味着在承担人是单位的情况下由科研人员享有科技成果知识产权,这种做法无法同时保障科技成果的公益性和转化使用。因此不应当由法律直接将原本属于单位的知识产权赋予个人。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技成果权属就应当固守国有的原则。《拜杜法》的思路依然具有借鉴的价值,因为私主体在科技成果转化上显然拥有比公主体更大的灵活性,科技成果转化最终也需要通过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主体来实现;事业单位在处理知识产权时仍然会受到繁琐复杂的行政程序的制约[31],这是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的原因之一。
因此,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的正确思路应当是以科技成果转化为目的,构建多元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权属模式,即充分利用私主体等与市场紧密联系主体的优势,发挥意思自治的功能,允许单位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处分给科研人员,同时允许科研人员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等就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权属与利益分配问题进行协商。这样一来,对于那些有能力自主转化的研发人员来说,拥有知识产权能够让他们更有效地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同时科技成果在最了解他们的研发人员手中也能获得最大化的转化效益。对于转化能力较弱的科研人员来说,与单位就利益分配问题进行协商可以充分保障其利益,由单位进行转化则可以获得较为高效的转化效率。这不仅符合赋权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思路,也符合中国实际。
(三)中国科技成果赋权要保障公共利益:政府介入权
《拜杜法》引入政府介入权作为保障公共利益、制约专利垄断的保障机制。中国的《科技进步法》也参考了这一做法,将政府的介入权认定为一种保障性质的条款,在定位上与强制许可相似;并且《科技进步法》还规定了知识产权人报告制度以监管知识产权的实际运用情况。因此在政府介入权的设计上,《科技进步法》三十二条的内容并没有在实质上对《拜杜法》的模式进行优化,仅仅是在《科技进步法》内对适用情况作出了较为原则性的规定。过于原则性的规定确实为政府介入权的行使提供较为便利的条件,但同样也会存在隐患:宽泛的规定既有可能造成权力滥用的风险,也可能由于缺乏具体指引而导致介入权被“束之高阁”。此外,根据科技部与全国人大法工委共同编写的《科技进步法》法律释义的内容,政府介入权的适用情形包括了强制许可的规定[12],因此当强制许可已有较为具体的适用情形时,相较于强制许可更为严格的规定当然更需要具体的适用性加以确定。
正如前文所述XsYrQHM6vu8LyIY+R2d7VGSYttk6Wa8qkvyCSD8JbF8=,政府介入实际上是利益平衡的产物,是为了防止政府资助的科研项目产生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被不合理利用或不使用从而损害公共利益而设立的,因此政府介入必须同时遵循保障公共利益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原则[32],实际上,政府介入追求的并不是扩大政府行政权的范围,而是通过制度设计发挥介入权的威力以规范科技成果转化行为[33]。这意味着政府介入应当是一种保障性制度。因此对于我国科技成果转化权属规定而言,合理的政府介入权设计需要在保障科技成果转化的基础上实现保护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这就要求对政府介入权的具体适用情形进行明确的规定,只有在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形下政府才能介入。
五、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的改革路径——赋权特定主体
(一)赋权特定主体的内涵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在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中,赋权的内涵不应当直接照搬美国《拜杜法》中的将专利权给予高校、科研机构以及小型企业的做法,而是应当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目的,综合考虑科技成果的国有财产性质和公益属性,将科技成果交到能够最有效实现其转化的主体手中。私主体是这些与市场紧密联系主体的代表,当然,中国是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的,存在国有企业或者其他由国家控制的市场主体,它们也是市场的参与者,自然也可以在遵循市场规则的前提下成为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受让者。这些市场主体与市场的接触最为密切,同时也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将知识产权放置到他们手中能够利用市场的作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因此,“赋权”在中国语境中应当是“赋权特定主体”,即将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给予能够与市场建立紧密联系的特定主体。当我们明确将科技成果赋权特定主体的内涵后,我们才能基于理论分析以及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现状提出具体的完善思路,为中国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改革提供充足的理论基础,并指出可行的完善思路。
(二)中国科技成果转化权属制度的完善思路
在法律体系建构上,中国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被规定在《科技进步法》之中,因此除了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目的外,中国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还兼具通过鼓励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发展的任务,这要求科技法内部与科技法和其他部门法之间要衔接有序。但是,中国的科技法与知识产权法的衔接仍然有待完善,科技法内部并没有完备的体系架构,《科技进步法》与《科技成果转化法》之间仍然存在立法上的不统一,并且各地方采取的科技成果权属的模式并不一致。在地方上,不同省份对科技成果转化采取了不同的模式,包括奖励科研人员一定比例的成果所属权;将国家资金支持的科技成果认定为单位,其余从约定;将职务科技成果权利全部或部分赋予完成人以及科研机构优先受让这四种模式[34]。因此,中国缺乏统一清晰的科技成果权属规则。
此外,现行中国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没有很好借鉴《拜杜法》的核心内容,没能充分发挥其灵活性,让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主体享有国家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尽管《科技进步法》第三十三条规定了探索多种方式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但这只是方向上的指引,缺乏统一且细化的规定。此外,中美在政府介入权上都不成熟,仍然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因此,基于上述对比分析笔者给出如下完善思路:
1. 完善中国科技成果转化的法律体系建设
美国《拜杜法》并不是一部单独的法律,而是与专利法制度紧密配合的法律规则,其与专利法及其他法律并不矛盾,并且在最后明确标注了与其他联邦规则在适用上的关系 ⑭;我国现行科技法则在科技成果转化领域存在着法律之间相互矛盾的情况,立法体系需要进一步完善。
首先,科技法与其他部门法之间需要进行良好的衔接。在目前的知识产权法领域,只有《专利法》规定允许单位以促进转化的方式处分知识产权,其他领域的立法缺乏相关规定。法律应当明确指出单位可以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目的和方式将相应的知识产权转让给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主体,而不是对转化对象的规定含混不清。这样《科技进步法》中的科技成果权属规定才能够有充分的法律依据。在法律关系上,明确《科技进步法》中的科技成果权属规定是知识产权法律规定中的特殊规定,对于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应当优先适用。
其次,科技法内部需要进一步自洽。《科技进步法》规定了促进科技进步的基本原则和措施[12],是科技立法的基本法,对其他科技法律规范具有方向上的指导意义和制度上的基础作用[35]。其他的科技立法不能与其相违背。因此,《科技进步法》需要对科技成果转化的权属给出明确的规定;现行《科技进步法》第三十三条指出了立法的取向,这尽管给地方探索建立多种形式的科技成果转化权属制度留出了空间,但缺乏统一且符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需要的具体制度构建仍然不是长久之计。考虑科技立法的发展趋势,应当明确赋予科研人员更为广泛的使用权,以及以法律的形式明确高校可以让渡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允许多种形式的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权属存在。此外,《科技成果转化法》立法并没有与科技法的立法趋势同步,需要对该法第十九条进行修改,允许科研人员与科研机构就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约定,删除不改变权属这一前提,以呼应《科技进步法》第三十三条的要求,避免法律上的矛盾,为科技成果转化改革创造条件。具体的思路应当是由《科技进步法》明确规定允许科研人员享有广泛的使用权,并赋予科研机构处分知识产权的权利,允许科研人员拥有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再由《科技成果转化法》对包括权属类型、处分方法以及处分形式等转化中的具体权属问题进行细节上的规定。在允许科研人员拥有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框架下,地方可以颁布行政法规对科技成果转化进行进一步的规定和创新。
2. 遵循赋权思路的正确内涵构建多元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
在具体的权属设计上,美国《拜杜法》的立法模式及其实践给予我们的启示并不是将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交到大学等科研机构手中,而是将其给予科研人员等最了解该成果并与市场紧密联系,能真正将科技成果进行实际转化的主体。在中国与市场紧密联系的主体是企业,而能与企业建立联系的除了高校外还有科研人员本身,因此可以做如下的制度设计:存在知识产权归属约定的情况下依照约定,不存在约定的情况下则知识产权归于作为承包者的单位,并允许单位将科技成果处分权给包括科研人员在内的特定主体,同时允许双方给予意思自治的情况下就科技成果的权属、转化以及利益分配等问题进行协商。
这种制度设计的理由在于科技成果是由国家财政支持产出的,带有公共利益,属于国家财产,出于保护国家财产、防止流失的需要,仍然应当坚持在单位作为科研项目承担人,且没有另外约定的情况下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国有,即由科研机构等单位享有。因此,为了在保护国有财产的前提下实现以权属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目的,对于承担人是单位的科技成果应当在以单位所有为原则的前提下赋予拥有知识产权科研机构处分知识产权的权利,单位在经过一定程序后既可以放弃相关知识产权,也可以将其转让或许可他人使用。对于放弃的知识产权则可以参考美国《拜杜法》由政府获得,政府放弃的则可以由科研人员获得。这样规定的理由在于,科研成果知识产权属于国有财产,在科研机构放弃时应当回归国家而非交由科研人员。在可以获得知识产权的主体上,应当在立法中明确科研人员可以享有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给予科研人员在意思自治基础上拥有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权利。科研机构在经过合理的评估程序后可以将知识产权转让或部分转让给科研人员或者与其共有,同时科研人员也可以在科研项目开始时与科研机构就科技成果的权属进行协商确定;而具体的权属实现方式则可以使用技术转让或许可合同实现。这样在防止国有财产流失的情况下,可以充分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同时,对于有转化能力的科研人员而言,多元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可以保障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在最了解它的人手中进行成果转化;对于缺乏自主转化能力的科研人员,则可以依托高校技术转化中心的平台与企业合作,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因此,多元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可以通过灵活处理权属问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从而实现以权属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目标。
3. 完善政府介入权的规定
政府介入权是一种保障性质的规定,美国《拜杜法》中政府介入权是为了保障专利的转化以及公共利益的实现,我国政府介入的定位也与之类似。但是,我国科技成果原则上属于国有财产,在允许科研机构处分的语境下,政府介入应当被赋予一种新的职责——防止国有财产流失和关键技术外流,如果出现关键技术流失的情况,则可以启动政府介入干预科研机构对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处分。因此,政府介入的规定在中国应当在科技成果无法有效转化、基于国家或公共利益以及防止技术流失三种情形下启动。在具体的适用情况上,美国《拜杜法》中政府介入权是使用条件过于狭窄而没有实际得到实施,中国《科技进步法》则缺乏明确的适用条件而无法适用。政府介入权不能无限扩张,因此在具体的适用情形上需要由《科技成果转化法》以及相关行政法规进行明确,同时也要规定相应的原则性条款防止政府介入条款被“束之高阁”。在具体的实施机制上,则可以参考《科技进步法》第三十二条的思路,依据项目承担者的报告确定是否要介入。
六、结语
中国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以“赋权”为思路进行。赋权的思路源自美国的《拜杜法》,其内核在于将联邦资助产生的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赋予与市场联系最为密切的主体。《拜杜法》规则背后的理论内核才最具有普适性和参考意义。中国高校大多为事业单位,因此为了充分发挥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实现以权属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立法目的,中国语境下赋权思路在科技成果权属制度上的呈现应当是多元的:在单位为科研项目承担者的情况下,让科技成果知识产权首先为单位所有,同时赋予单位处分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权利,科研人员可以因此获得科技成果的知识产权,也可以在项目开始时就科技成果权属问题与单位进行协商。这样能够同时兼顾不同的科研人员:对于有能力转化的科研人员自己进行科技成果转化,从而充分地调动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对于没有能力独立转化的科研人员,自己决定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归属也可以更加灵活地借助高校或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转化平台进行技术的转化。政府介入则应当作为保障性制度保障科技成果有效转化、国家和公共利益以及防止关键技术流失。
当然,中国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改革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比如,《科技进步法》从其科技立法“基本法”的定位出发,将科技成果转化规定适用于所有知识产权领域是基于我国实践做出恰当的立法行为,能够实现以权属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的立法目的。未来,在确立科技成果知识产权权属的基础上,仍有科技成果知识产权的权属变动方式、收益分配以及风险预防等多方面法律问题有待进一步研究。在充分研究基础上形成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不仅应当吸收外国经验,同时应当立足中国实践,克服中国和其他国家实践中遇到的问题,实现以权属制度促进知识产权的目的,促进科技发展,进而推动“新质生产力”的进步。
参考文献:
[1] 马忠法,张楚沁. 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与新质生产力[EB/OL].知产前沿(2024-03-25)[2024⁃3-30].https://mp.weixin.qq.com/s/AoEMj3iTOz53j2SmTnghJQ.
[2] 马忠法. 技术转移法[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25.
[3] 国家知识产权局. 2022年中国专利调查报告[R/OL]. (2022-12-04)[2024-03-30].https://www.cnipa.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20 22%E5%B9%B4%E4%B8%AD%E5%9B%BD%E4%B8 %93%E5%88%A9%E8%B0%83%E6%9F%A5%E6%8A% A5%E5%91%8A.pdf&filename=5485425747ed467397ebabdbc3172 93a.pdf:128,39,151.
[4] 刘强. 《专利法》第四次修改背景下职务科技成果混合所有制研究[J]. 知识产权,2022(10):83.
[5] 李政刚. 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的法律障碍及其消解[J].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2):68⁃75.
[6] 张栋,薛澜. 职务科技成果权属改革全方位法规体系协调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4年2月28日网络首发:1⁃11.
[7] 李晓鸣. 促进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的行政法路径研究[J]. 法学论坛,2023(4):139⁃149.
[8] 贾佳,赵兰香,万劲波. 职务发明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中外比较研究[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15(7):3⁃10.
[9] 肖尤丹. 全面迈向创新法时代——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修订评述[J]. 中国科学院院刊,2022(1):874⁃877.
[10] 胡朝阳. 科技进步法第20条和第21条的立法比较完善[J]. 科学学研究,2011(3):327⁃329.
[11] 徐棣枫.“拜—杜规则”与《中国科技进步法》和《专利法》的修订[J]. 南京大学法律评论,2008年春秋合卷:101.
[12] 李学勇,王志刚,张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释义[M].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22:6⁃122.
[13] CHAKROUN N. The Bayh-Dole Act: an exportable technology transfer policy?[J]. Queen Mary Journa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2012, 2(1): 81⁃89.
[14] BOJIC B. US technological transfer legal considerations with special emphasis on Bayh-Dole Act and federal technology transfer act[J].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on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2020, 50: 491.
[15] PULSINELLI G. Share and share alike: increasing access to government-funded inventions under the Bayh-Dole Act[J]. Minnesota Journal of Law, Science & Technology, 2006, 7(2): 404⁃410.
[16] LOISE V, STEVENS A J. The Bayh-Dole Act turns 30[J]. Science Translational Medicine, 2010, 2(52): 27.
[17] RAUBITSCHEK J H. Responsibilities under the Bayh-Dole Act[J]. Journal of the Patent and Trademark Office Society, 2005, 87(4): 314.
[18] EBERLE M. March-in rights under the Bayh-Dole Act: public access to federally funded research[J]. Marquette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Review, 1999(3): 160.
[19] 陈迎新,李施琦,周玥. 美国《拜杜法案》介入权改革及其对中国的启示[J]. 中国科技论坛,2017(7):170.
[20] 冯晓青. 知识产权法利益平衡理论[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660.
[21] GOSWAMI S. Windfall profits and failed coals of the Bayh-Dole Act[J]. Journal of Gender, Race and Justice, 2016, 19(2) : 391⁃392.
[22] PARADISE J. COVID-IP: staring down the Bayh-Dole Act with 2020 vision[J]. Journal of Law and the Biosciences, 2020, 7(1): 7.
[23] OUELLETTE L L. Addressing the green patent global deadlock through Bayh-Dole Reform[J]. Yale Law Journal, 2010, 119(7) : 1731.
[24] 马忠法. 论我国《民法典》中的技术合同规范[J]. 知识产权,2023(9):46⁃55.
[25] 刘强.《民法典》技术合同章立法研究——兼论与知识产权法的互动[J].科技与法律(中英文),2021(6):2⁃3.
[26] 吴汉东. 论“民法典时代”的中国知识产权基本法[J]. 知识产权,2021(4):10.
[27] 张 鹏,赵炜楠.《知识产权基本法》立法目的与基本原则研究[J]. 知识产权,2018(12):52.
[28] 申长雨.《知识产权强国建设纲要(2021—2035)》辅导读本[M].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2:8.
[29] 万 浩,黄武双. 论国有科技成果权属制度——使用权“类所有权”化[J]. 科技与法律,2019(1):41.
[30] 朱一飞.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法律制度的检视与重构[J]. 法学2016(4):85.
[31] 王影航,李金惠,李炳超. 职务科技成果赋权改革的法治标准及优化路径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3(4):100.
[32] 李石勇. 财政资助科技成果政府介入权法律制度探究[J]. 政法论丛,2018(4):85⁃86.
[33] 唐素琴,李科武.介入权与政府资助项目成果转化的关系探析[J].科技与法律2010(1):74.
[34] 王海芸,曹爱红. 立法视角下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规定模式对比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2(11):137⁃138.
[35] 陈宝明,彭春燕.《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重点内容解读[J]. 中国科技论坛,2023(2):1.
Comparison Study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Legal System for Ownership of Government-Funded Technology under the Empowerment Theory: Starting from Law of PRC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Bayh-Dole Act
Ma Zhongfa, Gu Chenwei
(Law School,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8, China)
Abstract:Bayh-Dole Act has been the representative law in technology transfer for its innovation that endow private subjects with patents of government-funded technology. By introducing the Bayh-Dole rules into the Chinese legal system,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exceeded the Bayh-Dole Act in that it extends the rules of ownership to all intellectual properties, which is an act based on China's legal practice. Empowerment in China is endowing subjects that are highly related to market, like researchers and companies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 Under the empowerment theory, the Chinese rules still have much room for further improvement. Firstly, researchers should possess a wider range of rights to use the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right to negotiate with the institu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R&D programs. Besides, due adjustment should be made on Law of PRC 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gress along with other related rules to constitute a complete legal system that is internally cogent and externally appropriate. Last but not least, march-in right should be used to stimulate technology transfer, protect public interest and prevent important technique form losing.
Keywords: ownership of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 Bayh-Dole Act; technology transfer; intellectual property
作者简介: 马忠法(1966—),男,安徽滁州人,教授,法学博士,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国际法;
辜辰炜(2000—),男,江苏淮安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国际法。
1 有论者或许会认为知识产权制度的中心目的应该是保护,但实际上这是一种有所偏颇的认知。诚然知识产权保护是知识产权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保护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智力成果的有效运用和转化。这一点可以从《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第7条中看出:第7条知识产权的“目标”中看出:“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实施应有助于促进技术革新及技术转让和传播,有助于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的相互利益,并有助于社会和经济福利及权利与义务的平衡。”显然,技术的转化和传播的重要途径是转化和运用,同时“技术知识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也说明技术应当得到转化;因此,技术的运用和转化是保护的目的。如果TRIPs协议是其成员国的共识,那么显然这些国家都承认了知识产权的目的之一是促进技术的转化。当然,知识产权的目的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话题,且并不是本文讨论的重点,所以本文不在此话题上进行进一步深入的讨论。不过我们至少可以认为:技术的有效运用和转化是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之一。
2 科技指科学与技术,前者包括基础科学与应用科学等方面,后者通常指“实际应用的系统的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及二者的结合)”更偏向对于科学的应用。但是在成果转化领域,二者都具有被商业化的可能,所以笔者将其统称为“科技”。
3 数据来自国家知识产权局分专利权人类型国内专利授权统计表,https://www.cnipa.gov.cn/module/download/down.jsp?i_ID=189727&colID=3187。
4 国家知识产权局的调查显示,除去专利不具有商业价值等因素外,科研团队缺乏转化意识,以及对于以转化为目的的专利缺乏对发明人的激励和缺乏对专利转移转化管理人的激励都是专利转化中主要的障碍。这实际上都是由于对专利权的不合理分配导致的。同时,合理的科技成果权属制度能够充分激发科研团队的专利转化意识,从而改善科研团队专利转化运用意识不足的情况。笔者注意到专利不以转化为目的、专利不能适应市场需要等是阻碍专利转化的最主要原因,但是这并不是完善权属制度就能解决的问题,因此不属于本文的讨论范围;改革是多维度的,不能因为某些问题是导致专利转化不充分现象的主要原因而忽略对于其他导致该现象问题的完善。
5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2007)》第二十条。
6 35 U.S.C. §202(a).
7 美国很多高校都设有“技术转移中心”负责科技成果的转化,这些技术转移中心负责与企业合作,将高校的科技成果转让或许可给企业。中国的很多高校也有类似的机构。
8 促进科技进步当然是《拜杜法》的最终目的之一,但这也是所有知识产权制度的目的。从直接目的上来说《拜杜法》主要强调的是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商业化是其最直接的目的。
9 有企业曾希望通过商业秘密保护相关的科技成果,但最终没能实现。这背后的原因在于,政府资助科研项目往往出于公共利益,而对科研成果采取商业秘密的方式进行保护显然对公共利益并没有好处,还会使得原本兜底性质的政府介入权没有适用的空间,这显然与联邦资助的目的相违背。专利与技术最为相关,所以通常采用专利保护科技成果。
10 该规定是指只有在美国产业无法生产或者与生产商的谈判没有成功时,获得专利权的小企业或非营利组织才能将生产或销售专利产品或者使用专利生产产品的权利授予第三方在外国制造,否则只能将该权利授予同意将相关产品在美国制造的第三方,See 35 U.S.C. §204。
⑪ 35 U.S.C. §203(a).
⑫ 关于职务科研成果权属的规定参见《著作权法》第十八条、《专利法》第六条以及《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条;同时,关于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专有权、植物新品种权以及计算机软件著作权等其他职务知识产权的权利归属问题,根据《植物新品种保护条例》第七条的规定,由于职务行为产生的植物新品种申请权属于单位;关于集成电路的权属问题《集成电路布图设计保护条例》没有对职务产生的集成电路布图专有权权属进行规定,但是规定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主持,并依据其意志创作,且由该组织承担责任的布图设计的著作权由法人或其他组织享有。因此在单位承担科研项目的情境下,集成电路布图设计的专有权应当也由单位获得。
⑬ 比如可能会导致团队内部利益分配不均等,同时所有的科研人员都为科技成果作出贡献,倘若采取共有则不利于知识产权的转让与许可;倘若不采取共有则可能会导致利益分配不均。
⑭ 35 U.S.C. §2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