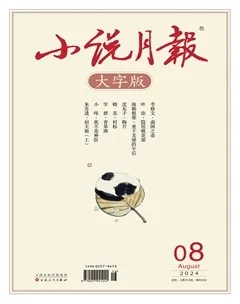青草湖
这一天的夜像是从黑壳楠烧黑的伤口那里来。一个带枪的男人穿过夜色,进了牛庄。进村的路像一段埋伏好的睡眠,每一张门都感到路在通向它。没有狗叫,门后面的夜像沉默的铁。敲门声在泽三爷家的后墙响起,再度响起时到了牛道坤那里。牛道坤的家只有一张门可敲,搭在一边的猪圈是一面布做的门帘。几条人影移过来时,门帘像旗子一样飘起。谁的食指和中指在门上头叩响,正在行进的鼻息蓦地一惊。牛道坤披衣出门,门外边不时传来嗡嗡的说话声。女人跟着穿衣出门,一个没穿衣的男孩擦着眼睛站到门口。
牛道坤跟着一个带枪的男人一起出了村。王村一样没有狗叫,两个人从屋后的竹林径直下到哈巴家的门口。隔着门听到鼾响,敲门没能把鼾声敲断。牛道坤一弯腰,把门从门轴那儿端了下来。门没了,鼾声照旧。带枪的人划了一根洋火,洋火找到灯,最后停在灯芯上。一个大胖子像一只摔死的泥蛙仰在床上,鼾声围着挺起的肚子在转。摇醒之后,这家伙半天才弄清楚进来的是牛道坤。牛道坤叫他走,他问做什么。牛道坤说,你这副身板,除了拿去堵枪子,还能做什么?他说好。
三个人穿过林子,穿过茅草,穿过稻田和红薯地,等到天从背后亮起来时,他们到了九马咀。水退到远处,湖草追着湖水一直往前长。不管下雨下雪,它们只能在这时候长,它们得赶在水淹过来之前完成这一轮生长。三个人踏着湖草往前走,一只船停在草没来得及长起来的泥滩上。
竹篙来到牛道坤手上,牛道坤一下回到水上的日子。手臂随着竹篙低下去,泥滩在船底滑动起来。立在船舱里的两个人兀地停顿了一下,入水的船随即牵起一簇浑水,一下一下往前窜。
船到湖洲边,芦苇代替水在高处簸着风。空心的芦苇足够柔软,涨水时,水牵着它们由北往南游;水退了,冬季风吹过来,它们又掉转身子往南跑。其实它们哪里也没去,去的只是风和水,它们一直在它们的根上。一千条叶子一千道风,拌上密匝匝的鸟叫和虫鸣。
他们把船拖上湖洲,藏进齐腰深的湖草里。牛道坤在前,身板宽的留最后,三个人分开芦苇往里走。芦苇叶子一阵厮磨,在他们上头裂出一条缝,到哈巴那里时裂到极限,好些芦苇因此折瘪了身子。天沿着那条缝隙听下来,它会听到中间那个呼吸得有些急促,后面那个却是笨重。芦苇过去是一片藜蒿和红蓼,再过去又是芦苇。一块苇塘,水看起来很深。苇塘那边,牛道坤一眼看到那块布。
一朵蘑菇一样从天上飘下来的云,到地上就成了一块布。难怪好多云像棉花,有了棉花就可以织成布。听带枪的人说,那个人不是住在天上,而是住在地的那一边。他还告诉他,东洋人从海那边来。牛道坤没去过海边,可他放过木排,知道过了汉口再往下,最后就是海。至于地那边,他爹他娘应该清楚,窑匠和三哑巴想来也知道了,眼前这家伙他怎么知道?明明从天上来,他却说人家从地那边来。牛道坤有些不喜欢这家伙。瞧他的样子,好像一个人腰上头挂了一坨铁,怎么说都是对的。
那天,天上有大鸟在飞。邵老爹吓软了脚,牛道坤代替他在湖滩上放牛。天上的东西,它要飞你不能叫它不飞。只要东洋人没到地头上来,地就还是他们的,牛还得吃草,人还得在地上走。没错,有时候大鸟会往地上掉。它要往地上掉,你没法叫它不掉。只求老天不要让它们往庄子里掉,田里地里,住人住祖宗的地方都不要掉。当然也不要往他和他的牛这里掉。
它真的在往下掉!说一声掉就一头往下栽,屁股竖起来朝着天,又是放屁,又是冒烟,还冒火。吃草的牛抬起头往上看,连嘴里的草都忘了嚼。眼睁睁看着它一头栽进湖里,湖水湖泥一齐往上蹿。真奇怪,好一阵他光知道岸和湖在震,却没有听到声音。直到那么多泥水从上头摔下来,巨大的声响才跟着浪一起奔过来。他看到浪翻起的铁皮和鱼,油污、泡沫和泥。火不见了,水在冒着烟。水又慌又乱,一会儿簇到一起像是要往上堆,随即又四散逃奔。愣在湖滩上的牛,突然放开四蹄跑起来。
牛道坤没去管那些牛,也没有再看湖里的水。他抬着头,脖子和身子都僵住了——天啊,人一生要看下好多东西!他看过被风抽打着往前跑的云,看过堆在天上的棉花垛,这一次他看到一朵蘑菇在天上飞。蘑菇带着茎和根,它越来越大了。湖和草滩慢慢转动起来,牛打开四蹄在飞,世界经由他的双眼系到一朵蘑菇上。谁想到蘑菇会摔到地上来!到地上才知道,蘑菇的根上头是一个人。怎么看都是一个人。可人怎么会从天上来,怎么驾着蘑菇在上头飞?
那个人站起来了,好像在朝他叫,叫他哈巴。可他不是哈巴,他是牛道坤,这牛庄和王村都知道,麋鹿渡临资口也有好些人知道。那个人在往这边来,他叫的好像不是哈巴。他说起话来像一群鸟在叫,他的头发像是着了火,他的眼睛看起来也不同。谁见了都会想,他是天上来的神,说不定就是火神。火神不往南岳去,跑到龙王爷这边来做什么?
白白看着他的嘴在动,从那里扭出来的声音半只也捉不住。牛道坤张着嘴,连自己的话都忘了怎么说,真的成哈巴了。他就这么呆呆地望着人家收起塌在地上的蘑菇朵,看着他往湖洲那边游。过了半天才看到牛,看到牛才想起骂一声牛,才知道平常说的话还在身上没有丢。地上的话跟天上的就是不一样。地上的话一句是一句,骂牛,就把那个?菖字戳到牛屁股上;天上的话像一群鸟连着飞,一会儿“一”字一会儿“人”字,还没看清楚就飞开了。
回到牛庄,牛道坤把这事讲给泽三爷听。泽三爷记起上次乡公所来人说过,看见黄头发红头发的,不要让东洋人看见,要告诉乡公所。
带枪的人也会说那种话。他一说话,黄头发就从芦苇里钻出来,跟他说上了。牛道坤和哈巴在一边白白听着。太阳一落到黄头发上就像烧起来了;太阳落到黑头发上,黑头发还是黑头发。一个黑头发怎么会跟黄头发说话呢?
没多久牛道坤就发现,那个从天上落下来的人看着不一样,却像他们一样喝水吃东西。这两天,这家伙大概没抓到什么像样的东西,捞到螺和蚌,就用蚌壳烧蚌肉,螺壳烧螺肉;抓到小鱼小虾,就用那只铁皮罐煮着吃。煮东西是那只罐子,烧水、喝水、吃东西也全是它。这家伙不光吃和喝,还屙,屙尿就把那根东西拿出来,屙屎就蹲着干活。明明看着他从天上来,天上的怎么能干这个!天上干这个,天上来的雨还有谁相信?王寡妇怀了孕,到底怪人还是怪天?你在天上干这个,我们喊天还有什么用?你要在刘四娭毑喊天的时候干这个,四娭毑的嘴不就成了茅坑?可是这家伙不但两样都干,还放屁还拉稀。打喷嚏放屁,两头响动一齐来,想来是喝不惯苇塘里的水,拉稀拉得到处都是。来的时候,带枪的那个家伙说要小心地雷,原来地雷是拉稀拉的。哈巴就中了雷,一脚下去,臭气里头还带着死鱼死蚌味。哈巴晃动大脑袋,连打两个喷嚏。哈巴声音大,苇塘里的媒鸭子在水上踏出一长串脚印,飞走了。
这个火烧眉毛火烧头发的家伙,点起火来倒是像火神。他不要打火镰,也不要划洋火,手里头不知怎么一拨弄,火就起来了。牛道坤特意去看了他住的棚子,那块天上飘下来的东西真的是一块布。说它是布,跟织布机织的布又不一样,搭在棚子上不漏雨,比他盖到屋顶的蓍茅草还要好。棚子里头,那个人的气味很浓,像夏天牛身上的气味。
这家伙看着怪模怪样,人倒是很和善。那对眼睛,一开始牛道坤和哈巴都避着不往那里看,看惯了,倒从那里看出友善来了。他说的话,耳朵也开始习惯了,听着就像流惯的水,一点碍处也没有。带枪的那个家伙说起来跟他有些不一样,像是水里头夹着冰碴子。后来“黄毛”也学着他们叫牛道坤,叫哈巴,叫章齐贤,硬糍粑一到他嘴里就软了。牛道坤也学着叫了他一声大维,就像田埂上扒开了缺口,塘一丘的水流到塘二丘。哈巴从来没叫过他,他只张着大嘴朝他嘿嘿两下。
他们得从水里找吃的,吃好了好赶路。牛道坤跟哈巴弄来一些柳条编了一只渔罩。大维一看到罩鱼就喜滋滋往苇塘里奔,那家伙抱着个铁家伙在上面等鱼吃。渔罩掌在牛道坤手上。罩到草鱼青鱼,渔罩里哗啦啦一阵乱响;罩到鲇鱼,鲇鱼滑溜溜的身子一个劲往泥里钻。大维那家伙大拇指插进鲇鱼嘴里,硬是把它从淤泥里拖了出来。须短身子粗,那是一条老鲇鱼,又细又密的鱼牙,加上黏液,把他手指弄得血糊糊的。他只顾望着鲇鱼乐。哈巴那家伙不知怎么抓到一只甲鱼,倒提在手上,甲鱼头伸出来老长。大维一看到就叫:A tortoise(一只乌龟)!章齐贤干瞪着眼,弄不清他在说什么。他指了指裤裆,又叫。牛道坤说:他是不是把这看成了乌龟?章齐贤想不起怎么告诉他这是甲鱼,就告诉他这不是乌龟。他指着裤裆:龟!问他怎么知道的,他说驼峰航线的中国朋友告诉他的,说男人有一只龟,女人有一只蚌。先是章齐贤跟他笑,牛道坤和哈巴弄清楚了也跟着笑。后来到了拉撒的时候,他就叫龟,拉小的拉大的都叫龟。
人跟人到了这一步,一些事情也就好懂了。或许,这个叫大维的家伙跟那个姓章的说的一样,就只是一个人。没错,他的头发,他手上脚上的毛都是黄的,那地方想来也是黄的。黄鸡黑鸡不都是鸡?
他们总是在天黑下来之后把船从芦苇中拖出来,往西南青草湖那边划。白天,湖里不时有东洋人的船贴着水面飞,天上还有大鸟在飞。大维光是听声音就知道,哪些大鸟不用怕,哪些得躲着。白天他们躲在芦苇和蒿草中,白天睡觉晚上划船。哈巴划上半夜,牛道坤划下半夜。时辰就在哈巴的身子里装着。时辰一到,哈巴张开大嘴打一声哈欠,就得赶紧把他换下。不换下他,他就坐在那里打起呼噜来,船摇他也跟着两边歪。瞌睡没来他听牛道坤的,瞌睡来了他听瞌睡的。你得及时过来叫他,让他来得及把宽大的身板运到船前头去。等到他一屁股坐到前舱,身子往甲板上一仰,什么黄毛黑毛,这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与他无关。他在这个世界上就只剩一道空气,出出进进都响。他不会去想,东洋人是黑毛,黑毛怎么打起黑毛来了?黑毛打黑毛,黄毛怎么跑过来了?他不想这些,就像打湖滩那一阵,他不去想王村怎么跟牛庄干上了。他只管有拳使拳,有呼噜打呼噜。东洋人一个雷打过来怎么办?他们要打过来,他也没办法。黑壳楠打得只剩一块皮,不照样歪着身子在那里打瞌睡?
牛道坤喜欢在夜深处划船。水从船边上流过,让他想起木排上的日子,想起活在那些日子里的人。那些留在水下的人,他们也在这些流水里吗?那些岸上的人呢,他们在哪里?时间在岸上跟在水里一样流过,每一个人身边好像都有一条河。他划着船,那条悬在上头的银河好像正沿着船往他这里来。他能感觉到,这湖里头走动的水,这水上头吹过的风,还有从他手上送到水里去的力,这一切都从头上的银河那里来。他的手沿着船桨伸进水里,哪里流急,哪里有起伏,哪里曲折回旋,都会传到他的手上头。他驾着船,并不是要斗着逆着水,他只是要从水里头借出9IYe9oJMV4uYY9grEMFfsB7hbIpmL4uKxYsRzLPajFg=一条路,往西南去。他会让船头盯住那些立起的水,让船偏着身子过,让船去就那些水送来的力。水里的鱼鳝和江豚就是这样,没有谁会硬起身子在水里走。那些留在水里的同伴也一样,他们说不定就在鳗鱼滑溜溜的身子上。他们在水底下,他驾着船在水面上游。
他不会睡。他醒在他的桨叶上,桨把一些水带上来,水滴又顺着桨往下落。不只是他一个人没有睡,还有好些声音醒在那里。有好些神秘的事物在给他做伴。一颗流星划过天空,坠向芦苇丛中。一只萤火虫从芦苇丛里飞起,连着画乱好几颗星星。一些声音像棉花里抽出来的线,一些声音像纺出来的布。船近浅滩时,会遇到出来觅食的董鸡。一只,两只,三只,它们一开始总是加快步子跑,到最后才很不情愿地飞起。董鸡飞不远,它们只相信夜,就像他们不敢相信白天。他觉得他看到了一只小董鸡的眼睛,跟他儿子的眼睛一样。儿子的眼睛在黑暗里看着他。接着是一只大董鸡睁着三哑巴一样的眼睛。三哑巴的肚子被打穿了,嘴巴喊不出声音,喊声都到了眼睛上。怎么会把儿子的眼睛跟哑巴连到一起?家里是不是出了什么事?他怕起来。他用手和桨一起祈祷,从上头一直祈祷到水里。苦恶鸟在芦苇丛中叫,它叫它自己的名字,也叫着人世间的事情。九马咀、静安庄、胡家窑的窑匠和屙屎的三哑巴,它好像都知道。小苇鳽喜欢一家子晚上出来跑,它们知道自己是肉做的。肉做的都知道怕。桨是肉做的,竹篙是肉做的,铁壳楠是肉做的。东洋人的船不是肉做的,天上的大鸟不是肉做的。章齐贤是肉做的,他的枪不是肉做的,不知道他会不会怕他的枪……
黄毛的眼睛醒在那里,像星星那里的天。章齐贤说他是开大鸟的,他从大鸟身上来。牛道坤看到的是大鸟先掉下来,他再从天上飘下来。可人家说你只知道你看到的。他看到他跟他们一样吃饭喝水屙东西,一样怕东洋人的烧火棍,看来他跟他们一样也是肉做的,可是他却不像他们一样说话。他知道布谷鸟说什么,知道鹧鸪说什么、喜鹊说什么,知道鸡什么时候说什么,知道猪、知道牛、知道猫号春,也知道狗,不管它是黑狗还是黄毛狗。鳜鱼用刺鳍拨水的声音,青蛙鼓嘴巴的声音,他一听就知道。可他不知道黄毛说什么,也不知道黑毛的东洋人说什么。有时候人跟人,比人跟别的东西还要远。人手里有了不是肉做的东西,是不是就觉得自己不是肉做的,就会离人远?
此刻,看着那双蓝眼睛,他一下觉得这个人的眼睛跟他是这样近。他听不懂他说的话,却懂得他的眼睛。眼睛跟眼睛,不只是近,还亲。一个人拿了鸟铳往另一个人那里打,他会把一只眼睛闭上,另一只眼睛躲到鸟屁股后面。他不会拿眼睛往另一个人的眼睛上看。
他们一路昼伏夜行,在湖洲湖汊中间穿行,最后到了青草湖。说是湖,水在这里只是一条狭窄弯曲的巷道,只有小船才能在里面穿行。隔一段会有一处稍宽的地方,往来船只可以在那里避让。水道两边是密匝匝的草,人踩在草甸上,脚步一摇一闪的。有时还听到水在下面响,可是看不到水。青草湖是草神的地盘。草神是龙王爷的乘龙快婿。草在草神这里,就只管发疯地长。风在龙王爷那里是波浪,到这里就成了草浪。湖草一年年累积,绞织到一块成了浮在水上的地。
青草湖长出来的鱼,很多是说不出名字的鱼。到青草湖来的人,大多是不问来龙去脉的人。青草湖的事,都是些稀奇古怪的事。青草湖中有不少人工岛。筑岛的人钻进水里,把青帆草和芦苇根挖出来堆成一大堆,用柳树干打桩把它们固定住。等到柳树干扎了根长起来,那地方就成了岛,就可以在上面搭草屋住上人。中间那座主岛,时间一久,来的人多了岛也跟着变大了,到后来就真的坐实成了地,上头有寨子,有水井,有树木和竹林。长在那里的竹子看着是圆的,伸手一摸却是方的。还有一些竹子,说是什么人的眼泪滴在上头长成斑,成了斑竹。那上头的水瓜,长出来都是五根手指。那上头的花翅膀鸟,都会说人话。那上头的猴子一生下来就很老,看脸相少说也有八百岁。那上头的男人是强盗。据说上头有过一个人当强盗当大了,大到一定时候就不是强盗了,就成了大人物。大人物装了一肚子男盗女娼居然想去考功名,没想到一考还真的中了,后来大概是酒喝多了,稀里糊涂就往水里跑。他一跑,水就往两边分,中间生出一条路来,就在他脚底下腾起灰尘。他就这样到了龙王爷的宫殿里,做了龙王爷的乘龙快婿,但龙王的宫殿全是镜子做的,住在全是镜子的宫殿里,他过得并不快活。他跟公主做第一遍就等于做了一千遍,第二遍等于是一万遍。做了一万遍的事,没有人愿意再做一万零一遍。他从龙宫里逃了出来。没想到镜子一直追到湖面上,太阳一照,一万面镜子一齐在闪光,想躲也躲不开。想起在宫殿里行房事两遍等于一万遍,他对着镜子栽了两根青帆草,跟着又栽了两根芦苇。一万面镜子万万根草,万万根草再加上万万根芦苇,这个地方就这样成了青草湖。青草湖亿万张叶子亿万片风,亿万鸟叫从夏响到冬。在这里什么时候都是鸟叫声拎着风。
东洋人在外面的湖里划大船,也想进入青草湖,大船快艇进不了,插了带太阳的旗子也进不了,换上小舟,来来去去几个回合又到了现地方。他们生起气来,就朝着里面放枪。是有一些鸟飞起来,一些鸟飞起来又栽进他们的枪声里。可是更多的鸟照样在叫。一万面镜子里长出来的草和风,很快把他们放出的枪声筛落。他们丢下青草湖走了。
青草湖中间那座大岛上,有人在等着大维和章齐贤。大维朝着牛道坤连着说了两个“拜”,还以为他要弯下身去拜,谁想到他两手一张就奔过来抱上了。牛道坤一点准备也没有——两个带把的,他这是干什么?还好,他抱一下就放开了。他身上有一股牛羊味。这家伙,明明吃的是腥味,身上还是那个味。他又朝哈巴说了两个“拜”,又赶过去抱哈巴。哈巴像一块喘气的门板,僵在那里没有动,把旁边的人都看笑了。
走的时候,大维叽里呱啦说了一大串。这些天,牛道坤和哈巴已经习惯了这样的声音。突然间,牛道坤想起,大维这一走,今生今世怕是再也听不到这声音了,心里一动,鬼使神差一般说过一个“哈”之后又说了一个“罗”。祖宗十八代不知道这是哪来的话,那个黄头发蓝眼睛的人倒是听懂了,哇的一声,两只手一齐跷起大拇指。其他人咧开嘴在笑。
大岛西边连着一座浮岛,中间是一道芦苇和藤草绞起来的浪桥。浮岛上有草屋,草屋里有酒有烟,有女人的笑声。牛道坤知道哈巴的意思,过浮岛时把船划得飞快。哈巴闷着一张大脸,在喉咙里咕哝:跑忒快。牛道坤哈哈一笑,打一个旋把船靠在浮岛边,哈巴脸上立马放出光来,还在喉咙里嘿嘿了两下。
牛道坤留船上,看着哈巴将硕大的身板往浮岛上移。没过多久,这家伙就像一堆水草带着烂泥卸到船上来。问他也不应,趴在船头上,身子抽风似的。牛道坤来火了,用脚踹他的两盘屁股。他打着哭腔,说他明明硬得像根棒槌,一到那里就泡了汤。牛道坤咬牙切齿发着狠:那就掐它。哈巴哼哼唧唧,说什么也不肯起身。
酒是好东西。哈巴喝了酒,回来时鼻孔那儿哼哼唧唧,听着像哭。牛道坤知道那不是哭,驴唇马嘴,谁也不知道他唱的什么。牛道坤往他肩膀上拍了一巴掌。想象得到,这家伙一脸的地米菜花全都开了。牛道坤不知道的是,他没到浮岛上的草屋里去,与一个人擦肩而过。他要是去了,就会看到那个静安庄来的女人。看到她,就会知道老闷头在哪里。哈巴去了,他只知道那里有女人,不知道那些女人都是谁。
到家时,牛道坤说了一声到家了。离家几天,像是过了好几年。三间茅屋还在,看着比以前小多了。
牛道坤动手砌房子时,东洋人就在大牛庄。牛去了湖滩,牛栏空着,他们住牛栏。人到一定时候就知道,牛住的地方人一样可以住。不知道怎么一来,他们的枪就不行了,就像哈巴突然萎了下来。枪一萎下去刀也跟着不行了,不再去砍猪砍人,顶多砍一砍山上捡回来的树枝。树枝哪用得上刀来砍,牛道坤弯起膝它就一折两断了。刀枪不行了,人也跟着不行了。他们还会排队,还会走成那种样式,可是原先鼓在衣服里的气没有了。饱满的稻粒瘪下去,发干的萝卜连皮都皱起来。没错,他们还会喊口令,可是喊出来的声音往下掉,听着像放屁。狗不朝他们叫,不是怕,是觉得没必要。公鸡过午和天快亮时照样叫,公鸡叫起来牛栏那边照样听。鸭子走起来像踱步。
这天女人带着木工在山上锯木,孩子跟着在山上玩。牛道坤从胡家窑回来,发现伙房里弓着一个人,他伸手捡了一根柴块。一个东洋人,正在灶上的潲窝里挖潲吃。给猪吃的潲,里头有糠皮和红薯藤,还有一些红薯皮红薯块。那家伙在里头挑红薯吃,吃得那样香,把背后给忘了。牛道坤想起他们砍猪,就是从背后,往腰上一刀。他不用刀,他只要在那里打上一柴块。代表胡家窑的窑匠,代表三哑巴,也代表他的猪。柴块举起来,停在上头。吃潲的人转过身。举起的柴块可以直劈脑门,也可以一道弧线扫向左边的腰。可是,他看到那面被猪潲糊黑的嘴和脸——眼睛睁得那样大,嘴张着,潲汁和口水正在往下掉。他打不下去。柴块跟着手软下去。
后来想起那根柴块,就想,那些拿枪的人,怎么就朝着人开枪了呢?那些刀又是怎么砍下去的呢?柴块毕竟是柴块,柴块也是肉做的,它不是枪也不是砍肉的刀。
原刊责编 易清华
【作者简介】学群,湖南岳阳人,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出生。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水来了》《西西弗斯走了》,散文集《牛粪本纪》《生命的海拔》《两栖人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