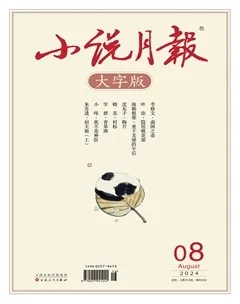陶片
我与乔小牙是发小,他喜欢看书,尤其喜欢读明史,他看的书比我多,对明代的生活了解很透彻。他是老师,我也是老师,我们都有业余爱好,他喜欢陶片,我喜欢石头。我们经常在周末结伴出行,在城市四处转转,只要遇上晴朗的天气,我俩都会出去走走,有时半途也会遇上暴雨,这种事很常见,尤其在南方。
我们消磨闲暇时光的这座城市,在明末是很繁华的,后来被清军攻陷,一度毁于战火,但存留的遗迹还很多,遍布城内的各个角落。这些遗迹有些什么掌故,乔小牙最清楚,说起来如数家珍,好像是自家的故事一般,颇有主人翁的感觉。比如江边有座塔,我们都知道名叫舍利塔,但是哪个朝代修建的,中间又有什么变故,我就不知道了,而小牙知道,我觉得他比我更爱这座城市。
与他一道上街溜达,看见一口井,一块石碑,他都有说法,可以说出当中的来历,可惜的是我没什么兴趣,我喜欢清洁自然的环境,感觉古人留下来的东西有一股陈腐味。我是一个没有城府的人,自然不喜欢陈腐的味道,如果不是跟他一起出行,看见那些石碑,我是不会特意去看的,只想着绕开走。
对于如今的城市改造,我跟他有不同看法,我基本上持开放的态度,而他总是惋惜。我说一座城市的房子破破烂烂的,拆掉有什么好可惜的,他说如果你生活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林徽因会骂死你。我说历史在发展,如果盖起来的房子由林徽因负责设计,她也会喜欢。乔小牙说那倒也可能,可是如果盖起来的房子比拆掉的更难看,难道你也高兴?这句话还真问住了我。
我承认我不喜欢如今的许多新建筑,可想想原先生活在旧建筑的老百姓,也还是觉得拆了好。我就是在破烂的旧建筑里长大的,连厕所都没有,唯一的公厕在几百米远的湖边,寒冬腊月撒泡尿冻得半死。那厕所还不分男女,墙上被人挖了几个窟窿,可以洞见隔壁如厕人的屁股,随着岁月的流逝,那窟窿越来越大,恨不得连人都可以钻过去,于是女人想解决问题,要走更远的路。
我说对于老百姓而言,生活中有厕所总比没厕所强。
他说拆你家那小破屋当然没问题,拆古建筑就可惜了。
我说北京那么多古建筑都拆了,林徽因也拦不住,小城市的古建算个鸟。
他听我这么说,似乎有些难过,不再吭声了。
我赶紧安慰他说,其实我也没那个意思,只是想说,老百姓过日子就是图个窗明几净的家,家里没个厕所,连婚都结不成,你说呢?
小牙的母亲与我母亲是医院同事,都是最好的护士,当然他母亲要更好些,是护士长。他家住在另一个大院,那边的条件也要更好些,大概没遇上公厕的事,所以对于城市拆迁,他持相反的观点,但也没办法阻止,只好用上自己的爱好,遇上哪里拆旧屋,尤其是挖地基,他都会去看上两眼,有时还拉上我。为什么要拉上我呢?因为我力气大,可以背麻袋。
我们一般会开车去工地,在附近停下后,往工地下方走,我会带一两个麻袋,用来装挖到的宝贝。空手而归是很常见的事,可是万一碰上宝贝呢,这种事情的乐趣,就在那万一,正如小牙说的,人生的许多乐趣,也都在那万一。
我们带上麻袋,就是为了那万一。万一碰上他喜欢的玩意儿,就用麻袋装回来。
那些只知道泡古玩店的玩家,是不懂得挖掘的快乐的,我们会把发现的古董连同周围的泥土一道装回去,回家后再慢慢刷掉泥巴,尽量保存古物的完好。人家古人做一个东西也不容易,如果被后代藏家随意弄坏,那也是很不道德的事,当然这里指的是藏家,贪图赃物的凡人不在其列。面对出土的古物,小牙与别人是不一样的,小牙看重的是古典美,而一般人只是想发财,卖个大价钱。小牙是从来不卖他发掘的陶片的。
这些年的城市改造拆掉了不少古旧房子,他面对即将拆掉的院落,时常会发出感慨:这是城市的残片,我捡的是残片里闪光的那么一丁点,不过是收藏城市记忆而已。对小牙这种古玩爱好者来说,拆房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房子下面的挖掘,但凡两米以上的深坑,只要不下大雨,他都会跳下去看个究竟。我有时也会跟他去,当然只是图个新奇,我对古董是外行,根本不会鉴NVpsEwvP3XsGPhCDfGmqYw==别,对挖古董自然也没兴趣,只是陪他玩。真正的好朋友,有时志趣是不一样的,因为志趣不一样,所以才不会有竞争。
小牙寻找的宝贝并不是金条或宝石,他最喜欢寻找的是陶瓷的碎片,这就与他的阅读有关系了。这座城市曾经归朱家皇帝的侄儿所有,皇族的家用瓷瓶都是在景德镇定制的,是特有的青花瓷瓶,每个陶件上都有美丽的青花,无论瓷碗、汤勺还是插花的瓷瓶,都是清一色的青花,衬托出皇族的高贵。
他说青花有一种苍凉美,尤其是在月色下,宛若吹箫的美人。
每次开发商地下施工,现场的围观者是很多的,当中也不乏行家,举凡金银玉器一旦出土,马上会被捡走,施工方拦都拦不住,有人甚至跟在挖掘机后面,挖出一只坛子便一拥而上,甚至砸开坛子分赃,抓到什么算什么。其实有时候坛子本身比里面的东西更值钱,但好多人是不懂的,只在乎里面有没有金元宝。所以事后赶到的人,通常捡不到什么便宜,也就是一些绿锈斑斑的铜钱,多半是清币,上面印着乾隆、康熙,或道光、光绪,不值几个钱,连“袁大头”都不如。
一次,挖掘机挖出一个巨大的深坑,露出古老城墙的基座,许多人都跳下去,我一时激动,也想下去为小牙找几块碎瓷片,被他阻止了。他说我们看看就可以了,没必要凑热闹,过几天再来转转吧。我说过几天都捡光了,还有什么意思。他说这倒也未必,经过一段时间的日晒雨淋,附着的泥巴脱落了,该闪光的东西总是会闪光的。
小牙跟别人确实不一样,他可以从被人丢弃的碎片中发现残缺美,通过残片的图案、色泽和边缘辨认出制作的年代,是明万历年、正德年还是成化年,这种能力也只有他具备,别人玩不来。我说万一不是明朝的,是清朝的呢?他说主要看出土地段泥土的颜色,颜色不同则朝代不同。算了,跟你说也没用。
跟我说确实没用,我分不清,记不得,也没兴趣,我喜欢的是天然美。
他说,他有个朋友看古书发现,景德镇一座古塔的下面,有不少成化年间的陶瓷,于是专程去景德镇住下来,租的是古塔旁边的民宿。
我问,是住下来研究吗?
他说不是,是挖掘。
啊?我大惊。
他说是的,他从住处悄悄往下挖,挖到三米以下开始横挖,挖了一条通往古塔的地道。
天哪,房东不会报警吗?
房东不知道。
我问,后来呢?
他说,后来被抓住了,判了十年,哈哈。
我说我还以为那人发财了呢。
他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不判死刑算好的了,他差点把那座塔挖倒了。
过了一会儿,我问他,你有没有想过,也去挖一下?
他说,除非你跟我去,挖到金条我就把你埋里面。说完他哈哈大笑。
我吓了一跳,不喜欢他开这种玩笑,好像不怎么吉利。
他又说,后来考古队发现,那古塔下面不止一条地道,有好几条呢。
啊?我又吃了一惊。
是的,历朝历代的盗贼都没挖到古塔的地基就停住了,不是被抓了,就是死了。说明那座塔有神灵庇护,不是随便可以挖的。
哦,那你还说要把我埋那?
谁让你出馊主意,你要我去做盗贼,我只能把你埋了。
我承认错在自己,不过我也只是开玩笑而已,当然他也可以说他是在开玩笑,我的玩笑是图开心,他的玩笑好瘆人。玩笑这种东西,最好还是少开,尤其是我这种人,因为读书少,最害怕一语成谶。
他会把捡来的陶片先放脸盆里浸泡几天,然后慢慢洗,轻轻刷掉上面的污垢,再进行拼接,尽量拼出大一点的画面,比如渔舟或柳条。你别说,也还蛮有点古意,只是这过程太烦琐,我看看可以,自己弄不来。我宁可去洗我心爱的鹅卵石,鹅卵石多光洁呀。
一次,他按花纹拼出一只鹤,心情大好,忽然说,其实我们的人生也是拼接出来的,哪来什么完美,都有许多残缺,我喜欢残缺美。说完给拼好的残片拍了一张照。
我说我反正不喜欢,所以不会跟你去抢那些脏兮兮的残片。
他笑了,说哪来什么脏兮兮,一点都不脏。
陆艾在旁边说,怎么不脏,邋遢死。每次你弄完,都要我清扫干净。
陆艾是他的女朋友,跟我也还算熟。他们认识好几年了。
她又说,我们家本来就小,厅里放这么多破烂,我都不好意思带闺密来玩。
小牙说,这些泥土都是陈年老泥,已经没什么腐殖质了,不会有臭味的。
那是你说的,还不知道有多少千年病毒呢,这些年病毒大流行,都跟挖地有关,盖那么多房子,挖出那么多烂泥巴,还有你这种人黏在身上走来走去,不感染才怪。她说。
照你这么说,病毒流行怪我了?小牙说。
人家科学家说冰山里都有病毒,更何况千年烂泥巴。陆艾说。
原来病毒是冰山上的来客呀。小牙说。
我觉得挺好笑的,但小牙说完并没有笑。
陆艾也没笑,把门砰地一摔,走了。
我想出去追,小牙劝住了我,说她是去打麻将,没事的。
原来男女之间的情感起伏,我们外人是不懂的,只要一掺和进去就会惹麻烦,看着都是些小事,谁知道当中有没有凄楚和哀痛。我这样说是夸张了,想为自己以后少去他们家找个借口,当然也对我自己的未来有些担忧,如果我的女朋友不喜欢我的石头,我该怎么办呢?
陆艾个头不高,脸圆圆的,但眼神很锐利,口齿也伶俐,看见什么不顺眼,她会一顿数落。可能因为个子小,她的生活有一种日式风格,喜欢把头发盘起来,吃饭也喜欢小盘小碟,连门帘都低垂,走进她料理的居所,很难相信那是小牙的家。她还喜欢喝点酒,那种日式清酒,这一点很特别,因为我认得的女人中,几乎没有爱喝酒的,当然我认得的女人也不多,可能爱喝酒的女人我都不认得。
清酒闻起来清爽,还是蛮有后劲的,我喝过一次。那次是陆艾做的菜,烧了一条鱼,我饭后回到家倒头便睡,竟然睡到第二天才醒过来,其间小牙还来过电话,想问我有没有醉,我也没听见铃声。
第二天小牙又来电话。陆艾担心你死了,怎么一晚上都没消息?陆艾还说,如果你死了,你父母肯定以为是她害死的,你父母一定听说过她,因为她曾经答应帮你介绍女朋友。
我说,我哪这么容易被害死,不会,不会,我不会死的,哪可能那么一两口小酒就死掉。我父母也不认得陆艾,我从来没提到过她,我在父母面前没提到过任何人,连你都没提过,更别说女人了。至于女朋友,你也知道的,我也不是一个都没有,只是懒得说,偶尔约会一两次,这种事情对我而言,几乎就不是事,哈哈哈。
小牙说,旁人以为你很正派,其实烂得很。
我连忙说,可能是真的喝多了,有点乱说话了。
小牙说,行了,你没死就好,我转告她你没死。
这么讲究精致的女人,怎么会跟小牙好上呢?说起来也不奇怪,小牙原先不是这样的人。
小牙原来没别的爱好,只喜欢读书,这是陆艾欣赏他的地方,她说过自己喜欢读书人,哪怕做不了官,挣不了大钱,她都无所谓,因为读书人内心干净,也蛮有情趣,能逗自己开心,这就是天大的福分。女人找男人,图的就“开心”二字,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这是她的人生哲学,所以她愿意嫁给老师,或老师的孩子,那是有教养的人家。
乔小牙的父亲是教书匠。我们教大学,乔父教中学,十几年前就去世了,没给小牙留下什么东西,要知道以前做教书匠是很清贫的。乔父教的是初中语文,唯一的藏书是鲁迅的书,但鲁迅的书印得太多,已经不值几个钱了。我说的是鲁迅的书,大先生的思想还是珍贵的。
好在乔家还有一些古旧书,是外公那边留下的,已经堆放在角落许多年,本来是害怕抄家,准备烧掉的,可后来不知为什么,抄家的人没来,或者去别家了,就一直搁在那,谁也没去动。直到有一天,小牙独自穿过城市,去河东看望年迈的外公,才在外公家发现那批藏书,偷偷拿了一些回来,他对古旧的东西有一种眷恋,总认为比眼下的东西更有意思。那是少年时代的事,距今已过去二十多年了。
拿回来的那些旧书,有几套是“三国”和“红楼”,小牙也没看,感觉是老男人和小女人的读物,他只喜欢看史书,比如简写本的《资治通鉴》,还有制陶史,讲述景德镇的制陶业。
陆艾觉得找个教书的做男朋友,也就是未来的丈夫,有很大的好处,那就是无论生活中遇上什么问题,都有个人可以请教,不用自己读书了。一个不喜欢读书的女人,找个喜欢读书的男人,他给她讲人世间的故事,她为他做人世间的美食,这也算绝配。
小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喜欢陶片的,我记不清了,陆艾应该是记得的,那是他们相识以后的事。我记得大约是五六年前,小牙在电话里对我说,我买车了,出去兜风去。我兴冲冲赶去他家,那是一辆天青色的东风日产。上车时我问,你不带上陆艾?他说她坐过了,不喜欢。我说怎么可能,日系车是她最喜欢的呀。他说他也以为她喜欢日系车,所以要的是这辆,不想人家瞧不上,没办法。
我们四处溜达,小牙,说我发现有辆车还是很方便的,以前听说哪里拆房子,想过去看看得骑电单车,有时嫌麻烦就算了,现在好多了。我说等我想去哪里捡石头,你帮个忙哦。他说没问题。我的爱好不多,捡石头是其中之一,我喜欢河床上那些圆润的石头,尤其是大块的。那些石头经历千百年的风化,时间之水的冲刷,变得非常圆,除了如鹅卵,还有浑圆和扁圆,最奇妙的是,有的上面还有波浪纹,鱼尾纹,纹路自然天成,非常漂亮。
我捡来的石头,也不想做什么展示,就想着以后修一个水池,用这些鹅卵石做装饰,镶在水池的边缘上,不仅养眼,也方便养鱼,这种有大自然味道的石头,最适合鱼儿栖身。我跟小牙一样,也不喜欢鱼缸,觉得太敞亮,任何生命的家都应该有隐秘的角落,我愿意为鱼搭建那样的角落。
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想法。我眼下还没房子呢,只是租住在别人的屋子里。
这些年,小牙确实拿回家不少出土的东西,都是从工地捡来的,沾满了泥土。他家的客厅摆满了坛坛罐罐,还有各种陶瓷碎片,把客厅弄成这样,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别说陆艾不喜欢,连我也受不了。在干净整洁这件事上,陆艾的看法与我比较接近,所以她对我去他们家玩,基本上不反对,有时还一起喝点小酒,但如果我们出门去捡陶片或石头,她是不会去的,而是去横街打麻将。
她在小区里有一群麻友,都是三四十岁的女人。小区的横街上有几家麻将室,是麻友们聚集的场所,喜欢打麻将的街坊邻居,哪怕不坐下来搓,也会进去看看,因为都是熟人,可以聊些家长里短,尤其是邻居的八卦。哪家的孩子考了个野鸡学校,哪家的女人跟隔壁老王好上了,都会从牌桌上传出来,传的都是人家不想被人知道的事,至于别人家的开心事,这些人则假装没听说。如果有新人加入她们,那是很受欢迎的,因为新人可以带来新闻。
我从未进过麻将室,但经常会从门前走过,要想去小牙家,横街是必经之路。
乔小牙家的客厅脏乱,我不喜欢可以尽量少去,我和他更多的是在各种工地上神游。
陆艾不喜欢就比较麻烦了。小牙对残片的摆放是有讲究的,有年代的顺序,也只有他记得具体的位置,比如他会按朝代的先后摆放,还走来走去巡视。但陆艾就不乐意了,她哪知道成化和万历谁先谁后呢,有时拖地碰上了,想归回原位都难。
他们两人在家会不会吵嘴,这我不知道,但我发现陆艾喜欢有我在场时发一下脾气。也许有第三方在,可以克制小牙发怒吧,反正我好几次听见她发难了。
那天我一进门,就听见她说,一个男人成天玩这些碎片,有意思吗?
莫非你希望我成天出去玩女人?小牙反击道。
说实话,对这种话,陆艾无力反驳,但心里依然是不舒服的。她转而问我,你为什么不玩呢,这些破烂碎片?
我说,这种爱好是需要学问的,我没学问,玩不来。
我本意是为小牙辩护一下,不想陆艾听了大怒,你的意思是不懂欣赏的人,就没文化?
我说,我是说我自己,没有说你的意思。
我承认我没文化,分不清唐宋元明清,你们这么有文化,也没见衣冠楚楚,还不是一副穷酸相!陆艾说。
乔小牙这下不高兴了,他说,我可没花你一分钱哦,我的这些爱好花的都是自己攒的钱。
你这是什么话,我一个女人家,花过你一分钱吗?我们认识多少年了,我花过你一分钱吗?好意思这样说!
我见这阵势,觉得自己今天真不该来,想劝慰他们两句。
我说,嫂子,你听我说两句……
别叫我嫂子,我们没登记呢。
好吧,我说陆姐……
别叫我姐呀姐的,我比你小好几岁。
好,好,那就叫你小艾妹妹。
她的脸色这才舒缓下来。
小艾妹妹,小牙这是一点个人爱好,说实话他既不是酒鬼烟鬼,也不是嫖客赌徒,还有一肚子学问,已经是很好的男人……
陆艾马上接住了我的话题,她说,做女人就是希望有人关心。他那一肚子学问关我什么事呢,说白了都还不如嫖客,妓女从嫖客身上得到的,不仅有钱财,还有快感,如果我身边的男人不如嫖客,我是不是连妓女都不如?
我被她这几句话镇住了,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同时看见小牙的脸上掠过一丝阴云。
你这是什么意思?小牙问。
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她说完扭过头去,谁也不再看。
我想小牙是知道什么意思的,因为连我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我慌忙说,哦,对了,今天我要去看一下老母亲,先走了。也不等他们反应便夺门而出,顺着楼梯一路小跑到小区外的垃圾箱旁边才停住,掏出纸巾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我很少出汗的,哪怕大夏天都很少出汗,可今天出汗了,说明我确实很紧张,好像偷听到了别人的什么秘密,而那些秘密,我本来是不应该知道的。
自从见证过他俩那次吵架,我再也没进过小牙的家,也再没见过陆艾。
其实说句心里话,我还是蛮喜欢她的,她说话口齿很清晰,人看着也清爽,是很典型的城市姑娘。据说她有个漂亮姐姐,多年前就嫁给了香港人,说是香港的富商,后来才知道是个经常出入口岸的货车司机。姐姐嫁人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我除了吃过陆艾烧的菜,还见过她介绍的女孩。
记得那次见那女孩是在一个雨天。陆艾安排我们在咖啡厅见面,坐在靠窗的位置上,我找到那位置时,她俩已经坐在里面了。她为我们要了两杯咖啡,就先走了。
我说过我喜欢大自然,那天的雨景是很动人的,细雨落在窗外的树叶上,晶莹而透亮,我掏出手机拍了照片,这才想起坐在对面的女孩。她化了浓妆,见我放下手机,眼里露出一丝轻蔑。
她说,都是成年人了,我们有话直说吧。
我说,好呀。
她说,我觉得男女交往,无非是两种形式,找乐子,或者过日子。你觉得呢?
我还没来得及回答,她又接着说,我找乐子已经腻了,想开始过日子,找个可依靠的男人。你是不适合过日子的,一看就知道,还想玩,对吧?
看着她的大红嘴唇,我觉得有点生厌。我端起咖啡喝了一口,问她与陆艾是怎么认识的。
我们一起玩认识的,她先玩腻了。说着她微微一笑。
我说,哦,玩腻了好玩的男人,然后找个不好玩的男人成家?
我这样说显然让她不太愉快,她站起来走了,咖啡也没喝。
对了,看你还诚实,转告一下你的朋友,女人是要哄的,懂了吗?如果久了不哄,难免会出事情。她忽然回头看着我,补充了一句,随后消失在窗外的细雨中。她说这句话显然是有所指的,想让我转达给小牙。我本来对她没什么感觉,但她回眸那一瞥,那晶亮的眼神,还是蛮迷人的。我对她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分手的那瞬间,或者说如果不分手,美好的记忆就不会有。这种女孩已经不是女孩了,是成熟的女人,成熟到弥漫着荷尔蒙的味道,她们什么都懂,懂掌控交谈,懂运用姿色,那都是用青春时光换来的,但哪怕懂那么多,她们距离幸福也很遥远,甚至是更遥远了。
我以为事后陆艾会给我打电话,问问见面的情况,不想她并没有打。于是我明白那女孩什么都跟她说了,既然那女孩没看上我,陆艾也就没必要再来过问,女孩是她的朋友,而我只是她男朋友的朋友。她不过问也是给我面子,而我也没把那女孩的话转达给乔小牙。
我对陆艾唯一的担忧是她的情绪反复无常,作为她男人的发小,我对她得有所提防,万一哪天她怀疑我对她有企图呢,或者明明是她想接近我,却说我想接近她?那我就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我不喜欢看见小牙和陆艾这样争吵,我觉得男女这样吵架,真的很伤感情。况且我总觉得,他们吵架似乎跟我有关,是专门吵给我看的。
再说一旦吵翻,两人的感情就像摔烂了的花瓶,是很难复原的。当然可以努力去修复,像拼贴花瓶那样,将残片一块块捡起来,用胶水粘上,可是无论怎样努力,都不可能恢复原状了,总会留下裂痕。这样想想,我对自己独身的选择也就更加坚定了。
陆艾曾说我喜欢躺平。其实不是喜欢不喜欢,是没有别的选择,表面上还是有的,但心里已经没有了。我和乔小牙继续挑选晴朗的日子,开车出去寻找快乐,寻找那些可遇不可求的玩意儿,或者也叫可遇不可求的“万一”。万一找到了呢?那是一种由衷的喜悦,明白的人都明白,不明白的人永远不明白。
我们关注的施工场地的范围是非常宽广的,并不仅仅局限于明城墙周边。一次他跟随我来到新修的高铁站场地,这次算是他迁就我的爱好了。那地方靠近河边,距离市中心比较远,也就是这几年的城市扩建才开始修整,古人是不会在此留下什么痕迹的,更不会有古董,但这地方我喜欢,原因是这里有大量鹅卵石。
因为在修高铁站,这里挖了许多深坑,埋设了各种管道。如今都是机械作业了,挖掘机、起重机、推土机等一应俱全,戴安全帽的工人倒看不到几个,可能都吃饭抽烟去了,深坑边有一些小推车和铁锹。
我看着坑里坑外的圆石头,满心欢喜,拿起一把铁锹便往下走。鹅卵石多的地方,深一脚浅一脚,是很容易打滑的,也很容易崴脚,结果我一脚没站稳便滑了一跤。随着一阵稀里哗啦的声音,我滚到了坑底,铁锹都飞出去好远,引来小牙哈哈大笑。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爬上来,拍了拍身上的泥土说,有什么好笑的,这里不怎么脏。
他指了指小推车说,要是摔在烂泥塘里,这一车石头滚下去,你就被活埋了。
他这一说,我倒是有些后怕。
是哦,这附近又没人,万一真的被埋住了,连鬼都不知道,等到工人休息回来,再把推土机一开,压得严严实实的,我岂不就成了冤魂?
好在我在坑底找到了几块漂亮石头,算是得到些安慰。我把石头装进麻袋,可能是这次捡到的确实好看,引起了小牙的注意,他拿起一块蓝色的说,不错嘛,还有点青花的样子。
我赶紧从他手上夺过来,放进了麻袋。
他笑了笑说,放心吧,我不会跟你去抢这些玩意儿的,我们的爱好不一样。
他这样说反倒让我有些尴尬,我说,没事,没事,你若喜欢就拿去。
那天我们去的地方是新开挖的,没什么人去过,所以找到的好看石头不少,装了一麻袋,沉甸甸的,差点把小牙的车后箱都压坏了,当然也累得我气喘吁吁。
临分手时,他还是忍不住挑选了几块天青色的鹅卵石。我知道他喜欢的不是石头,而是那颜色,天青色是他最喜欢的颜色,接近青花瓷。
我说放在鱼缸里挺好看的。
他说他家没鱼缸。
我说为什么不买一个呢,那种超大型的玻璃鱼缸,放在客厅里。
他想了一会儿说,那种东西虽然好看,但是很危险,客厅已经不够宽了,要是哪天搞卫生,不小心碰倒了,会出人命的。
我说,谁家搞卫生会碰倒鱼缸呢,净瞎说。
他幽幽地说了一句,陆艾有时候动作比较大。
我说,再大也不至于出人命吧?
他说,你不懂,上网查查看有没有。
我回家后上网查了查,发现还真有保洁阿姨一个人在家做清洁时,不小心碰倒了鱼缸,被玻璃碎片割伤脖子丧命的。
我感慨他是个心细的人,想法总是很缜密,也不再跟他提鱼缸的事。
从高铁站工地转回来,我们又去明城墙边走了走。
他指着城墙上的灯笼问我,是不是有古典美?
我说像老百姓家的腌腊肉。
他皱了皱眉头说,你的脑子坏掉了。
我说,这是实情,以前挨饿时,我看见别人家挂的腊肉就想偷来吃。
灯笼和腊肉是两回事。他说。
问题是那些灯笼褪色了,确实像腌制的腊肉。我说。
他说,好吧,反正是我看见诗,你看见吃。
有时候我们会有意外的发现。那天经过明城墙边拆迁的棚户区,小牙忽然停住了。按理说,棚户区只是拆掉而已,并没有挖掘,不会有什么遗迹。但他的眼力真是好,径直走向废墟,搬开几根朽烂的木条,又翻开木条下面的瓦砾,竟捡起一粒小东西。
看见了吧,这是什么?他拿给我看。
我凑近细看,居然是一枚戒指,上面还镶着一粒红宝石!
厉害!我说。
今天出太阳了,我看见瓦砾下忽然闪过一线红光。他解释说。
我说,这地方都拆迁好几年了,我们经常路过也没看见呀。
他说这是命运使然,问我,怎么办?
我说,这有什么好问的,这么值钱的东西,你好不容易捡到一次,给陆艾呗,也免得她经常唠叨,说你是不爱家的男人。
不会是这里原住家的东西吧?他问。
我说不可能,如果是原住家搬迁丢失的,不知道来找过多少次了。
他点点头。好吧,我给她,算是一件小礼物,我还没给她买过什么礼物呢。他说。
我忽然想起那个“烈焰红唇”要我转告他的话——女人需要哄。可话到嘴边又缩回去了,觉得此时此刻不合时宜,许多事他并不是不懂,他连明史都看得懂,有什么事会不懂呢,只是不想做而已。像他这样的男人,缺少的不是悟性,而是行动的决心。
那天我们都挺开心,在古城门的拐角道的别。
接下来的日子,我减少了与乔小牙往来的次数,几乎不再一道出门,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沉浸在另一种状态中,因为我认识了一个女孩,是我自己认识的。那天排队做核酸,忽然下起了阵雨,我也没带伞,心想淋就淋吧,估计也不会下太久,可身后的姑娘很善良,把伞移到了我头上。我回头看了看,接过她的伞,两人一同躲在伞下。
做完核酸后,雨也停了,我们便收起雨伞,交换了联系方式。
接下来的周末,我请她喝咖啡,就在上次见红唇女人的那家。
咖啡店还是同一家咖啡店,但同来的女孩不一样了,心情也随之大不一样。她很快便成了我的女友。
一天傍晚,我送女友回城东的家,回来时路过中心广场,被一个女人叫住。
哎,还认得我吧?她问。
我回头一看,原来是陆艾上回介绍给我的那个“烈焰红唇”。
我忙说,认得认得,真的不好意思,上次你让我转告给小牙的意思,我忘记说了。
她说,哦,没事。你认得陆艾吧?
我说,怎么不认得,上次我们见面,不就是她牵的线吗?
她说,哦,对了,瞧我这记性!一次你从我们的麻将室门口走过,陆艾说你是她老公的朋友,和她老公从小一块长大的,对吧?
我说,是,怎么了?
她说,陆艾好久没来打牌了,去哪了?
我说,我哪知道呀,我也好久没去他们家了。
她问,你有她电话吗?
我说,没有。
她说,你要是见到她,麻烦叫她来一下棋牌室,她还欠我的钱呢。
听见她这样说,我感到很厌恶,没再理睬她,转身走开了。
我心想,还不就是你们这些老女人把她给带坏了,否则她也不会跟乔小牙吵架。一群女人在牌桌上聊天,免不了发泄对男人的怨恨,不是嫌钱少,就是嫌体力不够好,总之没什么好话。回家后,我忽然有些不安,想着蛮久没联系乔小牙了,自从他捡到那枚戒指。他跟陆艾不会又吵架了吧?我决定给他打个电话。手机响了十几声,才有人说话。
喂,是我。是乔小牙的声音,沉沉的。
我问,在家吗?
他说,不在。
我问,在外面喝酒呢?
他说,不是。
我问,在哪里呢?
他说,在垃圾场。
我很惊讶,啊,为什么?
他说,不为什么。
我的睡意全消,马上骑摩托车狂奔过去,心里充满了焦虑。
我果然在他们小区的垃圾场看见了他。他蓬头垢面,在垃圾场里四处寻找,身上有一股恶臭,他已经在这里徘徊了好几天。原来三个月没联系,他们家出大事了。出事那天是礼拜天,早上起床后,陆艾又跟他吵了一架,吵得空前绝后,他连早餐都没吃,愤然开车出去,直到下午才回来。回家后他大吃一惊,客厅里干干净净的,他多年收集的陶片全都不见了。
陆艾呢?我连忙问。
他沉默了好一阵,扭头说,她走了。
啊,走了,不回来找你了?
不知道。要是我有个院子就好了。
你们分手了?
他没说话。
原来乔小牙出门后,他放在客厅里的陶片全被陆艾扫进垃圾桶,扔进了小区门口的垃圾场,等到小牙发现时,那些陶片已经被垃圾车运走了。他一连找了好几天,什么都没找到,其实他也不是在找,只是很木然地在垃圾场里走来走去。有不认识他的住户过来倒垃圾,还以为他是捡破烂的,拿了一些纸盒和空瓶子给他,被他一脚踢掉,人家只好赶紧离远点,以为他是疯子。看他变成这个样子,我也很难过,但帮不上忙。
我把他送回家,想一直送他进屋,被他拒绝了,说屋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不要进去了。于是我送他到单元门口,拍了拍他的肩膀,目送他走进门,算是做告别。
又过了些日子,究竟过了多久我也不知道,一天早上我从沉睡中醒来,看了一眼身边熟睡的女友,顺手拿起昨天的晚报,看见《本市新闻》的栏目中,有这样一条消息:
本报讯:昨天本市高铁站的地下管道发生泄漏,工人在挖开地面抢修时,发现一具麻袋包裹的无名女尸,死者年龄在三十岁左右,贴身衣服口袋里有一枚红宝石戒指。如有知情者,请与市公安局鉴定中心联系。
我猛然一惊,想起了那句古诗,“垂死梦中惊坐起”,一下子坐直了身体,又看了一眼报纸,脑袋有些发蒙,一阵冷汗淌下了脊背。
这时女友翻了个身,伸手摸了摸我,小声问了一句,你醒了?
我嗯了一声。
她说今天是周末,继续睡吧,你昨晚累了,身上都是汗。
说完,她翻过身,又睡着了。
原刊责编 李路平
【作者简介】沈东子,作家、翻译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漓江出版社资深编辑。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少不更事》《碎陶》,短篇小说集《空心人》《手感》,随笔集《西风·瘦马》《西窗剪影》《桂林人》等,译著有《呼啸山庄》《大盗巴拉巴》《都柏林人》《乌鸦:爱伦·坡传记与诗选》等。在新浪网、搜狐网、凤凰网常年开设时评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