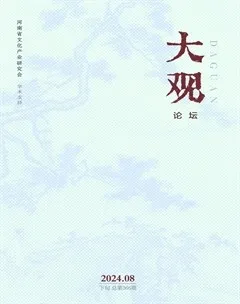数字技术时代沉浸式艺术的审美嬗变
摘 要:时代的发展影响着艺术发展的方向,每个时代都有代表性的艺术媒介,同时媒介也体现着每个时代的技术条件。数字技术时代下AI、VR技术的快速发展,对艺术家的创作方式产生了巨大影响,通过不断更新的数字技术所完成的沉浸式艺术作品更是如此。沉浸式艺术的变化促使观众产生新的审美需求,将美学推向新的阶段,并对传统审美产生一定的冲击。
关键词:沉浸式艺术;审美;互动;数字技术时代
数字技术的发展影响着艺术发展的方向,各类新的艺术媒介体现着当今时代的技术条件,为艺术家的创作提供更多可能。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计算机及网络的诞生为艺术造就了新的形势;直到20世纪90年代,虚拟现实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推动了艺术创新,为以沉浸为特征的艺术形式注入新的活力,使“沉浸式艺术”这一概念在现代社会兴起。在数字技术时代背景下,艺术与科学技术的融合作为现代艺术的特征越来越明显,新的审美方式与审美体验不断涌现,新的美学问题也随之而来,艺术家与观众开始注意到数字技术时代下创造的多种感官叠加的体验模式,同时对“眼耳独尊”的美学传统与审美体系进行反思。
一、沉浸式艺术相关概念
何为“沉浸”?中文的“沉浸”一词要追溯到韩愈《进学解》中的“沉浸醲郁,含英咀华”,意在形容细品典籍时仿佛沉浸在醇厚的美酒中[1]。由此可见,“沉浸”在汉字中的两层含义,字面含义为使物体沉入另一空间,延伸含义为使意识进入另一境界。英文中的“immersion”“flow”均有“沉浸”的含义,前者侧重感官体验上的沉浸,后者侧重意识和心理层面的沉浸。美国心理学家米哈里·契克森米哈赖(Mihaly Csikszentmihalyi)首次在研究视野中提出“沉浸”这一概念,他将“flow”描述为“完全专注或者完全被手头上的活动或现状所吸引”,并认为“心流状态是最佳的本能运动状态”。
何为沉浸式艺术?以沉浸为特征的艺术形式贯穿艺术发展的漫长历史,从原始时代的洞穴绘画到中世纪教堂,从园林到20世纪的电影院,而直到20世纪末,“沉浸式艺术”这一概念才开始逐渐被定义和阐述。黄鸣奋在《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中认为,沉浸式艺术是“在沉浸技术的支持下创造的艺术形式”[2]。迈克尔·海姆在《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中指出,沉浸式艺术能通过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重感官刺激来营造引人入胜的艺术氛围[3]。
沉浸式艺术是以新兴的沉浸式的数字媒介装置为重要呈现方式的现代艺术类型,既具有虚拟现实技术创造的媒介沉浸环境,又具有使观者心理上沉浸其中并引发思考的效果。
二、感知方式的演变:从视听到多重感官
在数字技术时代背景下,沉浸式艺术借助计算机建模技术、视觉跟踪技术等,为观者创造出集视觉、听觉、触觉甚至是味觉、嗅觉于一体的交互式虚拟场景。媒介理论家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提出“一切媒介均是人的延伸”,在当今时代,人们使用的每268f9f1eaf4dea9d56b5f347b56a869ca87756bcae227e756ed25fa716cf1cff种媒介工具,如电视、广播、VR设备等,无不在延伸和放大人类的感觉器官[4]。人们不再只重视视觉和听觉,而是运用多重感官去感知世界。
在过去,审美活动是通过欣赏现成的艺术作品完成的,观众通过用眼睛观看静止的图像和雕塑等来感知艺术。自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提出视听感官是理性的象征以来,用眼和耳进行感知的方式被置于至高地位,而触觉、味觉、嗅觉被认为会阻碍人类进行理性思考[5]。而自20世纪以来,人们开始关注人体本身。尼采提出人就是身体,身体是审美的主体,审美的前提和基本过程是肉体与世界打交道。理查德·舒斯特曼最早提出建立一门以身体为中心的学科,即身体美学,并提出了通过感知身体来提升灵魂的身心一体论。身体美学等理论的出现使更多人的目光转向了人体本身,人体的多重感官开始被作为审美经验和审美活动的媒介被观照。
数字技术时代,人们欣赏艺术作品已经不再只是通过视觉感官来观看,随着技术的更新迭代,很多沉浸式艺术作品能够调动观众的触觉、嗅觉等多重感官,进而提升观众的艺术体验。技术的不断进化强化着观众在感官层面上的沉浸感,在技术上完善观众基本的身体沉浸环境。以电影为例,电影从黑白到彩色,从无声到有声,从立体声到环绕声,从2D到4D,逐渐丰富观众的感官体验。在电影的播放过程中,通过加入震动座椅、雾气、雨水、气泡、刮风等效果,使电影的画面和声音变得更有质感且真实,从而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调动多重感官,进一步沉浸其中。艺术家通过作品帮助观众将眼、耳、鼻、手指等身体器官联系起来,从而全面感受面前的新世界。而当观众沉浸在作品中时,会主动去感受艺术品的人文内涵,并在内心产生思考,在极度沉浸之后产生认知上的变化。人的各种审美感官在数字时代得到了极大的延伸和统合,使感官突破了时空的限制。如今,身体的各感官作为审美媒介的重要性日趋显现。艺术的接受不局限于信息的获取,还可以通过调动身体的各个感官来体验,艺术体验由此前的视觉感知转化为多重感官的沉浸式体验。从视觉观看到视觉、听觉、触觉、嗅觉多种感官方式的叠加,是审美方式与艺术接受演变的必然趋向。
三、空间性质的转变:从客观空间到现象空间
传统的沉浸艺术所呈现的空间真实存在,如洞穴、园林、电影院等,审美发生于人们日常了解的客观空间,客观空间是绝对确定的几何体空间,不会随着情境产生变化。数字技术时代的沉浸式艺术打造的空间是围绕着观看者主体的空间,它不再是结构确定的几何空间,而是以身体为中心、情境化场域化的现象空间。同时,这里的现象空间包含数字化媒体,也包含声音、温度、湿度、人体等非数字化媒体。
20世纪胡塞尔创立现象学,在此基础之上梅洛-庞蒂继续研究并深入,在发表的著作《知觉现象学》中说道:“我必须从内部出发,沉浸其中,毕竟世界包围着我,而不是在我面前。”他认为意识通过身体展示出与外部世界的最初联系,而后又揭示出与之相关联的现象空间是由身体主体的知觉所创建的。现象空间通过现象身体向外部开放交流,紧密联系着身体的运动方式、观者所处情景以及感觉经验中被给予的具体内容,是一个不断在变化流动与重新分配的空间。奥拉维尔·埃利亚松(Olafur Eliasson)的《气象计划》就是体现现象空间的典型代表,观者沐浴在数百个黄色单色灯组成的“人造太阳”的光线之中,在这样的空间之中,人们不得不去面对自己、面对某些事情,回归通过现象身体感知一切的时刻。艺术家通过非日常的空间打破观众惯用的思维模式,使观众无法在空间中明确自己的位置,只能依靠作品中“人造太阳”和镜子中另一个空间的共同作用来构建对当下存在的感知,从而重新构建新的现象空间并反思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客观空间。
感知不仅是在视觉上,而且涉及人们的整个身体,世界的环境决定了人们如何感知它并与之产生联系,人们所感知的东西取决于当时的物理存在。处于现象空间内的现象身体对于不同情景的互动方式,每时每刻都在调动分配着现象空间的内部构造。人们得以从空间的内部出发,感受世界将自己包围并沉浸其中,现象空间随着现象身体的运动而形成不固定的场域。观者进入沉浸式艺术作品而产生的现象空间是以身体为中心的不断变化的场域,不断向外部世界开放并产生交流。
数字技术时代中的沉浸式艺术敏锐地感知并抓住了人体与空间之间的关系,在特定的空间内引导观者进入,从而建立起一种作品与观者相互依存的关系,生发出以观者为中心的始终随着具体情境变化而变化的现象空间,以改变人们对外部物质带有先入之见的观看方式。
四、互动特征的嬗变:从延时性到即时性
在传统沉浸式艺术中,观者与艺术作品的互动具有延时性,鉴赏者对于作品的接受与思考主要在作品被艺术家完成之后。而在数字技术时代,观众与沉浸式艺术作品互动的反馈是即时的,观众与作品间的互动和创造是同时发生的,艺术作品也会因观者的情绪、行为、表情等变化而产生新的变化,审美关系由此被重构。
即时反馈的形式又分为直接反馈和间接反馈。直接反馈是观者与艺术作品之间的直接互动和接触,主要的接触方式是观者做出手势、肢体动作,或者操纵控制杆和遥控器,比如部分虚拟现实系统中有专门的跟踪器,可以对观者的头部、眼球、手势等的运动进行实时跟踪,并通过数据即时反馈,从而更好地提升观者的审美体验。间接反馈是通过“探测”的形式进行系统即时反馈,不需要与观者直接接触。数字技术时代下的艺术家试图将视觉、听觉、触觉、味觉交互技术进行融合传播,构造出具有多种感官系统的作品。这种数字技术使每个观众在使用作品中的交互装置进行互动时,能将自己的身体动作转换为信息,并通过装置进行具象的呈现。随着相关技术的提升,在视觉和听觉信息交互功能诞生后,又产生了用触觉交互的新技术,观众通过使用与之配套的传感器就能使艺术作品在当下进行即时性的新呈现。
契克森米哈赖在其著作《心流:最优体验心理学》中提出,即时反馈是积极体验的一个要素,人类生活中的种种行为在大部分时候因目标而起,在行为产生之后通过反馈来了解是否达成目标[6]。数字技术时代的沉浸式艺术作品的意涵不是完全固定的,需要观众介入其中,观众与作品完成互动,才意味着作品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完整呈现。当下的沉浸式艺术互动是即时发生、相互作用的,所以互动的结果也包含作品、观众与艺术家之间产生的共鸣。认知层面的刺激是艺术创作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调动着观众的感官,影响着观众的知觉体验,进而增强观众对作品的情感共鸣。
五、当下沉浸式艺术所面临的问题与反思
在科技飞速发展的当下,数字技术为艺术提供了更多样的呈现与创造方式,但也产生了各种各样的问题。首先,作品内容良莠不齐。内涵是艺术的灵魂,但在一些沉浸式艺术作品中,数字技术的华丽外衣掩盖掉了艺术的内涵。随着网络的发达,一些作品开始以“网红”“流量”为出发点,忽视了作品内涵的呈现。艺术作品的呈现是为了带给观众美的精神体验,使观众在观赏和参与作品互动的过程中对作品的内涵产生更深入的思考。其次,技术的滥用也造成了观众的审美疲劳。一些炫酷华丽的灯光和不知所云的数字投影是当今数字技术时代特有的现象,借助各种数字技术刺激观众感官,使部分观众无法理解作品的内涵,更难以和艺术作品产生共鸣。艺术作品以娱乐化、接地气的形式呈现出来,打破了大众对传统艺术的固有印象,同时艺术家也应当重拾情感的表达与对美的追求,使艺术与科技更好地融合发展。
当今时代,沉浸式艺术作品应当通过数字技术与观众的参与共同创造独特的空间,捕捉并模拟观众的不同活动,创新艺术品的呈现形式,拓展观众的审美形式,引发观众的情感共鸣和对艺术与人性的思考。艺术家需要接受并将新兴技术有效转化为创作的工具,这个过程难免会遇到一些困难和问题,需要艺术家逐个攻破,同时也需要充分考虑大众参与其中的难易程度,不断完善艺术作品。
六、结语
随着各种数字技术的发展,艺术家的创作方式也随之产生变化。将沉浸式艺术与科技相融合,可以创造出新的审美体验。沉浸式艺术将实体的装置与无形的科技相结合,创造出新的艺术形式,使观者的感知方式从单一视觉转向多重感官。而在现象学、身体美学的影响下,身体作为审美媒介逐渐受到重视。沉浸式艺术作品与观者互动的即时性,为艺术互动的创新注入了新的动力。而如何更好地发展沉浸式艺术,使观者不仅体验到身体上的沉浸,还体验到精神与思想上的沉浸,避免科技手段凌驾于作品内容之上,是此后需要更加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
[1]韩愈.韩昌黎文集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564.
[2]黄鸣奋.新媒体与西方数码艺术理论[M].上海:学林出版社,2009:37.
[3]海姆.从界面到网络空间: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M].金吾伦,刘钢,译.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16.
[4]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M].何道宽,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78.
[5]张晶,解英华.数字时代沉浸式艺术的美学考察[J].社会科学文摘,2022(12):60-62.
[6]张依宁.新媒体时代沉浸式艺术作品的受众分析[J].文学艺术周刊,2022(4):67-70.
作者单位:
湖北美术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