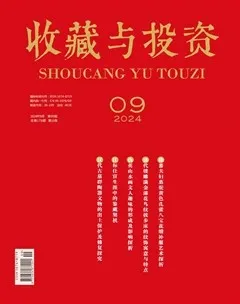仇英山水画文人趣味的形成及影响探析
摘要:仇英是明代“吴门画派”成员之一,他出身低微,偶然得到文徵明的赏识,在文徵明的引荐下拜师周臣学习院体绘画。后为谋生,其作为“驻府画家”长期寄住在项元汴、周凤来、陈官等大收藏家家中,他临摹了大量古代名作,并汲取诸家之长形成完备的绘画技能。他与文徵明等许多文人画家关系密切,因此受到文人画风的影响,是少数在绘画作品中体现文人雅趣的职业画家。本文主要探讨仇英所处时代社会背景、此期院体画和文人画各自发展状况,剖析仇英绘画为何能兼具院体画和文人画的特点,作为职业画家的他为何能跻身文人画家行列以及仇英绘画对后世画家的影响。
关键词:明代;仇英;青绿山水;文人趣味
仇英(约1501—约1551年),字实父,号十洲,与沈周、文徵明、唐寅并称“明四家”。明四家被其后的董其昌归为文人画派系。明代张潮《虞初新志》载:“起初为漆工,兼为人彩绘栋宇,后徙而业画,工人物楼阁。”仇英起初是漆工匠人,漆匠在当时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即便是后来成为画工,专工人物画和界画时,也没能改变其低下的阶层身份。后来仇英成为苏州地区炙手可热的文人画家,他的画被临摹仿制,赝品甚多。仇英能够取得后来的成就,与他的绘画风格密不可分,而其绘画风格的形成背后既有时代因素也有个人努力以及与文徵明等文人画家的往来带来的影响。
一、仇英所处时代背景和绘画发展状况
(一)时代背景
仇英生活在明代中期,经历了弘治、正德、嘉靖三位皇帝。明代永乐年间,随着郑和七下西洋,陆路和海上丝绸之路贯通,处于江南地区的苏州成为全国的纺织中心和商品集散地。弘治年间,孝宗皇帝励精图治,采取一系列政策刺激苏州经济,使得苏州得到全面大发展,成为全国经济和文化中心。贸易的空前发展促使物质生活繁荣,阶级意识被相对弱化因而萌发个性解放的思想。“成化至正德时期,随着国家长治久安和经济持续发展,文化消费需求逐渐上升,人们对精神享受有更多的追求。上层与下层、贵族与大众有着共同的喜好和需要。”同时社会弊端逐渐暴露,宗藩和宦官数量增多使社会负担沉重,政治环境恶劣,贪污腐败成风,在王阳明“心学”的影响下,遭遇科考失利的士人阶层转向书画之间,追求心灵的解脱。商人们利用手中的财富通过“捐纳”入仕做官,商贾阶层竭力追求文人士大夫的生活雅趣,成为艺术收藏主体。随着书画商业化发展,文人士大夫不再像元朝那样以隐逸自居,书画开始从文人士大夫抒发心中超脱逸气的工具中解脱出来,作为商品在艺术市场上流通,因此,文人画家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职业画家的身份。
(二)明代文人画与院体画的发展状况

晚明董其昌的“南北宗论”思想指出,文人画的鼻祖是唐代王维,五代董源、巨然平淡温润的山水画也属于文人画一派。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文人画作为一种较为明确和自觉的追求,当是出现在北宋 。他认为北宋苏轼是文人画思想的提出者和实践者。其后,米芾、米友仁父子以简笔淡墨的水墨山水画技巧创新发展了文人山水画。元代随着少数民族政权的建立,科举制被废,文人“学而优则仕”的理想破灭,遗民思想和遗民情结遂见于画端。元初遗民画家赵孟頫提出文人画应集诗、书、画印于一体和书画同源等思想,为文人全面介入绘画扫清了障碍,之后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则将文人山水画推向发展高峰。
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以青绿山水的风貌开创了中国山水画的端绪。唐代的“大小李将军”李思训、李昭道父子继承和发展了展子虔青绿山水的风格 。北宋在皇帝艺术家宋徽宗的带领下,画家王希孟的《千里江山图》成为翰林书画院青绿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宋代的赵伯驹也是青绿山水杰出画家,他的作品对仇英绘画风格的形成具有不可磨灭的影响。南宋刘松年水墨和青绿兼工,又精于界画,为仇英山水画风格提供了参考价值。元代虽是文人画家的巅峰时代,但元代文人画领军人物赵孟頫亦有师唐人青绿一体,元四家中的吴镇也对南宋的院体画风略有所取法。
至明代画坛前期以戴进为首的浙派在山水画风格上继承了南宋院体绘画的马远、夏圭。后来继浙派之后以吴伟为首的院体画派逐渐失去贵族支持,走向衰落。此期院体画风的职业画家们都开始慢慢调整自己的绘画风格,仇英也对青绿山水画作了进一步发展创新。可以说,顺应时代审美变化是仇英自觉调整自身青绿山水画风貌,并向文人画倾向转变的原因之一。
二、仇英的绘画之路和社交圈对其山水画风的影响
(一)仇英的绘画之路
仇英正式开始学习绘画是在认识文徵明后,文徵明对仇英的训练和指导,从教仇英识字背诵文章、吟诗作对开始。但由于基础薄弱,仇英的学习道路并不轻松。为此文徵明将自己的好友摹古高手周臣介绍给仇英当老师。周臣,字舜卿,号东村,以南宋院体李唐刘松年一派风格见长。周臣师陈暹,有史记载:“若临仿古人,真赝难辨。暹以其业传周臣,臣又以其业传仇英。”郎瑛在《七修类稿》中记载:“即近代论之,如戴进、吕纪、周臣辈,画亦神品,未见其能书也。”可见,周臣在当时可与宫廷院体画家戴进、吕纪并称,其老师名字却未出现,便知周臣的摹古技能远在其师之上,因此仇英后来临摹达到以假乱真并位居明四家之列与其师传不无关系。
早期漆匠生涯使仇英绘画过程具有非常明晰的程序性,画匠的经历也锻炼了他对色彩的把握能力,当然这些都来自仇英个人严谨的职业品性。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写道:“实父作画时,耳不闻鼓吹阗骈之声,如隔壁钗钏,顾其术亦近苦矣!”由此可见,仇英学艺时的刻苦程度非常人所能及。这也体现出仇英虽为一名画匠,但是并没有放弃自身对绘画的要求,也正是这种专注的精神,成就了他独特的绘画风格。

此外,仇英的绘画亦受到赞助人的影响,身为以画谋生的职业画匠,他的作品大多由赞助人定制。比如《汉宫春晓图》上便题有项元汴“子孙永保,值价二百金”。《子虚上林图》是仇英最著名的代表画作之一,也是赞助人周凤来为其母八十岁庆寿所定制的画作,全长十三米,历时六年之久。张丑在《清河书画舫》中称赞此画“可谓绘事之绝境,艺林之胜事”。可见,仇英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才完成,最终赢得赞助人等的好评。对于职业画家而言,绘制主题和内容不可避免地会受到雇主喜好的影响,同时创作的成果也要接受雇主的检验,因此,仇英在作画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持有一种严肃谨慎的态度,而这也反映在他的画作始终保持一种干净整洁的面貌特征上。
(二)仇英的社交圈
作为被冠以文人画风的职业画匠,仇英的诗文并未取得较好成绩,因此并没有严格恪守“诗书画印一体”的文人画传统,他很少在画面上题诗,而是以“仇英实父制”来落款,可能另一方面,也因为仇英个人认为画面的景物已经安排得很满,足够支撑起整幅画面,于是大多数作品便没有诗文题跋。为数不多的题跋作品,或是与诸多文人士大夫的合作,或是出自赞助人之笔。
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仇英与文徵明合作了《摹李公麟莲社图》,画中的人物出自仇英之笔,而山水由文徵明所绘,这足以说明作为文人画家之首的文徵明对仇英绘画的肯定,与此同时也从侧面反观出,正是仇英与文徵明的密切交往,使仇英的画作自然而然具有一种文人的意韵。在仇英早期的画作中,线条的勾勒上借鉴了文徵明的“细笔”手法,构图上也采用了文徵明画面中绵延平稳的态势,可见这是仇英有意识地接受和运用来自文徵明文人画一派的风格。除了合作之外,文徵明在仇英的诸多作品中都有题跋和题诗,虽然在同时期画作中也可见到文徵明的题跋,却远不及仇英作品之多,因而仇英能够取得后来的成就也与文徵明有意提携有关。
以文徵明为首的文人士大夫绘画团体也对仇英的绘画产生了深远影响。嘉靖十九年(1540年),文徵明的弟子彭年为仇英《鸳鸯图》题诗,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文徵明子侄文彭、文嘉先后为仇英《赵孟頫写经换茶图》题跋。通过仇英作品的题跋不难得知,仇英的绘画生涯始终与文人士子的交往交织在一起,在当时来说也是较为特殊的现象,暗示了仇英自觉向文人画坛靠拢的想法。仇英长期游走于文人雅集之间,参与书画鉴赏与交流活动,在文人的日常生活、文人传统、文人绘画题材等方面对文人画家达到精神层面的认同,继而开始从传统院体画风逐渐转向文人审美意趣。仇英对文人绘画的主题和文人所推崇的笔墨趣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他不断地在自己的画作中尝试融入文人画家所热衷的笔墨形式。
(三)仇英绘画风格的形成

除了老师周臣的教导和文徵明等文人士大夫的影响,仇英绘画风格形成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仇英临古、摹古和师古的绘画过程,这也是仇英能汲诸家之长的关键所在。在图像信息传播和复制技术相对落后的时代,艺术收藏更是极少数有钱人的专属行为,作为一个普通画匠很难有机会窥见历代名作,唯一的途径便是为收藏家临摹古画。因此,仇英一生中先后客居于项元汴、周凤来、陈官三大收藏家家中,为他们摹制古画。与大收藏家项元汴的结识,是在仇英中晚年时期,而项元汴仅有二十来岁,可谓忘年之交。项元汴为仇英提供了衣食无忧的生活和可以博览古代画作的机会,由于长期浸淫在古代名作中,作为职业画匠的仇英开阔了艺术视野,提高了审美层次,同时打下了夯实的绘画基础,习得了各种绘画技法。明代张丑在其著作《清河书画舫》中写:“仇英的山石师王维,林木师李成,人物师吴元瑜,设色师赵伯驹,资诸家之长而浑合之,种种臻妙。”仇英虽然师周臣学南宋院体画风,但是他又不局限于单一的院体画风,而是博采众家之长,这也使得仇英的绘画有机会和可能转向文人画。正是他不断地尝试将工整严谨的界画与青绿山水结合,又融入水墨写意的趣味,才使得他所创作的青绿山水画于工细精妙中带有一种宁静超脱之感。总而观之,仇英绘画风格得以形成的原因,首先在于,明代中后期浙派院体画的衰落以及吴门画派文人画风的兴盛和文人画家职业化的趋势以及职业画家文人化的倾向,这些为仇英山水画风格的形成提供了重要的时代氛围和先决条件。其次,作为职业画工仇英并没有把自身局限在某一种具体的画风中,而是抱有开放包容的心态,以“万法皆可学,万物皆有法”的钻研精神,将历代画家最为擅长的作画之法全部收入囊中,遂形成了自身独特画风。
三、仇英绘画对后世的影响
仇英在继承前人青绿山水画传统的基础上,创新性融入文人的审美意趣,形成了自身独特的绘画风格,赢得明代画坛及后世画家的一致好评。于精工谨细的青绿山水之中加入文人山水画的逸笔手法并以青绿山水的技法来描绘文人山水画的绘画主题,使画面既有青绿设色的富丽精美又有文人写意的雅逸之趣,为后世画家提供了许多可资参考的风格范本。
仇英对清代的三位画家影响尤为深刻,清初画家禹之鼎的部分作品在构图和笔法上与仇英有颇为近似之处,比如禹之鼎《秋江晚棹图》与传为仇英的《秋江待渡图》在构图上几乎一致,两者皆为立轴,表现巨岩之下扁舟横出,而且两幅画均是以青绿山水表现文人画的渔隐主题,可见禹之鼎在创作此幅画时受到了仇英的影响。清朝康熙乾隆年间的袁江“初学仇十洲”,袁江的界画作品《桃花源》,画面景物描绘细致精微,风格秀丽,严谨中略带飘逸,逸笔处颇有仇英韵味。袁耀活动于乾隆中期,和仇英一样擅长青绿山水和界画,袁耀取法晋唐绘画传统,与仇英的作品风格相结合,融入自己的绘画思想,形成了独特的艺术风格。袁耀的作品《阿房宫图》展现出阿房宫富丽恢宏的气势,画面建筑物由近至远,虚实相映,与仇英《仙山楼阁图》中建筑和远景空间的表现手法颇为相似,两者皆有一种辽阔崇高的缥缈气韵。
近现代以来,随着西方绘画的传入,传统的青绿山水画技法由于工序繁复遭受了极大冲击,呈现式微之态,其雍容典雅的富贵气息和精致工整的装饰意味在现代社会黯然失色。近代画家张大千重拾青绿山水作画传统,他通过临摹仇英的作品,学习借鉴仇英工整与写意相融合的笔法,将重彩与水墨融为一体并推陈出新,尝试用青绿泼墨泼彩的作画形式表现大山大水的气魄。他的青绿山水画用色大胆,虽是随意泼洒却有的放矢,粗放狂野中不失生动情节,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为青绿山水画在当代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四、结语
仇英的一生经历丰富从漆工到画工再到明四家之一的大画家,他的习画历程从摹古到师古再到形成个人独特画风,使其作品既没有职业画家的匠气,也非因循摹古的习者之流。虽有院体画风老师周臣的教导,也有文徵明等文人士大夫的指点迷津,但其画风形成最为关键的原因是仇英个人对自身身份的认知和定位以及他对绘画的思考和追求,他才得以跨越古代封建社会的阶层束缚,最后成为名垂千古的绘画大家。仇英在山水画中继承发展了晋唐绘画高古的色彩传统,将院体画和文人画结合,创造出个人独特的绘画语言,既迎合了当时各个社会阶层的审美需求,也对后世画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者简介
郭敏帆,女,山西临汾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美术史学理论。
参考文献
[1]牟建平.工而又雅:仇英的青绿山水画[J].收藏,2018(2):29-31.
[2]方志远.万历兴亡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朱琰.明代文人画的流变:略论吴门画派的兴起与衰落[J].东南文化,2013(4):123-126
[4]周林坡.十载遣怀[C].郑州大学美术学院教师学术论文集,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1.
[5]杨勇.周臣生平考[J].新美术,2010(2):30-37.
[6]胡蓉.论仇英《清明上河图》的摹古与创新[J].宁波教育学院学报,2018(1):118-120.
[7]董其昌.画眼美术丛书初集第三辑[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134.
[8]刘国.中国山水画新技法[M].延吉:延边人民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