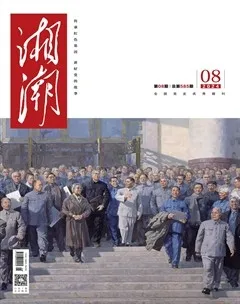『敌进我进』战略战术的运用特点

“敌进我进”是刘伯承一贯的战略战术思想,较早见于土地革命时期红军深入国民党军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实践。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敌进我进”战略战术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刘伯承将“敌进我进”概括为,我军敢于脱离自己的后方,进入到敌人的后方,与广大民众结合作斗争的行动。在日占区,“敌进我进”的主要方式是组建和派遣武装工作队(以下简称“武工队”),将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发动群众,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建立两面政权,把日伪统治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
1942年3月17日,刘伯承为一二九师起草下达了《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到敌占区工作指示》(以下简称《指示》),全文仅6条内容共计772个字,从任务选择和实施、组织领导和指挥员配备、政治工作策略和具体任务、战斗实施从属于政治工作,避实击虚的战术原则等方面进行了规定,体现了“敌进我进”的精髓。时隔82年后的今天,重温这篇历史文献,回顾和总结“敌进我进”战略战术在武工队实践中的运用特点,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和启示作用。
“武工队是以政治任务为主,合乎政治任务的就打,不合乎政治任务的就不打”
刘伯承曾将我军长期以劣胜优的一条根本经验概括为“善于以政治来战胜敌人”。他强调“部队具有良好的政治情绪与饱满的战斗精神,这就是启发和保障我们打胜仗的一个基本条件”,“打胜仗的战术要靠不断的政治工作”。刘伯承进一步明确指出武工队的基本任务是在敌后“繁殖游击战争,创造游击根据地,主要是以政治进攻为主,以游击战争为辅”,“武工队是以政治任务为主,GzMRwMGWM91nBg3Rrjl5wDv9woZ42yQSyXwJ3DO2R1s=合乎政治任务的就打,不合乎政治任务的就不打”,斗争原则是打击少数,争取多数。
《指示》开宗明义提出“武装工作队初次出动,应着重于简单的政治宣传”。全文共6条内容,其中5条提及政治工作的地位作用、方法任务等,如“战斗应根据政治工作任务的需要与否而决定之,不进行任何与之相违背的战斗”,武工队出动前“并由分区首长亲自教以切实的急需的政治工作与战术,并定出计划而演习之”,“政治工xNGeyl6NRlHzn42DUnQhAjB/hdPpfia3F3T7TOHJVSU=作,应以政策和革命的两面策略,运用宣传与组织的方法,察明敌人欺骗与压制人民、实施配给制度的情形,尤其秘密爪牙的分布,并乘机进行集会,做好团结群众(首先知识分子)的工作,而本身尤应严格遵守纪律”。
刘伯承还提出,不仅我军内部要进行强有力的政治工作,同时对于敌人,要开展政治攻势,把政治攻势变为物质力量。武工队高度重视对敌伪的工作。“对伪军首先要求它不摧残民众”,派敌工干部打入伪军伪组织内部进行瓦解分化,建立两面政权,争取起义反正。对日军的政治攻势主要通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散发宣传品、喊话、写信、打电话等方式,时机成熟后在敌据点附近组织专门演出,弹唱日本歌曲,在日本传统节日期间向其赠送小礼品、慰问袋等,针对性开展宣传战和攻心战。据载,太行军区就曾发生过争取日军被俘少将铃木川三郎加入反战同盟的情况。
“敌我的战术竞赛,将随之而更新颖更丰富的发展,急需我们在斗争中重视研究与发展战术”
刘伯承经常强调,作战要弄清任务、敌情、我情、地形与时间五个要素,其中最需要下功夫弄清楚的是敌情。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随着日军对根据地的“扫荡”愈发残酷和野蛮,守卫和坚持根据地越来越困难。他剖析了日军色厉内荏、外强中干、前硬后软、兵少防宽、此集彼虚等基本特点,全面系统研究了日军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战略战术,特别是七七事变以来对八路军作战的战术演变,针对性提出了“敌进我进”的战略战术,及时调整了我军反“扫荡”战术战法,从而有效粉碎了敌人的“扫荡”。
《指示》第二条即讲明,“出动前,应使全队将敌情研究清楚”。刘伯承曾指示武工队,“情报通信是进攻的,除奸防谍是防御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但重点在前一点,没有侦察就不能有除奸防谍”,并明确“情报通信所也可以作指挥所,基干的情报站要秘密,大众的情报网要多,并使之互相结合。对敌之情报网可能利用者利用之,不能利用者就打掉”。刘伯承作为高级指挥员,对查阅缴获敌军材料、研究敌俘(逃兵)的审讯记录、勘察地形等具体工作经常亲力亲为,充分体现了对敌情研究的高度重视。
刘伯承在《太行军区夏季反“扫荡”军事总结》中指出,“日寇特务机关、宪兵队、间谍、叛徒,以极大努力,做了长期阴谋的各种准备工作,也做了‘扫荡’中、‘扫荡’后衔接发展的工作。我们军事政治的情报工作远不如敌人”,“我们对于敌军组成与部署,对于敌占区地形、民众、政治、经济情形不及敌人清楚,就是对于自己本身某些事物也不及敌人清楚”。针对这种情况,他强烈要求“切实建立我们的情报工作,应认为是对敌斗争(尤其是防谍除奸)与争取反‘扫荡’胜利的最重要环节”。刘伯承用深入细致对比分析敌我双方情报工作的方式,强调了侦察和研究敌情的极端重要性。
“武工队是用避实击虚的奔袭战术,使得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捕捉”
1941年后,敌后抗战进入最困难阶段。为尽早解决中国问题,华北日军在加大对根据地“扫荡”力度的同时,针对我军游击战的特点,改变短促突击、长驱直入等惯用战法,研究制定“铁壁合围、捕捉奇袭、纵横扫荡、反转电击、辗转抉剔、分进合击、夜行晓击”等新战术,使根据地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甚至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口。以晋冀鲁豫根据地为例,其间,十字岭突围战中八路军总部被围,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等牺牲。涉县突围战中一二九师直属队被围,在一二九师首长指挥下,被围八路军乘夜从敌军间隙中跳出包围圈。
为使晋冀鲁豫根据地渡过难关,刘伯承根据华北战场形势,紧紧抓住日军兵力不足,只能占据城市及交通线上一些重要据点,组织“扫荡”时经常“拆东墙补西墙”等明显弱点,改变此前忽视日占区工作、在根据地“关起门”搞建设的做法,实施“敌进我进”战略战术。该战略战术主要有两方面特点:一是处于弱势的我军在受到力量占优势日军的攻击时,主动向日军后方进行攻击;二是与单纯军事进攻不同,“敌进我进”是包含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在内,且以政治进攻为主的对日占区的综合进攻,即武工队的斗争形式。
《指示》对武工队初到日占区的战术原则及行动要点作出明确要求:“一般说来,武工队是用避实击虚的奔袭战术,使得敌人措手不及,无法捕捉”,“如突遇小敌,可捕捉或歼灭之,大敌则避开之。受敌合击时,则以麻雀战分遣撤退,但须预定第一、第二集合场,而以便衣联络之”,“不老走一路,不久停一地(暂时停止也应在工作四通八达之处),一切使敌不意。应严守秘密,不露动向,依靠居民作我们潜伏地探,而通信极应秘密,行动应利用隐蔽地形和昏暗天气,声东击西,神出鬼没,散布‘谣言’,曲折运动,以迷惑敌人”。
武工队贯彻“敌进我进”战略战术,与敌对进,避实就虚,乘机深入日占区开展综合斗争,以日军后方的忧患牵制或削弱其进攻力量,打破其对根据地的封锁和围困,抢抓战争主动权,从而达到釜底抽薪的目的。
“实行全面的全力的战争,以粉碎敌人的所谓总力战”
偷袭珍珠港后,日军除妄图在武力上征服华北外,又在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加紧侵略、封锁和渗透,即实施所谓的总力战,在百团大战后更是达到了空前程度。为彻底粉碎日军总力战阴谋,我们针锋相对提出,在党的一元化领导下,发动党政军民的全部力量,对敌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全方面及全力的战争。1941年初,刘伯承在《关于太行军区的建设与作战问题》报告中指出,“党军战术的基本特点,就在于把战术与民众对敌人的一切斗争结合运用,以发扬全面战与全力战”。之后再次号召“实行全面的全力的战争,以粉碎敌人的所谓总力战”。武工队的斗争就是全面战与全力战的具体形式。
新的战争特点催生新的斗争方式。针对当时日占区群众劳役和经济负担奇重的痛苦,武工队深深扎根于日占区人民中间,将领导群众进行反掠夺、反劳役、反抓丁斗争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运用各种方式与敌周旋,保护群众的切身利益,赢得了日占区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在组织形式上,根据新的斗争形势需要,武工队采取在党的统一领导下,军队、政府和群众相结合的精干的、一元化的组织领导模式。在斗争任务上,武工队主要起到四方面作用:一是配合主力部队进行武装斗争;二是不断开辟根据地和扩大解放区;三是打击和破坏日占区统治秩序;四是对日伪实施强大的政治攻势。在斗争效果上,武工队斩断了日军伸向根据地的“扫荡手”和“蚕食嘴”,打击了其强化日占区的阴谋。同时,积极建党建政,变日伪反动政权为革命的“两面政权”,不仅恢复了部分失去的根据地,还在日伪心脏地区建立了许多小块的游击根据地,使日占区无法巩固。
“敌进我进”战略战术及武工队的斗争实践,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伟大创造。尽管这段历史已逐渐远去,但其中蕴含的坚持党的领导、重视群众工作、勇于改革创新等历史经验,以及避实就虚、攻敌薄弱、寻找敌人弱点、创造敌人弱点、打击敌人弱点等非对称作战的智慧,对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对垒强敌打赢信息化条件下局部战争仍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单位: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