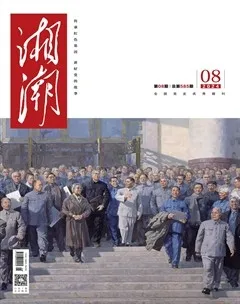毛泽东为什么让梁漱溟读《反杜林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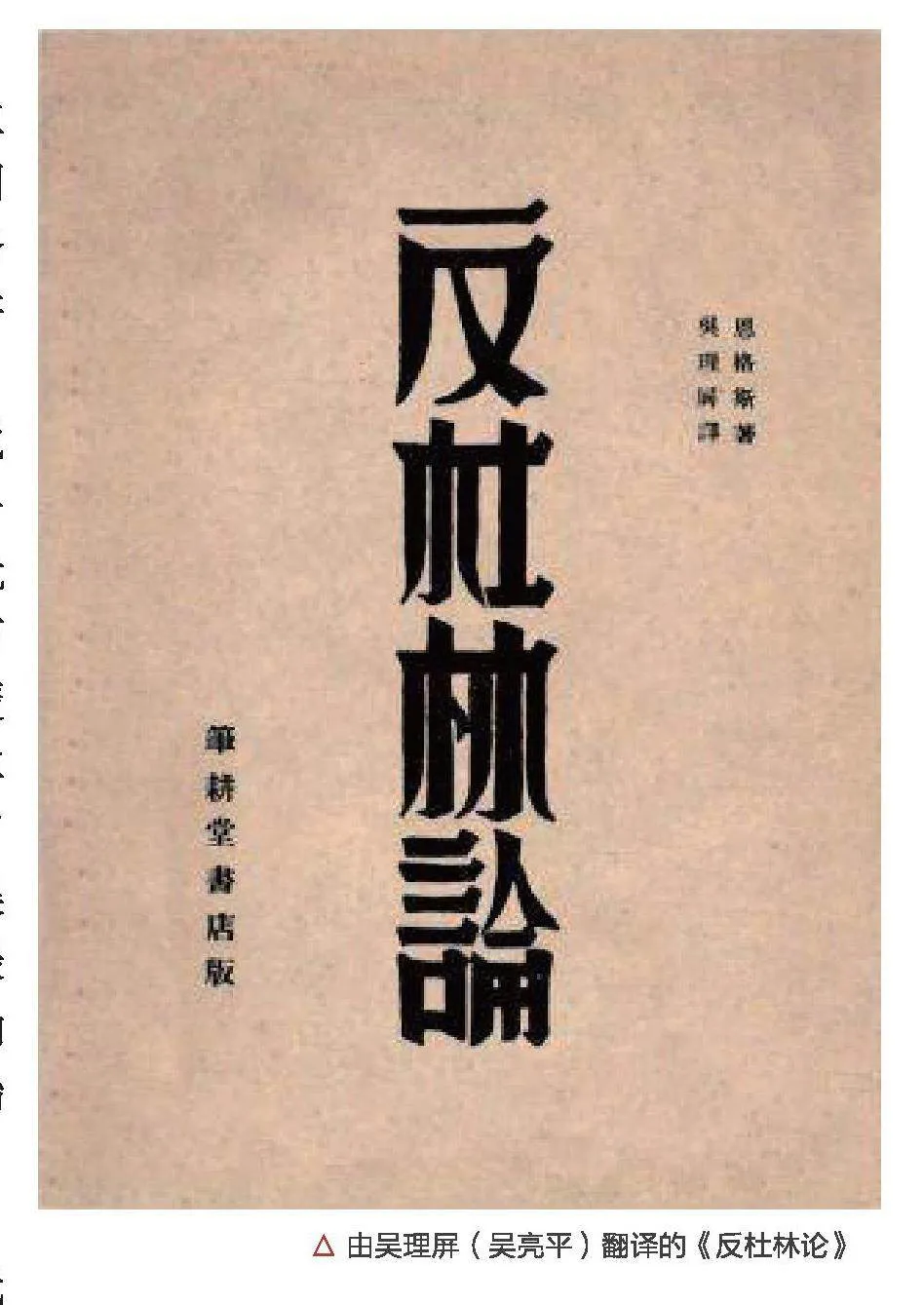
毛泽东给人推荐书目非常具有艺术性、针对性。在延安,毛泽东阅读了梁漱溟著的《乡村建设理论》,并和梁漱溟进行了多次交谈。针对梁漱溟的著作与观点,毛泽东向梁漱溟推荐《反杜林论》。毛泽东到底想让梁漱溟读《反杜林论》中的什么?毛泽东想表达什么?
对于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争论与交往,学界已有一定的研究;而关于毛泽东推荐梁漱溟读《反杜林论》的事情,学界却没有予以足够的关注。
《反杜林论》的写作背景以及对毛泽东的影响
1871年后,德国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并逐步崛起,阶级斗争也随之激烈。欧洲工人运动的中心也开始变迁,逐渐从法国转向了德国。德国资产阶级为了保证自己的地位不受侵犯,一方面选择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另一方面大肆围剿马克思主义。杜林是一个小资产阶级思想家。1867年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出版后,他就撰写过攻击性文章。然而,进入19世纪70年代,杜林突然宣布改信社会主义,并俨然以社会主义“改革家”自居,抛出了一套详尽的所谓社会主义理论和完备的改造社会的实践计划。杜林的理论在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内引起很大反响,很快形成了一个信奉杜林主义的派别,就连党的一些领导人也受到了迷惑,杜林主义给刚刚统一不久的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造成了很大的思想混乱。党的领导人李卜克内西等人深感杜林主义造成的问题的严重性,他们给恩格斯写信反映了情况,并请求恩格斯反击杜林主义。恩格斯又给马克思写信商讨反击杜林主义的对策。马克思给恩格斯复信坚决支持他的意见,紧接着恩格斯对杜林主义进行了批判,汇集成《反杜林论》一书出版。
《反杜林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贡献是全面的。第一编,哲学。批判了杜林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形而上学和唯心史观,捍卫并阐发了唯物主义物质观、反映论和唯物史观的阶级论、道德论、平等观等;第一次为唯物辩证法下了一个科学的定义,完整地阐明了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和范畴。第二编,政治经济学。批判了杜林的庸俗经济学尤其是“暴力决定论”观点,科学地论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正确分析了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及暴力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第三编,社会主义。批判了杜林的假社会主义的唯心主义方法论,阐述了社会主义学说的科学方法论;科学地分析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地位,论述了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必然性,系统地阐明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
这样一部巨著,当然引起了毛泽东的重视,这从他和译者吴亮平的交谈中就可以得知。毛泽东称吴亮平翻译《反杜林论》“功劳不下于大禹治水”,并经常与吴亮平讨论《反杜林论》中的理论问题。长征时,毛泽东即使在担架上也要阅读《反杜林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外出巡视时,也要带上《反杜林论》。毛泽东不仅自己读,而且将《反杜林论》印成多册大字本推荐给党内的干部读。毛泽东曾在自己的著作《矛盾论》中大段地引用过《反杜林论》第一编第十二节《辩证法。量和质》的原文,该书对毛泽东的影响之深也就不言而喻了。
就身份与思想状态而言,梁漱溟与杜林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自认为自己深受社会主义影响,却有着旧的世界观。他们并不是要打碎旧世界,而是要通过妥协、调和来修补旧世界。毛泽东与梁漱溟对于中国社会不同认识的根源即在于此。
毛泽东与梁漱溟的交谈与交锋
20世纪二三十年代,梁漱溟进行了乡村建设实践活动。梁漱溟在广东进行的乡村建设主要是依靠李济深。据梁漱溟回忆:“蒋介石要除掉李济深的势力,把李济深软禁在南京城外的汤山,共囚禁了两年。李济深倒了,我的乡村建设计划在广东搞不成了。于是,我离开了广东。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一阶段。”说到底,梁漱溟搞乡村建设依靠的是军阀,而不是人民。“1929年,河南村治学院招收了第一批学生,有400人左右。正在搞的时候,蒋、阎、冯中原大战爆发,河南是主战场。战火纷飞,村治学院难以继续办下去,学生学习了不足一年,便草草结业,学院也就结束了。这是我搞乡村工作的第二阶段。”“第三阶段,是在山东,在这里搞的时间最长。从1931年年初到1937年年底,日军侵占山东以后结束。”军阀混战、帝国主义侵略造成了梁漱溟三次乡村建设的失败。
全民族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邀集了社会各界的一些代表性人物到南京开会,梁漱溟是作为无党无派的社会贤达被邀请去参加此次“参议会”的。据梁漱溟回忆:“我个人也在(参议)会上讲过不少意见,中心是抗战民众教育问题。还记得会上发生过一段插曲:由于我发言较长,先讲乡村建设,后讲抗战民众教育主张,傅斯年打断我的话,说:‘别讲这些了,当前最要紧的是前方的军事和国际形势。你这种讲法,太耽误时间了!’汪精卫是会议主持人,他劝阻傅斯年,说还是让梁先生把话讲完。但我则不得不勉强结束自己的发言。会后我将自己的主张,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的《大公报》上,其要点是强调全民总动员,而当务之急是停办正规学校,大力开展全体民众的抗日救亡教育。”梁漱溟救国之心肯定是有的,但是看问题时多端寡要也是客观存在的。
当时国民党的所作所为令人寒心,梁漱溟对国民党失望,对抗日前景感到悲观。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为此,梁漱溟前往延安,希望从共产党这里得到答案。“梁说,他对目前的抗战情况甚感失望,战场上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国民党方面上上下下缺乏信心,个人心中亦十分悲观。如此下去,中国的前途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梁表示这次来延安,就是向中共领袖讨教来的。”毛泽东十分耐心地听完梁漱溟的叙述,才露出笑容,斩钉截铁地回答道:“梁先生,你所听到看到的若干情况,大体都是事实。但我的看法,中国的前途大可不必悲观,应该非常乐观!中华民族是不会亡的,最终中国必胜,日本必败,只能是这个结局,别的可能没有!”对于毛泽东关于抗日前景的回答,梁漱溟心悦诚服。但是两人在一些问题上也出现了争论。
梁漱溟认为:“中国社会可称为一种职业分立的社会。在此社会中,非无贫富、贵贱之差,但升沉不定,流转相通,对立之势不成,斯不谓之阶级社会耳。”接着梁漱溟就指出了中国存在的问题以及自己的解决方式:“今日中国问题在其千年相沿袭之社会组织构造既已崩溃,而新者未立;或说是文化失调。”“比如贫乏问题是中国人的大问题,我们就要大家合作生产,合作运销,不要单是消极的周济贫乏,我们要积极的使其不贫乏。我们要把一切经济上的事情,生产消费以及种种技术进行,都放在合作里面——也就是乡约里面。”很明显,梁漱溟是希望通过“乡约”这样的手段,也就是改良主义来解决中国当时的问题。进而,梁漱溟还对共产党提出的阶级革命进行了批判:“共产党的错误,仍在蹈袭外国阶级社会里农民运动的旧套,而不认识中国社会。”“今日中国社会需要整理改造,而不是阶级革命;农民地位需要增进,而不是翻身。”
熟读中国历史、对中国社会有着精准认识的毛泽东,自然不认同梁漱溟的看法。毛泽东认为中国是一个阶级社会,而暴力作为新社会的助产婆不可或缺。
这次争论可以看作二人的第一次交锋,当时的首要问题是抗日,两人的争论并不急于做出结论。据梁漱溟回忆:“现在回想起这场争论,使我终生难忘的是毛泽东的政治家的风貌和气度。他穿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在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说话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明明是各不相让的争论,却使你心情舒坦,如老友交谈。他送我出门时,天已大亮。我还记得他最后说:梁先生是有心之人,我们今天的争论不必先作结论,姑且存留听下回分解吧。”临别时,毛泽东给梁漱溟特别推荐了《反杜林论》。毛泽东想对梁漱溟说的话,也全部在这本书中。
毛泽东的暗示与梁漱溟的启发
“人们自觉地或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从他们阶级地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这大概就是毛泽东心中最想对梁漱溟说的话。梁漱溟的思想观点与实践活动来自其阶级地位及其所依据的实际关系。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梁漱溟的“伦理本位”实际上是文化决定论,但是在1938年,梁漱溟肯定是不自知的。而毛泽东向梁漱溟推荐《反杜林论》,实际上是想委婉地告诉梁漱溟,梁、杜二人有诸多相似之处。他们都持改良主义,却认为自己是革命的。正如梁漱溟所说的:“唯其似是而非,所以不革命而自以为革命。”
关于暴力,毛泽东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梁漱溟则是坚决反对暴力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讲:“暴力,‘用马克思的话说,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它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毛泽东的荐书之意就是让梁漱溟认识到暴力的积极意义。向敌人缴枪只能更方便敌人的屠戮,而勇于抗争才能建立新世界。为什么帝国主义对于甘地推崇备至?因为其不抵抗符合帝国主义的利益。梁漱溟对于马歇尔说他“是中国的甘地”一事颇为自得,应该就很能说明问题了。百万雄师过大江,翻天覆地慨而慷。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既开辟了道路,又碾碎了错误观点。历史的发展最终证明毛泽东是正确的,而梁漱溟也开始进行自我反思。
新中国成立后,梁漱溟写了《何以我终于落归改良主义》一文。他在文中毫无保留地说:“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而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
毛泽东对梁漱溟的劝诫,都藏在《反杜林论》中。很明显,毛泽东非常清楚地把握了两人争论的焦点和梁漱溟思想错误的根源所在。毛泽东非常高明地选择了荐书这一方式,委婉地点出了梁漱溟的错误所在以及产生这种错误的原因,他希望梁漱溟能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解决问题。不幸的是,梁漱溟当时并没有读懂《反杜林论》和毛泽东,以至于后来两人在1953年又产生了争论。庆幸的是,晚年的梁漱溟对毛泽东有了一些理解:“人们常说我良心上如此,本着良心来的。可这是世俗的,常常因时因地,不同的时代,不同地域、空间的人,他们都有所谓的良心,这良心浅得很,是同时、同地,实际上是个风俗习惯,一般的社会,通常这样为对。但这对,不一定真对,有独到的人、独到见解的人,不这样走,要革命的。他有良知的,超过世俗,所以旁人见到他,他是能够开创新局面,为社会开出新道路,比如毛泽东就是这样。毛就是这样的人,列宁都是这样。他从里面发出来,本着本心,不随世俗走,要革命,真革命的人,就是这样。真革命是本着良心来,真是有劲头的,所以能创新局面。这种人物当然了不起,世俗认为‘是’,他认为‘非’,不能跟流俗走,这样才能开出新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