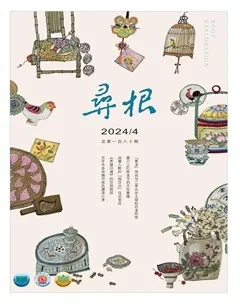清代诗人王友亮与江宁地方“乡愁”书写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指出:“然屈平所以能洞监风骚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乎。”这句话深刻地指出了“地方性”对诗人和诗歌创作的深刻影响。从人文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的意义上讲,“江山”其实就是一种独特的“地方性”。诗人可以书写“地方”,而“地方”反过来又影响着诗人的创作态度、创作风格和创作效果。
王友亮(1742—1797),字景田,号东田,又号葑亭,徽州府婺源县(今属江西省)人,寄籍江宁府上元县(今南京市),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进士,官至通政司副使,乾隆年间著名诗人,主要诗文作品包括《双佩斋诗集》《双佩斋文集》《金陵杂咏》等多种。江宁是王友亮的出生地、生长地、侨寓地,虽为他的“第二故乡”,但从居住时间来讲,王友亮对江宁的了解和研究,与“第一故乡”婺源不相上下。王友亮对江宁的地方书写包括景观、人文、人物故实与内心世界所生发的“乡愁”,除了散见于《双佩斋诗集》,都集中体现在《金陵杂咏》组诗。《金陵杂咏》卷首自署“新安王友亮葑亭”,可见江宁依然是作者的第二故乡。即便如此,并不妨碍诗人对江宁的热爱和歌咏,从年轻时期至人生暮年,王友亮一直在创作以江宁地方为写作对象的《金陵杂咏》系列组诗,热烈地歌唱江宁的山山水水、风土人情与人文故实。尤其自1779年直到辞世近二十年间,王友亮长期滞留京师,但在此期间,通过诗歌书写着江宁这个他终究再也不曾回过的“第二故乡”。
具象化书写:《金陵杂咏》与江宁地方空间景观和历史人文
王友亮晚年在《金陵杂咏》自序里,对自己集中创作这一系列组诗的原因做了交代:“乾隆丁亥六月,余居白鹭洲。偶读高季迪《姑苏杂咏》,因思金陵为六朝都会,继以南唐、有明,俱称繁盛,虽兵燹销蚀,陵谷变迁,故址遗墟,十犹一二。宋张敦颐《事迹》一书已不概见,元明凭吊之作亦复无多,殊为觖事。窃不自揣,就郡乘所载、山屐所经者,仿青丘之例,分体咏焉。此后中辍二十余年。壬子仲春,京居多暇,得旧稿于败簏中,友人阅而喜之,劝余卒业,计题二百三十一,诗二百六十三。弱龄吟兴,重拈颁白之秋;故里游踪,续入软红之梦。可胜叹哉!编次既成,为志其颠末如此。乾隆五十七年三月十四日,王友亮自序。”
高咏(1336—1374),字季迪,号青丘子,元末明初著名诗人,江苏长洲(今苏州市)人,长期居于乡里,集中创作以苏州为歌咏对象的《姑苏杂咏》,分为风俗、古迹、祠庙、冢墓、山川、泉石、园亭、寺宇、桥梁、杂赋十个类目,共计一百三十五篇,是大量书写家乡生活风物的苏州风土诗,堪称宋元以来文学“地方化”的集中体现。
由此可见,王友亮是在阅读了高咏《姑苏杂咏》之后,受到启发而生发出创作设想,觉得这本诗集体例很好,自己也可以尝试着创作一本跟高青丘类似足以传世的“地方”诗集。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一是江宁的名胜古迹、人文事迹已经大量湮灭散佚,王友亮觉得有必要通过创作组诗的形式,予以集中记录、考证、考订,以为史学的补充;二是出于对江宁这个侨寓地发自内心的挚爱。补充史实的功效,王友亮确实做到了,《金陵杂咏》每一首诗题之下,都单独撰有一段“小序”,把这首诗书写对象所处的地理位置、得名由来、主要特征、人物故实等情况,做了简要的解释说明。比如七律《摄山》小序称:“城东北四十里,山多药草,可摄生,故名。秋时人多看红叶于此。”该诗颈联云:“药苗春涧香生雨,枫叶秋林烧入云。”清代中后期江宁即有“四十八景”的说法,其中包括秋游栖霞看红叶,目前王友亮这首诗是所见最早关于秋游栖霞看红叶的文字记载,从这首诗中可知至迟在清初至清中叶这一习俗已经开始在江宁民间流行。
《金陵杂咏》共有263首诗,其中山岩类59首,川梁类29首,城市类34首,宅第类14首,园亭类21首,祠庙类13首,寺观类35首,陵墓类22首,宫祠类14首,杂物类14首。这部诗集的内容十分庞杂,书写对象几乎涵盖了当时江宁各个著名的空间景观和文化地标,充分展示了王友亮对当地名胜古迹和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与洞察。《金陵杂咏》目前可见三个版本传世,一是乾隆六十年(1795年)刊本,二是嘉庆十年(1805年)刻本,三是嘉庆十四年(1809年)刊本。从如此之多的版本传世,足见这本诗集应是深受当时广大诗友或读者的喜爱。
王友亮自称创作起始于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止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前后长达二十六年。但实际上,笔者将王友亮的《金陵杂咏》和《双佩斋诗集》这两部诗集进行认真比对,发现作者最早书写江宁地方的诗歌并非从乾隆三十二年始作,而早在乾隆十九年(1754年)起,就开始有意识地针对江宁进行创作,比如,明确标注创作时间为1754年的《蛾眉岭》《青溪》《梅花水》,1755年创作《劳劳亭》,1756年《雨花台》《金陵冈》等,早就有所发奋了。可以说,王友亮以江宁“地方”的空间景观和历史人文为书写对象的诗歌作品,几乎一生中的每年都不曾间断,经常性地对景抒情、借景抒情。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1779年王友亮长期旅居京师、不曾再回过江宁的近二十年间,都在持续创作《金陵杂咏》组诗。由于已经不在江宁当地的现场,所以这些作品肯定都是诗人利用头脑里的回忆,或者结合阅读江宁地方史志或其他类型的文献资料之后,重新进行创作的作品。已经远离《金陵杂咏》所书写的“地方”现实空间场景,这种离开江宁还继续书写江宁的书写方式,属于广义上的“记忆”或“怀想”,是发乎情之所至、情之所深,是一种文学意义上的“在物同骚,怀人有梦”。正如与王友亮同时期的优秀骈体文作家吴锡麒为《金陵杂咏》作序所称:“吾友葑亭给谏,生居佳丽,眼熟繁华,白鹭洲边,潮痕终古;凤凰台上,鸦影于今。分二水于帘前,俯六朝于楼外。每至笛残远步,曲罢长干,借笠冲云,拖筇犯雨。听官蛙之阁阁,玩野雉之斑斑。在物同骚,怀人有梦。砚北之孤悰远寄,江南之哀艳偕传,娓娓乎不自知其情之何以深也。”
可以说,高启《姑苏杂咏》在某种意义上是以想象和追忆建构出来的一个“苏州”,长期旅居京师的诗人王友亮依托想象和追忆方法所重新虚拟建构出的江宁第二故乡,也是一种重新建构。在此意义上,《金陵杂咏》组诗只有1779年之后所撰写部分才是真正意义上对“江宁这个“地方”的“故乡”书写;1754年至1779年间的创作是对江宁空间景观、历史人文的书写,属于在文学现场的“写实”创作,不算具有真正“乡愁”意义的“故乡”书写。因为诗人尚未离开“江宁”这个地方,还不存在弥漫心间的江宁“乡愁”情绪。
《金陵杂咏》与《双佩斋诗集》的编排体例不一样。后者是编年体诗集,但前者并没有注明作品的创作年代。笔者把既收入《金陵杂咏》又收入《双佩斋诗集》的诗歌作品挑选出来,发现两本诗集在1779年之前重叠的诗歌作品多达53首;1779年王友亮离开江宁长期滞留京师之后,两本诗集里面重复的诗歌作品数量则变得十分稀少,仅有一组,即1784年创作《江楼八景诗》八首,涉及景点包括龙江烟雨、鹭州晴照、长干塔火、浦口风帆、钟阜浮岚、定山积雪、新河观涨、晓渡候船。由此推测,长期旅居京师之后,王友亮通过回忆追叙的方式,直接以江宁的现实空间景观和人情风物作为创作题材的作品、直接歌咏江宁“地方”空间景观的书写作品,相对来说在王友亮日常诗歌创作中的比重已经大大降低,取而代之的是把自己对江宁这个“地方”的思念,融入其他类型的诗歌作品,在一些重要时间节点和特定的语境背景下,采用一些抽象化的空间景观词汇和思乡意象来进行书写。
抽象化书写:《双佩斋诗集》与江宁地方的空间景观和乡愁意象
意象是客观物象经过创作主体独特的情感活动而创造出来的一种艺术形象。古代怀乡思乡类诗歌常见的意象很多,比如:送别类意象(或表达依依不舍之情,或叙写别后的思念),多为杨柳、长亭、南浦、酒等;思乡类意象(或表达对家乡的思念,或表达对亲人的牵挂),多为月亮、鸿雁、莼鲈、鲈脍、双鲤等;愁苦类意象(或表达忧愁悲伤心情,或渲染凄冷悲凉气氛),多为梧桐、芭蕉、流水、猿猴、杜鹃等。古代诗人常用这些意象来书写属于情感范畴的一大类型——“乡愁”。作为传统时代的诗人,王友亮在诗歌中非常熟悉灵活地使用这些意象,而且还采用许多意象之外的词汇典故,来创作思乡怀乡类主题的诗歌。
与空间景观直接相关的地名意象,频繁入诗。比如,广义的江南和江宁地名大量入诗。王友亮诗歌创作大量使用了与江南、江宁、秦淮、金陵有关的地名,这些地名平时也大量出现在古代各种文学作品里。王友亮使用最多且与广义的“江南”有关的词语包括:江南(江南路、江南岸)、江楼、江上、江乡、江干、江滨、江皋、江隈等。这些词语既指广义的“江南”,更直接指代诗人王友亮自己居住在长江边上新河的居所,也就是自己出生、成长的小地方。与江宁直接相关的词汇(地名)则更多,包括:白下、白门、莫愁湖、金陵、秣陵、毗陵、秦淮、三山、二水、白鹭洲、六朝、六朝山等。这些词语频繁入诗,与广义的“江南”一样,都是第二故乡“江宁”的代称。
江南和江宁的风物特产及其意象,频繁入诗。江南水乡所出产的风物与特产,具有江南的特色。这些风物特产,有些经过历代诗人反复传诵,已经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南方“故乡”的代名词。比如,古代诗歌里面最能代表“江南乡愁”的词语“莼鲈”,这个词在王友亮的诗歌作品里也多次出现,总共使用四次。
王友亮1772年在京师创作一首《腹疾戏作》:“归心托莼鲈,行矣勿复累。”本年度中秋之后,诗人身体多病又频繁搬家,作诗也多为生病主题(《双佩斋诗集》卷四《腹疾戏作》)。当年深秋,诗人再次移居,侨寓香炉营头条胡同,在与婺源同乡、诗人俞凤的唱和诗中称:“飘零我亦惜秋残,赖有深杯取次干。已逝年华弹指易,未来事业称心难。徙居两处仍为客,卧病兼旬可罢官。揽镜不须嘲饭颗,天生骨相本多寒。注:时移寓香炉营头条胡同。徙居两处仍为客(时移寓香炉营头条胡同),卧病兼旬可罢官。”(《双佩斋诗集》卷四《秋日书怀次桐屿韵》二首之一)。可知王友亮此前已患病十余天。《腹疾戏作》在《双佩斋诗集》里面的编排次序仅次于《秋日书怀次桐屿韵》,可见应为差不多同时创作的作品。当年的正月初十日,王友亮正式离开江宁的家,踏上赴京师参加会试的旅途,不意考试失败,此时又频繁移居、卧病兼旬,也就难免生发出“飘零”之感慨,“年华”之叹逝,“为客”之感伤,以及“莼鲈”之归心。俞凤是王友亮的婺源同乡,同样侨寓金陵上新河,自然也完全能够洞察王友亮的这种“故乡”之思。早在1760年,王友亮族侄、婺源西清源人王佩兰曾经外出谋生路过江宁上新河,俞凤曾招饮于自建河亭,王佩兰有诗记之(王佩兰:《松翠小菟裘诗集》卷四《谋粮集·七夕饮集俞会冈河亭》),这些徽州故乡的老友们,早就心有灵犀一点通。
1773年闰三月,在京师为诗友兼同事张亦栻所藏的《水带山庄图》题诗,全诗如下:“一溪如环门外流,一峰如笏门前浮。开门水声在桥下,闭门山色来墙头。是名水带庄,景与图画侔。两边列乔木,四面开平畴。风胜闻叱犊,雨堤杨柳占鸣鸠。先生居其中,诗酒为朋俦。陆有舆,水有舟,乐哉何减万户侯。一朝舍之成远游,溪山如此挽不留。薇花照眼红七度,颇忆某水及某邱。柳东居士醉落墨,尺幅为写乡关秋。不知草堂前,松菊无恙不?莼鲈尚使季鹰恋,况复庐舍饶清幽。知君此举有深意,遂初早办他年谋。我亦因之忆三径,归心浩荡随江鸥(柳东居士,家舍人宸自号)。”(《双佩斋诗集》卷四《题方壶〈水带山庄图〉》)根据这首诗的诗末小注,可知这幅图是当时著名书画家王宸所作,王友亮在这首诗里已经对整个画面做了详尽描述。最值得注意的是,观看了这幅画竟引发了诗人浓浓的“乡愁”,而此时王友亮尚未完全旅居京师,还常年在京师和江宁之间往返奔波。
1775年春,王友亮参加了当年会试,再次落榜。落榜后,即将怅然返回江宁,挚友张埙送至卢沟桥外,王友亮作诗赠别张埙:“画角三吹又夕阳,真成携手上河梁。同心小别如天远,失意先归觉路长。万事已输鸥最乐,一春都作燕空忙。何时奉母吴中去,占断莼鲈作醉乡。”(《双佩斋诗集》卷五《瘦桐送余至卢沟桥赋别》)全诗充满了科举失意的惆怅悲伤。因为失意,更需要自我安慰、自我解嘲,要学闲鸥那般悠闲快乐地飞翔,即便是借酒消愁之时也会时刻惦念着自己远在“吴中”的“故乡”。
1784年,婺源同乡、王友亮诗弟子胡永焕参加当年的会试,落第,即将南返江宁,王友亮作诗赠别:“溪山佳处我深知,好去三年且下帷。涤研晴看鱼跃水,掩书夜听鸟啼枝。料来仙境能如此,况复天伦乐在斯。遥望归人真羡煞,莼鲈空费卷中诗。”(《双佩斋诗集》卷六《送奎若南归即次其留别韵末章兼送戴、董诸公》四首之二)在这首诗里,王友亮一面安慰胡永焕不要因为考试失利而伤心,毕竟还有“溪山佳处”在呼唤等待着胡永焕回去涤研翻书、享受天伦之乐;另一面却对胡永焕能够洒脱返乡而倍感羡慕嫉妒,对自己长期旅居京师而不得返乡感到遗憾,只能把对家乡的思念都放到“卷中诗”里面去。撇除强作诗意、“为赋新词强说愁”的诗人习性,王友亮此时已经旅居京师长达五年之久而未曾返回江宁,其“乡愁”情绪应为真实真挚。
类似“莼鲈”这样的风物特产,在王友亮的诗歌里比比皆是,随处可见。这些原本具象化的物象,一旦诗人落笔,就成为抽象化的意象,也就是“故乡”的代名词。包括鲥、瓶鱼(鲳鱼)、白鹭、篱笋、菰蒲、蓼花、芦花(芦花滩)、藕花、汀蒹、黄花乌桕等,在王友亮的诗歌里出现频率都相当高。此外,王友亮诗歌还多次使用具有江南水乡特色,描绘江南水乡环境、工具、生产作业和生产作业地点活动的词语,比如渔汀、渔蓑、鱼竿、鸥波、白波、钓矶、钓徒、溪山、烟雨、扁舟、短棹、下濑船、风帆、轻帆等。还大量使用小隐、旧隐、醉乡、浮云等词语,最终目的表达的是自己的思乡怀乡和归乡归隐之情。
常见的文学典故、典源,频繁入诗。王友亮诗歌作品也有许多常见的文学典故、典源,其诗歌作品常用的“思乡怀乡”主题意象和词汇,本身不少都是文学典故或者化用文学典故的词语。比如,与“忘机鸥”有关的白鸥、鸥鸟、双鸥、闲鸥、鸥鹭;与“阿戎”有关的兄弟、昆弟、三兄、伯兄;与“双鲤”有关的家书、乡书、双鱼、寒信、雁信、鸿雁、哀雁等。兹仅举一例说明。王友亮诗歌作品多有“鸥鸟”意象,但在人生的不同时期,同一个“鸥鸟”却有着不同的内涵。王友亮青年时期诗歌作品中的“鸥鸟”,大多是取其闲适、悠闲之意,比如1757年创作七律《晚晴》首二联称:“北窗浴罢葛衣轻,旋向江头踏晚晴。得意鸟知迎客语,忘机鸥解趁人行。”(《双佩斋诗集》卷一《晚晴》)一副长江边散步、怡然自得的青少年形象跃然纸上。1757年创作七律《江亭》:“踏遍苹洲与竹汀,晚来小憩有孤亭。月痕到水浮沉白,云气分山断续青。鸥自忘机来渺渺,鸿知避戈去冥冥。支颐高咏何人识,惭愧归樵驻足听。”(《双佩斋诗集》卷一《江亭》)长江之滨,孤亭屹立,黄昏月华初上、沙鸥翔集,水天一色,青年诗人借着迷蒙的夜色大声朗诵诗作,何等惬意。1771年创作四首七律赠予袁枚,其中第二首云:“北山小筑傍烟霞,廿载投闲鬓未华。海岳奇情惟拜石,河阳余事到栽花。忘机只许鸥同狎,避俗还将鹤共夸。留得甘棠舆诵在,野人争识使君家。”(《双佩斋诗集》卷三《谢袁存斋太史》四首之二)将袁枚筑小仓山随园,留连山水之间那种闲情雅致描绘得淋漓尽致。这几首诗,都直接使用《忘机鸥》这个源典,用于描写诗人对于那种超脱尘俗、忘身物外、倾心山水的田园隐逸生活的羡慕和向往。及至1769年王友亮开始任职内阁中书、开始相对较长时间旅居京师之后,白鸥、闲鸥、鸥鹭、双鸥等典源词语,依然频繁入诗,但此时用典,诗人更多的是在离开“故乡”之后,把江宁“故乡”常见的鸥鸟、白鹭等水鸟用来作为思乡怀乡的隐喻,作为叙述“乡愁”的衬托,把思乡怀乡的情感与对田园隐逸生活的追求向往,通过追寻“他乡”与“故乡”的融合脉络,进而实现将人生际遇、人生理想与“乡愁”回归的深度融合。比如,1791年夏夜不眠,作诗记事:“不觉追凉久,楼头鼓四挝。鸥波劳远梦,萤火恋贫家。移石聊支枕,敲冰可代茶。妙香来乙乙,知是手栽花。”(《双佩斋诗集》卷七《廿一夜即事》)在这首诗里,“鸥波”原指鸥鸟生活的水面,比喻悠闲自在的退隐生活,但此时王友亮已经旅居京师长达十三年之久,远在江南的“鸥波”已经不可触摸,故而唯有在酷暑的京师之夜,闹中取静,在心底里留存着对“故乡”的那场“远梦”,努力追寻那份带有茶香、花香的清凉与清静。
“客”与“归”的矛盾对立与折中统一:最忆还是“故乡”
不论是从江宁赴京师的旅途中,还是旅居京师长期为官之时,王友亮的心中总是充满了“客”与“归”的矛盾对立与折中统一。矛盾对立的是:旅途是苦、旅居是苦,而归途是乐、到家是乐;折中统一的是:理想必须让位于现实,“旅”与“食”在王友亮的“地方”书写里面完全可以并列使用。
诗人王友亮对思乡类主题创作所能选用词语的灵活运用,简直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笔者认真整理了王友亮《双佩斋诗集》关于“客”这个词语的运用情况,发现数量非常多,诗人常用与“客”有关的名词,包括客中、客过、客程、客棹、客舟、客路、客心、客愁,也有远客、病客、倦客、孤客、独客、久客、逸客等。动词则有作客、做客、为客、客过、客到等。可矛盾的是,诗人不管身处何方、客处何地,总不时回望着江宁这个“第二故乡”,时时刻刻充满了归意,因此与“客”相反的另一个字——“归”,有关“归”的词语大量入诗。常用与“归”有关的名词,包括归去、归思、归梦、归计、归心、归志、归舟、归帆、归兴、归期、归人、归燕、归巢、归鞍、归鞯、归路、归途等。动词则有东归、南归、先归、思归、遄归、伴归、成归、归来、归耕、归种、归田等。
行走与书写是诗人最重要的任务,在不断的行走中,“客”与“归”经由诗歌创作而形成了感人的人生体验、诗歌体验,有时候这种体验足以震撼人心。最典型的是“诗圣”杜甫在颠沛流离的行走中所创作的传世诗作。宋代朱弁的《风月堂诗话》卷上引“东坡云:‘老杜自秦州赴成都,所历辄作一诗,数千里山川在人目中,古今诗人殆无可拟者。’”李因笃《杜诗镜铨》卷七引“李子德云:‘万里之行役,山川之夷险,岁月之暄凉,交游之违合,靡不由尽,其诗史也。’”对于王友亮而言,“客”是行走,“归”可以书写,两者皆可入诗、皆可成诗。王友亮最喜欢用的几个典故,包括文潞公的“归意”,王友亮曾经多次集中表达了自己对“归”的理解:“文潞公致仕于洛,为耆英之会;韩魏公归荣于相,以昼锦名堂,志何尝专在归也。今先生奉恩命归里,可以归矣。”[王友亮跋《香亭先生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108册《香亭先生(吴玉纶)年谱一卷续编一卷》]又比如:“文潞公闲居洛下,同甲是征。”(王友亮《奉政大夫培翁张老先生暨德配洪宜人八旬双寿诗启》,道光《甲道张氏宗谱》卷五十九)无疑,在诗人王友亮看来,“客”是起点,“归”才是终点;“客”是手段,唯有“归”才是目的。关于这一点,最典型的阐释莫过于诗人自己留给我们的佳句:“我家远住楚江边,旅食京华偶然耳。”(《双佩斋诗集》卷二《留别诸同门》二首之一)最终,通过对地方“乡愁”的书写,诗人在内心世界里真正实现了“客”与“归”的对立统一与平和折中。
作者单位:上海自贸区陆家嘴管理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