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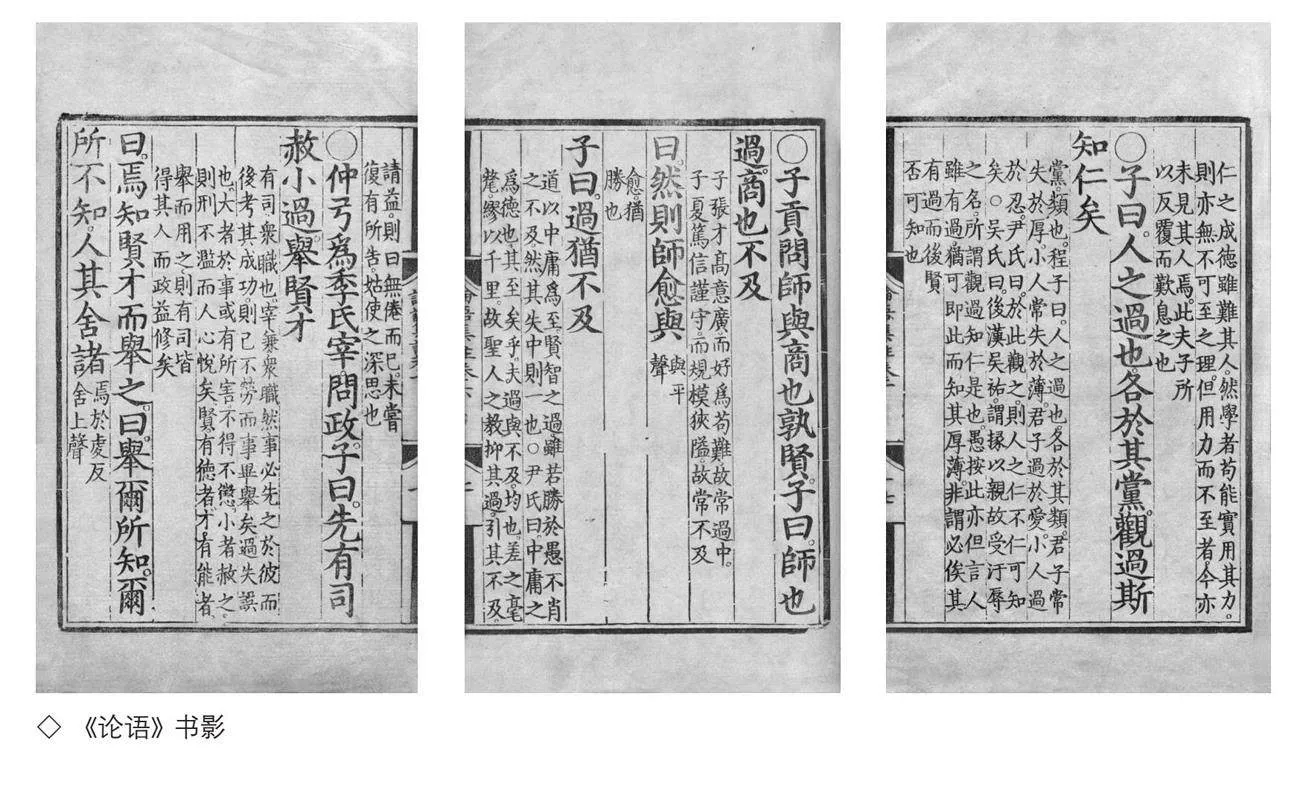
“过”的思想表达散见于《论语·里仁》《论语·卫灵公》《论语·述而》《论语·先进》等不同篇目中,其中有一些重要表述,譬如“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师也过,商也不及”“过犹不及”“不迁怒,不贰过”等,以“过”作为诠解《论语》的门径是合适的。本文通过辨析“过”和“中庸”“正”的关系,有助于重新理解“中庸”“中行”等重要概念。
“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过则勿惮改”
君子以礼持身,而有威重之质,此质表现在外则行事有威仪。同时,君子的“礼以行之”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时间、地点、场合的变化有相应调整。对礼之调适而得行之中的机制,来自“学而时习之”之“学”,也来自孔子在太庙的“每事问”之“问”。学所以行礼而不滞固,可中道而行,避免出现“过”或“不及”的失礼情况。孔安国释“固”为“敝也”,刑释“学则不固”为“又当学先王之道,博闻强识,则不固蔽也”,个体通过学习、体会先王的道,就能渐次厚重持其身,所谓以礼立身,通过具体行事而得时措之宜,没有固蔽之“过”。个体在“为学之说”与“礼以行之”两者间保持动态平衡,便等同于改过的过程。可见,个体通过学习礼,可以有效避免行为的固蔽之“过”。
个体通过为己之学,而使其忠信之质和礼仪讲求相得益彰。长此以往,养成手足有所措的威仪气象,便可以“正己”,可以是“过则勿惮改” (《论语·学而》)。
相反,个人若不能及时改过,则有其相应的后果与危害。张认为“饱食终日,无所用心,则放越而莫知其极,凡恶之所由生也”,个人放任自身之“过”的继续发展,至于无可挽回,则其超越了人本应走的居仁由义之大道,这样做使得自己与善道相隔绝,容易为恶。个体之行事脱离人道,趋向小人之“下达”,这样不仅戕害本有之仁德,而且可能将自己不想有的事强加于人。总之,个人不及时改过,导致出现“过越”的悖理行径,甚至会由“过”发展为恶。
个人要避免出现“过越”的言行,须通过着力地做修身工夫,摆脱“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论语·阳货》)的平庸状态。个人总有完善之处,“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论语·子罕》)“改过”对中等材质的人尤其可行。中人努力做修养仁德的工夫,从而不断日新其性,破除陋习,复归正道。
恕与“赦小过”
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
孔子答仲弓问为政,是有关从政者如何可以“正人”的问题。仲弓任家宰的职位,负责大夫家内的事务。在孔子的回答中,既区分了施政的先后次序,又具体说明举用贤才的道理。“先有司”,“先任有司者治其事”,仲弓总揽大夫之家事,具体执行和处理由专人负责。如此,“先有司”表示基本的制度保障,避免尸位素餐。“赦小过”体现了施政有宽的精神,然而施政之缓急的恰好,以仲弓的推己及人为基础,基于恕道,仲弓对那些专有职事者不当求其备。
对于“赦小过”,“过,失误也。大者于事或有所害,不得不惩;小者赦之,则刑罚不滥而人心悦矣”。朱子将“小过”作“失误”解,区分比较了“过”之大和“过”之小的不同影响。对妨害季大夫家事的“过”之大者,应当惩治。小过是小失误。况且,它不是个人有意要为之,通常是无心之失。对此,仲弓作为家宰,要体谅相关办事人员,给人以重新改过的机会。如果不放过,而惩罚或苛责于他,他只会谨小慎微做事,只求不出差错。苏轼指出“赦小过”对选用人才的积极意义。“然当赦其小过,则贤才可得而举也。惟庸人与奸人为无小过……若小过不赦,则贤者避罪不暇,而此等人出矣。”普通人难免有小过,苏轼认为无小过者通常也没有成就或是善于掩饰。“赦小过”要求为政有宽,伯禽被封于鲁地,周公训诫他:“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于一人。”(《论语·微子》)
为政者的宽厚可以带动臣民进行自我激励和反省,同时要继续任用以前的大臣,除作恶为逆者。在任用人才方面,不可因小失大,首先施政者不当过分苛求下属。上述训诫和孔子对仲弓的回答是相一致的。孔子期许仲弓在家宰的职位上,可以像大人君子一般,不过分苛求相关办事人员。“赦小过”既是为政者自身的修养,同时亦是为政之解决办法。
儒家一贯讲求恕道,它落实在个人修养上,表现为推己及人、自然及物。原宪以所得的俸禄,满足自家人以外,周济贫乏的邻里,这就是自然及物、与人宽厚的体现。个体修身成德,可以自然及物,从事政治活动同样也离不开恕道的修养,如此在施政方面会有宽惠的措施,从而“宽则得众”(《论语·阳货》)。为政者之“宽”也表现为注重上行下效的政治现实,取得民众相安的理想之治。当然,宽是有一定限度的,发生讼狱之事,听讼者要能不偏不倚,宽严适度,有和美之道,坚持法度与人情相统一。可以说,无论是宽人之过的行为主体,还是因人之宽而悔过自新的一方,其中存在德行的相互回馈。
值得注意的是,本节所论恕与“赦小过”,明显指向别人,适用于行为主体的交往,是“正人”的重要方面。自我纠偏以“正己”,正好与恕、“赦小过”存在一定的反差,从中可以看出儒学教化的重要特征。简言之,《论语》倡导对他人之过以“宽”为重,对己之过则近乎“苛刻”,所谓“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事实上,个人通过收敛身心,以此保持对时间流逝的敏锐感,从中反省领会自我改过的时机,假以时日,待人接物容易合于度,尽己之性而能尽人之性。当自身能够改正之时,会比较宽容地看待别人之“过”。
对他人之“过”,如果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则没有理由责备他。但更多的却是,人之有“过”很能反映个体性情,仅以此具体的、特别的、存在偶然性的“过”,一般也不足以断定其整个人就有问题。因此,《论语》指出与人宽厚、待人以恕这点是对人之“过”应有的,同样也是很合适的态度,《论语》更进一步指出,即使对不仁者也不当过于鄙弃,过于鄙弃有悖于“正人”之道,鄙弃不仁之人不如指出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通过率先垂范来影响不仁者。人与我都是有“过”的,反观自身在有过时的反应和处理,论人之“过”亦然,所以过分苛求别人有时也是不当的。而在生活中,过分苛责别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如此就不会真正做到平凡而伟大。自我改过是优先于注意到他人之“过”的,这除非是“据于德,依于仁”(《论语·述而》)者所不能为。通过为学工夫涵养德行,并不断培养“知人”的能力和关切,避免“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庄子·人间世》),有知见而仁德有未尽,非是《论语》论“知”之意。称人之善,恕人之过失,这是修身及处世的长久之法,展示了基于恕道对个体生命和价值的尊重,社会对无意的、无关紧要的过失可以更加宽容。“大夫何罪,吾不以一眚而掩大德”(《左传·僖公三十三年》),秦穆公对待秦国的将领,秉持了赦过不掩功的“恕”,如此促成治秦之道。
“过犹不及”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
在孔子所说的“师也过”与“商也不及”中,更加体现了“过”的丰富内涵。“师也过”之“过”是对贤德的某种偏离,而偏离的具体内容,我们通过曾参评价子张“堂堂乎张也,难与为仁矣”(《论语·子张》)可知子张有“堂堂”之过,这点会对仁德有破坏,相比之下,子夏行事经常不及而止,孔子不但指出二人之过的特殊与不同,而且由此差异指出一致之处,即对“中”的偏离相一致,所以是“过犹不及”。这种“多”而知“一”的思维方式,换言之,从不同的现象中洞见差异所包含的一致性。而“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同样蕴含这种思维方式,各种“过”的形态虽彼此不同,但都关联着“党”,且不论“党”的具体内涵,我们却可观取不同的过,能够通达具有共同性、普遍意义的“仁”。
观过而知仁
二程所言“君子常失于厚,小人常失于薄;君子过于爱,小人过于忍”,虽然君子与小人其情感的表达有不中节处,不能很好地以礼节情,与“正”相符,但是,有“过”则至少人我相感通的情实仍然存在,个体以此情实而行为,便能够“为仁由己”“以友辅仁”。这种不足意味着有“过”之人其内心是具有慈爱之心或是克制之意,只不过这不经礼之文修饰作用的慈爱心或单纯地忍受,它不完全符合孔子的论“仁”之意。
子曰:“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论语·里仁》)
在历史上对此句有诸多不同注说,这里的“过”主要作过失解,既是过失,便不是仁,“过”的具体内涵表达为“各于其党”。
在各有差异性、不同个体之“过”的背后,相同的是由不仁而来的过失,观此不仁之失,可以推知有此一失之个体,其为仁的方向何在。这种“观过知仁”的理解进路类似于二程解释“巧言令色,鲜矣仁”(《论语·学而》),讲“知巧言令色之非仁,则知仁矣”,通过察知非仁现象的情形、表现,如何可以是“仁”,就清楚了。“观过知仁”侧重提出以何方式来对待他人之“过”,其中“仁”代表有过者所以行仁的“正道”,意味着为仁的具体方向。对“观过,斯知仁矣”,本文倾向于傅佩荣所言“因此察看一个人的过错,就知道他的人生正途何在”。总之,本句是《论语》全文论“过”的重要关节处,对本句的分析能够比较全面地揭示和回答《论语》如何面对和处理“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论语·微子》)的问题。
结 语
《论语》对“过”的讨论,主线是“责己之过而改之,观人之过而宽之”,从中看出儒家“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论语·卫灵公》)的价值取向,反映了儒家一贯的忠恕之道。
“人之过也,各于其党。观过,斯知仁矣”,凸显了“过”的积极价值,“过”之形成与产生包含自身与发生之客观两个方面。借助《易》之随卦有助于全面丰富地认识“过”,“上居随极,固为太过,然在得民之随,与随善之固,如此乃为善也,施于他则过矣”。为政者虽处于随之极的大过,但因为“得民”,并且取善为法,犹有可观可取处。所以为“过”,或是“得民”存在问题,或是个人不能“择善而固执之”。“过”偏离中庸虽然不足为法,但是可以“观”之。朱子论“观”之意,其曰“比视为详”,所谓“观其所由”(《论语·为政》),追根溯源察见事物之情实。既如此便是经由“过”的表面消极价值,抵达人的内在主观,从而判别其人是否忠信之不足或有余,抑或偏重仁还是偏重义等,如此符合《论语》论“人”所持的宽厚之意。
作者单位:河北省委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