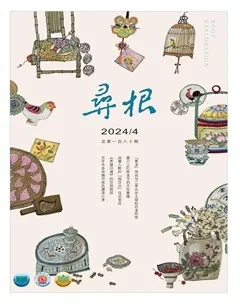民国女理发师与女子理发业
“头发”在近现代中国内蕴深刻的政治意涵与社会功能。辛亥以降,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剪发令,掀起自上而下的男子剪辫风潮。受其影响,部分女学生起而响应,率先剪去头发,但此举反遭学校及地方政府抵制,这与民国当局始终力倡废禁缠足形成鲜明对比。“五四”前后,女子剪发问题重又为舆论所重,“女子自决”口号的提出及国民革命的推进终使女子剪发运动势不可遏。
女理发师的出现与女理发店的兴起
学界通常认为,中国倡导女性剪发的第一人是《女界钟》作者金一(金天翮)。金氏在《女界钟》第3节“女子的品性”中主张:“今西方志士,知识进化,截发以求卫生,吾以为女子进化,亦当(自)求截发始。”但何者为近代中国第一位女理发师,学界则尚无定论。女学生群体是民国初年开展剪发实践的主力军,1912年湖南衡粹女校某生便组织“女子剪发会”,但女学生仅是互相为对方简单剪去辫子抑或发簪,并不可能在未接受训练的前提下摇身一变成为理发师。至20世纪20年代,女子剪发的热度较之民国初期甚至显露出退潮的倾向,“到了近来,非但实行不见增加,连讨论和研究的笔墨都不见了”。女子剪发未如男子剪发般形成潮流,时人将其归结为“怯于进取旧俗”。具体而言,家庭学校的阻挠、社会层面的非议及外国并无女子剪发先例均可能是让女子对剪发望而却步的动因。然而,剪发可能减损容颜美观或许才是女性不愿尝试“削去青丝”的首要理由。舆论界对女子“剪发”的讨论往往只停留于其是否有益,恰恰忽视了头发长度及发型发式等实践层面的问题。换言之,在当时并没有多少人清楚应如何为女子剪发,“初剪发时,都不知该梳什么发式好,连理发店的师傅也很感为难,因从来没有设计过妇女的短发,故只好拣个现成,按当时最流行的男发样式来剪理了”。套用为男子剪发的成法,成品自然可想而知。
有鉴于此,很难相信20世纪20年代末期女理发师的出现是女子剪发需求旺盛所致。由于男子剪发更为普及,理发店管理者雇佣女理发师,很大程度上与其希望利用女理发师这一噱头招徕男性顾客有关。1918年,上海一理发店始起用女理发师,这是迄今为止最早见于近代报刊的记载:
大新街某理发店主为扩充营业起见,异想天开,特用中国年轻妇女八人司理发之职,妇女已于去年冬间练习,至今其剪发修面而及挖耳拷背等皆与男子无异,各种化妆品应有尽有,并有某烟供奉,招待周到……其开幕期约在阴历八月,初想届时一般登徒子定必欢迎,是亦一种别开生面之新营业也。
1920年,北京一理发店也聘用女理发师:
北京孙公园锡金会馆附近春记理发店内近有一少妇在内做理发师,为人理发。此妇年约十八九,妖冶可鄙。好奇者莫不趋之若鹜,大有门庭如市概云云。
显然,风姿绰约的女理发师的确对“好奇者”及“登徒子”有强大的吸引力。女理发师为男子理发,无形中打破了长期横亘于民间的“男女之大防”,男性欣然往之,理发店的生意也水涨船高。但必须注意的是,男女隔离仍是北洋政府调适两性交往规范的道德准则。
在作为职业的女理发师出现后,坊间开始呼唤专为女子服务的理发女技师及理发场所。有论者直言,女性剪发难成气候的最大阻力在于熟练女理发师的数量严重不足,“自己剪头是剪不成了,同性的梳头妈是不会的,男性的理发匠吗?以中国没智识的男性轻蔑女性的恶习的结果,是万万做不到的事。所以就感觉得很是不便,阻碍了剪发的勇气。因此我觉得于提倡女子剪发的时候,同时要提倡女性剪发匠的职业问题”。同时亦有人力陈开办以女子为主要消费对象的理发馆的益处。一批支持剪发的女学生乘此东风,在“女子自决”口号的鼓舞下开始筹建女理发馆。1922年,长沙柑子园口吉庆街理发馆正式开业,理发师皆为女学生,且技艺相当娴熟,“对于女子之新式头簪,如东洋头、麻花头、麻姑头、燕尾巴头、辫子盘龙头,形形式式,修饰适宜,手术精良”。此外,她们亦能为男子剪发,但并不提供为男子捶背、捏腿等服务。这与由剃头铺转设而成的理发店划清了界限,亦清晰地反映理发店偏重女性剪发的定位与女权意识的初步觉醒。
在利益与社会诉求的驱使下,华北地区的女理发店亦开始冒头。北京理发工人徐省三与其妻子王氏鉴于北京无女子理发处,申请创设一处西式理发馆,但却被警厅以有伤风化为由一口回绝,“以该商场系公共游览处所,若以男子与妇女理发,殊与观瞻不雅,遂批驳不准成立”。徐省三的努力无疾而终,此后二三年间,北京城内迟迟未有女子理发店。1925年,女士党雅兰遂拟筹资花费重金从上海聘请理发女技师,设立北京文明女子理发所。北京女子理发店开设举步维艰,与京津冀及东三省一带警厅的高压态度难脱干系。1926年,直隶保安总司令兼省长褚玉璞颁布《天津禁止剪发布告》,明令“凡属妇女,一律不准剪发”以“维持风化”;同年,奉天省长公署亦发布训令,称“若不一并从严禁止,实不足以敦风化而正人心”,可见传统两性伦理道德的残余依旧挥之不去。
较之于北京,由于沪上女性多视剪短发为时尚,且上海较早受到国民革命波及,置办女子理发营业场所面临的困难要小得多。孙传芳盘踞上海时,据传上海对女子剪发严加管控,“在他的势力范围内,只要男子是学生装或穿西服,女子剪发者,均视为间谍,随便拘捕监禁枪毙”,其间理发店只能夹缝求生,惨淡经营。1927年初,孙主力土崩瓦解,国民革命军进军上海及南京,孙传芳先前针对女子剪发颁布的禁令便形同虚设,“革命军兴以来,勃然而起者,厥唯女子剪发一事。其来也似潮,沛然莫能御”。继龙泉女子浴室另辟一女子修发所后,1927年7月16日,上海女青年会开办女子理发所,所内理发师皆为曾接受女青年会培训的女子。7月27日,国民党江苏省党部特别委员会妇女运动部部长廖世劭颁布女子剪发令,女子剪发潮更一发不可收。
有论者认为,时人的性别隔离主张是民国女子理发场所的出发点,未免有将这一现象发生发展的前因后果简单化之嫌。一乐也、新新、华新等老牌男士理发店均已在1926年末或1927年开始为女子剪发,“沪上自女子盛倡剪发后,各大理发店,如一乐也、万国、东亚、两新、升新发、华洋、华新、成记等,莫不女宾满座,应接不暇”。说明善于捕捉风向的投资者无法对庞大的女性剪发群体坐视不管。“男女授受不亲”的羁绊在利润面前显得微不足道,暴露了社会基层与地方政府在处理两性关系态度上的殊异与分层。部分女子亦已卸下心中的堤防,“男女同剪”成为既成事实。然而,大部分女性仍难以接受到男士理发师主导的中国理发店剪发,时人观察到,“有许多剪发女子,他们都上外国理发店去,我去了几次,东亚、一乐也等处,没有碰到一个女子”。由于长期的伦理道德规训,传统女性不得不仰仗于梳头婆在内闭环境内整饬容貌。尽管梳头婆因现代理发业冲击而走向没落,但其影响却很难转瞬即逝。应当说,专事女子理发业务的理发店是这一时期女性消费心理所促成的特定消费需求的产物,是女性理发惯性的自然逻辑延伸,与所谓背离“女子剪发倡议之初的解放内涵”无涉。
女光公司始末
1927年末,女光公司在上海宣告成立。在女光之前,沪上尚无系统的女子理发培训机构,女性理发师资质芜杂,理发水平难有保证。作为女子理发培训的先行者,女光公司为近代上海女子理发业乃至全国女子剪发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女光公司的宗旨在于振兴女性就业,“在消极方面说,男子去代女子理发,还不如女子自代女子理发的适宜。在积极方面说,男子去代女子理发,女子何独不可代男子理发。我们本此宗旨,向前进攻,做一个改革事业的先导”。为此,女光公司主要经营两项业务:一是创办女子理发专科学校,二是经营女子理发店。颇为值得注意的是,女光公司发起者均为女界精英,拥有政界背景。各界名流亦鼎力支持女光公司,胡适、刘文岛、徐志摩等人皆为女光公司赞助背书。此外,女光公司亦有较为宏伟的扩张愿景:“不单在上海一埠,而且要推广到国内各大商埠,使得女子在职业界中,站一个相当的地位。”
在女光公司的构想中,女子理发专科学校与女子理发店是联系紧密的整体。从专科学校毕业的女学生,便将上岗执业,成为女光公司女理发师团队中的一分子。正因如此,女子理发专科学校仅招募20人,人数相当有限。但报名者的积极性则令女光公司猝不及防,由是不得不增设学额10人。为保证教学品质,女光公司花费重金聘请法国理发匠授课。或许是出于节省经费与急于开业,女子理发专科学校具有鲜明的速成特质,学生在2个月内便须修习完理发术、卫生学、化装术、社会心理、商店组织管理、商业簿记、美术、外国语等课程。12月22日,第一届学生毕业。随后,女光公司便紧锣密鼓地筹备理发店开业事宜并大肆宣传,“分送各界赠券,欢迎仕女到公司理发,不收费用”。
1928年1月1日,女光公司理发店开业,时人对其极尽溢美之词,称之为“中国用女子理发师之开创者”。因理发价格优惠,不少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前往女光公司体验,并对女理发师们的手艺赞誉有加:
女剪发员,一例着白色制服,上绣红色女光公司中西文名。……为余修建者,其年事二十以内,手术至敏妙,殊不弱于男子,惟身材略短,微嫌椅高……甚钦折主人之善选择,剪发虽小道,亦必其人性性情温婉,心思灵巧,成绩斯佳。女光诸人,则都温婉灵巧……彼即戴一口具,状如漏斗,人言先施等大理发所皆有之。
诸多女技师初不因主顾多而草率从事。
以上反馈皆出自男客,当中不乏具有凝视与窥探色彩的描写。令人遗憾的是,从所见史料中,无从得知女性顾客在女光公司理发时的真实感受与女客的占比情况。但可以肯定的是,女光公司生意一派欣欣向荣,“开幕以来,营业发达,内部设备精究,女职员艺术高尚,且招待周到。最近分送学界优待券,照价八折,故前往修发者,成争先恐后云”。
但出人意料的是,女光公司理发所不到半年便闭店歇业。对其短命而亡的原因,时人概括为以下五点:选址偏僻,价格过高,技术平常,工资开支过大及同业竞争激烈。这些说法可能不无道理,但至少在“技术平常”这一条上,未免与其他顾客的评价产生抵牾。事实上,女光公司无法坚持营业的最大原因在于无人主事。1928年春,女光公司发起人之一郑毓秀远渡法国留学,而廖世劭则因积劳成疾于上海病逝。群龙无首,女光公司理发所自然无法继续勉力支撑。上海女理发室格局也随之大变,天香女子理发社、美容女子理发馆与神仙理发室呈三足鼎立之势。值得玩味的是,三家理发店都不约而同争抢“女光出品”的女理发师,如美容女子理发馆“鉴于女子理发室技能精巧,特多方设法聘到女光第一届及第二届最优等毕业女技师十二人,特多方设法聘女光第一届及第二届最优等毕业女技师十二人”;神仙理发室“所有职员,亦俱改用女子,都系女光第一届之毕业生,手艺无不纯熟”。这无疑从另一个侧面再次证明:女光公司的解体无法完全归咎于女性理发师的职业素质不足。
尽管女光公司未长成女子理发业的常青树,但它所开创的女子理发培训事业却并未就此止步。女光公司女子理发专科学校前两届学生如期毕业后,教导主任沈叔夏“以是项新事业,有提倡之必要”,自任校长继续开设上海女子理发专科学校。每期招生人数介于十五人至三十人,学生学时通常为三个月,毕业后学校将代为介绍工作,优秀毕业生可赴国华等上海本地大理发店就职。1929年,沈叔夏更主导创办具有消费合作社性质的第一女子理发社,为学员提供实习机会。截至1932年,该校已累计招募十六届学生,毕业学生逾三百人。同年,上海女子理发专科学校更名为上海女子理发传习所,并免除学生一切学费,“于国难期中,免费招生(学费全免),凡失业妇女有志此项职业者,尽兴乎来”。而后,沈叔夏尝试在南京新设女子理发学校,但由于授课教师为男性,前来报名上课者门可罗雀,上海女子理发专科学校招生也早已陷入瓶颈,“萧条冷落,惨淡异常,以视当年门庭若市,不胜今昔之戚也”。1935年,上海女子理发传习所停止招生,喧嚣多年的女子理发培训事业无奈就此沉寂。
概言之,女光公司的发展历程是近代女子理发事业前进轨迹的一个缩影:女光公司“朝生夕死”,似如近代女理发师事业起初轰轰烈烈,随后却愈发停滞不前,渐露败相;学校管制与培养使女理发师进一步迈向现代化与职业化,但女理发师的择业之路却仍布满坎坷。除此之外,是何因素推动女性投身女理发师行业仍不甚明朗。
女理发师的出身与境遇
蒋美华指出,近代以来,妇女就业观念不断强化,就业队伍不断扩大,就业领域不断拓展;但妇女就业人数与全国妇女相比只占很小比例,妇女在同行业中与男子相比微不足道,且就业妇女受教育程度较低,整体素质一般。总体而言,女理发师亦概莫能外。但其亦有显著的特殊性:在这个基数不大的团体中,既有热心于女子运动的进步人士,也有因生活所迫被迫转行的困窘生民。清代以来,民间多视剪发为贱业,但为习得一门剪发手艺,多数女理发师不得不付出高额代价;为谋得稳定工作,她们中的某些人甚至需要远走他乡。
在民国报刊中,绝大多数以女理发师为主体的评论皆出自他者视角,极少见到女理发师为这份职业现身说法,而周凌敏恰恰是一个特例。周凌敏曾任女光公司及神仙理发室理发技师,曾多次刊文表白一名女理发师的心迹。如谈到为人理发的困难时,她坦承她将两类顾客视为畏途:一是身材魁梧者,“普通理发的时间,起码总要半个钟头,我踮起两只脚尖,伸高一双手,在他头上理发,要这许多辰光,真是吃力非常”;二是外国人,“外国人的胡须,比较上来得多而且硬……恐怕剃开他的面皮”。谈到本国理发师的弊端时,周凌敏则痛心地指出:“外国理发室的布置注重于清洁简单,我国人则偏偏要繁复华丽,所以新开的理发室,都要花整千元钱去考究装潢。这种浪费,实在是毫无价值”。周凌敏能够抒发意见纵情褒贬,与其受教育程度和国民党党员身份密不可分:
厥后青天白日飞展沪埠,外子参予戎机,余遂注意于党务工作,凡有集会,无不列席……同志佥以余热心工作,因谬举余为妇女部长……自问虽无殊绩,差可告无罪于吾党,然因生性率真,不习惯钻营阿谀之术,竟受腐化者联络之攻击,致迁职于远方……即日引退,稍事休养。
适女光公司,以谋女子职业而招请职员,余遂应募而往,迄兹数月,蒙主事者之优待,及外界之谬许,私心窃慰,且较之党务工作,尤觉有苦乐之判,从此安心守己,对于党务,拟完全脱离。
按:该篇系女工公司女理发师周凌敏女士所作,女士曾毕业某女校,学贯中西,尤工书法……
周凌敏“见了‘职业无男女’‘职业无贵贱’的两句话,毅然决然地去做那人人不屑做的理发师务”,无愧于民国女界精英中身体力行者。但周凌敏这样的妇运倡导者在女理发师群体中毕竟是极少数。正如前文所述,女学生是女理发师的主体,这从女光公司女子理发专科学校的招生宣言中可见一斑:“凡高小毕业或有相当程度,而年在十六岁以上二十五岁以下者皆可考入本公司。”南京女理发师年龄普遍在十八至三十岁之间,“其程度均在小学生之上,而常识之丰富,阅世之老练,举止之得体,远非一般伏处国中之小姐太太所能及”。严苛的年龄和学历门槛既维护了女理发师的先锋特质,也在无形中将一些有志于从业但年龄稍长且无文化基础的妇女拒之门外。
然而,亦有相当一部分女理发师在替人剪发前从事其他职业,其中尤为值得注意的便是娼妓业与女子理发业的关系。妓女在近代女子剪发潮中兼具双重标签:她们既是剪发的积极参与者,也是女子理发事业的拥护者。为招徕顾客和吸引眼球,妓女往往剪去长发,剪短头发的女学生被时人讥为“妓化”,足见妓女剪发之流行。而受1928年南京“废娼运动”的影响,无锡部分妓女也果断加入了女理发师的行业,时人对此不无赞许之意,“无业女子,及废娼革妓之戚戚谋生者,盍一习此技,得正适之归宿耶”。不过,也有声音质疑她们能否常驻,“等到发业一落千丈的时节,理发师不免感到过剩……那些从娼妓蜕变而来的女发师,或许就要还原过去,重理她们旧业呢”。
农民同样是女理发师人员构成中的一部分。20世纪30年代初“农村危机”的爆发使农村经济濒临崩溃,进而引发较大规模的农业人口离村潮。一批农村妇女来到城市后,遂开始学习理发技术以图维持生计,“晚近以来,农村崩溃,经济不景,而尤以顺德蚕桑女工最受打击,以此种职业,亦为谋生之一。于是纷起参加学习,学生日多,毕业日众”。
无论是何种出身,女理发师在上岗前均需在女子理发培训机构中接受培训,而培训费对她们而言往往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以女光公司上海女子理发传习所为例,“入学时一次缴纳二十元学费,书籍用具自备,如需膳宿月缴洋十二元”。与之相对的是,1929年上海市男工每月平均工资为15.43元,女工则更少。再如广州女子理发习艺社等理发习艺所,“征收学费七八十元不等”“所费颇巨,约需百元左右”,而1935年广州火柴业男工每月工资为15元,女工每月平均工资为9元。各地女理发师的工资与理发店当月的营业额和个人素质挂钩:在广州,“每人月中所入,无一定数目;有每月可得七八十元者,五六十元者,三四十元者不等,操理发职业女子,间为有夫之妇,亦有未结婚者,多数困于家计,出而工作”;在重庆,“她们的手艺,因为有高下的不同,所以每月所得的报酬,亦多寡不一,报酬高的每月每人能得一百元,报酬低的则在二三十元上下,学徒每月仍有三四元至五六元”。可见对于民国时期的女性而言,女理发师的薪酬已殊为可观。
地域流动则是女理发师求职过程中的常见现象。“广东帮”是上海女子理发业的重要派别,1926年开设的“美丽阁女子理发所”内20名美发师、美容师及助工皆为广东女青年。上海女子专科理发学校学生毕业后散于全国各地理发店就职,“统计本埠二十人,首都十八人,汉口四人,哈尔滨六人,宁波五人,南洋仰光二人,其余武昌、南昌、广西、广州、常熟、如皋、南翔、嘉善等处均二人,近大连来校聘请技师十一人,月薪七十元;宜昌二人,月薪六十元。”国内跋涉最远者至哈尔滨,一度使巡警生疑,学生许桂英则交代称:“系上海女子理发专科学校学生,现由李云甫招往哈尔滨理发馆工作,每月薪资五十五元”。更有甚者远赴越南、暹罗等国华侨所开理发店工作。
工作之余,女理发师亦迫切希望通过其他途径提升和实现个人及社会价值。当时的剪发男性留意到,一些年轻女理发师下班后并未立刻回家,反而到另处学习外语,“她们催促着给我理发的女郎快些竣事,说大家要去,她们相互的称呼是用蜜斯黄、蜜斯李。我问替我理发店女郎,你们忙着到什么地方去呀?她和缓地告诉我,她们每晚九时以后,要到一个法国女人家去学习法文。”九一八事变后,一些女理发师们感于国仇家恨,主动为东北义勇军筹款,“实行节衣缩食,将每日所积之款,置于扑满中,作为捐助义军粮械之需”,从中不难窥见民国女理发师积极向上的精神面貌与强烈的爱国情怀。
两性竞争中的女子理发业
先前已有学者指出,女理发师的崛起是梳头婆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的一个诱因。而事实上,女子理发业的野蛮生长,起先亦猛烈冲击了男子理发师的生存空间,但随着男女理发业竞争的不断演化,女子理发业反倒渐入下风,甚至有消亡之虞。在上海与广州两座口岸城市内,女子理发业的发展模式几乎如出一辙,而岭南男女理发师之间的直接矛盾,较之江南更为尖锐突出。
江浙女子理发业勃发之际,其已不可避免地被卷入同业竞争的纠葛之中。1927年7月29日,理发匠金氏因拟开设女子理发室,呈请公安局备案。为争取有司首肯,金氏强调女子理发室开设的必要性:“今当省党部妇女部通令全省妇女一律剪发之时,上项设备诚有不可缓者。”公安局的确无意阻拦女子理发店开张,但当地理发同业公所对此却颇有微词,指责金氏的做法破坏了行规:
民等素开理发店为生,同业向有公所,由同业推举,按年轮值经理公所事务,旧有业规,创设理发店,须离老店十间门面以外,方可开设,同业无不遵守,历无违背,因此素称相安。兹有金调良自崇安寺新新书局内创设女子理发店……伏查金调良创店地址东面有美容轩,西面有和源公司理发店,新新书局介乎期间,与该两理发店相距不过四五间门面,殊与旧规不合,况且同业中寡孤,藉店生活者甚多,设或旧规破坏,势必效尤踵起。
因此,警厅不得不收回成命,重又勒令无锡总工会跟进此事。尽管同业公所提出的诉求合情合理,但这也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女理发师并不受其时由老派男性理发师掌舵的同业公会所庇护,倘若女子理发师不结成同盟抱团取暖,在实际工作中难免左支右绌。或许考虑到这一点,上海的女子理发工会于1928年率先成立。
然而,女子理发工会绝非上海女子理发业的保命符。在“剪发潮涌”后的几年内,上海女子理发业竟悄无声息地滑向衰亡。1930年,女理发师仍是人人艳羡的美差,“女理发师,也成了新职业,超出于三百六十行之外的一种了”;女理发馆随处可见,“理发铺大有五步一阁,十步一楼之概”。但在四年后的上海,则很难觅得女理发店的影踪,“到了现在,上海仅存了一家女子理发所,其名叫维多利”。南京女理发馆也不好过,“至二十一年,乾坤、万国、民生相继停业。二十二年,东方迁至贡院街,改名姐妹理发馆,今年新民姐妹均停业,于是南京之女子理发店,硕果仅存者,只南洋与东方两家矣”。
江浙沪女子理发业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要归结于无法留住男性顾客。尽管女子理发店设立的初衷是解决女子理发问题,但就周凌敏收集的数据而言,女子理发店的男性客户仍旧牢牢占据半壁江山。
而据时人观察,女性理发店收费普遍较男性理发店高,“女子理发馆之价目,往往较同等设备男子理发馆为高,与最上等男子理发馆相同”,但女理发师的服务水平却不能与较高的收费标准相匹配,有论者甚至直言“女子理发的技术不如男子”。修业年限的差距决定了彼时男女理发师剪发技艺的差距:男性理发学徒往往要三年方得出师,而女学生们在接受三个月培训后便可从业。必须承认的是,当时步入女理发馆的男性多持尝鲜猎奇之心态,倘若女理发师的剪发手艺不够过硬,有理发需求的男子只会回归更为质优价廉的男子理发店,男性顾客的流失可想而知。理发热潮退去后,由于女性剪发的频率远不及男性,女子理发店无法仅依靠女性顾客生存,每每到了冬季,女理发馆的生意只能仰仗于已与店内某一女理发师建立友谊的“老主顾”,而他们本身“醉翁之意不在酒”。这既是因女子理发业快速发展所遗留的结构性痼疾,也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此外,20世纪20年代的农村危机也是压垮沪宁女子理发业的重要因素。“农村破产”的破坏力远超乡村一隅,富庶城市也难逃其辐射,“东南财富之区,现在亦已凋敝不堪。试看上海电报所述废历年关上海和其附近内地歇业者至多,可见一斑,南方如此,北方更不待论”。在极不景气的工商业环境下,女子理发业很难独善其身。
较之于上海,20世纪30年代广东地区男女理发业的争斗更为刺刀见红,双方争执的焦点在于理发工会问题。在潮汕,尽管女子理发风靡,但当地理发工会却拒绝接受女理发师入会,由是导致女理发馆无法为男子剪发;在佛山,情况则翻转过来:为统一营业规章,三水理发工会勒令全市理发女工必须加入工会,否则强制剥夺女理发师工作权,但各“发花”则坚决反对加入男性所把持的理发工会,双方始终僵持不下。而在广州,女理发师则是起初相对强势的一方。1933年,广州理发工会向市政府“大吐苦水”,称女理发师数量激增将放大失业问题,致使男理发师丢失经济来源,因而应当取缔女子理发训练所。这近乎无理取闹的要求自然被广州女理发师猛烈抨击。而后,因广州女子理发店营业时间较长,广州理发工会恐生意被女理发师尽数掠夺,请求女理发师加入工会协调营业时间及营业价目,又遭以杜秉珊为代表的女子理发业魁首一口回绝。1935年,广州茶楼男女工人发生冲突时,女理发师阵营领袖迅速与女招待方面达成同盟,双方“联成一气”以捍卫女子职业。直至“新生活运动”之风刮遍广州,男女理发工人之争才渐次消弭。广州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代表原打算劝诫女理发馆和男理发馆在工作时间上保持一致,但在女理发师的据理力争下,市“新运会”最终亦同意女理发馆夜间九点闭店。从这个角度出发,广州女子理发师似已取得了斗争的完全胜利,但荣光背后实则暗流涌动。就理发技能而言,广州女理发师与男技师相形见绌,这使得广州女子理发店面临着与上海女子理发业相似的窘境:就理发门店而言,女子理发店数量因经济大萧条日益萎缩,但女子理发培训方兴未艾,这导致女理发师远远供大于求。失业的广州女理发工人最多时逾2000人,迫使杜秉珊带队出省为女理发师谋职,但这样的举措显然无异于杯水车薪。
由于男子长期垄断大量职业,近代女子“走出家门”后,男女职业工人因就业机会、就业环境和就业待遇产生龃龉并不罕见。倘若暂且不论国内国际经济形势动荡的影响,从表面上看,女子理发业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遇挫是女子理发业在两性交锋中失败的结果,但从本质上讲,击倒女子理发业的是女子理发业的自身积弊,而非男子理发业的打压。后者所做的仅是进一步曝光这些问题。女子解放的社会舆论与急功近利的社会心理裹挟着女子理发培训事业,使其朝着速成化快餐式的培养方向一往无前,女理发师难以真正掌握理发技能;而民国男女理发业的激烈竞争固化了双方畛域之见,摧毁了健康的行业生态,也因此葬送了女子理发师通过相互交流提升剪发本领的契机。作为一项新生事物,女子理发业的演进趋势在相隔千里的两座城市内呈现着相类的面貌,无疑在一定程度上折射出民国女子职业初创的艰辛与不易。
余 论
作为新兴职业的女理发师拓宽了近代妇女的就业渠道,其主导的女子理发业是民国女性追求职业平等的重要平台。大体而言,女子理发业的普及呈现出先南后北的态势。纵然各地女子理发业的发展阶段参差不齐,但无不与盘扎当地的男子理发工会爆发冲突,且多为高开低走,令人扼腕。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是,20世纪20年代普通女子碍于“男女有别”的世俗目光,更倾向于到女子理发店剪发;在20世纪40年代前后,女子却更愿意到男子理发店而非女子理发店理发。消费观的理性化与性意识的开放化何者左右了女性的理发选择,尤为值得探究。此外,由于部分地痞无赖常到女理发馆寻衅滋事,女子理发室成为近代城市治安的新痛点,“女子理发馆一多,公安局的事务,也跟着加多”。女理发馆等女性营业商铺与警政的交互关系兼及处理新型女子职业相关问题时治安条例与实际管理之间的张力,或是日后社会史领域可供挖潜的方向。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