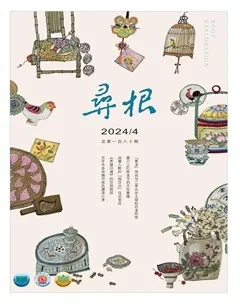从狂欢理论中的“二元对立”看山西秧歌小戏
民间小戏一直是文艺学和民俗学研究的重要主体,同时,作为乡村社会实践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集中反映了乡土社会的伦理观念和精神风貌。秧歌小戏是活跃在三晋大地上的一朵灿烂的文艺奇葩,“生于斯长于斯”的特性使其在形成之初就深受民众喜爱和推崇。秧歌小戏具有较纯粹的民间文化特质。
一
作为民间文化的秧歌小戏,出身乡野,流行市井,一直被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乡音俚曲,受到精英文化阶层鄙夷。我们再看秧歌“自正其身”的传说:
传说一:(太原秧歌)明末农民起义军领袖李自成从西安进入北京时,路经山西太原,村村接应,处处欢迎,有人即兴编唱时调欢迎义军,李自成见此十分高兴,即号召百姓仿调大歌大唱,义军去后歌声未绝,反而遍及各村,秧歌从此兴起。
传说二:(介休秧歌)北宋年间,赵德芳和寇被困幽州,杨六郎带领八姐九妹及杨家兵将前往营救,因敌军防守严密,几次攻打都不得入城。于是改用计策,杨六郎头戴风帽,手举红伞,八姐九妹等扮成秧歌演员,杨宗保等人持大锣、小锣各一面,组成一班子秧歌队,才闯入幽州,救出赵德芳和寇准还朝。
可以看出,民间希望通过将精英人物嫁接于秧歌起源之上,赋予其正统地位,作为论证其正统性的依据。事实上,这些传说本身充满了民间杜撰的痕迹,但也证实了其来源的民间性。
虽说秧歌尝试用上述方式来证实自身的合理性,但精英阶层似乎并不买账,反而对其实施限制和打压。在今长治市柳林寺庄大庙东墙石碑上刻有“奉口官禁止演唱秧歌。同治四年,阖村公立”的字样。曾任高平知县的龙汝霖在其主编的《高平县志》中提出“二十禁”,秧歌就是其中之一。光绪年间,续修《高平县志》时,对这一禁令作了进一步阐释:“春初演唱秧歌,每至耕耘收获时犹不止,知县龙汝霖严禁之。”同一时期,忻州知州方戊昌也提出,对于秧歌“地方官应出示严加禁止,违者重惩”。1920年太谷县正式发布《禁止秧歌文》:
查唱演秧歌,多系淫词俚曲,伤风败俗,莫此为甚。太谷秧歌素即驰名,现值春节甫过,深恐人民习沿旧惯,仍有唱演情事,合亟布告禁止,仰县属各村,一体知照。如有违犯,定行从重处罚,决不宽贷。勿谓言之不预也。特此布告。
从以上禁令我们便可得知,秧歌小戏之所以不被接纳,在于官方认为其唱词有损教化,《徐沟县民俗志》中充溢着对秧歌小戏的贬抑,从中也不难看出地方文化精英对秧歌小戏“有伤风化”的影响的担心:
在乾嘉道咸之晏安耽逸时,每届春正,村之农夫作土剧,谓之“秧歌”。所演略同戏剧。曰“大套曲秧歌”,以步太原县所传者为正宗。同光以下,人穷物绌,渐至汰除。而邻县稍富地方,异军突起,更为淫鄙不耐之词,确为经济消沉、生活堕落时之一种背景。唱白之语,全为当地亵言。妇孺文盲,直接所受观念,毫无缓冲之力以解少其烈。县所辖之教育不良村庄,有私邀演之者。
在秧歌小戏中体现出来的寻求和追逐自由,并本能地爆发出源自生命原始的粗朴、开朗、热情的精神状态,颇有巴赫金所提倡的“追溯到人类原始制度和原始思维”的意思。禁者自禁、演者自演,秧歌小戏在官方和民间文化二元对立的结构中呈现出繁荣之势,自明清以来逐渐成熟。
二
乡村社会中的秧歌小戏起源于元宵节的社火活动,廖奔推断:“大概说来,秧歌演唱形式最初传到北方,由于其通俗、新颖的格调,立即受到人们的欢迎,继而便结合北方各地的民间舞蹈,发展成为当地的年节舞蹈——这是通过方氏的责难而推测出来的。”虽说在后世发展中,秧歌表演散布到乡村喜事的每个节点,但是其最具规模和最重要的演出,莫过于“闹元宵”。
据资料记载,乡村集体活动的非功利性,使得乡村社会中的秧歌活动参与者,几乎涵盖了社会各个阶层,在整个狂欢中都具有双重身份——既是观众又是演员。太原乡绅刘大鹏在其《退想斋日记》中提到了本地富人参与唱戏的情形:“世有一种人呼群结伴团聚一处,手弄乐器,口唱戏曲,名之曰自乐班。这些人大半是游民居多,而最为富汉所喜悦。其中唱者富汉亦不少,盖彼以为得意事,而不以此为羞惭事也。”在《襄垣秧歌》中也记录了当时远负盛名的秧歌艺人的出身:襄武秧歌的代表人物张金川是铁匠出身,因擅唱旦角,就被当地人称为“铁匠旦”;襄武地区著名秧歌班社“富乐意”的掌柜曹双喜,出身贫寒,没上过学,从小和父亲学做挂面,艺名就叫“挂面旦”;以“小须生”名扬襄武地区的韩德三生于世代牧羊家庭。
到了清末民初,秧歌逐渐走向成熟,出现了许多职业或半职业的演出团体,继续在乡民的非功利性的广泛参与中与乡村社会保持着紧密的良性互动。
一方面,在中国的传统伦理道德中,讲求“纲常伦理”“存天理灭人欲”,有严格的等级制度和“理”的信仰,所言情欲,尤其男女情爱被官方文化、精英阶层视为不齿,而根植于乡野的秧歌小戏则以婚姻家庭为最胜,用质朴俚俗的小戏,打破伦理束缚,追求本真自由的感情态度,代表剧目有《缝小衫衫》《剂白菜》《做烟口袋》《雇驴》等。这些剧目以日常生活劳作为背景,讲述了男女主角偶然相遇互有情意,于是私下相好的故事。除了本身创作于民间的故事外,还有一部分是改编自历史故事、传统大戏。值得关注的是,在改编过程中多被“提炼”成男女情爱的感情戏,例如《白蛇传》变成了《游湖》,《西厢记》变成了《张生戏莺莺》,等等。
另一方面,传统官方准许流通的戏曲多有明显的纲常伦理,而在秧歌小戏的情感戏中,表达感情时多为女性主动,颠覆了传统观念中男女交往的被动形象。例如《雇驴》中,女主人公玉凤的父亲用计骗了男主人公吴金成的钱,吴上门讨要。这时,玉凤看到吴金成忠厚老实,主动提出用自己去顶银,得到皆大欢喜的结局。在家庭戏中,婆媳矛盾是戏曲叙事中的常客,而秧歌小戏与之相反的是,结局总以长辈承认错误、晚辈恪守孝道结束。秧歌传统剧目《小姑贤》讲的是婆婆只喜欢自己女儿,不待见儿媳,处处与儿媳为难,最后在女儿的劝解下,幡然醒悟,与儿媳和好。类似于这样的故事在秧歌小戏中屡见不鲜。
由于狂欢的全民性的特征,语言使用势必会显得粗浅、夸张放肆。巴赫金通过对文学作品文本的研究,分析出其背后所蕴藏的狂欢精神。这种通过语言表达出来的狂欢感受,被称为狂欢化文学。在语言风格方面,巴赫金提出广场语言的概念,它包括夸张、反讽、插科打诨、双关语等,与官方语言的规范、严肃、单一的特点相对。秧歌小戏由于情节简单、体裁短小,所以插科打诨自然就成了其增色添彩、博取众彩的重要方式,与官方文化的语言形成强烈对比。
在秧歌小戏中插科打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惯用歇后语,如祁太秧歌《背板凳》和《借妻》中就用了“蚂蚁戴上谷壳子——你冒充大头鬼了?”“蛇儿爬到明柱上——混充二龙戏珠了?”“蚧蛤蟆圪蹲在门蹲石上——混充石狮子了?”等等。其二是戏谑夸张,《缝袍子》里,丈夫嫌妻子把袍子缝得不好,妻子辩称:“前襟遮不住膝盖,外也不是无用的,丈夫你给财主担水的,上坡坡踩不住袍襟子。”“后襟子比前襟子长的二尺,外也不是无用的,丈夫你上大街下象棋的,省的拿咱家的椅垫子。”“两只胳膊三只袖,外也不是无用的,丈夫你进城赶集的,不用拿咱家的捎马子。”“领口挖在脊梁骨,外也不是无用的,丈夫你这几年运气不对的,上搭背叫你贴膏药。”以非官方的语言样态作为其表演语言,一来源自地域性特征,为了增强与受众的互动,二来使地方的、个体的、边缘的语言登上“台面”,且以插科打诨的方式呈现,是对官方文化语言权威的一种挑战。
三
秧歌小戏的狂欢性的内生动力来自乡土之根和生命之本,所表达出来的精神是关于释放和重归生命原始状态的热情和质朴,用其来观照现实,对现代性危机都有“疗愈”之意义。
一方面,民俗是指特定国家、民族区域的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所形成的并传承于世的风俗习惯,它见于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是一定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心理的直观反映和体现,对当今乡村治理、文化发展等都能产生深刻影响。但乡村现代化发展挤压了乡村传统民间文化生存的空间,出现民俗文化物质象征体制被消解、民俗文化内容的“被改造”和“被适应”等现代性问题。因此,重新关注传统民俗文化并给予多元化视角的解读就显得十分重要。
另一方面,无论是源自西方文化土壤的巴赫金的狂欢理论,还是根植于本土的民间秧歌小戏,根本目的都是“呼唤人的回归”。虽说参与狂欢活动的大多是乡野村民,无从可谈“自我意识”,但正是这种无意识的“自我意识”,才见生命之本真。世俗化驱赶社会文化价值,传统不断被祛魅,失去神秘,所有东西都变得可以随意复制、唾手可得,节日的狂欢性被消解,取而代之的是物质主义和形式规范,更多的民俗习惯我们只能嗅其味而不知其行。在这样的背景下,程序化的仪式表演是无法使人摆脱束缚的。于是,类似于秧歌小戏这种民间盛行的狂欢游戏才显得尤为不可或缺。置身于其中,人们忘却不快与烦恼,摈弃繁文缛节,打破生活惯式,释放沉积在心中的压抑,获得一种回归式的自由,在这之中,体悟人的意义,认识并肯定自我的存在,唤醒内心深处的热情、率真以及对自由的渴望。
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