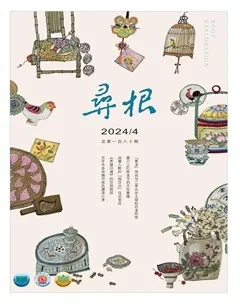漫谈两晋官员释褐与家世门第的关系

众所周知,两晋是中国古代门阀士族制度成熟稳固的时期,其发展形态与此前的战国秦汉及以后的唐宋元明清截然不同,最显著的特点莫过于身份地位继承制和资源权益世袭制的盛行,由此塑造了阶级固化、对流停滞的封闭式社会结构。门阀士族制度在这一时期起到支配作用,家世门第为决定因素,清浊流品是游戏规则,旨在按照不同家境出身彝伦攸叙、各司其职,达到各得其所、泾渭分明的理想格局。这种“世卿世禄”的贵族制原理集中反映在体制内的仕进层面,尤其是登仕首获正式官职的环节“释褐”。“释褐”,顾名思义就是脱掉庶民穿着的由兽毛或粗麻编织的衣服,换上官服摇身一变成为官僚的过程;它又称“起家”,意为士子脱离各自的私家,而在国家的公共场域实现同皇帝新的人际结合。作为政治生涯之起步,释褐或起家又被赋予“出身”资格的含义,浓缩几乎全部家世信息和对未来前程的预期。最早研究六朝释褐起家问题的是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他说:“弄清楚九品官制的轮廓,就可以推测连接九品官制和中正乡品的是起家之制。在现实中规定贵族门第高下的,除此起家之制外,别无其他。这在当时的社会里,大概是大家都十分清楚而无须特别指出的情况。但是,随着时代的变迁,它变得最为模糊不清。其模糊程度不仅仅对于我们这些外国人,就是对中国人来说,似乎也完全一样。”(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刘建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也就是说,释褐起家可以体现家世门第,而弄清家世门第则是六朝史研究中解决一系列问题的突破口。
以释褐起家反观家世门第,前提是两者按特定比例匹配关联。受宫崎市定的影响,学界普遍关注起家官品与人物乡品之间的数量关系。宫崎市定提出著名论断:“获得乡品二、三品者,可以从六、七品的上士身份起家。其次,获得乡品四、五品者,可以从八、九品的下士身份起家。……要言之,制定了起家的官品大概比乡品低四等,当起家官品晋升四等时,官品与乡品等级一致的原则。然而,在实施过程中,想来会允许在上下浮动一个品级的范围内酌情调整。”(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从理论上讲,所谓“乡品”实则是借清议乡论之名行铨量门第之实,因为乡党评议人物的道义行为与其在乡里社会中的责任贡献紧密挂钩,高门大族实力强,自然责任重、贡献多,加之资源丰厚,在培育卓越人格和知识素养方面得天独厚,高门第本身就意味着高品质,反之亦然,时人便直接以门第评估士人了,乡品后来逐渐蜕变为单纯表示门第的门品。不过,魏晋士族体制初成,阀阅壁垒尚未完全固化,阶级流动的大门也未彻底关闭,才学、德性、业绩等非门第要素及中正官主观意愿仍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乡品等级。如《晋书》卷四六载燕国霍原举寒素科被中正刘沈评为乡品二品。《世说新语·贤媛篇》刘孝标注引王隐《晋书》载,卑微的陶侃因缘际会,经十郡中正羊荐举为鄱阳小中正,“始得上品”。而且乡品并非固定不变,会因各种变故随机调整。《通典》卷十四载:“有言行修著,则升进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傥或道义亏阙,则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李含、郄诜、韩预皆因名节,夏侯湛因贤良考试成绩欠佳而降乡品。受意外因素的干扰,乡品会出现背离门第的现象,在此情况下探讨乡品与起家官品的对应势必产生误差。鉴于此,笔者有个不成熟的想法,即跨越乡品,将乡品所代表的核心内容家世门第与起家官直接挂钩,这样可以尽量滤除乡品评议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更能彰显士族社会唯门第是从的本质。
为弄清释褐起家与家世门第的关系,而不再纠结其与乡品的搭配比例,兹搜集《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起家28事例(如右表)加以分析。
28事例的搜集筛选遵循两条标准:第一,登仕必有明确标识,如起家、释褐、解褐诸语词,杜绝把传记履历的首位官职简单视为起家官的现象。这是因为当时官贵仕进以职务众多为荣,履历芜杂冗长,史家撰史无法面面俱到,只得截取某个辉煌的片段,除起家外,特别留意出身门第准许跨越的资格线和所能达到的终点线。易言之,史传所载履历缺少标识的首项官职,虽不排除起家官的可能,抑或为具备身份象征意义的某个显职。故笔者甄别起家事例采取宁缺毋滥的态度,以确保结论的稳妥可靠。第二,起家人物的世系官资必须明确,上限追溯至曾祖,毕竟士族多为晚近显贵,三代百年足够积淀家业。联想后来南齐御史中丞沈约弹劾与富阳满璋联姻的东海王源,辨其门第即从位登八命的曾祖王雅开始(萧统、李善:《六臣注文选》卷四十,中华书局,2012年)。北魏江阳王元继追忆:“伏见高祖孝文皇帝著令铨衡,取曾祖之服,以为资荫,至今行之,相传不绝。”(《魏书》卷一百八《礼志二》,中华书局,1974年)据曾祖以降三世官资核算阀阅等第,或许是魏晋积习的延续。史传若未记曾祖,暂且以父祖为准。
起家官及其品级,《通典》卷三七《职官·秩品二》一查便知,困扰笔者的是世资门第的核定。祝总斌先生系统剖析六朝士族的层级构造,他在“二品系资”的基础上继续拓展,指出二品乡品是由累世五品以上官资换来的(个别可适度延伸至六、七品的清官部分),在官品一至五品范围内又以三品划界区分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祝总斌:《材不材斋史学丛稿》,中华书局,2009年)。这似乎还透露出一条隐含信息,即一流高门授予乡品一品,一般高门授予乡品二品。我们知道,九品官人法乡品设九等,但归属高门士族的却只有一、二两等,是为上品,岂不恰好对应一流和一般高门?联系日后北魏孝文帝厘定胡汉姓族的量化标准,胡人的“姓”与“族”,汉人的“甲乙”和“丙丁”之间,约略同以三品划界(刘军:《论北魏士族的门第等级——以释褐为中心的考察》,《西南大学学报》2019年第4期)。六朝士族的等级体系又被古代日本模仿,五品以上的堂上贵族,三品以上称“贵”,四、五品称“通贵”,权力待遇迥然有别。有理由相信,北魏和古代日本的贵族制都是魏晋典章的翻版,礼失而求诸野,据此反观制度母体何尝不可。世资不只一代官爵,只好采取计算均值的办法综合衡量,均值一至三品为乡品一品之一流高门,四、五品为乡品二品之一般高门,再由此探寻门第与起家官的搭配关系。
通过28例材料,我们从两个角度进行统计分析。先以起家官品为基准,四品官起家1例,五品官起家2例,固定对应一流高门,且世资均为一品。六品官起家15例,对应一流高门者4例,其中1例世资一品,3例世资三品;对应一般高门者11例,其中3例世资四品,3例世资五品,3例世资六品,2例世资七品。七品官起家9例,其中对应一流高门者4例,1例世资一品,1例世资二品,2例世资三品;对应一般高门者5例,3例世资四品,2例世资五品。八品官起家1例,对应一般高门,世资四品。再以世资均值为基准,一流高门四品起家1例,五品起家2例,六品起家4例,七品起家4例;一般高门六品起家11例,七品起家5例,八品起家1例。通过两方面的数量统计,可大致推导如下结论:
首先,28例中绝大多数人物的世资在五品以上,少数为六、七品清官,俱系士族身份无疑。其释褐起家的层级分布在四至八品间。乍看起来无甚稀奇,但如果将六朝官品与上古宗法内爵分封及秦汉禄秩串联起来,便不难发现问题的端倪。中国古人习惯把宗法内爵、秦汉禄秩和六朝官品三类完全不同的事物置于同一发展线路上,认为相互间存在紧密的关联。宗法内爵序列中的公卿,对应禄秩万石至中二千石,官品一至三品;大夫对应禄秩二千石,官品四、五品;上士对应禄秩千石至六百石,官品六、七品;下士对应禄秩六百至二百石,官品八、九品。庶民之府史胥徒对应禄秩百石以下之斗食小史、官品流外品(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由此说来,起家官四、五品相当于内爵大夫和禄秩二千石,六、七品相当于内爵上士和禄秩千石至六百石,八品相当于内爵下士和禄秩六百至二百石。我们知道,内爵士以上皆属贵族阶级,士又分上士和下士,前者是贵族的起点,后者为庶民的终点,由此在士庶之间形成过渡缓冲带,以调解阶层间的关系。按照宗法制嫡长子继承的原则,大夫的嫡长子继承大夫职位,余下别子分封为上士;上士的嫡长子继承上士职位,余下别子则为庶民,庶民奋斗尚可跻身下士,成为最低级的贵族。这样的话,四、五品起家者可视为大夫的嫡长子,六、七品起家者可视为大夫的别子或上士的嫡长子,而八品起家者则视为奋斗成功的庶民。他们覆盖了宗法贵族的底缘,自然也就成为六朝判定士族身份的准入资格线。值得注意的是,无论宗法内爵还是门阀士族,在理念上均未完全封闭士庶流动的大门,而是酌情为庶民升进预留一定的空间,以保持社会应有的活力,这个良好的初衷直到南北朝仍然保持,只是缝隙狭窄、作用有限而已。就贵族内部来看,五品以上起家和六品以下起家是大夫与士之质的差别,两者地位之高下,应体现在各自的门第差异上。
其次,门第等级与起家官品绝非精确的定点对位,而是概略式的区域对位,所以,不必过分纠结乡品与起家官品究竟差几级的命题。大致而言,内爵大夫层位的四、五品高阶起家是一流高门的特权,宫崎市定指出,四品是臣下绝对不可能获得的起家官,属于“宗室选”的特殊层位;五品官起家则多为三公子弟,超越了中正所能评议的范围(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可见,四、五品起家者非但出自一流高门,而且必须位极人臣抑或皇室血脉,四品起家的司马贵为宗室元老,五品起家的何尊、王济皆三公之后,足为明证;除此之外,世资逊色的一流高门释褐只能就任六、七品官,双方的差距好比大夫的嫡长子和别子。六品是一般高门起家的上限,如果一般高门正常授予二品乡品的话,那么起家官品的确比乡品低四级,宫崎市定显然以此作为综合铨量的基准线,未必士族都以六品起家,只要折中起来达到这个平均水准即可。也就是说,二品乡品七品以下起家者与一品乡品五品以上起家者互相抵消,均值恰好为六品,当然宫崎市定还有其他方面的考虑,促使他视六品为贵族线的最优解。不过,这样一来,一流高门中宗室和三公子弟以下者的乡品就不能是一品,而是退居二品了,其与祝总斌先生门第层级划分的根本分歧就在于此。一般高门释褐以六、七品释褐为常态,符合内爵上士及其嫡长子的身份,别子就只能以八品下士起家了,28例中恰有1例八品释褐者,完整补齐了拟制宗法贵族的分封体系。足证,古人以门阀士族比拟宗法贵族是有一定道理的,或者说是模仿宗法贵族的构造机理设计阀阅流品规则。
再次,衡量士族门第与起家官的关系,不能只看官品的表面文章,还要留意职务的效力属性。起家官品与门第差距未及四级者,主要有四类:一是东宫及王国属员,如王文学、太子舍人;二是幕府僚佐,如相国参军、征西参军、护军参军;三是清望上选的文职,如秘书郎、佐著作郎;四是官府的实权要职,如尚书郎、县令。前两类均可享受国主或府主的人脉资源,借其势力搭建日后升进的跳板。后两类则以崇高的声望度和实际权力攫取政治资源。总之,都能以丰厚的利益回报补偿起家环节暂时的低落。实际上,只要对家世背景和个人能力充满自信,根本不必计较仕途起跑线的前后,士族释褐降阶倒转也是比较常见的现象。与其在本品末流拥堵,不如选择次等上选;与其深陷竞争旋涡,不如保持“止足”心态退而求其次。
最后,宫崎市定乡品与起家官品相差四级的理论,确如很多学者所说只是趋势概略性的,因偶然因素造成的个别偏差势所难免。他为此设定了误差修正量,即基准值上下各浮动一级,还从史料学的角度特别强调:“我们在正史列传中能见到的人物经历,更多属于打破标准形式的特殊情况。但是,如果因为个例人物的情况不相符合,就完全否定原则的存在,那就失之偏颇了。”(宫崎市定:《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韩先生补充解释:“可以原则上认同宫崎的判断。至于是否严格按照相差四级授官,恐怕就未必了,这样的例证不难找到,毕竟那是一个人治的社会,左右的因素颇多。但是,因为执行上的浮动而欲彻底否定乡品和官品之间的大致对应关系,把具体操作上困难重重的人事完全理解为随心所欲的长官意志,那就偏差太远了。有制度就有规矩,一定的准则实际上有利于官府的具体执行,却限制不了特权阶层的法外运作。准则和特权反映为常例和破例的情况,两者并存,并不是非此即彼或者相互否定的关系。”(《九品官人法研究:科举前史》译者序)依笔者愚见,只需作两方面的思路调整,即可规避上面烦琐的说明。跨越乡品,把释褐起家同阀阅世资直接挂钩已如前述,以最大限度减少清议乡论等主观因素对硬性制度的干扰。再有,分析起家官品与门第等级关系时,变定点对位为区域对位,以各自上限为基准衡量整体差距,一流高门和一般高门释褐的上限分别是四、五品和六品官,若两者理论上分授一、二品乡品,则起家官品与门第乡品差四级的结论确凿无疑。不过,应当注意到,起家官品是向下兼容的,以四、五品官为上限的一流高门可以六、七品官释褐,以六品为上限的一般高门可以七、八品官释褐,兼容的部分与上限都在合理的范围之内。如此一来,既能体现不同门第间的落差,又能解释相互重叠的交集,何必宫崎市定那般浪费唇舌。
综上所述,门阀化是两晋社会的典型特征,不同家世出身者在身份等级体系中均有固定的位置,其个性发展和人生旅程被宿命般决定。就政治权力的分配而言,仕途的起点、终点以及连接二者的晋升通道与阀阅世资保持密切的关联。尤其是官场最为注重的释褐起家,更是具有标榜门第的特殊功效。它与门第等级的比例对应关系实则是流品秩序的集中反映。宫崎市定提出的起家官品与乡品相差四级的著名论断有合理的成分,但是无法解释众多的特例,因而存在改进的余地。乡品固然应与门等合流,但毕竟还受人为因素的左右,远不如先世官爵世资稳定可靠,直接探讨释褐起家与先世官资背景的关系更能展现门阀体制之特质。所谓四等差,仅指各级起家的上限而言,至于向下兼容的部分自然就不成立了。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中古鲜卑拓跋氏士族化进程研究”(项目编号:19BZS056)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