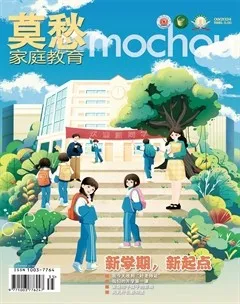一树荔枝四代情
“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岭南之地,荔枝种植历史久远。对荔乡子弟而言,荔枝不仅仅是甜美的水果,还是乡土情感的寄托。“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荔枝树不言不语,见证了我家几代人的情感交织与时光流转,成为记忆深处最温柔的那一抹红。
20世纪80年代的一个夏天,阳光透过轻纱般的云层,热辣地洒在这片富饶的红土地上,漫山遍野的荔枝,红绿相间,像燃起的一个个小灯笼。村头的荔枝园中,爷爷年轻时栽下的那棵桂味荔枝树红得最为耀眼。在物资匮乏的年代,荔枝是我们童年梦寐以求的佳果,每天早上天没有亮就起来捡落果,假如能够捡到一个,那是一整天快乐的源泉。爷爷小心翼翼地摘下最成熟的荔枝,他舍不得吃,作为家中长孙的我才有机会吃上当时价格昂贵的荔枝。我剥开硬壳,举起晶莹多汁的荔枝肉,半天也不舍得放进嘴里。荔枝的甜蜜与爷孙俩的笑声,交织成了一段温馨的记忆。
爷爷告诉我,早在南北朝的冼夫人时代,家乡就开始种植荔枝,还形成了买卖荔枝的市场——蕉荔之圩。小时候,老家有一个习俗,每到清明谷雨时节,荔枝花盛开,村里的荔农便准备猪、鱼、鸡“三牲”到果园拜祭荔枝树,爷爷口里念念有词,大意是祈求今年风调雨顺、荔枝丰收,小孩子跟着大人一起唱《拜荔歌》:“螃蟹红红,荔枝大如灯笼;螃蟹圆圆,荔枝载满车船……”在爷爷心中,这棵荔枝树是他对家族未来的期许,也是他对后辈无尽的爱与关怀。
后来,爷爷年纪大了,爸爸接过了爷爷手中的扁担和锄头,精心打理这片绿意盎然的荔枝林。每当荔枝成熟,爸爸都会组织全家人一起采摘。大人们在树上忙着摘荔枝,小孩成群结队地在树下玩着游戏,捡拾掉落的荔枝尝尝鲜。那时候荔枝产量低、单价高,依靠这棵荔枝树,我家拆掉原来的砖瓦房,建起了两层的“荔枝楼”,爸爸还在一楼入户的地方设计了弯弯的拱门,贴上不同颜色的瓷片,这在那时候是很时尚的设计,引得周边邻居纷纷效仿。直到今天,荔乡人每迁新居,必在院子种植荔枝数株,荔枝树茁壮成长,乃至成园,人居荔园中,成为一道独特风景。
再过些年,我也步入中年。爸爸妈妈已经退休,但是这棵荔枝树并没有“光荣退休”,反而焕发第二春,产量比以前都要高。面对日新月异的时代变迁,我尝试借助互联网平台,将这份来自岭南的甜蜜推向更广阔的市场。我家的荔枝园在广东偏僻的农村,早上摘下来还带着露水的荔枝,在田间地头就能找到冷链物流的寄送点,只需要在中午之前打好包交付邮寄,即使寄往西北、东北也是隔天就能到达,再也不用担心荔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看到远方的朋友对家乡荔枝赞不绝口,我的心中便充满了自豪与满足。
我的儿子和女儿,作为荔乡家族的第四代,虽然生活在高楼林立的城市,但对那棵老荔枝树的情感却丝毫未减。经历几十年风雨,老荔枝树的树梢已经比家里的楼房还要高出一截,枝叶婆娑。父亲在树底下安置一围石凳,每个周末,孩子们都会拉着我的手,来到荔枝树下,听大人讲述“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的故事。每到荔枝成熟的季节,孩子们会爬上树梢,尽情采摘、品尝荔枝,实现了我儿时“荔枝自由”的梦想。大人们则聚在树下聊家长里短,享受夏日的美好,在繁忙的生活中找到一份宁静与甜蜜。
岁月悠悠,荔枝树依旧挺拔,它见证了我们家族四代的变迁,也承载了太多的情感与记忆。从最初的种植到后来的守望,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诠释着对荔枝、对这片土地深沉的爱。在这棵荔枝树下,四代人的情感如同荔枝的香甜,绵绵不绝,温暖而深远,无论时代如何变迁,家族的根永远在这里。
编辑"东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