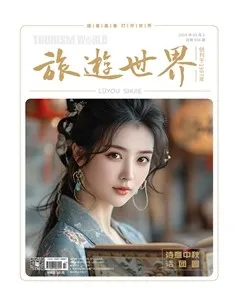《封禅仪记》:泰山游记的开山之作

《封禅仪记》,东汉马第伯创作的散文,记录了汉光武帝封禅泰山的经过。虽早佚,但幸有东汉泰山太守应劭将其载录于《汉官仪》中而流传。宋代之后,应劭的《汉官仪》亦大部亡失,后人可睹者有南梁刘昭为《后汉书· 祭祀志》作注所存的《封禅仪记》。《封禅仪记》被认为是中国最早的一篇游记,是早期描绘泰山山水、风物的佳作,对后世文学影响较大,史料价值日益凸显。
叙事:足为史鉴
东汉建武元年(25),光武帝刘秀即位。建武三十二年(56)光武“奉图书之瑞”,于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甲午,禅于梁父”。马第伯作为刘秀身边随行的侍从官,将他亲闻、亲见、亲历之事详实记录于《封禅仪记》,其文献性更为真实、丰富,可弥补一般史书之不足。其中,很多资料具有唯一性。
治泰山道:
建武三十二年,车驾东巡狩。正月二十八日,发洛阳宫。二月九日,到鲁。遣守谒者郭坚伯将徒五百人治泰山道。
……
十一日发,十二日宿奉高。是日遣虎贲郎将先上山,三案行。还,益治道徒一千人。
泰山很早就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就登山的道路而言就有周御道、秦御道、汉御道之说,但对道路修治的记述尚属首次。光武帝的这次封禅先后驱使“道徒”“五百人”“千人”修治其道,可见工程量巨大,不过从时间上看,应主要是道路阻碍的清理及平整。在这段文字中,从光武帝启程、至鲁,再到泰山,相应的具体事项安排,在时间上具体、明确。
封禅助祭:
……(二月)十五日,始斋。国家居太守府舍,诸王居府中,诸侯在县庭中斋。诸卿、校尉、将军、大夫、黄门郎、百官及宋公、卫公、褒城侯、东方诸侯、洛中小侯斋城外汶水上。太尉、太常斋山虞。
关于这一方面的信息,《后汉书·祭祀志》仅提示“汉宾二王之后在位。孔子之后褒成侯,序在东后,藩王十二,咸来助祭”。而以《封禅仪记》所记较之,更为详实。这为进一步研究东汉封禅从封成员的构成,提供了第一手资料。
封禅立石:
马第伯自云:某等七十人先之山虞,观祭山坛及故明堂宫郎官等郊肆处。入其幕府,观治石。石二枚,状博平,圆九尺,此坛上石也。其一石,武帝时石也。时用五车不能上也,因置山下为屋,号五车石。四维距石长丈二尺,广二尺,厚尺半所,四枚。检石长三尺,广六寸,状如封箧。长检十枚。一纪号石,高丈二尺,广三尺,厚尺二寸,名曰立石。一枚,刻文字,纪功德。
秦始皇、汉武帝封禅,都有立石颂其功德的刻石,故在相关记载中有“上石”“立石”的说法,但往往为人所误。如现立于岱顶的无字碑,因“无字”而多疑惑。有云:汉武帝以为功高盖世无以文对,故无字。或云:由“无字”委推于秦始皇,“本意欲焚书, 立碑故无字”。
《封禅仪记》的记载清晰明了,封禅刻石有二:一为“立石”,一为“功德石”。“立石”是封的标志石,也号封石(即“坛上方石”),自然无字;“功德石”也就是纪功刻石,一定会有文字。“无字碑”是封石,本就不应该有刻字。有了其所记封禅“石二枚”,一枚“立石”,一枚“纪功”石,无字碑无字的疑问迎刃而解。
风物习俗:
早食上,晡后到天门。郭使者得铜物。铜物形状如钟,又方柄有孔,莫能识,疑封禅具也。得之者汝南召陵人,姓杨名通。东上一里余,得木甲。木甲者,武帝时神也。……乡坛再拜谒,人多置钱物坛上,亦不扫除。国家上坛,见酢梨酸枣狼藉,散钱处数百,币帛具。诏问其故,主者曰:是武帝封禅至泰山下,未及上,百官为先上跪拜,置梨枣钱于道以求福,即此也。上曰:封禅大礼,千载一会,衣冠士大夫何故尔也?
泰山东上七十里,至天门东南山顶,名曰日观。日观者,鸡一鸣时,见日始欲出,长三丈所。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黄河去泰山二百余里,于祠所瞻黄河如带,若在山址。……山南有庙,悉种柏千株,大者十五六围,相传云汉武所种。小天门有秦时五大夫松。始皇封太山,逢疾风暴雨,赖得松树,因复其下,封为五大夫。西北有石室。坛以南有玉盘,中有玉龟。山南胁神泉,饮之极清美利人。
“置钱物坛上”“散钱”“置梨枣钱于道”,这些泰山封禅祭祀遗俗,不见于其他书册中。泰山日出,是历代文人骚客所歌咏、赞美的奇观,马第伯的“鸡一鸣时,见日……”“欲出”“长三丈所”是对泰山日出的首次记载。所谓“四观”的说法,也是首次出现在泰山的史料中。山下的岱庙,以柏树为特点,且其树为汉武帝所植,是对庙貌特点最早的记述。还有“玉盘”“玉龟”“神泉”之说,也首见于其记。
写景:另辟蹊径
《封禅仪记》围绕封禅这一主题事件,以时间为轴记录其所历、所见、所感。似乎有所“跑题”,马第伯关注最多的还是登泰山的整个历程。一路走来,山水相拥,峰回路转,别有洞天。“极望”“仰视”,其人、其道、其石、其峰、其水,视觉的、心理的,虚实相生,物我交融。
是朝上山骑行,往往道峻峭,下骑,步牵马,乍步乍骑,且相半,至中观留马。去平地二十里,南向极望无不睹。仰望天关,如从谷底仰观抗峰。其为高也,如视浮云。其峻也,石壁窅窱,如无道径。遥望其人,端端如杆升,或以为小白石,或以为冰雪,久之,白者移过树,乃知是人也。殊不可上,四布僵卧石上,有顷复苏。亦赖赍酒脯,处处有泉水,目辄为之明。复勉强相将行,到天关,自以己至也。问道中人,言尚十余里。其道旁山胁,大者广八九尺,狭者五六尺。仰视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若在云中。……遂至天门之下。仰视天门,窔辽如从穴中视天窗矣。直上七里,赖其羊肠逶迤,名曰环道,往往有絙索,可得而登也。两从者扶掖,前人相牵,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所谓磨胸石,扪天之难也。初上此道,行十余步一休,稍疲,咽唇焦,五六步一休。蹀蹀据居顿,地不避湿暗,前有燥地,目视而两脚不随。
……
日入下去,行数环。日暮时颇雨,不见其道,一人居其前,先知蹈有人,乃举足随之。比至天门下,夜人定矣。
这一部分在《封禅仪记》中最为抢眼。从“是朝”上,到“日入”下,是一整天的历程。
记录行程,写景状物。从马第伯提到的地名及当时人文地理环境来看,光武帝是从“东御道”上山,入山口位于今天烛峰景区(大津口乡上梨园)。这是一条山脉较为开阔的溪谷,地势相对平缓。沿溪西上可达中天门。从山下到“中观”(大致相当于今之中天门)的行程中,虽然道路“峻峭”,但尚可步、骑相替,到了“中观”只好“留马”步登。登途之中,可见“处处有泉水”“岩石松树,郁郁苍苍”。而艰难的“天关”(今之南天门)之登,步足难开,一路险阻。最困苦的是“直上七里”,依靠“絙索”方可登也,乃至疲惫不堪,两脚不听使唤。落日下山,傍晚又有雨雾遮道,尚需有人在前探知路径。到达天门下,已经是夜深人静。写景记行,山路难、人劳困。上山、下山,时间、地点,具体完整。路途经历,曲折多变、惊心动魄。
以视觉感受, 言山之高。马第伯用“ 极望”“仰望”,写泰山之高。他们到达“中观”,这时的高度“去平地二十里”,放眼南去已是“极望无不睹”。北向而视,则只能抬头“仰望”,望天门“如视浮云”。近观,石壁遮目,道径难寻。“遥望”远处之人,端立如光秃之朽木,“或以为白石或以为冰雪”,因有所移动“乃知是人也”。到达天门之下,视天门如视“天窗”,是在由下而上的“直望”。登山者“后人见前人履底,前人见后人顶,如画重累人矣”,极强画面感如同现实影像。马第伯又记:“东山名曰日观,日观者……秦观者望见长安,吴观者望见会稽,周观者望见嵩山。”同样,也在说泰山之高,于此可观日、观秦、观会稽,观嵩山。
以肢体感受,写登山之难。天门似“殊不可上”,登山者心神疲惫,不得已只能“四布僵卧石上”获取喘息,在食以“酒脯”后,并在“泉水”止渴明目的加持下,始有精神再登。文中的“磨胸”“石”“扪天” ,是用举止动作来修饰上山之“难”。上山途中,初有“十余步一休”,后到“五六步一休”,先有“咽唇焦”的“稍疲”,再到 “目视而两脚不随”的疲劳过度,以致出现坐卧不择干湿的窘迫境地。然正是经历如此之“难”,才能于山顶 “四观”,才有了“南向极望无不睹”、北瞻天门“如从谷底仰观抗峰”的惬意。

谋篇:堪为范式
关于《封禅仪记》的文学属性,历代学者多有评判。其中,清·袁枚《古人摹仿》中说,“古人作文摹仿,痕迹未化,虽韩柳不免……柳子厚作记与汉马第伯《封禅仪记》句调相似”。
作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柳宗元(字子厚),其山水游记一贯被视为典范之作,故人们每每说到游记,必以其论优劣。从以上评论看,作为山水记游的《封禅仪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柳氏之文对其还就有所效法。
钱锺书先生在《管锥编》中谈及历史上的游记之文,有如此批评: “按前此模山范水之文,惟马第伯《封禅仪记》、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二篇跳出,其他辞、赋、书、志,佳处偶遭,可惋在碎,复苦板滞。吴之三书与郦道元《水经注》中写景各节,轻倩之笔为刻划之词,实柳宗元以下游记之具体而微。”在教育部“面向21 世纪课程教材”《中国文学史》中,将马第伯《封禅仪记》定义为“现今所能见到的最早的游记” 。
纵观历代评说,可见《封禅仪记》在中国山水游记中的崇高地位,它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得到了世人的充分肯定。在体式上,以“雄浑雅壮”为特点。在描写手法上,则以视觉为主导,大小、高低、远近、色彩、动静等,都会成为触动文思的重要元素。以身体验、用心感受,去察示人与景物的联动契合。在语言上风格上,则“碎语如画”,写人状物文字“极工”。《封禅仪记》是泰山历史上现存最早的游记;同时,在中国文学史上开山水游记体式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