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祛魅时代的人才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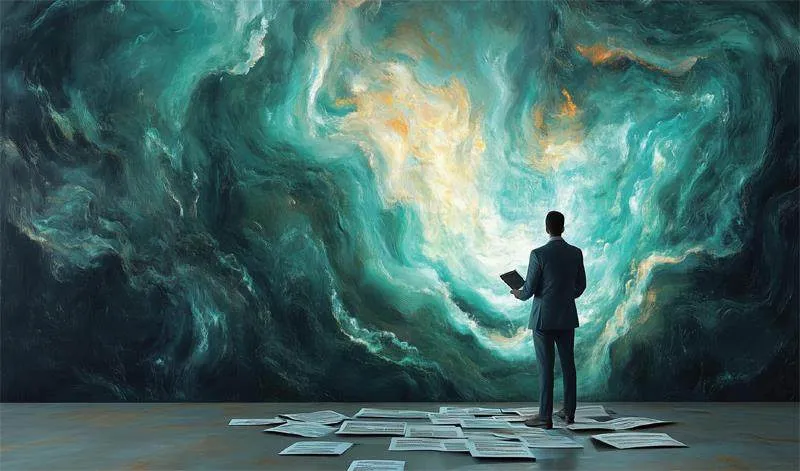
对全球金融业来说,2024年最醒目的关键字莫过于“裁员”。无论是在纽约、伦敦,还是亚太的中国香港和日本东京,或者中国内地的北京和上海,不少金融从业者都遭遇了职业生涯的去留危机。
从宏观来看,危机来自三方面原因。首先是经济和技术周期的因素,IPO项目大量减少,投行人士“僧多粥少”,从初级分析师到董事总经理,甚至区域负责人,很多岗位都显得多余。无论中美,还是东南亚,很久都没有出现过去20年那种成规模的科技公司上市大潮了。
其次,全球也处在货币周期的低谷之中。美元降息迟迟没有到来,全球很多主要经济体的货币政策相对收紧,这使得除了美日等发达市场的股市之外,全球资产价格一直都处于相对低位,资产管理行业只能被动收缩,从而面临结构性的人才过剩问题。
地缘政治也是造成金融人才供给失衡不可忽略的因素。美元资本在全球进行地理上的重新配置,使得一些经济体的投资机构必须重新寻找LP(有限合伙人),展开更激烈的本土募资争夺战。所有人都必须及时转变方向,稍慢一步,即被别人抢占先机,自己只能裁员降本。
不过,由于金融行业的特殊性,所谓的“就业问题”本质上是结构性的,而非普适性的,即技术型人才可能面临严重过剩,但资源型人才依然会供不应求。在货币相对紧缩、募资越来越难、项目资源愈发短缺的时代,这种人才供需的结构性问题将更加突出。
这将深刻地影响行业的每一个人。
两种人才
尽管已经过去一段时间,但中信建投“体育生事件”注定会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行业内外时常被引用的“典故”。事件也必然成为中国金融业转型的一个有趣注脚。
人们对事件之所以产生激烈反应,显然在于一种不公平感。男主角出生于富裕家庭,不但以体育特长上名校,而且还能进入中国最好的投行之一去实习。在券商界,中金公司、中信证券、中信建投和华泰证券被认为是最好的四家本土投行,业内所说的“三中一华”,指的就是它们四家。如果不是京沪最顶级的名校,要进入这些投行实习,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如果把事件仅仅定义为普通人因不公平感助推,而产生的一次舆论事件,那么就实在太过肤浅。它真正反映的问题是,部分券商的内部管理出现了一些状况,看似小纰漏,却是不容忽视的风控问题。
实习生在社交媒体曝光重要项目和重要客户的信息,这对任何一家正规机构来说,都是无法原谅的错误。对新员工和实习生进行保密培训,是最基本的流程。然而,错误依然发生在一家最头部的券商。
差不多和事件同时,一组数据也反映出了行业正处在转折期。按照东方财富Choice数据,截至2024年上半年,券商行业共有34.01万从业者,但相比今年年初,人数减少超过万人。其实,从2023年下半年开始,券商行业裁员和降薪就成为了稀松平常的现象。一些个案性质的悲剧性事件,也被认为和行业的裁员降薪有关。
在券商的裁员潮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在不少资深员工被裁撤的时候,应届生新员工的招聘却并未停止,而且,业务部门依然在招聘实习生。这样做的原因并不复杂,主要是降成本。
技术型人才一般拥有最顶级的学历、过硬的行业资格证书,以及没有瑕疵的从业履历,但这些优势和是否被裁掉并没有直接关系。
我国的主要券商很多都是上市公司,而且股东持股相对分散,这意味着资本市场对券商的经营有着较为硬性的绩效约束。一旦遇到经济周期,券商的业务总量减少,营收出现下滑,那么就必须要对成本动刀,从而实现降本增效。资深员工往往底薪较高,这是一种固定成本,而新员工和实习生往往底薪较低,属于可变成本。因此,前者更容易成为降本增效的对象。
相反,实习生招聘则受到较小影响,因为其成本可以压缩,而工作量却可以没有上限。在一些券商的研究部门,实习生已经是重要生产力,一些研究报告的基础工作基本上都由初级分析师带领实习生完成。
在券商的投行部门,由于直接和客户打交道,涉及上市融资等关键业务,容错空间较小,因此实习生承担的职责相对也少一些。比如,新闻事件中的“体育生”,就是在投行部门实习,而不是在研究部门。
研究部门和投行部门对人才的需求类型截然不同。除了对公司进行实地调研之外,研究部门可以看成是一种“闭门造车”,即通过调研写报告,为市场尤其是基金经理们提供投资参考。在研究部,研究能力是第一位的,所谓资源是第二位的。在很多时候,资源是由好的研究带来的,而不是反过来。
但在投行部,情况截然相反。投行部存在的价值,本身就在于资源,能拿到项目,永远都是第一位的。以国内的IPO市场为例,这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各家券商提供的服务大同小异,触达的销售渠道也没有差别,因此券商之间本质上不存在服务的重大差异化。这个时候,资源就更容易成为核心竞争力。
而且,僧多粥少日益严重。Wind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共有44家企业IPO上市,总共募资325亿元。而2023年同期,数字分别是173家公司IPO,募资近2100亿元——IPO公司数量是今年同期的近4倍,而募资总量是今年同期近7倍。显然,在一个存量市场,对券商投行部门来说,资源的价值必然不断凸显。
以券商的投行业务为截面,不难发现金融业人才市场未来可能出现的一些趋势。随着市场增量减少,进入存量竞争阶段,纯粹的技术型人才有更大概率出现过剩。技术型人才一般拥有最顶级的学历、过硬的行业资格证书,以及没有瑕疵的从业履历,但这些优势和是否被裁掉并没有直接关系。相对来说,资源型人才依然会短缺,甚至可能越来越短缺。
全球趋势
2024年9月,全球知名股权投资机构华平投资的第三代CEO即将上任。这并不算什么震动全球金融市场的大新闻,但在相关新闻稿中却出现了一个让中国金融人士熟悉的名字——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
盖特纳是奥巴马时期的财政部长,他已在华平投资工作超过了10年,未来将继续担任华平的主席,和新任CEO一起领导这家全球投资机构。2013年,盖特纳离任美国财政部长之后,很快就加入了华平。
盖特纳显然属于金融机构中那一类最顶级的资源型人才。对任何一家全球性投资机构来说,美国财长这个级别的资深人士的加盟,意味着很多。美国财长绝非一般意义上的财长,通俗来说,他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实权“三把手”,仅次于总统和国务卿,不但管理财政,而且也是金融业的大总管。
这个级别“人才”的加盟,至少可以为一家投资机构带来两种利益。在融资端,大型机构在全球扩张时,面临募资本土化的挑战,而资源深厚的美国政客可以接触新兴经济体的财金管理者和核心企业负责人,从而为在当地募资创造便利。在投资端,前者同样拥有不可比拟的信息优势和资源链接优势,可以从一些新兴经济体的经济体制改革中,寻找一流的投资机会。
除了华平之外,其他全球一线私募投资机构,也都是美国政界精英的“退休去处”。比如,和华平齐名的另一家私募投资机构凯雷,甚至被称为“总统俱乐部”,全球一些国家的离任政要纷纷在这家机构担任顾问,而布什家族也和凯雷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除了离任政要这种最顶层的资源型“人才”,一些全球性金融机构在初级分析师的招聘中,同样非常看重员工背景。
一个被全球财经媒体广泛报道的现象是,在伦敦的投资银行,不少初级分析师都是东欧政要和企业大亨的子女。在纽约的投行,拉美的世家子弟也是分析师队伍的重要组成人群。当然,这些年轻人在担任初级分析师一两年,初步熟悉了全球资本市场的规则和资本运作的操盘经验之后,会毅然回到祖国怀抱,从事更重要的工作。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并不复杂。无论对于高盛、摩根士丹利、美银,还是对于瑞士和德国的投行来说,它们为新兴国家政府和企业所提供的金融服务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人才争夺战”在决定业务发展方面,才有着不一样的价值。
如此剧烈的降幅,意味着募资难的急速加剧,而“资源”的重要性将更加不言而喻。这必然深刻地改变着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
如果投行作为中介机构存在“寻找项目难”,那么对于私募基金来说,除了寻找优秀投资标的过程存在激烈竞争之外,它们还在融资端存在“融资难”。它们需要富人愿意投资,成为私募基金的LP,基金才能存续和发展下去。
以另一家知名度极高的投资机构黑石为例,这家机构的一些基金近年来一直有推动投资人变得多样化的趋势。在2024年初,黑石推出的基金产品BXPE,即是专门针对高净值个人,投资门槛为500万美元。此前,黑石募资的主要目标是机构投资者,如养老金、主权基金或者保险公司等。
在私募行业,随着投资机构所管理资产规模的不断膨胀,大型机构投资者可以说已被开发殆尽。投资机构太多,但LP却不够用了。于是,很多人开始将目标锁定为富人阶层。尤其在美元降息迟迟没有来临、全球流动性依然相对紧缩的时候,投资机构的资金饥渴症表现得日益明显。因此,一些募资能力稍弱的投资机构在招聘员工时,“带资进组”可能就成为了一种潜规则。
在2016年前后,正是国内风险投资最火爆的时候,大量的民营创投崛起。一些创投公司招募员工的标准除了看中学历之外,另外就是要自带资源。员工的学历和知名机构任职经历一定程度代表了投资机构的“技术实力”,而自带资源则意味着一些企业家LP,会将自己的子女送到投资机构工作锻炼。这在当年的民营风投圈子,并非个案。
在资金充裕的年代尚且如此,在普遍募资难的时代,情况更加容易预见。按照RimeData的数据,2024年上半年,新成立私募股权、创投基金2063支,同比减少47.5%;认缴规模为6649亿元人民币,同比减少28.3%。如此剧烈的降幅,意味着募资难的急速加剧,而“资源”的重要性将更加不言而喻。这必然深刻地改变着行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
这是一个金融行业被逐渐祛魅的时代。这个行业依然重要,它是国民经济的血脉,依然会有优秀的年轻人前赴后继,加入其中。诚然,行业内部的人才需求,在过去的某些时段和某些情境下,的确存在一些隐性的规则。但随着监管的不断完善,以及行业本身市场化改革的加速,相信金融业将走上更健康的发展之路,也将给年轻人或资深职业人士提供更多、更公平的才华施展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