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鸟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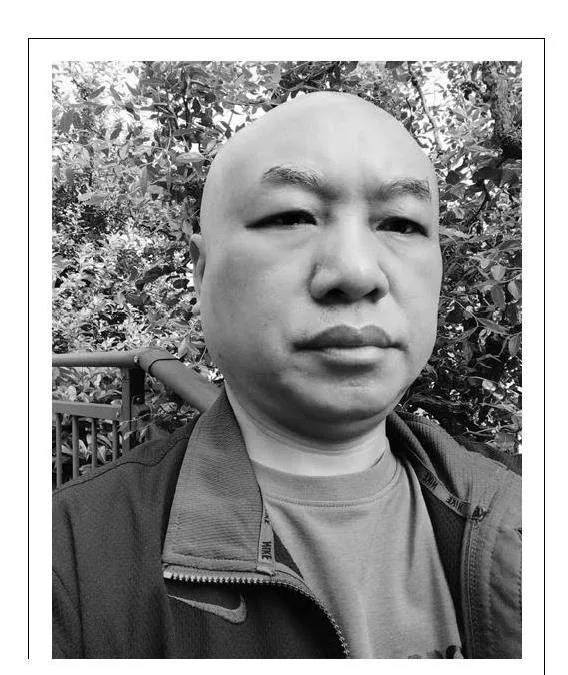
河马,本名蔡嘉彬,1968年生,湖北襄阳人。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著有诗集《鸟群飞临》《风花雪月》,曾获省级文学创作奖励。
樱桃河谷的樱桃红了,又到了吃樱桃的季节。
樱桃河谷离市区有一个小时的车程,难得周六赶上这样一个好天气,前几天还是阴雨天呢。抬眼一望,天空舒展得像天鹅绒床单,几朵白云随意游走。虽然已经是春天,下雨的时候还是要套一个外套,但田野里的颜色已由深色变成浅黄淡绿。
今天天气晴好,早晨微有凉意,她就在裙子外面套了一件鹅黄的风衣,脖子上系了一条白色的丝绸纱巾。这条纱巾是他到苏州出差时买回来送给她的,纱巾上绣着一枝粉色的垂丝海棠。她就喜欢粉色,虽然年龄已到四十,但她常笑自己还有一颗少女心。
周末来摘樱桃的游人很多。樱桃河谷漫山遍野都是樱桃树,娇红欲滴的樱桃挂满树枝。河谷有近五公里长,他们固定在最里边的一家采摘,几乎每年樱桃熟时都来。主人家姓李,很和善的老两口。
老李家有个院子,靠墙边有一排共六棵樱桃树,都是三十年的老树,尽管今年雨水偏多,也没影响樱桃的挂果,依旧满树红宝石一样的樱桃,很热闹。小茶桌上两杯清明节后刚采的毛尖,快开的热水一冲,根根悬立,嗅一下一股清气直冲脑门,顿觉神清气爽。樱桃要自己去采摘,她嚷嚷着让他给她搬梯子。一会儿的工夫就摘了两大盘,山泉水略冲一下,就可以坐下来品尝了。
老李家的院墙很矮,坐在院子里,视野很好,抬头就可以看见远处连绵起伏的山峦,大片的樱桃树就生长在这条河谷里。山脚下有一条奔腾的溪流,再远处是近几年刚修的高铁,半山腰是黛青的马尾松林带。山顶却是光秃秃的,从远处只能看见白色的巨大岩石,像还未融化的积雪,在太阳的照射下熠熠闪光。
这山脉的走向看起来像是一群马呢。她用手指了一下。
是吗?原来没注意。他喝了一口茶。
倒真像是马群呢,在草地上奔跑的马群,马背上套着白色的马鞍。
她是小学的美术老师,对事物经常有些职业的想象。他的专业是哲学,长于逻辑思维,在一个和文化沾点边的部门混日子。上班不需要哲学,混日子倒需要一点哲学。
樱桃果然熟了,甜得跟别的瓜果不一样,樱桃是淡淡的甘甜,不带一点杂味,是他们期待了很久的那种味道。
从远处飞过来一群麻雀,哄的一下落在樱桃树上,麻雀也喜欢啄食樱桃。她扬手叫了一声,高音很尖利,麻雀又哄的一声飞走了。她平常没有这样高声叫过,正常讲话都是慢声细语的,他喜欢听。
他们认识也有三年了吧,时间都去哪儿了呢?他是在女同学虹影组织的聚会上认识她的。她和虹影是闺蜜。怎么互相介绍的,谁要求留的电话,那天喝了不少酒,有点想不起来了。四十多岁,一个尴尬的年龄,想混个一官半职基本没希望了。看起来人的痛苦来源于财富和地位,其实真正的痛苦是你没有按照你希望的样子生活过一天,这不是哲学吗,他的专业在这里倒用上了。
每周他们要见一次面,有时候在闲叙咖啡馆里喝半天咖啡,有时候像今天这样到郊区走一走,有时候就躲在宾馆的客房里,对家里照例说单位加班。时间一长,见面也成了生活的一部分,如果一方有事不能赴约,另一方还有点不习惯。
闲叙咖啡馆也有他们的一个专座,就在吧台的后面。城市不大,要把遇见熟人的概率降到最低。他喜欢香草拿铁,她喜欢卡布奇诺。话题是远离日常生活的那一部分,主要是电影,她迷恋英格丽·褒曼,看过她主演的所有电影,《煤气灯下》,《美人计》,《卡萨布兰卡》。他喜欢美国的西部片和公路片,喜欢的是无家可归的人在流浪路上的自由。她的电影里主角都有个好结局,而追求自由的那些浪子们大多都以悲剧收场。悲剧才是生活的底色。
他讨厌冗长的开会和一大堆套话,每次部门开完会,他就觉得皮肤痒,大腿上手臂上长满红色的疱疹。他想离开,又不知道离开了应该怎样活下去。好在他也不想进步,对别人没有威胁,得过且过吧。
他感觉有点喘不过来气,像一个溺水的人,水已经淹过了鼻孔。他脱得赤条条的,仰卧在宾馆的大床上,器官萎缩着。
他问她:宾馆和医院的床单咋都是白色的?
她回答不上来。
她把他搂在怀里,用手抚摸着,他又行了。
他替她想到了答案,医院和宾馆都是治病的地方。那她就是他的私人医生。她就让他喊她大夫。他们常去的房号是407,她就跟他开玩笑。
407该吃药了。
407该做心电图了。
407该打针了。
最后病人和医生搂在一起睡着了。
麻雀又飞过来一群,可能还是刚才那一群,也可能不是,麻雀都叽叽喳喳的,互相之间根本分辨不清。这次他也高声叫了一声,想把麻雀轰走,但麻雀不理他,他只好从地上捡起一个石子向麻雀们扔过去,麻雀这才轰地飞起。麻雀总是一群一群地聚集在一起,很少看见单飞的,这个叫集体无意识或者无独立思考能力吗?他喜欢对日常生活的细节进行逻辑分析。
让它们吃吧,也许该有它们一份呢。她有些漫不经心。
老李家的小黑狗懒洋洋地卧在树荫下睡觉,一只老母鸡带着一群鸡雏在草稞间觅食,老李两口子在清洗刚从菜园里摘回来的芹菜和豌豆尖。他喜欢这些蔬菜鲜活的样子。山顶上的石头怎么会是白色的呢?他在脑海里搜寻唐诗里描写雪山的诗句,在想下次有必要登上山顶看看。
她眼睛眺望着远处奔跑的马群,淡淡地说:我离婚了。她像是在说别人的事,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又像是老电影的女主在念台词。她有个女儿,去年去了上海上大学。她还有一只小黑狗,今年老死了,她再也不想养狗了。把内心的东西说出来,她觉得突然好轻松。
山脚下有一列白色的火车开过去,映着山顶上白色的石头,恍惚间是新干线列车驶过日本的富士山,还有些异国情调。日本人喜欢坐在樱花树下,一边喝清酒,一边击节高歌。樱花一开就落了,人生苦短,他忽然有些感慨。
竹林里传来布谷鸟的啼鸣,割麦插禾,割麦插禾。每年小麦黄的时候,这些鸟就开始提醒不要误了农时。布谷鸟叫完后,大山雀、斑鸠、强脚树莺、乌鸫都开始鸣叫起来,像是在开一个演唱会。他专注于这些鸟叫声,并没在意她在说什么。
上个星期六下午,他们去了咖啡馆,照例坐在吧台后面的卡座里。咖啡馆里人并不多,一个女孩在抽烟,一对小情侣在安静地说话。她脱下黑色的外套,他接过来挂在衣架上,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打底毛衣,衬托得皮肤愈加白皙。她的衣服上有一种味道,他熟悉的香味。高大的彩色玻璃窗投进来的光影不停地变幻着,有一种不真实的幻觉。前一天晚上看了电影,《时光尽头的恋人》,一个女人永远二十九岁,阿黛琳。她说话的时候,一道光刚好打到她脸上,光线上泛起一层细细的绒毛。永远二十九岁,拥有不老容颜,女人们梦寐以求,不是吗?他看过这个电影。她呷了一小口咖啡,你说阿黛琳爱威廉多一点还是爱埃利斯多一点。埃利斯是威廉的儿子,父子俩先后在跨越四十年的时空里与阿黛琳恋爱。
这是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小情侣突然提高了说话的音量,他们为一件小事吵了起来。
她从未刻意给他讲过她的家庭,她和丈夫的关系,她一直在淡化和回避。他也从不跟她聊家事,他们仿佛达成了某种默契,维系着一种脆弱的平衡。她离婚了,和某人并无直接关系,那只是她自己的事,她是想这样表达吗?
她:我只是告诉你我离婚了这件事。
他:我知道。
她:你不知道。
他:我怎么不知道?
她:你就是不知道。
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谁也不能说服谁。
她:我对你没有要求。
她有点生气。
他:我对自己也没有要求,我已经放弃自己了。
她:我是说我们未来没有改变。
他:没有改变吗?
她:我们还像原来一样。
他:我们还像原来一样?
像一架天平,两边的砝码一样,天平是平衡的,现在一边把砝码拿掉了,另一边的砝码也要迅速地掉下去,才能达成新的平衡。
两只拖着长长尾巴的鸟从他们头顶飞过。
她惊叫:绶带。
确实是两只罕见的绶带鸟,拖着长长的白色的尾巴从樱桃树上面的天空飞过,并没有鸣叫。绶带总是成双成对,他给她讲过,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曾在竹林里用弹弓打下过一只,石子击碎了鸟的脑袋,鲜红的血滴在竹子上,另一只在他头顶哀鸣盘旋,久久不去,他吓得掉头就跑。那只死去的鸟有两条长长的白色的尾巴,美极了。那天晚上他开始莫名其妙流鼻血,怎么也止不住,流了好多血,他认为自己就要死了。
她几乎每次都要追问,那只活着的绶带鸟最后怎样了。
他骗她,那只鸟后来飞走了,他把死去的鸟挖个坑埋了。但事实是另外那只鸟一头撞在树干上,把自己撞死了,他埋了两只鸟。
又是一群麻雀飞过来,落在老李家的樱桃树上。老李并不在意,人喜欢吃樱桃,鸟也喜欢吃,那就吃呗,几个樱桃而已。他却从屋檐下取了一根竹竿,想在上面绑点布条之类,一时间也没看见合适的东西,她就从脖子上解下纱巾,系在竹竿上。微风一吹,纱巾顺风展开,倒真是好看又实用。纱巾上绣的那枝垂丝海棠在竹竿上舒卷着,像是活物在春风里往上生长着。他其实并不是真的要去驱赶几只麻雀,白纱巾飘在春风里,很有仪式感。
去山上走走吧,她看时间还早。
她在邀请他吗,也许并不是。他跟在她的后面向河谷那边的溪流走去。
她:我没有给你压力的意思。
他明白她想表达的意思。
她:我只是不能再这样将就下去了,我受够了。
当然,谁没受够呢。他和妻子已经八年没有性生活了。
她离婚了,只是告诉他一声,没有别的意思,他不要有压力。
他知道她的意思,他理解。他们说来说去想表达的真是这个意思吗?
虹影离婚了吗?他那位喜欢热闹的女同学。他的思维岔开了,好像刚才从远处走回来,心不在焉的样子。
他想起来好久没见过虹影了,虹影喜欢组各种各样的饭局,喜欢和人群建立各种各样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探讨过虹影的生活方式,虹影喜欢在这种生活中找到自己。可是她不行,她们是两条铁轨上跑的火车,可以并行,永远不会交叉和重叠。在她和前夫老吴婚姻存续的二十年里,她扮演的是一个贤妻良母。老吴在银行做事,别人花天酒地,老吴不喜欢和人打交道,唯一的爱好就是钓鱼。别人钓鱼就是钓个鱼而已,是一种休闲,老吴钓鱼达到了忘我的境界,除了上班就是在钓鱼,和她一个月也说不了三句话。有时候她觉得他们可能都忘记了彼此的存在。尤其是孩子上大学之后,老吴开始了夜钓,整夜整夜地不回家。老吴钓了鱼又不吃鱼,她只好见人就送。她怀疑老吴并不是喜欢钓鱼,只是不想待在家里。他们离婚倒简单,她提出来,她希望老吴生气,跟她吵架,问她为什么,但老吴连象征性的挽留都没有。第二天他们就去办了手续,好像有点迫不及待。离婚证书拿到手里,她有点不甘心,问老吴,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老吴笑了笑,你别多想,我只是喜欢一个人过。她和老吴一起生活了二十年,她以为她了解老吴,但在春节后送女儿上火车的时候,她看见老吴挥手和女儿告别,火车走远后,老吴流泪了,尽管他掩饰得很好,她还是看见了。
溪流的水很凉,溯流而上,有一个几块巨石合围而成的石潭,水清见底。日近正午,他们又走了这么远的路,就有些燥热。看看附近没有人,她突然有个疯狂的想法,三下两下脱掉衣服,赤条条地跳进了水潭。凉水一激,浑身起一层鸡皮疙瘩。他被带着,犹犹豫豫的,还没来得及脱衣服,被她一把拉进水里。这是还没经历过夏天的雪水,透心凉。
等她穿好衣服,他只好把湿透的衣服摊在石头上晾晒,石头热乎乎的,躺在上面很舒服,他拍拍石头让她也躺下来。他眯起眼看向天空,天空里飘满七彩的气泡,大大小小的,有的单独一个,有的串成一串,他就在这些气泡中飘着,轻得像一根羽毛。春风在河谷里浩荡地吹着,又一列火车快速穿过,她把手伸向他,轻轻抚摸着,它一直低垂着没有动静,最后她放弃了。
中午老李两口子给他们安排了四样菜,一盘烧土鸡,一盘烧豆腐,清炒豌豆尖,香椿烘鸡蛋。这样贴心的小菜,喝一杯吧。她平常很少喝酒,今天却想喝点。他从车厢里拿了一瓶白兰地,一个朋友送给他的,他喜欢白兰地的琥珀色和绵长醇厚的口感。
她是把这一餐酒当作最后一餐。
尽管他从不提他的家庭,但她知道,在这个城市的某个房间里,有个女人在等着他回家。他晚上要回到那个房间睡觉,早晨要从那里出发。他们连喝了三杯酒。第一杯酒他祝她像阿黛琳一样永远二十九岁;第二杯酒她祝他有个好身体,有个坏记性;第三杯酒他们一起敬了被他们赶走的麻雀,剥夺了它们吃樱桃的权利。三杯酒都是一口干掉,过去还没有这样喝过酒呢。
太阳明晃晃的,她又燥热起来,就把风衣脱了。裙子是淡绿色的,和环境很配。她画了几十年画,对颜色有绝对的信心。
她不确定,是该了结了吗?她抬起头,看见远方的马群奔跑起来。风声、马蹄声、马群嘶鸣声、绶带鸟的啼叫声一起奔涌过来,河谷里的小溪流漫延成了一条大河,汹涌着,河流漫过了她的鼻尖,她有些醉了。
竹竿上白纱巾微微飘动,好半天都没有鸟飞过来了。也许她就是想找个人说一说,他只是一个倾听者,什么也不会改变。河谷里的风吹过樱桃树,他有些希望那群麻雀再飞过来,他也变成了一只麻雀,他们一起站立在樱桃树枝上啄食樱桃。
他的电话响了,家里的电话,他接了。家里没有酱油了,让他晚上回家时带点酱油回去,要买那种无添加剂的。
回城的时候,老李不放心,一再交代进城了就叫代驾,喝酒开车很危险的。他答应着,她固执地要坐在车后排。她尽量装成一个情绪稳定的成年人。好吧,也许这样挺好。等回到家里,老婆已经做好了饭菜,他坐在饭桌前正准备吃饭,一滴鲜红的血从鼻孔里流出来,滴到碗里白花花的米饭上。接着是第二滴。他赶紧把头仰起来,血从里面回流到口腔里,有一股腥味。老婆赶紧拧了一条湿毛巾,垫在他的后脑上。他睁开眼睛,看见客厅的吊灯突然旋转起来,恍惚中他看见绑在樱桃树上的竹竿,白纱巾还在上面飘着。
他们把白纱巾忘在竹竿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