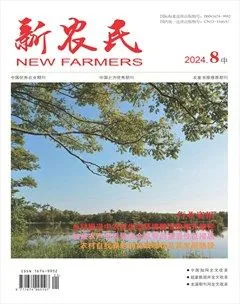农村自我养老的实践现状及其发展路径
摘要:农村老人由于制度设计的历史遗留问题,在养老服务方面所获得的支持远远不及城市,导致农村自我养老现象十分普遍。但学术界的研究往往集中在家庭养老、机构养老等方面,而较少对其展开单独研究。因此,本文选取无锡市G村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无锡农村自我养老的现状、特点,分析该模式的发展困境,分析困境形成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改善农村自我养老现状的对策建议,以期促进农村自我养老的发展,达到老有所养的目标。
关键词:老龄化;自我养老;农村养老;发展困境
当前,我国农村社会已经进入人口老龄化的快速发展期,老龄化进程正在逐年增加。在这庞大的老年人口中,约有60%的老年人生活在农村,农村老龄人口比例远高于城市地区,老龄人口问题也比城市地区更加严峻。数量庞大的老年人口激发了对老年保障需求的持续性增长。然而由于传统家庭保障不断弱化,社会保障供给严重不足,使得自我养老成了当前农村最主要的养老方式。因此,本文选取无锡市G村进行调研,分析农村老人自养资源的来源、农村老人在其自我养老过程中可能存在怎样的困境,并提出政策性建议,以期促进农村自我养老的持续健康发展。
1 农村自我养老资源的获取
1.1 经济来源
由于无锡较早地进行了工业化,大部分农村居民都有进厂务工的经历,因此在达到退休年龄后,享有职工养老保险,每人每月有2 000元左右。此外,没有退休金的农村居民也可以领到1 000元左右的农保。尽管无锡地区的农村居民基本上都能领到一笔能保障日常生活的养老金,但是他们只要在身体允许的条件下,积极参与到当地的第二、第三产业的生产。
由于东部发达城市农村与中西部地区农村发展存在巨大差异,因此,中西部地区最为重要的自养方式“以地养老”在东部地区农村并不适用,多数老人已不再依赖土地为生,因此,土地在东部地区的养老功能并不显得特别突出[1]。根据调研资料显示,上面案例在当地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因此无锡农村自养老人经济来源主要由三项构成:
1.1.1 养老金或农保
无锡农村老人在达到一定的年纪后就能每月领到相应份数的养老金或农保。无锡市居民养老保险基础养老金标准在2021年调整至每月585元,而在参保的老人中,养老金基本上都在500~600元,少部分被征地农村老人保养金为1 080元,极少部分退休职工养老金高达 2 000~3 000元。
1.1.2 务工收入
在G村,高达九成的老人依然积极投身于各类生产活动,而余下的十分之一则因身体条件所限或子女的顾虑,未能参与劳作。这些老人主要是去绿化队、附近小区当环卫工等,有时社区也会提供一些适合老人的岗位,如在村上发宣传单之类,这些工作的日薪都在100~150元左右。
1.1.3 经营收入
在G村,除了以上两种经济来源方式,还有小部分老人从事着一些经营活动。这些老人主要是个体经营,主要是开店或者凭借自己的手艺,外出做一点木匠、漆匠之类的零工。这类人工作比较灵活,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安排工作。
1.2 精神慰藉
老人的精神状态好坏,是老人能否进行自我养老的一个重要因素。根据调研结果显示,自养老人的精神慰藉主要有三个来源:
1.2.1 家人陪伴
在调研过程中,大部分老人表示亲人的陪伴对他们来说是最为重要的。但是由于子女忙于工作和生活重心向第三代转移,他们能够陪伴老人的时间仅仅在周末或者是只有一顿饭的时间。尽管如此,大部分老人表示他们从与子女互动中感受到的情感与精神慰藉是其他活动所不能比的。
1.2.2 熟人社会
许多学者指出,社会交往与老人精神慰藉需求存在正相关,社会参与、交往频次越高,获得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收益也会更大。因此农村老人间的日常社会交往是老人实现精神上自养的重要途径之一。在调研过程中。G村许多老人表示,邻里间的互相倾诉、陪伴是她们缓解孤独情绪的最主要的方法。
1.3 生活照料
在当前空心化程度严重,村庄只留有老人居住的情况下,大多是老年夫妻互相照料的养老模式,子女在老人生活照料方面比较缺失,尤其是只有儿子的老年家庭更是如此,丧偶老人只要没有瘫痪情况,也是自我照料生活自理,只有极少数卧床瘫痪老人由同样是老年的子代照料。此外,在当前阶段老年群体通过长期的互动与交往,在乡村社会中形成了深厚的守望相助的默契关系。在村庄中,邻里与亲友之间彼此扶持,共同应对生活中的挑战与困难。这种对日常生活中细微难题的及时响应与解决,有效地保障了大部分具备自理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老年人在乡村中的稳定生活[2-3]。
2 农村自我养老的特点
2.1 “开源节流”式的自我积累
当地的老年群体,在通过多元化的方式进行了养老资源的积累之后,却普遍选择了一种“开源节流”的生活方式。他们的主要生活开销包括医疗费用、日常生活开销以及人情往来费用三项。在医疗费用方面,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或多或少都会患有一些慢性疾病。为了维持身体健康,老人们每月都需要购买固定的药物,即使经过医保报销,平均每月仍需花费200~400元。若不幸罹患如癌症等重大疾病,则治疗及药物费用更是高昂。至于日常生活开销,主要集中在饮食方面,当地老人的饮食相对简单。平时,他们只有在周末子女回家时,才会上街购买新鲜的蔬菜和肉类。此外,人情往来费用也是一项重要的开支。在当地的村庄中,人情和亲属关系的维护主要由老人们负责,每次的人情往来费用在500~1 000元。以上所述开支,均为维持老人个体生活所必需的物质资源,属于他们的“刚性支出”。然而,老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却严格遵循“能省则省”的原则,如夏天能使用风扇便尽量不使用空调,能看清楚便尽量不开灯。他们普遍认为,现在所节省的每一分钱,都是为将来无法自理时所做的准备,现在多节省一点,未来就多一份生活的保障。
2.2 熟人社会的支撑
以血缘认同和村落共同体认同为基础的村庄熟人社会是老年人自养的社会基础。不同于城市通过相对充足的公共服务资源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支持和保障,农村能够利用内部的人力资源和社会性基础实现养老服务的自我供给[4]。一方面,现阶段老年人在长期互动中形成了守望相助的默契,村庄中邻里亲友能够互相帮助克服生活中遇到的困难。老年人在串门聊天的同时也能够了解对方的身体状况,当发现个别老年人在洗衣、做饭等方面存在困难时其他村民会主动伸出援手。往往对日常生活中小困难的解决就使得大部分有自理能力和行动能力的老年人实现了稳定地以村生活。另一方面,村庄老年群体内部的互动和关联,实现了村庄内部资源的整合与动员。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大部分务工老人的工作机会都或多或少与“熟人”有关,例如一个绿化队里的老人,都基本上是附近几个村庄的,他们通过熟人互相介绍获得这个工作机会。
2.3 自养风险性较强
自我养老风险性较强。首先是老年人自身的身体状况。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逐渐下降,可能面临各种慢性疾病和突发疾病的困扰。这使得他们在自我养老的过程中,一旦遭遇健康问题,往往难以独自应对,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由于农村地区的自养老人普遍对保健知识缺乏了解,对医院的繁琐检查和费用心存畏惧。他们往往只注重日常劳作,只有当疾病严重影响到正常生产生活时,才会选择就医。这种对健康风险的低关注度,无疑增加了自我养老的风险性。同时,由于老人的知识水平较差,对于作为第三支柱的储蓄型养老保险认知度较低,加之本就普遍不富裕,部分代际资源甚至要流向子代,许多老人缺乏养老资金的储备,更别谈养老规划了。因此,从整个养老生命周期来看,自养老人在养老决策上普遍缺乏风险意识和规划。这使得他们在面对健康、经济等多方面的风险时,往往处于被动和脆弱的境地。
3 农村自我养老模式的困境
3.1 身体健康状况堪忧
老年人的健康是顺利自养的前提和基础。如果老人的健康下降或生病,他失去了工作的能力,或者不能自己耕作意味着他们将提前退出自养阶段,日常生活将依赖于子女。他们不仅要忍受自己的疾病,还要面对自责。农民的经济来源大部分是出去务工获得的报酬,而现在他们身患疾病被困在家里,这必定增加了子女的负担。这些负担也将以其他形式传给老年人自己:子女的不满和照料时的抱怨,这将增大他们的生存压力。因此,农村老年人的健康不仅关系到他们的日常生活水平,而且是关系其生存的基本因素。在农村,老年人身体透支,其生存风险逐渐在升高。
3.2 代际理性化增加第二阶段生存风险
随着代际关系理性化,亲子关系不再是传统的“反馈式”。目前代际互动中的互惠交换与过去不同,老人并不能在养老阶段及时得到子女的反馈,甚至还要面对“代际剥削”,对经济不富裕的老人来说也是不能接受的。因此,避免与子女过多接触,减少与子代间的代际资源交换,以经济独立为主要特征的自我养老是解决家庭问题的一个出路,但是这仅仅适用于老人有自理能力和劳动能力的第一阶段,但在第二阶段,他们的生计依赖于孩子,有些子女会拒绝这一阶段的赡养,因此老人可能会出现生存困境。
3.3 家庭主体情感传递不足
当前“出门一把锁,进门一盏灯”是我国农村老人真实的生活写照。由于社会转型和代际关系理性化,大多数子女都进城定居并且将重心转移到第三代,很难兼顾自己的父母,老年人难以享受子孙满堂的天伦之乐。此外,与城市相比,农村的文娱活动较少,老人的文化生活比较单一。这些扑面而来的双重不良情绪需要他人的陪伴和帮助才能排解,农村老年人难以在情感慰藉上实现独立。
3.4 各主体支持力量薄弱
首先,针对农村自养老人的政策较少,关注度较低。一方面,农村极大部分自养老人都还没退出劳动力市场,而是进入到当地的第二、三产业,但是,都以零工或兼业为主,并未签署劳动合同,所以,以劳动契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保障制度,对这部分老人来说并不适用,因此,老人也将面临不公平的待遇和更高的风险。另一方面,农村自养老人比城市自养老人更需要政策层面的关注,但是养老政策经常向城市老人倾斜,从而导致养老资源也流向城市。其次,社区对农村自养老人支持力度不强。除了小部分特殊的老人外,许多自养老人表示社区对他们的自养生活并没有帮助,也不知道社区能够提供哪些服务,由此可见,农村社区对老人的养老生活支持力度并不强。最后,缺少社会组织。据G村村民介绍,从来没有志愿者或者正式的社会组织来这里对老年人进行服务。
4 农村自我养老的发展路径
4.1 转变传统养老观念
一是重塑老人的养老观念,积极树立自我保障意识。最有效的老年保障并非依赖于他人或社会的临时援助,而是应在年轻时便明智地筹划与积累老年所需的资源。老年人作为这一保障的主体,从思维、情感到行动,都应树立自我保障的意识。二是弘扬“孝文化”。孝道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在于对老年人的尊重与支持。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子女的关爱对于提升老年人的自我养老能力具有积极影响。子女关怀程度越高,老年人的自养能力便越强。然而,自养并不意味着子女可以完全推卸养老责任,反而应当感激老年人所展现的理性与体谅,并在其自养阶段提供必要的支持。为了使农村自养老人获得最基本的精神慰藉,子女应增加与父母的沟通频率,营造温馨的家庭氛围,进而促进家庭关系的和谐与团结。这样的举措不仅能让老年人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还能为他们提供生活的动力和希望。
4.2 加大政策关注力度
一是要完善乡村养老服务体系,必须强化基本医疗服务,提升自养老人健康水平,增强其自我养老能力。针对“就医难、贵”问题,加大农村卫生保健投入,优化医疗服务布局。同时,扩大医疗保险赔付范围,增强老人卫生风险意识,提高参保率,减轻因病致贫风险。二是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和新农保制度,提高覆盖率,优化参保流程,增强参保意愿。加强对自养老人的关怀,结合社区信息和个体状态精准施策,提供制度支持。国家应制定符合地方实际的养老政策,建立激励与监管机制,确保政策有效执行和服务持续提升。
4.3 充分挖掘社区的支持作用
在养老问题上,社区作为家庭与国家、社会、市场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媒介,培养其能力有助于应对复杂问题,促进各类主体之间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首先要培养专业人才。社区作为基层单位,在养老服务供给过程中,需要配备与之相匹配的专业人才,根据社区具体需求选择人才类型,并对其进行创新能力和专业能力的培养。除此之外,还需要在社区中发掘并加强志愿者的力量,以此促进社区养老能力更深更广地辐射到更多老人。其次加大资金支持力度。除了社区的经济收入和公共服务基金之外,还必须接受政府的拨款、经费和补贴,以及社会企业和个人的捐赠等。最后是重建农村社区的社区功能,促进农村社区的精神实现自我关怀,社区观念的构建是实现自我关怀的坚实基础。不断提高老年人精神慰藉,努力推进农村社区公共文化建设,给老年人提供便利的条件能够参加到社区文化活动中。
参考文献
[1] 孙敏.大都市近郊“自主养老”模式的机制分析——以上海市近郊W村为考察中心[J].南方人口,2017,32(1):48-57.
[2] 李怡.无锡农村自我养老的实践形态与支持机制研究[D].无锡:江南大学,2023.
[3] 王婷.我国农村留守老人自我养老的困境及对策研究[J].西部财会,2022(12):64-67.
[4] 周佩萱,陈辉.农村老年人自养秩序:主观意愿、现实条件与实践样态[J].内蒙古社会科学,2023,44(2):171-1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