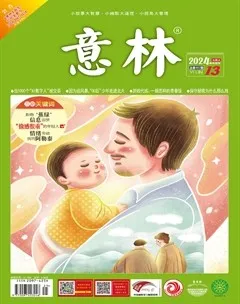因为追风暴,“00后”少年走进北大
2020年,风暴摄影师刘屹靖正式开始追逐和拍摄风暴。至今,他已经跑了8万多公里,拍摄了五六百场强对流风暴。
在刘屹靖的镜头下,风暴诡谲绚丽、触目惊心,而在气象作品背后,风暴又切实地给人类带来灾难。从最初只为艺术创作,到后来致力于科普,刘屹靖的内心逐渐发生变化。
以下是刘屹靖的讲述:
1.“与生俱来”的兴趣
我出生于江西南昌。据母亲所说,在我很小的时候,她给我买了一大堆小人书、动漫书,还有一些关于自然和气象的书。
当时,我就对一本叫作《风力歌》的书爱不释手,每天晚上睡觉前都要母亲读给我听。
4岁左右,我已经能看懂一些简单的字和图片。因为特别喜欢这本书,直到每一页都被翻烂,我才把书丢进垃圾桶里。可能我与生俱来就对气象学比较感兴趣。
还在上幼儿园时,我就非常关注天气变化,吃晚饭的时候爱看电视上的天气预报。
上小学时,同龄人都在看动画片,但我更爱看自然和地理类的纪录片,比如《动物世界》和《地球脉动》。那时,我对整个大自然中变化迅速的、充分调动感官的事物都感到新奇。在南方,大雪很罕见。每年冬天,我的心里都会期望下一场大雪。
进入初中,我的兴趣完全集中在气象学上,加入了一些兴趣群,找到了志同道合的朋友,逐渐接触到一些专业名词。
我上高中后,兴趣开始集中到研究强对流风暴天气,尝试读和风暴相关的大学教材、专业论文等。彼时,我开始运营气象科普类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布信息和文章,提醒大家注意天气变化等。

高二升高三的暑假,我被南昌市气象台邀请参加了气象会商活动,跟台里的专家、老师们一起讨论未来天气该如何预报、它的极端性有多强等。
这次参与气象台的活动后,我就下定决心要报考气象专业,将来成为一名气象预报员,对天气进行研判和预测。
然而,就在高三,我为了梦想冲刺、成绩刚有起色的时候,被查出患上慢性结肠炎。
2.生命中的一道光亮
我度过了一段十分无助和艰难的时光。某一天,我从卧室朝南的大窗户向外望去,看到几公里外有一团非常强的风暴。
当时我的肚子很痛,想找些事情转移注意力。于是,我翻箱倒柜找出2012年家人买的一台相机,想尝试拍一下闪电。
那时我还不会专业的摄影技术,只知道乱按快门,按了一两百次后,还真的抓拍到十几条闪电。我从中选取了9张照片,发到微博上,没想到当天晚上就火了,南昌本地的媒体报道,很多气象官媒也转发,第二天还登上中国天气网的图片头条。
这次经历在我心中埋下风暴摄影的种子。我开始自学摄影知识,并尝试把气象和摄影结合在一起。
我在南昌尝试过很多次拍摄,熬通宵去等凌晨袭来的风暴。幸运的是,大部分都拍摄成功了。这让我坚定了走风暴摄影的道路。
于是,我掏出积蓄,带着器材,准备去内蒙古大草原上追一次完整的风暴发生过程。
2020年7月,我收拾好行囊,来到内蒙古,开始正式追逐风暴。之所以选择内蒙古作为拍摄地点,是因为草原阻挡少,路况好,天气比南方干燥,能见度也更高。
追风暴前我会做很多准备。首先就是看气象资料,确定风暴所在区域,在其中选一个比较好的城市作为中转点。拍摄前,我会去大型超市买物资,之后会一直在野外奔波。
对我来说,自热米饭是最方便好吃的食物。我有一个物品清单,上面写了三四百件东西,从相机到三脚架再到各个零部件。我每次出门拍摄,都像搬一次家。
当天拍摄时,我会参考实况气象资料,比如卫星云图、气象雷达图等,实时观测风暴具体的强度、移动方向、位置和形态变化。
追逐风暴的成功率并不是100%的。在早期,因为经验不足,我曾经判断错了风暴的状态,觉得它还能够维持,等跨越一两百公里到那里时,风暴已经消失了。
3.我觉得应该去做点什么
第一次在内蒙古拍摄风暴,我花费了5天时间,效果不是特别好。于是2020年8月,我又去了一趟呼伦贝尔,成功拍下了一团巨大的风暴。
当时,一道悬在空中、像长城一样的乌云墙出现在草原远处,慢慢地扫过来,特别震撼。
为了拍摄到完整的风暴,我在原地等到最后一刻,当看到大风在几公里外扬起一道沙墙,想要赶紧收拾拍摄器材时,已经来不及了。
风速很快,一下子就扑了过来。相机还没收好,就被直接拍在地上。我被吹到完全站不稳,开始只能蹲在地上,后来死死抓住越野车边缘的行李架才没被吹跑。
这样的经历还有很多次。那次拍摄完后,我又前往乌兰察布继续追风暴,碰到整个2020年我拍过的最强风暴之一——超级单体雷暴。
超级单体雷暴最为少见,却是最强大的一类雷暴,可以产生各种各样的灾害性天气。那次雷暴,伴有乒乓球大的冰雹,要不是上车及时,可能我的头都要被砸破了。
当晚,我遇到对我职业生涯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暴雨冰雹过后,天空中出现了非常壮观的火烧云,我一直在外面待到晚上,拍摄完整个过程。
一群牧民看到我,跑过来问,小伙子你是谁?我说我是风暴摄影师,在拍风暴。
牧民脸色大变,带着哭腔,用非常着急的语气对我说,你们这些摄影师要多拍一下我们,你知道今天下午的冰雹多严重吗?把我们种了一年的庄稼都打坏了。
听到这里,我已经有点蒙了。其实,我一直沉浸在追逐震撼景观的兴奋里,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事会对一个个活生生的人产生多大的影响。
从那时起,我觉得我应该去做点什么,于是想起了科普。
2021年年初,我开始尝试结合科普知识,在摄影作品中标出风暴的名字、特殊结构和对应的灾害性天气等,没想到作品的浏览量出现指数级增长。
我意识到,这种形式的作品不仅能够将科普知识更好地传播出去,也能呈现出多维度的价值,受到大众的喜爱。
当年,我拍摄的一张超级单体雷暴作品直接登上SCI期刊的封面。我因此受邀去北大等高校院所做学术报告和讲座,2022年至今,还参与一个科学研究项目。
虽然我对自己的终极定义还是风暴摄影师,但我已经可以承担起更多的社会责任,让人们更加了解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