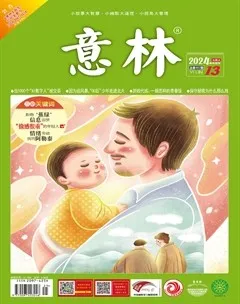你也可以勇猛地老去

过去一段时间,我每天上午都固定在一家咖啡馆喝咖啡。这让我明白,谁是这家咖啡馆最“活跃”的顾客:一位80岁左右的女士,不但经常来,而且很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
昨天,她在落座的时候有点忙乱,把咖啡杯碰倒了,大喊一声“shit”,服务员赶紧给她续了一杯。
她总是一个人过来喝咖啡,摇着自己的轮椅。在开门的时候,会有一些困难,有人帮她开门,她会大声感谢。
如果碰巧没人,她要花上两分钟,才能进来或者出去,慢慢消失在街头。她一定住在附近,可能是刚从一场病中恢复过来,要在轮椅的帮助下恢复行走。
当然,也有可能,轮椅就是她的日常工具——在百老汇街头,经常看到老年人自己摇着轮椅。也有一些老年人坐在电动轮椅上,一个人前行。
很少看到有人推轮椅,这大概是此地特色:子女都不和父母住在一起,只是偶尔过来探望,老年人都“顽强”而“独立”地活着。
开始我不太喜欢她,因为她用目光和你接触,逼迫你和她讲话,而且她经常要调换座位,以方便和“朋友”聊天。
有一次她帮一个朋友占了座位,结果那位绅士来了,她一直在和旁边的人聊天。但是时间久了,反而觉得她的热情中有一种动人的东西:这家咖啡馆可能是她最后的“世界”了。
好友的母亲住在波士顿,患癌症已经好几年。不久前她再次住院,这一次是胃出了问题,无法进食。
她住的医院几乎是美国最好的,但是医生建议放弃治疗,转入临终关怀中心:不能正常进食了,人的生命就无法真正持续,再靠输液维持意义不大。
朋友非常悲伤,作为中国人,她不能接受这样的现实,因为已经预约了进一步的癌症治疗,医生说可以尝试最新的试验药物。
朋友坚持给母亲治病,而神奇的是,过了几天,母亲胃部的状况好转了,又可以从临终关怀中心转到癌症治疗病房。
但是很多美国老人,在这一步就停留在临终关怀中心了。两个社会对“生命”的理解就是如此不同。
我们会认为父母和子女是“一体的”,而美国人更多把生命看成“个体选择”。很多老年人情愿过一种更有尊严的“最后时光”。
这位经常来咖啡馆的老太太,如果有几天没来,我就会担心她的生命可能终结了。
她的“那一天”大概真的是这样的,不能去咖啡馆和人聊天了,也就该和世界告别了。所以,她很珍惜在咖啡馆的每一天,发自内心地关心着每一个陌生人。
有一次我去布鲁克林看望艺术家贝西·达蒙(Betsy Damon),她在20世纪60年代读过哥伦比亚大学艺术系,是成都活水公园的设计者。
不久前,她在一场活动中遭遇腿部骨折,我见到她的时候,她躺在沙发上,腿部绑着石膏,哈哈大笑着和我握手。
但是,当我表示想看她最近的创作的时候,她竟然能够起身,拄着拐杖,上了楼梯,说“走,去楼上工作室”。
她的女婿、儿媳妇那天也在,和我一样站在旁边看着,没有上去扶她。我们都很开心,因为在她身上,我们看到了生命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