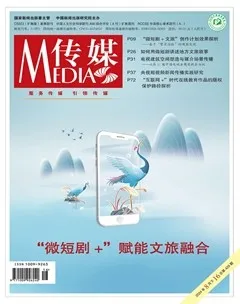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认同与建构
摘要: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并取得了巨大成就,本应为全球提供“中国经验”的中国脱贫故事却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遭遇认同危机。文章对关于中国脱贫事业的西方媒体报道内容进行分析发现,西方世界对中国长期存在认知缺失、双重标准,以及社会、文化、制度等因素的差异都是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出现认同困境的问题所在。从新修辞中的认同理论视角出发,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应以真实为基础,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以人类思维、价值理性、文化增值作为关键策略。
关键词:中国脱贫故事 国际传播 认同困境 国家形象构建
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的第一个目标就是“消除一切形式和规模的贫困”。我国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完成了消除绝对贫困的艰巨任务,也是全世界第一个实现联合国制定的“贫困人口减半”千年发展目标的国家。而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已向超过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派遣不少于60多万援助人员,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这份成就不仅是中国对自身贫困问题解决的答卷,也是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下向全球消除贫困难题所贡献的“中国方案”。作为“世界脱贫故事”一部分的“中国脱贫故事”具有全球性话题属性,它是向世界展现中国能力、行动、姿态、善意和形象的绝佳议题和途径。本研究以“认同”概念为线索对西方媒体对中国脱贫故事的报道以及深层原因进行阐释与分析。
一、国际媒体对中国脱贫成就的报道概况与认同困境
中国脱贫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是举世瞩目的,世界各大洲的媒体都在关注中国的脱贫攻坚胜利,并对其进行了多元化的报道呈现。
1.国际媒体对中国脱贫故事的正向宣传。在关注中国脱贫攻坚胜利这一重要议题时,大部分国际媒体给予了相应的正面报道。2021年2月28日,新华社国家高端智库面向全球发布《中国减贫学——政治经济学视野下的中国减贫理论与实践》的中英文双语报告,解读了中国特色反贫困理论。在《报告》向全球发布的当天,海内外全媒体、全渠道浏览量突破10亿次,在全球广受关注和赞扬。此外,西班牙《国家报》网站、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荷兰《忠诚报》、德国电视一台《世界明镜》节目、泰国《曼谷邮报》、瑞士《新苏黎世报》网站、肯尼亚《旗帜报》、比利时弗拉芒语版《今日中国》、阿根廷《方向》杂志与柬埔寨《高棉时报》等多国媒体都对中国脱贫的措施、经验及取得的成果进行了积极报道。
2.部分西方媒体对中国脱贫故事的曲解。反贫困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大事件,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所称的“最美好的故事”。然而,在西方媒体中却充斥着质疑和曲解之声,甚至不惜违背新闻真实性原则,编造谎言、恶意诋毁中国。例如,美国《纽约时报》曾刊登一篇题为《工作、住房和牛:中国为消除极端贫困而开销巨大》的文章,尽管彼时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且即将达成目标,但该文章却选择视为不见,武断地质疑中国脱贫项目投资“耗费高昂”和“不可持续”,偏见地认为对一个超过14亿人口的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印度评论员Maitreya Bhakal对西方主流媒体有关“中国脱贫故事”议题的报道进行了统计分析,发现西方媒体对中国脱贫故事的报道带有明显偏见,报道手段展露出心理学“悲伤五阶段”特征:否认(Denial)、愤怒(Anger)、讨价还价(Bargaining)、沮丧(Depression)、接受(Acceptance)。可见,西方媒体的蓄意曲解昭然若揭。
3.中国脱贫故事的认同困境。在新技术带来的全球化和个人主义兴盛的后现代语境中,我们日益理解每个主体所认为的现实可能并不是唯一真实的现实。对于生活在其中的人而言,“中国脱贫故事”即其生活经历的真实映照,但对于中国之外全球的他者来说,“中国脱贫故事”可能更多的是社会性建构的现实。在西方世界零和博弈的心态下,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中存在认同困境。国际社会对中国存有误解和曲解原因主要来自五个方面。一是外国民众对中国缺乏深入认知。二是某些西方媒体对中国施以双重标准,负面报道中国的框架成为惯性。三是某些外国政客对中国的阐释带有“先验性”色彩。四是中西新闻运作模式不同造成的误解,表现在新闻理念、写作方式、新闻作品用引语说话的方式不同等方面,西方媒体以中国媒体为政府服务为由,不信任中国媒体的消息来源,从而对中国媒体报道的新闻产生误解。五是某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成就存在事实曲解与文化差异,是中国脱贫事业在国际社会中出现认同困境的表象,而真正的困境在于中国在面对曲解与差异时如何提升自身的传播效能。
二、认同理论与叙事的认同修辞功能
国家形象与认同建构是一项系统性工程,更多的是“体”层面的议题,但没有“术”的中观操作,再正确的宏大理论也无法落地。因此,需要聚焦国家形象与身份认同在“术”层面的探讨,即以建构主义作为视角进行审视。中国脱贫议题作为国家叙事若想完成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实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国家形象的塑造任务与效果,可以在话语修辞方面加以努力,在世界文明史意义上让他者理解“全球中国”。
1.认同及其修辞策略。修辞学家沃尔特·费希尔(Walter Fisher)在《作为人类交际范式的叙事》中提出了“叙事范式”:世界由故事建构而成,我们必须在选择叙事方式以获得美好生活。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话语修辞的问题。而“认同”是当代新修辞学中一个重要概念,修辞学家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提出的“认同理论”蕴含三种构建认同的修辞策略:对立认同(identification by antithesis)、同情认同(identification by sympathy)和误同(identification by inaccuracy)。对立认同是双方面对相同或类似的问题时因选择一致而达成的共识,即通过“分裂”而达成“凝聚”。同情认同是双方在相同特性和相同境地中在情感方面形成“同一”即产生情感共鸣之后的认同。“认同”实际上是对旧修辞学中核心概念“劝说”的一种扬弃,它们之间的差异被视为西方新、旧修辞学的分水岭。新修辞学改变了“叙述者单向对受叙者进行叙事修辞”的观念,转向强调传受双方互动以达成“认同”的观念。从新修辞学视角看,“认同”并非一个本质主义的概念,而是一种话语的实践,在“叙事范式”中,“认同”是叙事中修辞选择的原因或目标。
2.叙事的认同建构。“叙事”“修辞”“认同”三个概念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在《叙述学词典》中,“叙事”是“由一个、两个或多个叙述者向一个、两个或多个受叙者传达一个或更多真实或虚构事件的表述。”用传播学5W框架分析,其中的“事件”是通过表述或话语进行传递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修辞的过程,而此过程最终期望得到的传播效果或对“事件进行表述的目的”就是为了构建“认同”。这一过程可以被概括为“叙事的认同修辞功能”,伯克“认同理论”中的三种认同假设是对这种功能较为全面的总结,中国脱贫故事报道案例成功的原因是在报道中采取了一种或多种叙事的认同修辞策略。例如,专题报道《诺奖得主尤努斯精准扶贫到河南》和《黄河滩区脱贫大迁建》采用了对立认同的修辞策略,通过凸显脱贫难题的地方性与世界性,将中国与世界统一在一条战线之上。专题片《摆脱贫困》采用了同情认同的修辞策略,通过微观视角和细节刻画达成了情感共振。融媒体内容产品“中国那些事儿”则采用了多元化的修辞策略,以借船出海、借嘴说话的方式将“他者”声音进行了整合传播,营造出了国际认同的舆论氛围。
3.中国脱贫叙事认同的修辞要求。肯尼斯·伯克认为,共鸣与认同是一种修辞行为,人类关系确定和行为互动均由意义决定,而意义的产生离不开语言修辞。从修辞学视角看国际传播,讲故事是为了让自己与他者理解我们的生活和世界,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故事要讲,尽管各具合理性,但位置、视角和立场不同,每个国家对现实的解释各有不同。因此,在中国百姓真实生活经历的基础上,从全球他者的视角出发,建构“中国脱贫故事”的社会性现实,是讲好“中国脱贫故事”的基本前提。“说什么”是故事,而“谁来说”“对谁说”“怎么说”“在哪说”“何时说”都考虑到才算“精彩表达”。为此,叙事者应从新修辞范式的“认同理论”视角和“叙事的认同修辞功能”出发,在叙事中通过客观真实的话语让对方参与互动,进而构建某种程度的认同是可以实现的。
三、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认同”建构
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实践中的“认同”建构主要体现在:从“种思维”到“类思维”、用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避免“文化折扣”和追求“文化增值”三个方面。
1.从“种思维”到“类思维”。网络社会的崛起正在导致传统合法性认同逐渐瓦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理念的提出就是要重新定义“我”与“我们”的关系,将“我”与“我们”从一种对立状态的“种思维”观念转换为“类思维”观念,即我们都是人类。在全球脱贫实践中,人类需要团结,以让中国和世界人民对贫困问题和脱贫难题认知、关心并采取行动作为脱贫故事的修辞目的,自然能够构建发人深省的信息场景。例如,山东广播电视台系列报道《黄河滩区脱贫大迁建》,记者通过跟踪采访、蹲点采访,抓取迁建重点之处,还通过丰富的视觉和文字修辞展现细节,精准聚焦人类同自然灾害博弈的时代脱贫故事,其中“不得安宁”“提心吊胆”“繁衍后代”这几处细节描述直击人心,这样的新闻话语正是“类思维”的体现。将“搬迁”作为解决区域贫困的方式,在BBC的报道“Has China lifted 100 million people out of poverty?”中也得到了认同,即“The government has relocated millions of people from remote villages into apartment complexes. Sometimes these were built in towns and cities, but sometimes new villages were built near the old ones.”“黄河”是世界知名的河流,“洪涝灾害”是全球性的自然灾害,“搬迁”是脱贫的一种方式,这种“坚持人类优先”的“类思维”就是中国同世界共通价值的基石,是在传统合法性认同式微中无法抹去的价值理性光辉。
2.用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现代社会中,人们对工具理性的追求将个人的主体性无限放大,人从目的变成了手段,除“我”之外全是“他者”,工具理性的膨胀正是现代世界各种分裂思想和危机的根源。“同情认同”意指双方在相同或相似的情感基础上实现的认同,即思想观念或道德价值的一致。人性的基本感情价值在全世界基本相同,新华社在海外社交媒体中发表的英文稿件“Unveiling 12 years of miracles in an all-girls high school”在当天海外媒体中的中国新闻点击量第一。用“Zhang Guimei”为关键词在Twitter和Facebook等海外社交媒体中进行关键词搜索,评论几乎全都是因同情而认同。记者庞明广表示:“典型人物绝不仅适合于对内报道,其精神内核和散发的人性光辉同样能感染海外读者,进而向世界讲述中国脱贫故事,展现中国脱贫成就。”
价值理性是国际传播的基石,传播者无论用何种修辞方式,实际上都在迎合传播对象的道德标准。算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网络信息技术重构了全球国际传播的结构,谣言、假新闻、后真相充斥其中,传统媒体在网络时代的多元竞争中声量也逐渐式微。在当今多元化的国际传播中,如果我们的媒体在讲述中国脱贫故事时依然仅以工具理性为标准的话,如果脱贫故事的国际传播过于追求合理、有效与真实的工具性,那么诸如算法带来的所谓“个性化”推送只会进一步固化刻板印象。在脱贫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叙事者既要充分认识到工具理性的局限性和片面性,又要充分意识到价值理性中情感和情绪的重要性,以价值理性驾驭工具理性。
3.避免“文化折扣”和实现“文化增值”。在大众媒体的叙事中,修辞者经常用“我们”代替“我”,将每个人都带入语境之中,从而让受众达成了一种无意识认同即所谓“误同”。国际传播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尤其在碎片化阅读和多层级的转发后,“文化折扣”现象频频发生。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过程中,应当遵循传播的基本规律,承认“文化折扣”此类现象的存在,以深入了解对象文化基底为前提,进行本土化内容制作和精准化传播,尤其要对受众文化中的风俗、习惯、传说等民间文化充分了解,谨慎编码,勿踩文化“雷区”,尽可能减少“文化折扣”发生的频率。
“文化增值”指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文化产品在异域获得的传播效果和价值不小于其在本土获得的传播效果和价值。故而,中国脱贫故事在国际传播中的文化增值取决于其所产生的正面影响。在文化增值的国际传播实践中,中国日报网的融媒体内容产品“中国那些事儿”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它立足于“国家站位,以我为主”的基调连接中外,整合海外主流媒体、专家学者、自媒体等多元主体对中国各方面的报道与评价,通过全媒体方式与全球网友互动,借船出海、借嘴说话、借力打力,将国际各界“他者”对中国各种正面评价的声音转播给国内国外全网用户。例如,2024年7月24日中国日报的《海外专家热议中国式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 惠及世界繁荣》等作品针对国际传播中关于中国的舆论热点进行主动作为,传播正面的中国国家形象,取得良好效果。
(作者王天瑞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博士研究生;张开系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战略、流程、效果研究”(项目编号:22ZDA08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张远新.中国贫困治理的世界贡献及世界意义[J].红旗文稿,2020(22).
[2]王慧.论国际传播中国家形象的媒体误读现象[J].新闻爱好者,2012(20).
[3]赵磊.从偏见到共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转变[J].人民论坛,2020(11).
【编辑:杨石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