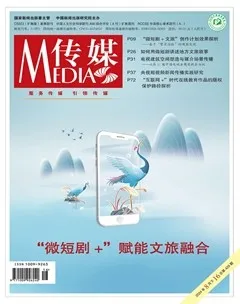华语电影的跨文化传播研究
摘要:电影作为国家形象的展示窗口和意识形态的表达先锋,在跨文化传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本文以“唐探”系列电影为研究对象,基于霍米·巴巴文化杂糅理论,从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与传播受众三个维度围绕文化差异、文化翻译、文化杂糅展开论述,通过对电影文本、创作策略和商业营销的经验总结,寻求一条文化杂糅视域下中国商业电影的跨文化传播路径。
关键词:文化杂糅 跨文化传播 “唐探”系列电影
近年来,中国电影及电影工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并积极探索走向海外的可行路径。在此背景下,以《唐人街探案》为代表的,国外华人聚集区(唐人街)背景融合探案元素的电影成为“时代新宠”。《“十四五”中国电影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电影是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阵地,是深受人民群众喜爱的文艺形式,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标识。“唐探”系列电影因其在商业上的巨大成功和年轻群体的强烈反响而备受瞩目,其作为商业电影在跨文化传播中杂糅混搭的成功经验十分值得探讨和梳理。
文化杂糅理论是印度裔文化研究学者霍米·巴巴后殖民主义理论中的核心内容。巴赫金在语言学中进行了“话语杂糅”的研究讨论,认为“杂糅”就是在一个单一的话语(Utterance)范围内,对两种社会语言的混合。霍米·巴巴和巴赫金都十分注重杂糅过程中异质性、变易性、断裂性的特征,因为文化杂糅的过程不仅包含无意识的融合、统一,而且包含对话性的接合、共生。对于“唐探”电影的研究,此前更多地集中在艺术美学和产业实践两方面,忽视了其作为第三世界的电影文本与西方世界对话交锋的努力和尝试。在“唐探”系列电影跨文化传播中,杂糅策略在传播内容、传播方式、传播受众中得到一以贯之的体现,这一策略的尝试也是民族文化现代化转型进程中的有机组成。
一、包容性的文化差异
霍米·巴巴批评文化多样性是对文化之间差异的绝对化、固定化,文化多样性依赖“认可事先给定的文化内容和风俗习惯”,而文化差异则始终保持着一种对“总体的文化合成的权威”质疑的姿态,强调“表意性的文化边界”。正是因为文化差异在发声层面的话语不稳定性所导致的“暧昧模糊性”,实现了“混杂的身份认同”的构建。“唐探”系列电影借助文化文本的多元、类型元素的复合旨在通过开放的、不确定的意义空间在跨文化传播过程中建构起自身电影文化的身份认同。在这一意义空间中允许文化差异的存在,包容“少数民族文化”、边缘文化的介入。因此中国式侦探片的叙事框架内允许非中国话语、非东亚语境的文化点缀与填充。
1.多元的文化文本。霍米·巴巴的理论主张使人试图超越中心与边缘、东方与西方之间的两极对立——并让人理解其根源。“唐探”电影创作尝试超越有关文化认知与文化价值的二元对立表达,即没有毁弃自身文化传统的特性,也没有对异域文化的强势和差异表现出深刻认同,而是在具有混杂性、居间性的文化文本内部保持一种“暧昧模糊”的立场,以此来获得跨文化传播中的优势。“唐探”系列电影在中国文化传统基础上不断吸纳异域多元文化,从舅舅外甥的血缘伦理到漂泊无定的游子心理,再到街头修面、“突突车”出租的泰国文化;从“一阴一阳”的周易文化、“阴阳调和”的道家文化到“凝视深渊”的尼采哲学等,本土文化与异域元素融合愈加明显。而影片的底层叙事逻辑仍是中国式的,人物设置方面显露出集体主义文化的影响,不论是侦探一方抑或Q组织一方都呈现为群体塑像,迥异于好莱坞电影中个人英雄的单打独斗。
“唐探”系列电影的故事文本有其延续性和互文性,每部影片都会设计一个当地警方代表参与叙事,而警方时常处于一种“暧昧模糊”的站位——忽而成为侦探一方的得力助手,忽而抓捕扰乱秩序的侦探们,但并未将警察这个极具国家文化的符号贴上一元论的标签。故事主旨打破“正义—邪恶”针锋相对的单一叙事套路,巧妙地化用了东方哲学思想“中庸之道”。思诺继父的行凶、美国医生的求生、小林女士的栽赃等都有着复杂的行为动机和难言的内心苦楚,电影借助中西哲学思想的并置建构起超越善恶对立的叙事模式。
2.复合的类型元素。好莱坞创造了类型片,类型片成就了好莱坞。类型元素复合的电影往往试图满足不同的观影爱好者的需求。中国式系列电影也在商业发展中逐渐自我探索和调整,“唐探”系列在“侦探+喜剧”类型基础上,融合了黑帮片、悬疑片以及少量的惊悚片、爱情片等类型元素,将破案推理、幽默搞笑、复仇追杀与追逐戏、打斗戏、枪战戏和飙车戏等巧妙地整合在一起,共同推动故事叙事进展和类型模式成熟。
“唐探”系列通过类型元素的复合以应对文化差异,进而降低西方观众的接受门槛。与此同时,侦探类型片外壳下注入港式喜剧元素,打破了好莱坞电影对类型元素的固化,开启“唐探”自身的中国式电影进程。作品中,唐人街教父闫先生、日本最大帮会黑龙会的六代目渡边胜等人物角色的设置成为黑帮片类型的最强佐证。黄金失踪、杀人取死者器官、渡边胜的嫌疑、小林杏奈的身世等悬念安排和阴暗场景布置、恐怖怪异的背景音乐使用等元素共同构成了惊悚悬疑片的类型特点。这一连串的故事情节和画面细节都在类型元素复合化与杂糅化维度上进行了较好的整合与建构。
二、混杂性的文化翻译
霍米·巴巴反对自由主义将文化多样性指称为一种多元化选择,自由主义的文化观念试图把文化差异标准化、规范化。霍米·巴巴引进了“文化翻译”概念,借助翻译策略实现不同文化间的最大公约。同时,文化翻译的混杂性策略避开二元对立式表述所带来的社会对抗,在协商空间中寻求出现能动性的可能。
1.高语境文化的消解提纯。霍尔根据不同文化在交流传播过程中对语言环境依赖性的高低,将文化划分为高语境文化和低语境文化。一般而言,高语境文化在交往过程中大部分信息多内含于交流者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或潜藏于交际人的内心,因此明显的语言符号负载的信息较少。反之,低语境文化在交往过程中明显的语言符号负载着大部分的信息量。因此低语境文化中的群体更加习惯借助于言语本身的含义力量进行交流。东西方通常在这方面具有非常悬殊的差异,东方文化属于高语境文化,西方属于低语境文化。
中国民间风水作为高语境文化中的典型,经由文化翻译策略被创作人员开拓出碰撞交流的意义空间。“寻龙尺”一词在电影字幕中对应“Dowsing Rod”——西方一种占卜寻水术、探测术使用的棍棒,这两个中西文化符号进行糅合并借助其共通性实现灵活的文化翻译。唐仁在影片中的台词“老美找外星人都用它啦”便是对寻龙尺文化的消解与提纯。在这个复杂的侦探推理游戏中,传统文化不再是缺乏主体行为能力的镜像的东方,而是以古代存留元素介入当下现实环境。
如何让国外观众轻松理解中国式侦探推理,依照霍米·巴巴的主张应找到中外侦探推理文化的最大公约地带。首先,主要角色设置上参照“福尔摩斯+华生”双人组合,“唐探”系列在“唐仁+秦风”双人组合的基础之上又不断加入新的搭档,如宋义、KiKo、野田昊。其次,人物台词多次引用福尔摩斯名言,将歌野晶午《求道者密室》和约翰迪克森·卡尔《密室讲义》的经典作品作为推理依据,导演“引经据典”对秦风的推理过程进行了文化上的翻译和替换,在完成对著名推理作品的致敬中构筑起一个带有混杂性和间隙性的互文语境。利用这一语境将著名作家的推理小说与自导的推理电影实现某种程度上的意义接合,以此来完成对“唐探”推理文化的消解提纯并扩大电影传播影响力。
2.视听语言的模拟改造。霍米·巴巴认为欧美强势文化在全球攻城略地,非西方文化和被殖民者在单一的进步观和发展观的话语体系中被视为落后的、腐朽的和专制的。殖民者以胜利者的姿态相信可以利用文化翻译同化异域文化、征服新的文化地盘。这一行为过程始终伴随着模糊与对抗,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文化求生策略。
“唐探”系列电影在视听语言方面的文化翻译策略正是后殖民主义批评家所提倡的作为文化存活的策略。好莱坞商业电影制作存在不成文规定,即演员表演过程中不得直视摄影机,因为演员直视摄影机意味着将来会直视电影院的观众,从而打破电影第三维度的幻觉。《唐人街探案3》中演员多次直视镜头的画面成为对这一规定的反抗,在电影自身的视觉语法系统注入不确定性和偶然性因素。观众借助视觉观看与银幕建立互动关系,而影像究竟是索取(Demand)还是提供(Offer)则指涉着完全不同的视觉关系与心理结构,“唐探”系列电影中人物直视镜头与观众达成某种直接的互动,或分享戏中笑料,或将观众放置在局外人(侦探)的位置博得理性的关注,是索取意味,旨在向观众提问或“索取”某种情感的、理性的关注或要求与观众拉开审美距离。
电影视听语言方面的模拟改造策略还体现在配乐的使用,中泰美日四国语言的流行歌曲混杂交织配合视觉影像支撑起独特的“唐探”杂糅风格。对他国流行音乐的借鉴和嫁接帮助电影在充满模糊和对抗的协商空间中确立起自身文化身份,《草帽歌》《Welcome To New York》《Heal the World》经由文化翻译——游离、改造、对抗的转化规则下,抛去了歌曲原本的创作背景和意义指涉,被“收编”在“唐探”电影文化系统之内。中国传统的热情好客、世界大同等文化元素,以及现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等政治方案,在整个侦探破案惩恶扬善的故事中经由著名英文歌手泰勒·斯威夫特(Taylor Swift)和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各自广为流传的代表作得到全新的诠释。
三、互动性的文化杂糅
在互动的过程中展示不同文化间的冲突,并实现良好的互动结果,这一结果往往带来杂糅性美感,也使得基于文化冲突而形成的场景描述更贴近现实。“唐探”一方面利用互动性的文化杂糅实现了角色的跨作品联动,另一方面也充分展示了其与第三空间的互动关系。
1.“唐探”IP的互动延续。霍米·巴巴所主张和坚持的身份认同是一种矛盾、协商式的,以及带有不确定性的双重身份和移民身份。“唐探”IP的延续便在艺术创作、商业规律和影迷诉求等众多因素的合力下实现了自身的能动发展。这不再是电影创作者单向、孤立的行动,而是与影迷双向、分享的文化和商业行为。电影的类型化媒介生产是类型生产、营销和消费三者循环往复的过程,电影品牌意识的养成更需要影片摄制方在电影生产上努力。作为成熟的系列电影,“唐探”在好莱坞圆滑的电影发展经验基础上展开了电影发行的进阶探索道路,这便是同一IP的影剧联动宣传。《唐人街探案》网剧基于电影架构的“唐探”世界设定而衍生出新线索,网剧内容独立成章、剧情互为勾连,电影人物偶尔客串,“唐探”文化内涵和主题价值一脉相承,以影院和流媒体两种媒介的协同叙事取代单一的媒介本位,影剧文本的交替拓展与观众形成文化互动。
“唐探”系列在对好莱坞电影产业发展策略的“模拟”中,实现对其颠覆性的反抗,通过本土电影和好莱坞电影商业策略的融合以建立起自身的产业经营模式。为最大限度地打开“唐探”宇宙,在电影设定的基础之上打造全新的故事序列,漫画《唐人街探案不祥的记忆》作为国内首部影改漫,是“唐探”IP尝试的一大创新;针对电影情节开发的侦探解谜游戏《Crimaster犯罪大师》同步上线与影迷达成深度互联;实物文创产品平安福卡包、刺绣文字钥匙链、人物金属胸针等赶在《唐人街探案3》上映前抓住机会,掀起一波营销热度。对“唐探”IP的拓展行动,在对话协商、接纳摒弃、打破重组的过程中,最终形成了复合的多重“唐探”身份。
2.第三空间的协商建构。“第三空间”是一个重要的跨学科批评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爱德华·W·索亚(Edward W.Soja)提出,并在人文地理学中作为一种变革性的方法,激励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对空间意义进行思考,之后在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理论资源的扩充下用作抵抗文化帝国意识形态和颠覆父权中心主义传统。霍米·巴巴提出“在文化翻译的过程中,会打开一片‘罅隙性空间’(Interstitial space),它既反对返回到一种原初性‘本质主义’的自我意识,也反对放任于一种‘过程’中的无尽的分裂的主体”。影片中异质空间和异域叙事风格不期然地命中了霍米·巴巴所规定的第三空间的意义指涉,既非完全意义上的中华空间,也非绝对的他国空间;它既不是完全意义上的中国人的故事,也不是绝对的他者故事,是带有模糊立场、摒弃二元对立模型、呈现出一片间离性的空间,是重新整合华裔或移民身份和他者视角并以此获得最大创作自由度的叙事。
第三空间作为跳出二元对立的接受与拒绝的空间,为来自不同的种族、阶级、性别的受众在自身文化立场出发对所获得的信息进行阈限性的协商提供可能。受众将自身的文化属性与陈思诚导演的“唐探”电影的文化表达进行协商认同和意义交换,建构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混杂空间。豆瓣、IMDB等专业的电影评论网站的建立促进了世界各地“唐探”系列电影侦探粉丝社群的诞生,观众在观影体验和文化认知方面进行互动交流。
(作者单位 常帅武 四川音乐学院传媒学院;李辰系河北师范大学附属民族学院教授)
本文系四川音乐学院社科项目“四川省高校动漫配音人才培养现状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CYXS2022013)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1]HALL E T.Beyond culture[M].New York:Anchor Books,1977.
[2]杨翼飞.陈思诚导演电影的叙事研究——以“唐探”系列为观照[D].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19.
[3]程星梅.从受众角度探究中国电影的类型化发展[J].西部广播电视,2020(01).
[4]生安锋.霍米·巴巴的后殖民理论研究[D].北京:北京语言大学,2004.
【编辑:曲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