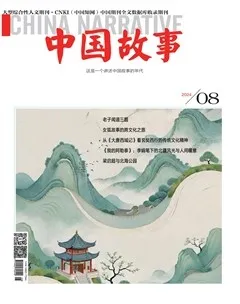梁启超与北海公园
【导读】梁启超自1913年在民国政府任职起就居住在北海团城,后在北海快雪堂创立松坡图书馆。在泰戈尔来华、国内著名学者演讲时,梁启超都邀请其来北海讲学,充分发挥了北海公园启迪民智、教育民众的教育功能,这对北海公园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梁启超在民国政府成立后,曾在政府中任职,其间短暂居住在北海团城,辞职后他积极参与图书馆事业,在北海快雪堂创立了松坡图书馆,并且在北海讲学、集会。本文将通过史料对梁启超在团城生活经历、快雪堂开展图书馆建设等情况展开研究,力图理清梁启超与北海公园的重要联系。
一、梁启超在团城
梁启超于1913年在民国政府中任职,1913年5月入住团城,同年11月从团城搬出。关于梁启超入住团城的原因,或许与同年3月宋教仁遇刺有关,他在4月15日的家书中写道:“乃昨日黎宋卿(元洪)复电政府,请加意保护。政府复以二十骑来,几令我不敢复出游(不敢往琉璃厂,仅此仪从烜赫欲买书画,必索值十倍耳)。”4月17日,“此次入京住东单二条之住宅(系光绪帝师翁同龢旧宅)环以千数人。”团城自民国政府从清皇室接收后即为政府官员占用,又因地理位置距离中南海总统办公处所极近,所以从安全角度、地理位置考虑都是绝佳的居住场所。
民国政治家黄群曾经写诗回忆梁启超居住团城的历史:“旧愁新恨忽交并,剩对西山眼暂明。为展松茔过海淀,追思夜雨话团城。任公(梁启超)先生曾住此。执戈几处能坚守,著屐何人故倒行?直欲十千沽斗酒,尽浇万念一时平。”
1913年7月,梁启超曾在信中表示北海居住地过于炎热,“酷暑如处蒸釜,殆欲焦铄肌肤,连三日不敢入北海(现行新华门,去丰泽园极远,乘舟车皆苦暍),惟每日以书往耳,极思逃归。”同年9月梁启超的家人欲来京居住,这或许都是梁启超不得不重新考虑居住地的原因。他曾先考虑在漪澜堂安家,8月5日家书中说:“今日适北海,答访一客,循海周遭行,弥望荷花十顷,杂以菱芰黄之属,水佩风裳,冷香飞上,湖外老柳古槐,圆阴匝地,蝉声豪迈,如诉兴亡。胜赏既殚,继以幽感。假使一年后觚棱无恙,则漪澜堂终为我息壤也。”
随后,他又在9月14日的家书中说:“房子看数处,终不合适。今日往看北海之镜清斋(静心斋),其地风景绝佳,布置精雅,号为北海之冠,回廊曲折,居室错落,在山坡上,分五六座,以廊通之。其景殆为颐和园所无(南海、中海无此佳构,漪澜堂大而无当),外则弥望荷菱,以全海为一大园。小动物居此,当喜欲狂矣。惟室少不能容客,且交通极不便,是隐士所居,非政客所宜也。今拟另租一较小之房,在近市之地(此房中亦设上房,眷属随时来居),而家眷则居海上,吾日间皆在市中治事,间日则归海上避客。”
可知梁启超认为团城、镜清斋、漪澜堂作为居住地都有不便之处,因此最终没有选择北海作为暂住之地。而梁启超最终离开团城或许也有失意于政治,另觅住所的原因。黄秋岳记载:“记戊午任公居团城时,一日严寒,坐沁香亭中,望液池波欲成冰,大风作浪有声,任公方辞职,叹曰:求去亦何所谓?世事兴衰,大势略定,何人为之,皆不甚相远。”
二、梁启超与松坡图书馆
梁启超为纪念蔡锷将军,向国民政府申请在北海快雪堂成立图书馆。1922年,北海尚未正式开放,梁启超为此向当时的总统黎元洪写信申请,在信中写道:“陆军上将蔡锷于帝制一役,躬冒万难,首义滇中率以兵谏积劳故,大局粗安,而长城据殒,启超等追念前勋曾于民国六年提议建立图书馆,以资纪念。濒年以来虽以大局之变故纷乘而陆续所募之捐款已得数万金,所集图书以及数万册,欲就此基础形成,先行草创然后徐图扩充。大总统复位之始,即有开放北海作为公园之令,查公园为公共娱乐之地方,图书馆为群众教育之基础,而纪念前勋尤足以资,国民之观感公益事业虽多性质之相宜莫逾,为此合词,拟请于北海内指定地点官房拨充图书馆之用,以资提倡。”黎元洪于10月6日批准拨北海官房作为图书馆之用的请求。快雪堂是一座三进院的院落,第一进院落澄观堂设为松坡图书馆阅览室,第二进院落浴兰轩设为藏书室,第三进院落设为蔡公祠。
1923年6月20日,梁启超作《松坡图书馆记》:“民国五年十一月七日蔡公薨,国人谋所以永其念者,则有松坡图书馆之议,顾以时事多故,集资不易,久而未成。仅在上海置松社,以时搜购图籍作先备,十二年春,所储中外书既逾十万卷,大总统黄陂黎公命拨北海快雪堂为馆址,于是以后庑奉祀蔡公及护国之役死事诸君子,扩前楹藏书,且供阅览。诗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入斯室者,百世之后,犹当想见蔡公为人也。民国十二年六月二十日,梁启超记。”文中将建立松坡图书馆的起因、经过记录下来。
松坡图书馆成立后梁启超任图书馆馆长,民国十二年(1923年)十一月四日,松坡图书馆成立大会在澄观堂举行。梁启超在写给女儿的信中表达了对图书馆成立的喜悦之情:“昨日松坡图书馆成立(馆在北海快雪堂,地方好极了,你还不知道呢,我每来复四日住清华三日住城里,入城即住馆中),热闹了一天。今天我一个人独住在馆里,天阴雨,我读了一天的书,晚间独酌醉了。”
民国十三年(1924年)五月十八日,在快雪堂第一馆又举行了松坡图书馆第一次成立大会。
1924年的档案记载了一段曹锟与松坡图书馆的历史:“曹锟至北海,令卫兵将松坡图书馆前址拔去,招致学人非议”“‘松坡图书馆’之筹设系梁启超于去年六月二十日择定北京北海快雪堂为馆址,并为馆记一篇,十一月四日成立,以纪念反对袁世凯之志士蔡锷,不意为当时贿选总统曹锟所忌,乘梁启超离京二小时后,即亲至北海令卫兵将该馆界址木桩全行拔去,据当时代梁负责监督该馆之蹇季常将馆役目击实情函告曰:前月二十七日(原注:公行之后二小时)曹忽巡幸北海,步行至松馆前,(原注:馆役亲见)令卫兵将松馆界木桩全行拔去,不知何意。三十日干事会佥谓置之不理,近日并无下文,此事琐琐不足告,惟未尝与馆无关,敝以奉达,似可不议也。”(民国十三年七月二日蹇季常致任公先生书)可见松坡图书馆的成立并非一帆风顺。因为地理位置的原因,如果没有执政者的同意,图书馆很难顺利在北海内部开放。
松坡图书馆从成立之初就为筹集资金所扰,经常入不敷出。1923年开馆之后,由于当时的北海尚未正式开放,图书馆书籍尚未整理编目,因此图书馆并未对公众开放。1925年8月北海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同年10月1日,图书馆正式对外开放,并且需要购买门票才能进入。但由于读者不多,所以经费依然不足,梁启超为此在1925年5月专门为该馆撰写了《松坡图书馆募捐启》,为图书馆运行筹集资金。但仍然难以维持、梁启超在图书馆开放仅一年之后的1926年,就在写给长女梁令娴的信中写道:“晚上还替松坡图书馆卖字,自己又临帖临出瘾。(民国十五年十月十九日)” 记录了自己为图书馆资金卖字筹钱的处境。同年十一月八日是蔡锷十周年忌日,这一天梁启超在松坡图书馆为蔡锷举行了公祭。梁启超的同乡袁思亮为蔡锷撰写祭文,梁启超为祭文点定数语,并且亲自书写,祭文后挂于蔡公祠内作纪念。
1923年图书馆成立后,梁启超还曾在松坡图书馆开办“松坡平民读书处”,他亲自担任训练助教,将北海发展成为民国时期平民教育的起源地之一。除了为“松坡图书馆”竭尽心力,1926年梁启超兼任北京图书馆的馆长,而图书馆的馆舍同样是租用北海公园内的庆霄楼、悦心殿、静憩轩、普安殿等建筑。可以说梁启超晚年为之奋斗的图书馆事业与北海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梁启超逝世后十八年的1947年,梁启超的好友和门生还特别借用北海松坡图书馆举行纪念仪式,这大概也是对梁启超在北海多年经营图书馆建设事业的一种纪念。
快雪堂也成为梁启超演讲、授课的场所。“研究院师生间,除了经常的论学问难及聚宴外,梁任公还把在万木草堂追随康有为时,每逢春秋佳日,十五月夜,师生漫游粤秀山麓等处,畅所欲言,其乐无穷的经验,推行于研究院,他预定每年暑假前邀约同学作北海游一次,或邀名师讲学其间。”第一次北海之游于1926年夏季举行,第二次北海之游于1927年夏季举行,但是由于时局原因,没有邀请名师讲学,梁启超仅与同学同游,并且为同学们作了讲演,后来他的学生将这段演讲笔录整理形成《北海谈话记》,其中写道:“先生每于暑期将近时,约同学诸君做北海之游,俯仰咏啸于快雪浴兰之堂,亦往往邀名师讲学其间。去年夏宝山、张君劢先生因事来京,为诸同学讲宋贤名理,盖穆然有鹅湖、鹿洞之遗风焉。” 可知在梁启超眼里,快雪堂不仅仅是图书馆,更是授课、讲学向鹅湖之会、鹿洞书院效仿,讨论学术、表达意见的绝佳空间。
三、梁启超邀请泰戈尔访问北海
1924年印度诗人泰戈尔抵达上海,4月下旬到北京访问,梁启超和蒋百里等人先是在静心斋设宴欢迎泰戈尔,后亦曾在北海快雪堂参观,据《申报》记载:“讲学社特柬约学界人士及在野名流,在北海开茶会,以便太氏游览。昨日风和日暖,确是北方春季模范日,北海苍松古柏,碧水绿茵,不愧为北京名胜。徒以近来门禁森严,不易观赏,昨亦为此远来诗哲,开放数小时。三时前后,主人梁任公、汪大燮、熊希龄、范源廉先后莅止。三时二十分太戈尔(泰戈尔)·鲍司·沈三人同乘一汽车到静心斋,因布置未妥,先至松坡图书馆参观,并游览小西天,胡适、梁漱溟、庄士敦(英人)等约五十余人,五时开茶会,及半由梁任公起立致欢迎辞,梁任公演毕,由张逢春译成英语,继由太氏答词,历三十分钟之久,为到华以来最有兴趣之演说。”泰戈尔访华是当时北平文学界的一次盛事,梁启超选择当时尚未对公众开放的北海作为欢迎仪式的举办地,也体现出了北海在梁启超心中的重要地位。
梁启超在欢迎泰戈尔的致辞中提到中印两国文化的交流:“北海的琼华岛,岛上‘白塔’和岛下长廊相映,正表示中印两系建筑调和之美。我想,这些地方,随处可以窥见中印文化连锁的秘密来。”
四、结语
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他与北海的不解之缘最早可追溯至其1913年入住团城的工作、生活经历。1922年至1929年的数年间,梁启超作为快雪堂松坡图书馆、庆霄楼北京图书馆馆长,致力于民国图书馆事业的发展。而图书馆在北海的设立,也赋予了北海公园启迪民智、教育国民的文化教育职能。在快雪堂形成的讲学、集会的风气,对宣扬文化起到了良好作用。而北海作为印度诗人泰戈尔的访华北京参观地,也展现了其在文化界、建筑界的重要地位。
参考文献
[1] 梁启超. 梁启超家书 1898—1928[M]. 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7.
[2] 黄群. 黄群集[M].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3] 民国文林编著. 细说民国大文人 那些国学大师们 白金增订版[M]. 北京:现代出版社,2018.
[4] 王洪新,著. 京华通览 北海[M]. 北京:北京出版社,2018.
[5]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编辑委员会编.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 初稿 中华民国十三年(1924)一至六月份[M]. 台湾:中华民国史料研究中心,1983.
[6] 丁文江,赵丰田,编. 梁启超年谱长编[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7] 葛兆光,主编. 清华汉学研究 第2辑[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8] 讲学社招待太戈尔游北海[N]. 申报,1924-4-28(10).
[9] 泰戈尔,著. 远方的邀请 泰戈尔游记选[M]. 北京:中国旅游出版社,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