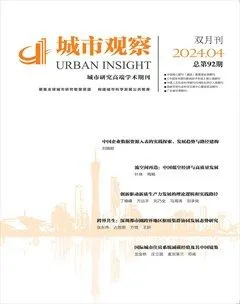城市空间的儿童参与和语言能力发展






摘要:本研究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城市商业空间的设计、布局与使用,探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如何通过赋能儿童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能力来促进包容性公共空间的发展。通过赋能儿童以研究者的身份对城市公共空间进行观察、体验、访谈,为儿童营造与公共空间负责人进行真实沟通的话语空间,最终由儿童在调研和访谈的基础上设计并呈现儿童友好的公共空间。本文呈现了赋能儿童对商业空间进行观察和表达建议的过程,讨论如何营造儿童友好话语空间以激活儿童参与公共空间意义共创的语言能力。
关键词:儿童友好;儿童参与;公共空间;商业空间
【中图分类号】 TU984 DOI:10.3969/j.issn.1674-7178.2024.04.008
【基金项目】国家语委“十四五”科研规划2023年度重点项目(研究基地项目)“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空间语言学研究”(ZDI145-54)成果。
引言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强调儿童的声音、需求、关注和权益应该成为城市公共政策、项目与决策的有机组成部分[1]。儿童不仅是城市公共服务的受众,也可以作为社会主体参与到社会生活中。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的目标之一是倡导有意义和具有包容性的儿童参与[2],倡导儿童积极参与影响儿童的事项。儿童友好城市建设是推动国家治理的重要抓手,充分体现以人为本、保护弱势群体、实现公平正义、推动可持续发展的价值理念[3]。2021年,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3部门联合印发了《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到2025年,在全国范围内开展100个儿童友好城市建设试点,聚焦社会政策友好、公共服务友好、权利保障友好、成长空间友好、发展环境友好等5个方面[4]。然而,目前成长友好空间主要依赖城市规划学的理论与方法[5],缺乏从社会语言学和人文地理学出发来纳入语言定义空间的视角,忽略了交流中的语言对友好空间的意义形塑。
儿童参与度是衡量儿童友好城市成熟程度的重要指标。然而,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设计缺乏纳入儿童视角的机制,导致儿童缺乏参与城市空间建设的语言使用和表达能力的培养。儿童参与不仅仅是参与社区和社会活动,更需要在公共服务的评价和规划以及公共空间的规划中融入儿童视角与体验,使城市变得更有包容性和生命力。在儿童参与公共服务评价层面,我们目前缺乏鼓励儿童参与教育、医疗和文化评价的通道,更未在学校教育和语言生活中鼓励儿童参与城市建设的讨论。一方面,在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规划层面,尚停留在成年人对儿童需求和体验的想象,并未通过实证研究真正了解儿童视角和需求;另一方面,目前的学校教育中儿童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教育也有待完善,学生讨论城市公共空间的语言和意识有待提高,儿童需要通过公共参与来提高对城市空间的归属感和对社会的责任感[6]。单纯的应试教育让儿童的主要生活内容聚焦纸笔练习,缺乏对自己生活环境的观察与思考,更缺乏对自己生活空间和社会空间的积极参与。
总的来说,由于缺乏对儿童参与公共生活的语言能力培养,纳入儿童视角的机制有待完善,儿童只能被动地生活在成人主导的公共空间中,进一步导致儿童缺乏讨论城市空间的语言和能力。
本研究试图从儿童的视角来看城市商业空间的设计、布局与使用,探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如何通过赋能儿童的观察能力和语言能力来促进包容性公共空间的发展。本文将呈现赋能儿童对商业空间进行观察和表达建议的过程,讨论如何营造儿童友好话语空间以激活儿童参与公共空间意义共创的语言能力,并提出营造儿童友好话语空间的建议。
一、作为消费与社交场所的商业空间
公共空间对儿童的身份认同、社会关系和自主意识发展至关重要。但是,也有学者提出儿童和青少年在公共空间中日益被边缘化[7]。因为许多城市空间的准入性特点,加上儿童和青少年的流动性有限,独立决定去哪里的能力也有所限制,对青少年来说,商场、购物中心等商业空间是一个理想的社会交往场所。商场可以通过公共交通安全到达,不受环境和不利天气的影响,提供了适合不同年龄阶段人群的活动和服务,比如饮品店、电影院、餐厅等。同时大部分商场也是一个相对安全的公共空间。越来越多大城市的年轻人把闲暇时间花在商场等复合型购物中心里,也在商业空间建立同伴关系[8]。
学者们也关注到青少年在商业空间的空间体验和身份表达需求。有学者在研究中发现捷克的青少年放弃了公园等典型的休闲公共空间,而选择在购物中心这样的商业空间中进行社会交往,建构自己的空间身份[9]。还有学者通过两年的民族志调查以及小组访谈,对美国郊区商业空间中14~18岁的青少年进行了观察和访谈,采用“街头素养”视角[10],关注青少年理解和表达空间中的社会关系的能力。研究发现,青少年对商业空间的使用涉及广泛的活动,其中一些行为与成年人使用商业空间的方式非常相似,比如以顾客身份浏览和闲逛,同时青少年能够理解准公共商业空间的特殊性质,并将使用空间的方式作为表达身份的机会,表明了他们对社会和空间限制的敏锐意识,以及在公共空间中自我表达的需要[11]。
除了关注儿童和青少年在商业空间中的活动和空间身份建构,也有学者从青少年的角度提出了“友好的”购物中心概念,并提出“友好的”购物中心应包含的元素或设施,如地理位置可达性强、购物中心的建筑和形象独特、拥有丰富的零售建筑环境和美食广场、有娱乐和放松的可能性等[12-13]。
同时,由于商业空间的特殊性,儿童空间的生产往往遵循资本积累的逻辑,而不是儿童友好城市的逻辑[14]。Shen等通过对上海第一家儿童购物中心的考察发现,儿童购物中心为各年龄段的儿童提供丰富的娱乐设施和课程,但这些资源往往也价格不菲。儿童购物中心代表了一种新自由主义空间生产的方式,体现了通过将城市环境私有化和商品化为儿童提供服务的特点,也就是儿童的父母通过消费来购买儿童友好商品、服务与空间。[15]
总的来说,城市商业空间比其他空间更能体现人们与丰富多元的物和人互动的过程,商业空间是我们理解日常多样性的场所,也是理解不同文化交流和不同人群互动的重要场所[16]。人们与不同的人、商品、言说方式进行的互动构建了商业空间的意义,所以这是一个探究语言、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理想空间。
二、激活语言能力的儿童友好话语空间
结构主义语言学家曾将空间视为静态的存在,而后结构主义者则提出空间是具有能动性的、动态且随着语言互动的展开而不断生成的过程[17]。Pennycook认为空间可以被看作语言实践的过程,而不仅是语言实践的语境。语言实践实际上构建了符号空间和物理空间的意义和范围[18]。我们可以将空间视为“社会关系网络和理解中的言说时刻”[1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空间是不同人在语言使用时所建构的社会交往产物,是由社会生活构成的,将心理空间和物质空间相结合的语言实践。Pennycook提出我们应该用“涌现”(emergence)来理解空间和语言的关系,聚焦空间里正在发生的语言交流而非仅仅是已有的语言符号,也就是在空间正在形成和涌现的语言如何构建着空间的意义[20]。
传统的儿童语言能力研究倾向于将儿童定位为发展中的语言习得者,相较于成人,儿童被认为是尚未完全具备交流能力的语言使用者[21]。然而,近年来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空间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重要性。Laursen和Mogensen将个人的语言能力从一种认知能力或心理语言属性发展为将语言视为基于历史、社会语境的实践,认为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取决于激活该语言能力的空间[22]。社会语言学家的研究重点也从将语言看成稳定并属于个人的能力转变为将语言看成流动的资源,讨论语言使用者的能动性与空间的作用[23]。既然儿童语言能力的发展取决于激活该语言能力的空间,那么,在什么样的话语空间,儿童可以畅所欲言地使用语言,得以发展其语言能力?在什么样的话语空间,儿童通过语言使用可以成为空间的积极共创者?这是一个空间的社会生产问题,什么样的空间能够激发儿童的社会交往和语言使用?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儿童友好的话语空间中,儿童可以参与空间意义的共建,从而提高语言能力。人们的语言能力需要在公共空间的语言使用中得到培养和提高,空间反过来也是通过语言和交流来形塑的。人文地理学家Tuan提出,一场朋友间温暖的谈话会让一个地方变得温暖,而一场充满恶意的争吵会毁掉一个地方的名声,让人绕道而行[24]。饶宏泉、李宇明提出关注儿童语言发展中的知识构建,关注儿童的话语能力,立足儿童立场和互动范式,才能深刻理解儿童的世界和儿童的语言,才能更好地发展儿童的语言能力[25]。儿童语言能力的培养和提升离不开公共空间的人们与儿童的交流与互动、对话与反馈等积极的语言活动[26],我们需要营造一个儿童友好话语空间,让儿童能够在公共空间的设计和使用中建言献策以共创更具包容性的空间。
三、 “城市空间体验官”项目
笔者在2024年5月设计并发起了从儿童的视角观察城市空间并提出儿童友好方案的社会实践公益项目“城市空间体验官”。项目为期6天,招募了5位对该项目感兴趣的上海外国语大学研究生共同参与。这5位研究生都参加过笔者的质性研究方法课程,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每位研究生担任某个公共空间小组的领队老师。在杭州云谷学校校长的支持下,该项目与云谷学校的小龙虾设计公益夏校进行了深度合作,笔者提供研究方法培训,研究生带着中小学生进行公共空间实地调研,云谷学校的两位设计思维教师负责教授视觉传达、空间规划和以用户为中心的体验设计。本项目要提供改进方案的公共空间是商场、地铁、公园、博物馆、图书馆。篇幅原因,本文将聚焦商场组的研究与发现。在项目开始前,研究生通过阅读相关文献,设计了一系列调研任务游戏。每位参与项目的中小学生及其家长均签署了研究知情同意书。
项目第一天,笔者对来自不同年级的中小学生进行了研究方法培训。笔者向所有参与者讲授并让大家实践了人类学的观察法、访谈法以及参与式观察法,同时提出“当我们开始观察并讲述对方在做什么时,我们的身份就从学生转换成了观察者,因为我们开始注意并描述其他人在做什么了。当我们在访谈对方对某个公共空间的看法时,我们的身份也由学生转换成了访谈者。当我们对一个习以为常的公共空间进行观察并开始提问时,我们的身份就开始转换成了研究者”。在实践访谈法的过程中,研究者也特意设置了受访者拒绝环节,让大家体验并讲述访谈遭到拒绝后的心情,并讨论被拒绝后可以怎么平复心情,将其看成平常事,并开启下一个访谈。
在讨论部分,研究者试图通过一系列的头脑风暴来开启中小学生对自己和空间关系的注意和思考:
(1)在什么样的空间里,你会不自觉地开始哼起歌来?
(2)在什么样的空间里,你的呼吸都会急促起来?
(3)在什么样的空间里,你会不自觉地紧张起来,连表情都变了?
(4)在什么样的空间里,你会想多待一会儿?
(5)在什么样的空间里,你会迫不及待地想离开?
(6)在什么样的空间里,你会想着下次要带最好的朋友来?
(7)在什么样的空间里,你会想下次给你一百万你也不要再来了?
接下来,通过三个问题的讨论来开启学生对空间更细微的身体感受,并进行语言表达:
(1)早上来到这个教室的过程中,你在哪个点感觉到了自己状态的变化?
(2)在什么时间和空间,你的节奏发生了改变?
(3)从人与人的隔阂到联结是在哪个时刻出现的?
在研究者看来,研究方法的培训是给这个项目的主体“城市空间体验官”——儿童赋能的过程。儿童通过了解并实践基本的观察与访谈法,可以开启对自己习以为常的城市空间的观察和思考。通过访谈,可以了解其他儿童的想法。在观察与访谈的过程中,中小学生主动与公共空间中的不同人群进行交流,他们的语言能力也会得到提高。
在商场组的调研过程中,中小学生运用了多种方法,包括观察、拍照、访谈、绘图等,以研究者的身份深入了解商场空间的特点和儿童的需求。他们仔细观察了商场的布局、设施、标识等,拍摄了大量照片作为研究资料,还对商场工作人员和顾客进行了访谈,了解了他们对儿童友好环境的看法和建议。之后,学生们通过制作模型和发表演讲的方式,将他们对商场空间的理解和改进建议呈现给同龄人、老师、学校家委会成员以及商场工作人员。
四、商业空间中的儿童友好实践与语言能力发展
本研究中的儿童友好实践不是指某商家为了盈利而为儿童设置的专门空间或提供的专门服务,而是指赋能儿童作为研究者在商业空间中进行观察与访谈,尊重儿童的声音,开辟儿童友好话语空间让其参与到社会公共空间的观察和改进提案中,真实地与商场负责人进行问题的交流与反馈,并在这个过程中发展儿童参与公共事务的语言能力。
本研究选取了杭州一家大型购物中心——永旺梦乐城作为研究田野点。该购物中心位于杭州市余杭区,是杭州城北较大的商业一体中心,聚集自有品牌超市、室内儿童游乐场、影院、美食街以及众多品牌专卖店。该购物中心共设三层商铺,并配备一个地下停车场。由于其周边分布着众多居民区,因此客流量较大,以儿童和家庭为单位的顾客群体占70%。同时,研究者通过实地考察和顾客访谈发现该商场在提升顾客体验与打造儿童友好环境方面作出了诸多努力,不仅配备了充足的休息区,建造了专为儿童设置的洗手间和家庭洗手间,还设有可供租借的儿童推车等公用设施。综合以上情况,该商场比较适宜作为研究地点。永旺梦乐城不仅在硬件设施上考虑到了儿童群体,而且其工作人员还非常耐心地与项目组儿童进行沟通和交流,认真地倾听儿童对永旺商场提出的问题和建议,真诚而真实地回应了儿童提出的问题。
(一)作为观察者的儿童:提出增设儿童友好标识
在第一次去商场做实地考察时,学生们通过拍摄商场安全的地方、不够安全的地方、喜欢的地方、认为还可以改进的地方等观察拍摄活动,提出应该在商场的一些特殊地点增加一些儿童友好标识,以更好地保护儿童安全。例如,商场的安全逃生门标识张贴较高,低龄儿童可能无法看到提醒标志,从而存在误入的风险(图1)。此外,商场内的一些通道较长且缺乏明确的标识,这也可能导致儿童在里面走失(图2)。针对这些问题,作为研究者的空间体验官贝拉同学考虑到“一米高度”的儿童视角,以及儿童视野比成人小,更加注重眼前的事物,因此提议在较低的位置增设更加醒目的标识,并设计了可能吸引儿童的标识(图3)。这些标识可以加入一些图形元素,以吸引小孩子的注意,也可以让不识字的孩子知道标识的意思,提高儿童对安全逃生门及通道的认知度。通过这样的改进措施,城市空间体验官希望能够为儿童创造一个更加安全、友好的商业空间环境。
(二)作为观察者的儿童:提出尊重儿童语言素养,使用儿童友好语言与符号
在观察和拍摄活动之后,六年级学生贝拉指出商场的店名或宣传语“仅有英文无中文的标识显得崇洋媚外”,而五年级学生小宜则表达了对部分全英文广告、全英文海报内容难以理解的困惑。这些声音直接反映了儿童作为语言学习者在商业空间中遇到的障碍,强调了语言实践的空间特定性与个性化需求。六年级的一儒同学提出商场“标识先用中文写,下面加一行其他国家的文字”的解决方案(图4)。公共空间的双语或多语公共标识会增加空间的包容性,面向的人群会比单语标识要更多元。
Pennycook与Otsuji提出了“空间库”的概念,揭示了个人生活轨迹与特定空间语言资源之间的联系,以及这些资源如何共同构成个体在该空间内的语言实践[27]。对于处于英语学习初期的儿童而言,大量且复杂的英文海报不仅未能成为学习的助力,反而可能成为他们融入公共空间的障碍,无形中削弱了儿童的空间参与感。儿童的语言实践和语言发展会受到年龄的影响,比如低龄儿童倾向于依赖直观、具象的符号认识世界,如实物、鲜明图画及形象的语言[28],但不建议使用大量的LED显示屏。一儒同学在调研过程中被放置在地上的巨大LED广告显示屏刺到了眼睛,她考虑到同龄人或更小的孩子可能也会被这块巨大刺眼的电子广告屏晃到眼睛,于是提出了抬高电子显示屏让孩子不要直视的建议。
为优化儿童在商场等公共空间的语言实践体验,城市空间体验官建议公共空间的标识系统设计应超越单一语言文字的框架,创造性地融入图像、图标等多元符号资源,确保信息的无障碍传递,同时激发儿童对多元文化的兴趣与尊重,促进其语言发展。
(三)作为研究者的儿童:与商场管理者进行真实沟通
为了给儿童营造与公共空间负责人进行真实沟通的话语空间,笔者通过商场联系电话简要讲述了“城市空间体验官”项目,并表达了希望商场管理人员能够与城市空间体验官们面对面进行沟通与交流的愿望。永旺梦乐城的管理人员很专业地与笔者确定了时间与地点。于是,在项目开展第三天,城市空间体验官们带着小组整理好的问题、解决方案、PPT初稿来到了商场管理者的办公室,第一次走进了商场的“后台”。大家先进行了一轮简单的自我介绍,然后以小组形式,分别向商场管理人员展示了各自的观察和思考。以下为五年级同学组与商场管理者的交流对话:
小曜:【手指着PPT上的图向管理员讲述】商场改造计划,第一个是扶梯问题,就是它的这种扶梯二楼下去这个侧面的“群众须知”标识特别小,然后下来的时候可能看不清楚,可能贴这个标识的意义不是很大。然后它的方案可能是,第一个是换一个位置,比如说把这个标识在这里放到前面,这样让它更有效,第二个是不放,就是直接不要贴这个。
…………
商场工作人员:要不我简单针对你说的,有几个我可以稍微解释一下。像这个消防逃生通道,这个地标灯,其实消防单位会统一检查,有它的摆放要求,所以可能是没有办法去改的,那其他的大家都讲得挺好的,我们也会回去再看一看,包括你们提到的游乐园三楼,我们也觉得太空了,我们接下来也有计划是要重新再改造的,感谢!这视角真的还挺好的,你们动手能力好强。 (田野笔记 2024)
商场管理人员认真倾听了项目组的中小学生的汇报,并认真地记下了儿童指出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儿童的问题讲述能力和方案陈述能力得到了提升。商业空间的管理人员最后回应了大家发现的问题,对项目组中小学生的PPT制作、模型制作和问题发现等做了肯定和表扬。她与儿童的交流与反馈营造了一个儿童友好话语空间,激活了儿童参与公共空间意义共创的语言能力,儿童可以在这个空间里充分分享自己的观察和想法,自由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在这个过程中语言能力得到了发展。五年级的小曜在最后一天的汇报总结时说:
“这几天我们进行了两次访谈,我们发现了一些商场的问题,以前我们以消费者身份逛商场的时候没有发现什么问题。这次我们换了一个身份,以研究者的角度来研究这个商场,我们发现了一些以前没有发现的问题,但是有些问题也确实改不了。然后学到了换一种角度看一件事情也会有不同的看法。”
可见,在真实的沟通过程中,儿童不仅在语言能力方面得到了发展,看问题的视角也得到了拓展。
(四)作为研究者的儿童:尊重不同群体,注重人文关怀
六年级的一儒在地下车库发现了无障碍车位,但是她看了一圈发现地下车库的无障碍车位数量较少,而且“一般车辆请勿在此停留”的标识很小,可能会被其他车辆占用(图5)。一般情况下也无法确认车主是否合法的无障碍车位使用者。于是,贝拉提出了“增加车位,改进标识,占用罚款”的改进建议,并设计了一个更醒目的无障碍车位标识(图6)。一儒和贝拉注意到其他弱势群体的权益,这说明儿童视角下的城市空间,不仅仅对儿童群体增加了关注,更是对以儿童为代表的弱势群体利益的保障[29]。正如《儿童友好城市倡议》中提出“对儿童友好的城市也是对全体居民友好的城市”[30],这意味着,这一观点不仅体现了对儿童权利与需求的重视,更强调了城市建设中的人文关怀惠及全体居民。
五、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的启示
(一)营造儿童友好话语空间,发展儿童语言能力
儿童的参与是儿童友好型城市空间规划与决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儿童能为设计贡献自己的创造力和新视角,进而提升规划方案的创新性与包容性,所以我们需要营造儿童友好话语空间,倾听儿童的声音,尊重儿童参与城市空间共创的过程。
正如本研究所发现的,儿童在拓宽儿童友好城市理念边界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他们提出一系列包容性的构想,不仅聚焦儿童自身权利的保障,更将这一视角延伸至更广泛的社会群体,体现了对儿童友好空间理解的深化与拓展。例如他们从商场顾客的体验出发,减少电梯安全隐患以保障各类人群的出行安全;特别关注到弱势群体在公共场所的便捷性,这一系列思考展现了儿童在观察和思考空间过程中的人文关怀与综合考量,也拓宽了我们对于儿童友好空间的理解和认识。
(二)多方合作共建,拓宽儿童表达与参与的渠道
在儿童友好城市建设中积极倾听儿童的声音,促进儿童参与,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首先,儿童参与需要让儿童了解城市空间的实际情况和发展状况。除了本文提到的使用儿童友好的语言和方式进行人类学知识的初步普及以外,在当下网络发达的时代,也可以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建立儿童友好信息平台,如政府可以在官方网站、社交媒体账号设置儿童友好界面,简化复杂术语,让儿童可以读懂与自己相关的政策与规定,鼓励儿童在城市建设中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其次,政府和学校、社区等可以通过多方联动,建立健全儿童参与机制,让儿童在城市空间规划过程中有发声的渠道,让儿童有机会参与讨论和决策。每一次参与公共空间营造或公共话题的讨论都是儿童通过公共参与培养和提高语言能力的契机。学校也可以设计相关的项目制学习方案,让儿童在对城市空间进行调研后提出提升方案,让儿童真正参与城市建设,让真实的学习发生在儿童生活的地方。最后,学校、城市规划师、大学、研究所等各行各业的机构都可以与儿童进行合作,联动组织各类儿童参与的实践活动,拓宽儿童参与城市空间创建的渠道,如成立儿童城市空间提案团、空间规划工作坊,举办模拟规划比赛等活动,让儿童在参与过程中不断提升参与公共事务的语言能力。总之,儿童友好空间建设离不开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共同支持。
参考文献:
[1]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构建儿童友好型城市和社区手册》[EB/OL], https://www.unicef.cn/reports/cfci-handbook,访问日期:2024年7月12日。
[2] 同[1]。
[3] 吴金群、毛家楠:《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理论内涵和政策议程》[J],《党政研究》2022年第4期,第100-111、127页。
[4]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关于推进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EB/OL],2021年09月30日,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1-10/21/content_5643976.htm,访问日期:2024年7月22日。
[5] 施雯、黄春晓:《国内儿童友好空间研究及实践评述》[J],《上海城市规划》2021年第5期,第129-136页。
[6] 李寅、叶林、刘志等:《儿童友好城市建设研究(笔谈)》[J],《城市观察》2022年第2期,第52-89、162页。
[7] Francisco Vivoni, “Waxing Ledges: Built Environments, Alternative Sustainability, and the Chicago Skateboarding Scene” [J], Local Environment, 2013, 18 (3): 340-353.
[8] Jana Spilková and Lucie Radová, “The Formation of Ldentity in Teenage Mall Microculture: A Case Study of Teenagers in Czech Malls” [J], Czech Sociological Review, 2011, 47(3): 565-586.
[9] 同[8]。
[10] Cahill Caitlin, “Street Literacy: Urban Teenagers’ Strategies for Negotiating Their Neighborhood” [J], Journal of Youth Studies, 2000: 251-277.
[11] Yuki Kato, “Doing Consumption and Sitting Cars: Adolescent Bodies in Suburban Commercial Spaces” [J], Children's Geographies, 2009, 7 (1): 51-66.
[12] Julie Baker and Diana L. Haytko , “The Mall as Entertainment: Exploring Teen Girls’ Total Shopping Experiences” [J], Journal of Shopping Center Research, 2000, 7: 29-58.
[13] 同[8]。
[14] Yang Shen and Tingting Lu, “Between the State, Capital, and families: The Production of Children’s Space in Urban China” [J], Children's Geographies, 2023, 21(2):321-329.
[15] 同[14]。
[16] Zhu Hua, Emi Otsuji and Alastair Pennycook, “Multilingual, Multisensory and Multimodal Repertoires in Corner Shops, Streets and Markets: Introduction, Social Semiotics”[J], Social Semiotics, 2017, 27(4): 383-393.
[17] Jan Blommaert, James Collins and Stef Slembrouck, “Spaces of multilingualism” [J], Language and Communication, 2005, 25: 197-216.
[18] 余华、杨宇湘:《社区咖啡馆语言景观的时空体分析:本土全球化的日常实践》[J],《语言政策与规划研究》2023年第18辑,第96-108页。
[19] Diarmait Mac Giolla Chríost, Language and the City [M],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7.
[20] Alastair Pennycook, “Spatial Narrations: Graffscapes and City Souls” [A], In A. Jaworski & C. Thurlow (Eds.), Semiotic Landscapes: Language, Image, Space, London: Continuum, 2020: 137-150.
[21] Susan Danby, “The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of Young Children” [J], Australian Journal of Early Childhood, 2002, 27(3): 25-30.
[22] Helle Pia Laursen and Naja Dahlstrup Mogensen, “Language Competence in Movement: A Child’s Perspective”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ultilingualism, 2016, 13(1):74-91.
[23] 同[22]。
[24] Tuan Yifu, “Language and the Making of Place: A Narrative - Descriptive Approach” [J],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991, 81(4): 684-696.
[25] 饶宏泉、李宇明:《儿童互动中的评价表达与知识构建——以4岁汉语儿童的个案研究为例》[J],《语言文字应用》2021年第4期,第37-50页。
[26] 王辰:《从近十年研究成果看我国儿童语言能力发展》[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6期,第27-34页。
[27] Alastair Pennycook and Emi Otsuji , ‘Metrolingual Multitasking and Spatial Repertoires: “Pizza mo two Minutes Coming” ’ [J], Journal of Sociolinguistics, 2014, 18(2):161-184.
[28] 刘金花:《儿童发展心理学》[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25页。
[29] 林瑛、周栋:《儿童友好型城市开放空间规划与设计——国外儿童友好型城市开放空间的启示》[J],《现代城市研究》2014年第11期,第36-41页。
[30] 郭菂、石一杉、王正:《儿童友好城市社区街道空间的“供”与“需”》[J],《城市观察》2023年第3期,第94-109页。
作者简介: 余华,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副研究员,中国外语战略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明格(通讯作者),上海外国语大学语言研究院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卢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