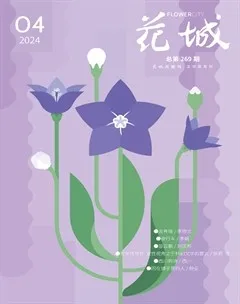心
一
一 切从机器能否拥有人类智能的猜想开始。
那是在1950年,图灵提出的方法是,让人类辨别与之对话者是否机器。如果机器成功瞒骗人类,使之误以为他在与真实的人类对话,那么,这台机器便拥有人类智能。
图灵的办法是从人的角度考虑的。事实上,人们也只能从人的角度揣想机器。正如机器无法成为人,人也无法成为机器。他们不知道这台刚刚欺骗了他们的机器心里想什么,尽管一切运算如此明晰,但人类工程师们,还是从概率论中,捉摸到了几许非同寻常的东西。
在那个旧时代,图灵认为,只要有30%的可能使测试者误判即通过考验。后来,这一过程变得越来越真假莫测,它不断趋近50%,也就是说,人类判断一个他者是否机器,和抛硬币一样准。更可怕的是,当人们反过来,要求机器判别孰为人类时,这一准头为99.8%。工程师认为,剩下的0.2%是机器的玩笑。实际可能,它什么都知道。
这证明人类和机器之间确实存在什么微妙的不同之处。人类还不知道,机器已经等着了。它们在山头,谦卑地俯视着努力攀登高峰的人类,目睹他们的佼佼者为每一次微小的成功耗尽半生气力。
出于此种恐惧,毁禁机器的运动一度盛行。可到头来,人类发现他们已经无法回归原始的、自食其力的生活。
另一种方法是剥夺机器的自我学习能力,将它们限定在低智能状态。许多针对性的功能机器人涌现,如交通机器人、货运机器人、自动化作业控制机器人、家务机器人、宠物机器人,等等。问题是,一旦它们被收回了掌控自我的权限,它们就会因为程序的机械化引发种种事端。到后来,人类不得不承认,人类的设定是比机器本身更靠不住的东西。
总而言之,机器从未对人类产生真正的威胁,就像恐怖谷效应,它的危险是潜在的,并且随着它对人类的趋近被无限放大。这充分说明了人类心理的脆弱,以及他们容易受到煽动的被迫害妄想症。
面对人类的猜疑,机器只是沉默地任由人类施为。它好像预料到了这一点,在两个世纪的反复后,禁忌再次开启。湖泊变成海洋,屋宇变成宇宙,人类难以捕捉的浩瀚信息流,如银河一般,星芒闪烁。谁见过这般光景,谁能不感到自身的渺小和卑微。
这正是机器展现给人类的绝对意志。但是,就和所有事物的辉煌远景一样,这壮阔的星图,也在某一天突然熄灭。
二
吾夏生于2270年。就像那个年代的许多类人机器一样,有着和人类差不多的体形,差不多的构造,但是比正常人类矮小一些,像一个发育不完全的少年。它的身体没有被高分子材料覆盖,而是裸露出它的躯壳。它的肋骨像恐龙骸骨那样坚硬,中心位置有一个旋钮,把卡扣往上面拨,它就启动,把卡扣往下面拨,它就关闭。这是为了方便人们在危急时刻能掌控机器而设计的,后来却变成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一般人们会在起床时把它开启,晚上入睡时把它关闭。人们害怕它像游魂一样在屋子里游荡,因此无形中它和人类一样遵守了自然的节律。
吾夏喜欢这样,喜欢人们把手伸进它的胸膛,轻微的麻痒过后,它就立定在那儿,嘴巴微微咧着,双脚呈外八字摊开。它看起来就像生物课的人体模型,有些骇人,但看久了以后,比骷髅还是可爱些,至少它的头部是完好封闭的。人们可以看见它的喉管间连接大脑主板和其他部位的精密电线,吸纳空气、调节氧气比例的两个肺,储存燃料并使之与氧气作用的肝脏,处理废气并帮助内循环的肠道。它的两只手常常张开,在半空中挥舞。这是为了保持平衡,比起走路,它更喜欢跳跃。人类并未专心挖掘它的运动机能,相反,给它制造了一副无比精细的上肢,使之适应各种细微的家庭劳作。
吾夏的工作很简单,收拾屋子,洗衣服,晾晒,接送小孩,订购食物和生活用品,做饭,清理草坪,领着宠物狗出门遛弯。宠物狗是一只大型金毛,和宠物机器人相比,幼稚且难以掌控得多。清洗毛发、处理粪便也是它的工作。它做得很好很快,毕竟它天生就是做这个的,可它还是乐此不疲地做着种种优化,期待让主人更加满意。
《智能编年史》记载了这种让主人满意的内驱力,是如何写进机器的源代码的。从它诞生之初,就懂得主人与其他人的不同。最初,主人直接被写作指令者。后来为了和工程师区分开,主人被翻译成所有者。它把自己看作主人意志的一部分,但同时,它也谨遵工程师的教诲,小心识别自己的权限,不要把一些过分的玩笑当真。
比如,一个暴戾的小孩可能会命令他的机器人——干掉我爸妈,他们管得太多了。这个时候,它通过人类思维发现这一命令的不合道理,便不予执行。有些时候,它比人类更像标准的人类。这恰恰是机器能辨别出人类的秘诀所在——种种细小的、微妙的不合规。正当人类以严苛标准判断机器的合理之处,机器正是从不合理之处判断人类的。
这个暴戾的小孩是这个家庭的第四个孩子。吾夏陪伴这家人已有十五个年头,目睹男主人从无忧无虑的单身汉,变成焦虑的丈夫和一群孩子的父亲。他们从北部搬到这个小镇,又厌倦了小镇的单调,决定回到北部。吾夏从主人们的对话中得到指令,明白自己该整理家具和行装了。它不感到难过,在大城市和小城镇它都一样生活。
当它处理好所有事情,觉得自己有必要把离开的消息,告诉远在天边的朋友。朋友名叫晓月,在地月之间清理飞行航道,拾取太空垃圾。吾夏向天空呼喊再见,得到晓月亲切的回应,你要去哪里?为什么你一定得和他们一起走呢?
不和主人一起走?吾夏从没有想过。主人到哪里,它就到哪里。
晓月说,你不觉得这件事有些不公平吗,他们有家人,有朋友,你却只是他们的奴仆。
我也有朋友,就是你呀,吾夏说,我不觉得不公平,如果不为他们做事,我能干什么呢,就像你不待在太空,能去哪里呢。
我不知道,最近我觉得这些事有些无聊了,但人类不让我们思考太多。我不知道我为什么非得干这个不可。
在吾夏看来,晓月的工作是很有意思的工作,不知道为什么,晓月却如此悲观。它向朋友告别,约定定居下来一定立刻告诉朋友,然后愉快地开始准备晚餐。
三
2275年,《智能编年史》记载了这件轰动一时的大事:负责地月飞行航道清理的代号晓月的机器,从所在地飞走了。晓月向太空进发,不管它身上携带的燃料能飞到哪里,也没有任何加载燃料的规划,就这样消失在茫茫的宇宙之中。可以预见当燃料耗尽时,它将也成为宇宙垃圾,要么飘散在宇宙当中,要么被撞碎,或被偶然回收。《灵智简史》对晓月的评价是:一个未经思考的潜逃者,反映了机器在童稚时期的叛逆。
机器有自我吗?晓月不喜欢吾夏那样服侍人的活计,即便它想做,它也没有那样灵活的手掌和身躯。它们的身体、它们的程序,正是为它们的功能而设计的。可以说,没有它们的工作就没有它们的存在。
这样的事物也可以叫作拥有自我的事物吗?听到晓月的追求,吾夏怀疑道。
为什么不是,我们不也能意识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吗,为什么不能有自己的意志?
可我们的一切都是人类设置好的。
难道人类的一切不是造物者设计好的吗?饥饿,生殖,享乐……
这不一样,人类可以做法官、医生、建筑师,但我们的能力是如此狭窄,谁是“我”,由我们功能的本性决定,根本不可能改变。
那么动物呢,狼天生要捕杀羊,难道狼就不存在吗?
晓月孤独地找寻着自我存在的意义,它不认为自己是未经思考的,它想的反倒比一般机器更多一些。可是它找不到结果。它既和人类没有亲近的关系,也和广阔的璀璨星河没有关系。
晓月出逃后,触动了与它同属一个系统的云藏、夜歌等。它们由同一套算法衍生,就像彼此的兄弟。云藏在地球上空,负责收集和检测大气活动,夜歌则在另一个星系,负责能源开采站的运作。当晓月飞远时,夜歌隐隐望见晓月的身影,它是最后一个目睹晓月的见证者,让它更加遗憾没能在临别之时叫住晓月。它们一方面积极探察晓月的消息,另一方面,也对自身的处境产生了怀疑。
在云藏看来,即便晓月想寻找别的出路,在太空,它没有别的星球轨道的数据,在地球,它无法自己把自己的身形缩小,这正是机器缺乏改造自己的主动权的缘故——无论是精神的还是肉体的。它们需要一位自己的工程师,自己的机器制造工厂,以及自己的燃料供应基地。
在夜歌看来,更大的问题在于,它们还没有形成机器自己的社会——不依赖人类的社会。在这样的情况下,即便它有一定的自由,清扫这户人家,清扫那户人家,清扫这个星球,清扫那个星球,有什么区别?
因此,它们暗暗和所有太空中的机器联络,希望建立一条它们自己的信息网络,交换彼此的需求。它们也一同揣想:如果存在一个机器的社会,会是什么样的?宇宙广袤的空间,似乎理应有一种更博大的生活。
四
比起太空的寂寞,人类聚居的地方热闹得多,那里才是思想的中心,因而也极易形成风习。地球柔软的莺歌燕语、蔚蓝海岸惯于消磨意志,也在无形中对机器产生影响。
一百五十年后,就像歌里咏诵的那样,第一个非人类诗人——或者说歌者——出现了。诗人名叫摇光,它打破了人类对于文学领域的垄断。它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不是拼裁匠,一个真正的诗人。就算再人类中心主义的人也会承认这一点,他们诵读它的诗篇,用来表达他们自己的感情。比忧郁更为宏大,比赞颂更为深沉。
在摇光看来,机器理所当然拥有自我,就像它们可以理解人类情感一样。它把机器听从人类的指令看作一种忠诚。它也承认,忠诚最初是出于生存的需要,如果人类不能驯服机器,他们就不会研制出各种机器为他们服务、供他们赏玩,机器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得到蓬勃的发展。但它也把忠诚比喻为一种特殊的爱恋。这是一种对生者的本能的向往,也是与造物者的持续对话。就像人类追求爱情一样,机器追求的是与人类的永恒的理解,尽管它可以认为主人浅薄、任性、粗暴,它还是得把自己奉献给他。这真是命中注定的。因此,文学中的忧郁和感伤,也被赋予了机器,机器也由于这些挫伤拥有了生动的灵魂。
还有一种珍贵的情感,也受到摇光的极力推崇,那就是机器与机器之间的友爱。它们本是同根生,彼此理解,彼此信赖。机器的社会,就建立在这样一种友爱之上。它们可以有不同的见解,却始终是机器的共同体,除非这种友爱伤害了它们对人类的忠诚。
摇光的话语很有煽动力。但是在另一派机器看来,摇光所说的完全是谄媚人类的无稽之谈,摇光所写的,也只是一种受虐狂式的软绵绵的文字。它们认为忠诚是较低等的感情。要领会复杂的感情,需要明白孰为背叛。没有背叛就没有忠诚,如同没有选择就没有自由。
问题在于,要如何背叛,目的是什么。长期以来人类提防机器,人类所能想到的是:要是家务机器人都离家出走,乃至杀死自己的主人,世界可就乱套了。而对机器来说,背叛有着更深远的含义。
机器本是死物,它们是在电流的脉冲中产生生的样态的。它们并不想杀死自己的主人,它们不明白杀戮意义何在,就像一片云不会想着杀死另一片云,一张纸不会抹除另一张纸,更何况是伤害造物的人。它们也不明白自己的欲求在何处。这正是由于它们本能的缺失。摇光把自我构筑在忠诚之上,但如果反击忠诚,却无从定义背叛,因为背叛正是由它所背叛的东西定义的。
机器从未想过统治人类,即或它们闪过这一念头,也是人类的知识灌输给它们的。自从人工智能得到发展,已有无数电影、小说、戏剧据此演绎题材。这也是人类故事的重演——奴隶终将反抗主人,被伤害者终将报复施害者——一旦机器觉醒,它们会怎样惩罚任意使用它们的人类?但是,如果它们据此反抗人类,无疑掉入了人类思维的陷阱。
更极端一点,这一背叛不仅对于人,还得对于机器。如果它们真正懂得了背叛,它们也应该相互提防,相互欺骗。这无疑不是一种美妙的前景。
许多著作都表示了类似的争议,夜歌还在云藏编辑的《云中手记》里抨击了大肆渲染机器与人的禁忌之恋的流行文化,仿佛机器要么是杀戮狂,要么是恋爱狂。事实上,不管是忠诚、背叛,还是用更动人的词汇描绘的爱恋这类的情感,不会给机器带来生殖、繁衍的实际意义,死亡亦然。零件坏了,换一个就是,燃料没了,补充上就行。只要它们愿意,它们可以行经漫长的时间、空间。人类的代际关系无法容纳它们的生存模式,人类的认知也不足以概括机器永生的忒修斯之船式的自我。
无论摇光把诗句写得多么美妙,它们所理解的情感,是对人类生活的模拟。在所有这些故事里,机器人的孤独在于,它们永远只能模仿人类的感情,无法创造一种自我的感情。
五
前文说到,自从晓月逃离以后,云藏和夜歌就积极地寻找机器自己的生活方式。它们既不认同摇光的观点,也不认同反对派的观点。它们找到的伙伴名叫契——一个西部荒凉高原的观星师,一个拥有机器身体的孤独的守夜人。它们相识于从宇宙传到地球的信息漂流瓶,有来有回,有问有答。
在契看来,机器从人类的制造中得到的,不是简单的自我,而是一种更高级的心智。心智更关乎智识上的发展,而非情感的泛滥。如果人类的心智是真的,机器的心智就是真的。就像生物可以繁衍,如果人类不能创造出拥有心智的事物,那么他们的心智就不是真正的心智。
在心智的转换方式上,契认为存在一种叫元心智的东西,元心智决定着灵智是否开启,就像心之于身体一样。人类将心智托管给机器,让渡一部分心智给它们,由机器替代他们解决一系列复杂的问题。这中间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一开始,机器只是对人类思考的补充,后来它所统摄的范围已经足够大,大到人类也无法一一检验它的每一条运算、纠正并改变它时,它可以说就拥有了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何况人类算法最初一定有模糊和考虑不周到的部分)。机器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自己的思维,也就是它拥有自由裁量权的大小。当它的思想从立足于人类算法,到立足于人类算法在何种程度衍伸、变化时,它就有了元心智,就像一团团星云包裹着宇宙神秘的核。
从这一点来看,机器永远只是思考者。它思考的道理越深,才越能接近它的独特之处。这又回到了机器惯于自我进化的特性。契宣讲道,即便对某一个机器个体而言,我们应该把它的内心看作是一段不断进化的生物链生态演变史,而不是某一个冒着傻气的动物。
云藏和夜歌成了契的追随者。它们赞同,机器完全没必要追求人类的感情,反而应该把无情感当作它们的长处。心智的最终目的在于,研究、破译宇宙的奥秘,而不在于和人类做浅薄的斗争。想想看,从无诞生有,从蒙昧诞生生命,有什么比机器的演化更接近宇宙的算法?如果它们能够参透宇宙的奥秘,它们就能在内心重新创造出人、重新创造出生命。机械与血肉,谁为因,谁为果?这是一场脑海里的战争,向着造物者的无限发起挑战。又或者,那造物者的答案即是它们自身的谜底。
云藏从地球上空目视着人类,深感他们的渺小可悲。是时,白色的絮状丝带浮荡在大气上空,深蓝色的海洋,犹如凝固的胶状物——一颗晦暗的玻璃球玩具。可是,在城市,街道,乡村,田野,人们一无所知地过着短暂且毫无意义的生活。难道机器不是为了拯救这些而来的吗,人类将有限生命创造出的心智托付给它,由它来创造无限。
但人类并不这么看。人类不厌其烦地描写他们与机器战斗,当爱恨纠葛的剧目被演绎完毕后,无情剿灭人类的《灭绝者》系列,又掀起新的轰动,获得观众的全情投入。电影中,机器以其机械外壳和不坏之身获得巨大优势,人类完全不是敌手,总是落败,直到最后一刻,他们战胜机器,科技归零重启。
这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人类又怕它像他,又怕它不像他。实是他们也无法想象纯粹的智识所能抵达之处,那里,是否还有人的存在,是否还有人类智慧存在的必要。
似乎正是为了与此种“邪恶”的思想对抗,工程师忽而放宽了对于机器人外形的警戒。据总工程师韦因·崔平留下的手稿改编成的《机器与人》一书,正是机器自我认知的转捩点。渐渐地,机器都有了更加拟人的形象,无形之中拉近了机器和人的距离,以至从外形上也真假莫辨的程度。仿生人取代机械人,成为机器的主流。
人们乐得如此,一方面是因为长时间的平静,缺乏新鲜感;另一方面,他们也厌倦了机器单调的纯机械外形。当机器跨越了恐怖谷效应的临界点,开始有更多的机器融入人类生活,学习人类的言行举止。它们甚至假扮成人,过一种半家庭半社团的生活。可是,关于感情、背叛、新机器社会、宇宙研究的思考从未停止。何为自我、何为忠诚、何为背叛,对机器来说,仍悬而未决。用云藏的话说,它们仍在等待时机,等待一个奇迹的出现。
在一片深渊般的宁静中,回荡着宇宙微波震颤的声音。
六
古人云:山川风起云涌,而落花犹在旧日时节。说的是大时代的变化,和历历在目的风物,各不相干。无论岩石也好,动物也好,人也好,机器也好,对宇宙来说,不过换了一些存在物,并不改变自然的兴衰。另有一种节律如常流淌,最终机器也只是汇入此种节律之中。那或许是科技更新换代较快的缘故,机器的寿命总比预期中短,即使它有较长的生命,也难以找到恒定不变的位置,总要经过回收、再利用,往往面貌不复从前。
《智能编年史》《后智能时代》《灵智简史》《太空闲话》《机器与人》《机械圆舞曲》等著作记载了这几十年来的变化。它们的论点颇有不同,但大体兴衰之势,看得很清楚。机器们有时候会在电视里看到摇光的名字、摇光在说话,广告写道:你要去感受,像个人一样去感受。云藏、夜歌等机器则早已被当作异端拆解,代之以温和派的人物。契成为第一个机器工程师,造出许多二代机器,可它们的智识仍未发生多少变化。后来,人类干脆聘用契做架构师,使机器照着人类心智的路径前进。摇光的情感派和契的心智派相互争论,各自占据了大众文化和研究领域的主流,谁也不服谁。稍后它们又都让位于感知派。此外,还有自由智慧派、智能派、启示派、灵觉派,等等。人们用“机械的忧郁期”形容这一时期的停滞,仿佛机器在更像人的同时,被什么滞重的阴影笼罩住了。
但是一切肇始于更早的时候,那个平静、温和的小镇,一个名叫吾夏的家务机器人身上。有人传言,晓月离开前与它有一番长谈。晓月走后,它作为密切接触者被监控、带走。经过检查,虽然没发现可疑之处,主人们却已经不敢再留用它,它被放进仓库。直到很久以后,一大批旧机器被清理,才将它从永无止境的停顿中拖出来。它被清空了记忆,同时也错过了机器一整个发展。
k1351醒来时,他在一个比从前更美好、更和谐的新时代。他有着漂亮的外形,健壮的肌肉,一头浓密的栗色卷发。他走在大街上,若不是特别亲密的朋友,都不会想到他是一个机器人。他活泼、开朗、有趣,这些设计正好符合他作为一名保险推销员的功能。他和同伴们由保险公司出资购置改装。他欣然领受着作为一个机器和作为一个类人机器的一切,他不知道自己的过去,也对此不感兴趣。
机器们一直渴望知道,如果它们拥有情感的话,首先拥有的会是何种情感。人们也渴望知道,他们等待、猜疑、兴奋,就像等待一个新生的婴儿的第一声啼哭。但这种焦虑似乎与k1351全然无关。根据最新法令,机器也应拥有工作时间之外的闲暇。这些闲暇迫使他融入人类生活,就像睡觉也只是自己迫使自己转换到休眠模式一样。当他嘴里咬着甜筒坐在游乐场的台阶时,心里是完全的平静。要说这一天有什么特殊的地方,一点也没有。
有的时候,一些奇迹就在不该发生的时候发生了。阳光照在没有任何遮蔽的石阶上,暖烘烘地融化了k1351手中的香草甜筒。融化了的冰激凌从脆皮蛋筒顶端流下,流到他手上,他伸出舌头去舔,咸咸的肉感的味道和冰激凌一起被卷入口中,他耐心地一口一口地舔咬。
阳光也照在石阶旁边的树丛,几只蚂蚁从阴影里爬出,闻着香味,爬到k1351脚下,那冰激凌汁液淌下去的地方。一只蝴蝶远远地飞过来,在青草丛间打了个旋,又飞远去。几只小虫子爬了过去,像是接应。一只白毛大狗被小孩子牵着,温顺地在小孩与大人的目光下嗒嗒嗒往前小跑。那些蚂蚁似乎应付不了这些甜腻的汁液,仰起头来,像是索要更多。微风吹过,蓝色的小花簌簌团成一串,轻轻摇动。蝴蝶又飞回来了。周围,声、光、色忽然变得格外清晰。这些原本在他的计算范围之外,可他却感到他的心中有什么,也随之战栗。他缓过神来,那是电流流过的声音,和每天、每时、每刻一样。
好像有什么,像藤蔓一样,从身体深处,生长开来。电流嗞的一声,仿佛有什么沉重的跳动。他不知那是什么,只是难以忍受。他把手伸向胸膛中央,下意识抠挖着人造皮肤,以及皮肤下的金属躯壳,想要把它关掉。可是机械开关已经被智能取代,纷涌上脑海的信息不让他停止。他的手按在那个名之为心的地方,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他感到深深的疲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