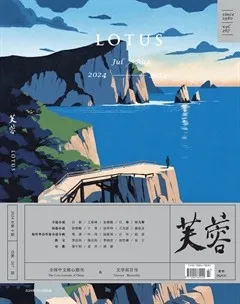纸屑飘落河流
李达伟,1986年生,现居大理。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大益文学院签约作家。有逾两百万字作品见于《青年文学》《散文》《清明》《天涯》《花城》《大家》《美文》《散文选刊》《散文海外版》等报刊。出版有散文集《暗世界》《大河》《记忆宫殿》《苍山》等。曾获第十二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第三届三毛散文奖、云南文学奖、云南省年度作家奖、滇池文学奖、《黄河文学》双年奖等。
0
到了雨季,我再次出现在象图河边。其实,我不用有意去强调。只是很多时候,我们往往会忽略一条河流。河流被忽略之时,我们把注意力放在了哪里?说不清楚,我们那时恍惚了,至少我是恍惚了。当我有意识地开始沿着河流行走时,是有意把注意力放在了河流之上,对河流我开始倾注着某种特殊的情感。我一开始只想把注意力放在冬天的河流,就想看看冬天河流的样子。当把沿着河流行走的步伐放慢,当把沿着河流行走的次数增多,河流在不同季节的样貌开始展现在我面前。
雨季,会让我格外留意象图河的存在。雨季,象图河开始上涨。当澜沧江的这条支流开始上涨时,我们能想象澜沧江的其他支流都在上涨,有一段时间,澜沧江的流量将令人咋舌。雨季过去,象图河开始隐入山谷之中,也开始从我们的现实生活中暂时退去。到了雨季,特别是今年的雨季,我们已经无法将它忽略。雨水长时间下着,就像是梦魇一般,不分昼夜地下着,有几天甚至在人们的梦中也不曾停歇过。在一场把记忆弄得潮湿的雨水面前,人们不敢做梦,人们活得胆战心惊,人们慢慢失去了做梦的能力。我们想在人们的记忆里追溯这样一场雨。记忆是无力的,记忆也无法用距离来度量。讲述中没有这么大的一场雨,也没有连着下了十五天的这样一场雨。这样的一场雨曾经在那些魔幻的热带雨林里下着,把大地所有干的地方都弄湿,河流开始涌上河堤,开始涌入房间,很多东西都浸泡在水里,梦也被浸泡在水里。
象图河真涌上了河堤。一些桥真被河流冲垮了,还剩下一座低矮的桥,那唯一的桥连接着外界。如果那座小桥被冲走,那个世界就将暂时封闭起来,像曾经的一场大雪对世界的覆盖与封闭。只是我们习惯了一场又一场大雪的封山,却不适应一场洪水的阻隔。象图河与其他很多河流一样,也展示着自己的破坏性,把曾经空落的河床填满,把河床继续拓宽,把建在河谷中的乡村农贸市场淹没,把一些人家养着的牲畜冲走,河流边的那所小学里的学生在雨中的湿滑泥地上被转移。我开车从已经涌上公路的河水经过,内心会莫名恐惧。
中元节,雨水并未停歇。中元节过去,雨依然下着。那个民间艺人要扎一些纸马之类的东西,要在中元节烧给刚刚逝去的亡魂。民间艺人抬起了酒杯,又放下了酒杯;民间艺人拿出烟抽着,又让燃烧的烟蒂长时间夹在指尖。民间艺人陷入了沉默。已经扎了一匹纸马。民间艺人扎了那么多的生命与物件后,是否想过要扎一条船,把自己扎的那些东西燃烧后的灰烬放入船中,让船载着它们从奔涌的象图河往下,抵达沘江,然后是澜沧江。当河流猛然涨起来,涨到让我们无法想象之时,那个民间艺人开始意识到一定要扎一条船。
来自原始丛林中巨大的原木,才可以做一条真正的船。沿着澜沧江往下,在那些繁茂的丛林中,我们能见到一些现实中的造船人,伐倒一些古木,开始造船,造成的船开始在澜沧江上漂着。澜沧江边的一些人伐倒树木,还为了做一些棺木,一些棺木漂浮在澜沧江上。眼前的民间艺人,他在丛林中砍伐一些竹子,那是做成船骨的材料,别的东西用那些绵纸就可以完成。当那些船只剩下残破的船骨时,阳光还有月光照在了它们上面,释放出让人内心一惊的光芒。民间艺人扎的一些东西,只有通过澜沧江和它的支流才能真正抵达另外一个世界。河流成为一条界线。
民间艺人确实是出现在了澜沧江江边,他一开始加入了砍伐甘蔗的人群,他们砍伐甘蔗时要乘船渡河。他成了众多渡河人中最普通的人。与那些偷渡者,与那些亡命之徒,与那些在大地上行走的僧侣和诗人,都不同。唯一相同的是,他们每个人都有着关于生活与灵魂的秘密,有些是隐秘且难以启齿的痛楚。当他真正成为造船者那一刻,他觉得自己不再普通。他开始认识那些渡船人,然后他开始认识那些造船人。他开始学习造船。他跟人们说起,象图河某一天也会涨起来,涨得至少需要一条船。人们原谅了他的浮夸与臆测。民间艺人还在澜沧江边,学会了如何制造一条用来专门搭载亡魂的纸船。
当我在雨季再次遇到民间艺人时,他说自己正在扎一条船,他要把自己扎的那些纸马都赶上这条船,那些纸马将在澜沧江上纷纷复活,将在澜沧江上驰骋奔腾。这条船将在澜沧江上一直漂浮着,它搭载那些放归于澜沧江边的峡谷中的纸马,还有那些流落荒野的灵魂。
1
逆着弥沙河往上,到白石江。白石江开始离开我的视线,隐入村落与河谷。我不再沿着白石江走着。我翻越雪邦山,出现在象图河边。雪邦山两面的河流,流向不同,最终都汇入澜沧江,都是澜沧江重要的支流。我在象图河边生活了很多年,一些东西依然藏在表象之下。这是我最近才意识到的。原来,我以为,许多事物早已显露于我面前。有一段时间,我有意出现在很多条河流边,却忽略了象图河。我朝象图河望了一眼,然后携带着目光朝另外一条河流移步。我出现在了澜沧江的许多支流边,不只是为了看河流,还为了拜访那些民间艺人。我以为象图河边已经没有真正的民间艺人了。事实是,许多民间艺人在日常生活中以另外的身份存在着,他们成了被我误读的对象。
总以为这个世界无论是文化还是植被,都已经变得苍白和荒芜。世界以村落开始往外扩展,扩展到象图河,扩展到以雪邦山为范围的世界。我在的位置,已经是在雪邦山中。我见过木材开放那几年,雪邦山中出现了众多砍伐木材的人,当禁止伐木之后,还有人去偷砍一些古木,直到最近几年,偷偷砍伐古木的情形才少了下来。众多的红豆杉曾在雪邦山中大片大片生长着,现在已经很难找到有一定树龄的红豆杉了。我在的位置,有很多树墩,它们腐朽而冷漠。一些鹰偶尔停在上面,一些乌鸦偶尔停在上面,让人觉得轻盈的鹰和乌鸦轻轻停靠一下,就会把那些树墩压垮。我轻轻一推,其中一个树墩果真倒了下去,内部已经朽烂。众多的树墩,聚集在一起,会给人内心很大的震动。以树墩聚集的那小片大地,近乎是死去的大地,腐朽的树墩下面,没有任何的杂草与其他低矮的树木。也许,要等所有的树墩朽烂,死亡的大地才会复活。我跟很多人说起这个交通不便的世界,说起了那些树墩,语气里充满了不负责任的鄙夷。
这次,翻越雪邦山时,内心很复杂。我这次回来是要与二舅告别。生与死的告别。我们已经看到死亡的影子。二舅患上癌症已经一年多,病情恶化,身体暴瘦,再无法吞咽食物了,只能靠止疼药,靠舔舐着水慢慢熬着最后的时日。大家都知道二舅无法再熬多长时间了,二舅自己也在计算着还能活在世上的时间。从他的话语里,他已经接受死亡的过早来临。这样的情形很容易让人睹物生情。雪邦山和象图河,在这样复杂情绪的侵扰下,呈现出了另外的样子。它们不再只是山与河流。雪邦山上的那些草甸还未变绿。象图河,依然是很瘦小的样子。我们也看不清死亡的影子,媳妇家这边的二舅刚刚动了心肌梗死手术,看着恢复得很好,康复只是时间问题,最终两个二舅在两三天之内相继去世,先后一天安葬。最终,我翻越雪邦山,跟两个舅舅告别,一个六十六岁,另一个五十六岁。
这几年,象图河,慢慢发生了变化。从流量上开始的变化,小得让人猝不及防,同样也让人倍感忧伤。除了雨水季节,河流会涨起来外,瘦小已经是河流的常态。在很久以前,象图河一年四季流量都很大。我们会从一条河流上,会从河床与河流构成的图画上,看到众多河流的命运。读二年级时,要去象图卫生院看望长期因心脏病住院的表姐,第一次见到了象图河,那是我见到的第一条大河,洪水季节,浑浊,木头在里面翻腾,没有人敢尝试卷起裤脚渡河。此刻,我卷起裤脚,轻易就可以过河。象图河上,没有古桥。象图河往下流淌,汇入沘江后,就会有好些古桥。古桥的形式多样,有风雨桥,有拱桥,有藤桥,有铁索桥,有钢桥。其中一座钢桥,是英国人在很多年前建的。前几年,英国人寻找着这座桥的下落,他们是想告诉人们那座桥已经过了它的使用年限,已成危桥。这样一座看似没有多少特点的桥,却被人们记录在册,且没有被遗忘。许多人在面对这样的现实时,都觉得不可思议。从此,那座钢桥,被封了起来,不再使用。我们在那座钢桥边停留时,感慨不已。沿着河流往下,就能见到这些古桥。河流的文明史,需要那些古桥。我也曾为那些古桥着迷不已。象图河上的桥,都是一些钢筋水泥桥,还有一些木桥,这些桥没有多少特点,它们比起那些木质甚至是藤蔓修的桥更易坏。
眼前的河流,把河流固定在象图境内这一段,那是地理世界对于河流的命名,也是地理世界对河流的塑造过程。慢慢地,事物开始发生倒置,是河流在改变着地理世界,河床开始变得宽阔,众多砂石开始裸露在外,满河谷的核桃树也无法把河床惨白的一面覆盖,砂石给人的感觉是干燥的,是在太阳暴晒之下滚烫无比的,连水鸟都不敢在那些砂石上稍做停留。象图河缓慢地流淌着,如果不去介意它流量的变化,我们依然可以在河流边度过惬意安宁的时光。
当我再次认真审视这条河流时,它不仅仅是一条河流,它与在这之前我见到的那些河流一样,已经与某些民间艺术联系在了一起。惯性的思维,必然要让我把它们在短时间内经常联系在一起。对于具有老人特质的河流,我们看到了一个气喘吁吁老态龙钟的老人,我们无法在这条河流上看到一个年轻的身影。对于具有老人特点的民间艺术,我们见到的那些民间艺术背后的艺人,往往是老人。是有一些年轻的民间艺人,只是我选择去拜访的人中,老年人很多。有一段时间,我甚至产生错觉,只有老人在延续着那些民间艺术。
经过象图河,往上,朝乡政府所在地走去,会看到一个古老的照壁,上面的图画斑驳陆离,已经无法看清上面的任何一幅画。画已经掉落,成为碎泥。照壁上长着一棵低矮的树,模样和几十年初见之时并无什么变化。它一直在生长。而在一些人的视角中,那已经是一棵死亡的树木。枯木在古老的照壁上生长,形成强烈的隐喻意味。除了那唯一的低矮的树木外,照壁顶端还长着一些仙人掌,仙人掌总是给人生命力旺盛的感觉。曾经见到有人坐在仙人掌丛中,虽是背影,但依然因为这种植物的存在,让那个人显得坚毅而隐忍。这些植物,让照壁的时间感很强烈。那是旷野中的照壁,与庭院中的照iFsmTW9BajD+RUsndOuMNQ==壁不同。那个照壁与对面的山崖之间有着某些民间意义上的联系与相互制约。那样的意义早已远去,当我出现在那里时,照壁就是一个照壁,是一个功能已然消失的物体。它成了一个地理坐标。我再次确定了一下,照壁上面生长的植物,我已经无法分辨出是什么植物,我问了许多人,大家都模棱两可,各执一词。那就是一种植物,它成了一切植物的代称,它长得像任何植物,又不像任何植物。我们看到了一切植物的一种生长姿态。我们确定了一下,上面低矮的树,没有任何要枯死的迹象,它只是以无比缓慢的速度生长着。一种放慢的生长速度,与雪邦山顶生长的杉树呈现给人们的生长速度很相似。用土夯起来的照壁,只是那些艺术的东西在脱落。艺术在旷野中被天然消解。建造照壁的人,并没有留下任何信息。还有一种可能,照壁上曾经关于民间艺人的信息,都已经脱落,重新归为泥土。照壁旁没有任何的文字记录,当放弃文字,当文字消失,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充满偏见。照壁,从一开始,给人的印象就是斑驳残缺的模样,几年过去,依然是原来的样子,似乎风侵雨蚀到一定程度后,时间和外部的力量都无法再对它产生更多的影响了。我们会产生错觉,照壁将会一直存在于那里。印象中,照壁上曾画有一条河流,可能就是象图河,也有可能是澜沧江。斑驳的墙体上,已经没有河流的影子。
2
象图河的发源地,在雪邦山中。当我第一次出现在雪邦山,那是冬日。在雪邦山的褶皱间,一些溪流开始出现。一些溪流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剔透的光亮。一些溪流需要我们俯下身子,贴着那些溪谷中的石头聆听,它们在石头下面流淌着,听那些汩汩的水声便可断定溪流大小。如果是其他季节,堆积的石头之下流淌的河流,会满溢出地面,把那些石头淹没。如果不是去往离雪邦山很近的老君山,我将会忽略那些在砂石下流淌着的河流。我开始注意到雪邦山中同样有着这样的河流。雪邦山和老君山很近,它们的一些东西很相似。植被和山形相近,上面生活着相近的牧人,他们放牧的那些牛羊也相近,有时我们会恍惚以为进入的是同一个世界。
我猛然意识到那些石头河的尽头就是河流的源头,那便是一条河流初生的模样。越往上越发现,河流的源头在雪邦山中铺散开来,它们成了沼泽的一部分。慢慢地水开始渗出来,慢慢地它们开始汇聚在一起,慢慢地它们成了一条溪流。我在那里激动不已。我坐在雪邦山中,久久凝视着一条初生的河流,在阳光的照射下,释放出洁净阴冷柔弱的光。散文我需要花很长的时间,在那里与一条初生的河流对视。有黑熊出现在那些河谷,我们远远就看到它们,它们有时也像我们那样俯下身子听流水声,它们不只是在听,它们也在寻觅水源。我们往往只是远远见到那些黑熊,当我们出现在那些地方找寻一条河的源头时,它们消失了。在冬日,雪邦山中的那些溪流并未断流,只是很小,有些河床却很宽,已经遭受了洪水泛滥的影响。这与在苍山深处看到的那些溪流一样,都会在一些季节里涨水,水流浑浊,甚而会发生泥石流。
许多河流,我们已经无法看到它们原初的样子,除了那些牧人。他们在雪邦山上不断迁移,迁移的范围不是很广,在冬日他们会把羊群赶到半山腰,那里很少会出现积雪难融的情形,夏日牧场不断往雪邦山顶迁移。要举行祭祀活动,让存在于雪邦山上的众多神灵护佑羊群和牧人。河流最原始的状态,存在于那些人的记忆中。我遇见了一些牧人,当我把这样的想法跟他们说起时,他们说还有猎人会见到,还有砍伐树木的人会见到,那是还未禁止砍伐和捕猎的时候。在雪邦山中,我曾见到有很多山谷里,只剩下行将腐朽的木墩,密密麻麻。在雪邦山中,在黑夜中,还会有黑熊和牛群躺在一起,互不侵扰,这样的情形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亦真亦幻,许多人都说是亲眼所见。我相信了这些说法。雪邦山,是一个无比依靠说法的世界。
如果你不相信一些说法的话,我们无法真正进入那个世界。曾经那是一块到处充满传说和各种说法的土地,我们没有人会去怀疑它们。我最深信的是雪邦山中的那些溪流,牛羊马和许多野兽虫鸟共饮,有时它们会相互打量一下后,继续饮水,或离开。当我出现在那个叫“东方红”的村落下面的桥头时,看到了一些水鸟沿着河流往上或往下,往下就是一个电站,那个电站继续往下不远处,又是一个电站。都是小型的电站,这些电站对于象图河的影响,并没有电站对黑惠江的影响那么大。当从沙溪开始沿着黑惠江往下,我们看到了河流的形态在许多河段时的瘦小,我们也突然看到了河水把河床涌满。河流的变化,不只是对河床产生了我们所能看得到的影响。河床被改变着。河流的真实也在改变着。与河流有关的生命,也被改变着。
去寻访一条河流的源头时,内心总是有强烈的对自然世界的畏惧感。我能在雪邦山的那些深谷中,听到融雪的声音,还能听到一条新生的河流潺潺流淌的寂静声响。我出现在雪邦山,我们经过大山红满山红,这些村落隐藏在雪邦山深处。还有一个叫江头的村落,变得更为神秘,它隐藏得更深。直到现在我还没有看清整个村落的模样,我只是偶尔看到几户散落的人家,以及建在公路边的村公所。我们出现在那些河谷中,我们看到了河流的真实。许多植物把那些河流覆盖,有时,只看到笔直的白桦树。当海拔高到一定程度后,植物开始变得单一。杜鹃林、杉树林,是在雪邦山上让人印象最深刻的植物,还有那些低伏生长的植物,它们中的一些,即便在冬日,我们依然能认出它们的影子,那是报春花的影子,那是龙胆花的影子。
五月出现在雪邦山,种类繁多的杜鹃开始开放。在很长时间里,只有那些在雪邦山放牧的人看到了漫山遍野开放着杜鹃花的绚烂景象。当杜鹃花和其他的花纷纷开放之时,雪邦山上的河流流量开始慢慢变大,我们能在呼呼地吹过雪邦山上的风里捕捉到它们的声音。那些牧人的听觉无比敏锐,那是我们羡慕的敏锐,他们还能在风中捕捉牛羊马的气息。许多牛马常年在山上,只有在大雪飞扬的季节里才会回到海拔相对低一些的地方。我也曾在雪邦山中放牧,七八天才回家一次。那时,山上还没有电,在暮色降临之时,洗漱一下便开始沉睡。每天与我为伴的就是羊群,还有那些长年都生活在山上的牛和马。很多时候,还有父亲的陪伴,他的衰老年弱并不影响在雪邦山中给我的安全感。父亲在火塘边给我讲述着世界神秘的那部分。在火塘边,最适合谈论的是想象的世界,风呼呼地吹着,想象的力不断顶着木门不让它被冷风撞开。现在雪邦山上到处看到的是风力发电机缓慢转动着,已经不是那些牧人熟悉的雪邦山了,一些公路开始出现在雪邦山顶,我们翻越雪邦山,不是走路,是开车。许多人出现在山上,只是为了去看杜鹃花,去看雪。当众人出现在雪邦山中,一些原初的东西开始被改变,我们一眼就看到了世界的变化。
有个人开着车要翻越雪邦山,我开始进入雪邦山被讲述的那部分中。在黑夜中的茫茫雪野,他迷路了,他那时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身上不多的钱往车窗外丢去,并与雪邦山上的亡灵们说着什么,在经历了多次返回原点带来的绝望和焦虑之后,他再次找到了路。他说如果那晚,他不去跟那些亡灵对话的话,根本不可能安全地翻越雪邦山。他跟我说起这个事情时,我们正参加同一个葬礼。当我一个人开着车翻越雪邦山时,车辆很少,人影也稀少,放牧的人把摩托车停在草甸上,人隐藏在看不到的地方。在这途中,我总会想到那个给我讲述故事的人,我竟会莫名加快速度,想赶紧从那个世界中抽身。我看到黑色的绵羊在草甸上悠闲地啃吃着草。这样的情景,又会莫名让我减速。
在翻越雪邦山时,内心和行动是矛盾的。杜鹃花还未开。雪早已在别的季节消融。据说刚刚过去的四月,雪邦山上降下了一场雪,下了三天三夜。那些雪早已消融,融入草甸,让一些草破土而出,远远望着,雪邦山上的那些草甸开始有了忽隐忽现的绿意。许多在雪邦山上放养的牛马,正静静等待着那些草的生长。一个多月过去,天大旱,雪邦山中的一些溪流已经断流,我们通过象图河的流量就能想象得到。那与冬季的河流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我曾以为如果河流在冬季不会断流,河流就不会断流。我的这些想法是错的。我对于象图河的认识,也往往是错误的。对于象图河边的那些村落,同样如此。我误解了一个世界。
这个世界于很长时间(三十多年的时间),在我内心形成了固有的认识。这么多年时间,我以为对于象图河的认识已经相对准确,人们在说起与象图河有关的村落时,我都有话说。村落名,村落所在位置,村落里的一些人。但这些东西都只是碎片,就像我在寻访的这些河流,都只是澜沧江的一些支流而已。象图河的源头,也是澜沧江的源头。
3
我关注着一场葬礼的细节。我逆着象图河回到了雪邦山下。河流隐人山谷之中。沿着那些河流行走,由河流反思我们自身、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精神,还有我们的普通日常。我们暂时不去顾及河流的样子,也暂时忽略河流与人类的关系。我在这个村落里待了几天之后,开始意识到,一个村落的真实,需要一场葬礼。在葬礼上,一些东西才真正显现出来。只是在这之前,我还未真正意义上参加过在象图河边这些村落举行的任何一场葬礼。我参加过某一场婚礼,在快乐的氛围中,同样忽略了很多东西。一场葬礼则不同,大家沉浸于悲伤之中。悲伤让人变得更为敏感,也让人对很多东西的印象更深刻。记忆用心痛来加深刻度,悲伤可以用一些东西来度量。
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纸扎艺人。四代都是做纸扎的。他是第四代。当他这样强调之时,隐隐说明着他的后代可能也会继续从事纸扎。一问,他的孩子长年在外打工。我们没有说起,当他和自己的搭档离开人世,或者是其中一个人离开,是不是也意味着这门民间艺术的不完整和日渐消亡。许多民间艺术的消失,就是伴随着民间艺人的离世。还有一些民间艺术的消失,是随着民间艺人的衰老而发生的。民间艺人开始衰老,民间艺人已无力创作。我没有表达出自己的忧虑。我在他身上还感觉不到这样的忧虑。他的搭档,与他的性格有一点点不同,沉默寡言,时不时端起酒杯意味深长地自饮一口,那个行为里,反而隐隐透着一些忧虑。我们无法阻止一些民间艺术的消亡,也无力减缓它们消亡的速度。
只有在葬礼上,他们才是纸扎艺人。那是身份在特殊场合下的外露。他们已经无须隐藏。在其他的时间里,他们会把自己的身份隐藏起来吗?不只是他们,象图河边的那些村落不经意间,就把自己的某些真实隐藏起来。举行葬礼的几天,他们都会出现。在一场婚礼上,他们以另外的身份出现,他们以另外的方式变得忙碌起来。他们出现在葬礼上,用绵纸扎一些东西。他们把绵纸拿出来,他们用刀把青竹子破开,用竹片扎出大致的形状,那是扎的骨,贴上去的绵纸才是它的形。我离开灵堂,来到他们旁边,他们有两个人,只是有些时候,我往往觉得他们是同一个人。这只是错觉。我不能离开灵堂太久。771e3a4cea6c4b995d84bb321e9b744477b40c9c93afcdbf09a7b04f1b4c43f4我抑制着内心想对他们深入了解的冲动,那时我最应该表现出来的是悲伤的样子。当大家都沉浸于悲伤中时,我又怎么能去跟他们进行关于纸扎艺术的长谈。我也不能影响他们的进度,他们需要在规定的日子里,把所有要扎的东西扎出来。看日子的人出现,纸扎艺人关注着最终选定的日子,他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不用在夜间昏黄灯光中继续扎那些东西,他们在那几天的白天扎,就可轻松完成。他们也早已习惯,在夜间扎那些东西。
那些纸马、纸伞、纸门、纸的十二生肖,都是竹子和绵纸做的。它们在被烧灭之时,伴随着缕缕黑烟的消散,抵达了那些村落认识世界的另外一个维度。它们成了通灵的物,在烧灭那一刻,反而拥有了虚无又广阔的生命与力量。它们被放在棺木前面,放置了好几天。看着那些纸扎的东西,会有一些不适感。与我熟悉的世界不同,我的老家离这里只隔了两座山,走路三个多小时的路程,还有两条河流将流入象图河。我在出生地看到了另外一个纸扎艺人。他扎了两把纸伞。他还曾扎过一棵纸钱树,那是高寿之人过世之时才会扎的,那个过世的人年过百岁。他们之间无法进行对比,民间艺术之间无法比较,民间艺人在不同的世界中要创作的艺术不同。我们看到了数量和种类的不同。数量和种类的繁多和稀少,这里面同样有着各自不同的对于死亡的认识。他们应该有相近的地方,他们都扎了纸伞。出生地的那个老人,扎的东西很少,这并不是因为他无法扎其他的东西。当然他可能在多年不练习后,确实也已经无法扎出其他的东西了。他们没想过自己是在创作一种艺术。至少出生地的那个老人不会有这样的想法,他只会想到在那里扎两把纸伞的重要性。眼前的这个人不同,他说自己已经是州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每年还有几百块钱的补助。虽然只是不多的钱,但已经与那个未获得任何补助和称号的人之间有了距离和差别。眼前的这个人,在谈到这些时,话语里,多少还是有自豪的意味。
未获得称号的那个人,并未因此而失望过,他们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着纸扎艺术。他们在很长的时间里,并未把自己当成一个民间艺人。眼前的老人,开始有了自己是在创作一门艺术的意识。他的民间艺人身份已经被唤醒。他跟着送丧的众人,出现在了下葬逝者的地方。他看着自己创作的艺术品,被众人抬着,走了很长很长的路。
那些纸伞纸马后面是抬棺木的人群,里面有老人也有年轻人,这与曾经在苍山中见到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在抬棺木不同。这里面就有着逝者的老友,只睡了两个小时,便起来跟逝者聊天,聊过往,聊命运,聊人生,聊着聊着恸哭不已。他说自己一定要抬抬自己的老友。逝者的体重有二百多斤,加上棺木,重量可想而知,人们不断互换着,都是上坡路。人们在公路上抬着棺木,如果是在以前,人们得在那些小路上抬着棺木,艰难前行。逝者的兄长也跟着送丧的众人走了很长一段路,他突然停了下来,让人们继续往前,看着长长的送葬队伍,自己含泪往回走。在那样的情境下,这样的送葬,让人动情不已,也会让人想到他该怎样才能忍受自己兄弟的过早病逝。那是另外一个逝者的兄长,双腿残疾,拄着拐杖在天还未亮之时,混入送丧的队伍,当我无意间看到了缓慢而磕绊的老人时,眼泪忍不住簌簌往下掉。前后两天,我参加了两次葬礼,都是我们的舅舅,都是兄弟中最小的那个先离开了人世。一个突发心肌梗死,另一个是癌症。疾病蔓延的乡村,忧伤遍布的乡村。那个双腿残疾的老人,是我的大舅,不久前,也因病离世。当我回去参加他的葬礼时,葬礼很相似,参加葬礼的人基本相同,当大舅七点多被抬往墓地时,我挥除不走脑中他拄着拐杖含着泪水送自己兄弟一程的形象。
我从这些忧伤中暂时抽身。我要把目光放在葬礼中的那些纸扎艺人身上。他们都跟着送丧的队伍来到墓地上,他们主持着丧葬仪式的一些环节。他们跟送葬的人说把其中一把纸伞放入墓中焚烧,要让那个冰冷的墓穴变得温热一些,让亡灵与尸体都能感受到另外一个维度的温热。他们指挥着众人把其他纸扎的东西在别处焚烧,在一棵树下,或者在墓地旁的土堆上。其中有位死者因为去世时,周围没有人,算是意外死亡,就暂时不能葬到祖上的墓地里。我们也在这个行为里看到了充斥着的狭隘与偏激,人们争议着,至少要过三年后才能把尸骨迁到墓地。面对着各种非议,逝者的后人只能接受。人们在一片玉米地里挖了一个暂时摆放棺木的地方。那几日,天大旱,刚长出来不久的玉米被灼热的阳光晒得耷拉着颓丧的身子,我们踩踏着那些玉米苗。那些纸扎的东西焚烧之时,一些玉米被瞬间烧死。我把注意力放在两位老人身上,他们并未因自己创作的艺术作品被焚烧而有什么反应,他们早已知道自己的作品最终的归宿。他们并未表现出任何我所希望的心绪上的波澜。他们中的一个,主持完葬礼后跟着众人回家。另外一个,只是负责扎那些东西,便不再参与葬礼的任何一个环节。
每一次扎那些东西,在我看来,便是一次练习。平时,他们把那些绵纸好好藏起。没有人会在平日里扎下一些东西备用。绵纸做的东西,都具有易朽性。火一点就着。水一触就会烂掉。他们不曾把每一次葬礼上扎东西当成是练习。每一次,他们都变得严肃而庄重。他们认真地做着。我观察着他们,他们不曾做出一些失败的作品。那只是我在观察他们的那段时间里。失败的作品,一定曾扎出来过,只是很少有人会把注意力放在它们精美与否上。它们只是代指的东西,人们更看重它们的象征意义。
扎的纸马会让人想到甲马。不同的民间艺术。它们在一些时间的作用相近。要走很远的路,需要一匹马,一匹华丽的马。我在很多葬礼上见到了相似的马。当它们像甲马纸一样被焚烧,化为灰烬之时,它们开始有了作用。甲马,起着通灵的作用。纸马,可以自由穿行于另外那个神秘的世界。当我有意问其中一个老人,纸马的用意是什么?不就是逝者要骑。这样的回答,很明显并未让我满意。我希望这样的行为背后会有一些复杂的意蕴,而事实有可能真是如此简单。
4
当纸扎艺人一跟我谈起他创作的民间艺术时,我知道自己能理解他,也理解他在纸扎上倾注的热情和表达的精神。我们开始对话,我们把那些蜘蛛网下的各色绵纸拿了出来,是他拿了出来,他摩挲着它们,轻轻地把那些蛛丝和灰尘擦掉,那个行为本身就是人与艺术的交会过程。老人讲述着自己从事纸扎的一生。毕竟这是一门很特殊的民间艺术。这与老人学会唱戏不同。老人学会唱戏的过程,有着那种从小就深受熏陶的感觉,还有自己对唱戏的热爱。纸扎,与死亡与葬礼有关,让这门民间艺术的传承往往是家族式的。我们能想象学习这门民间艺术时,年轻的他内心的抗拒之意,当不再年轻,成了一个老人之时,那个学习的苦涩过程竟也没有了往日的苦涩。老人现在也面临着一个问题:该如何让自己的后人掌握这门艺术?自己的后人同样抗拒过,但老人早已相信他们的命运和自己是一样的,纸扎艺术对他们而言,近乎就是一种宿命。我似乎理解了老人,理解了这门民间艺术,我又似乎对此一无所知。
葬礼上,几个纸扎艺人和扎的那些东西都已经在暗示和说明,在那个世界里,人们无法忍受朴素地活着,更无法忍受朴素地死去。这也可能只是悖论和我的胡乱臆测。众多纸扎就是为了让葬礼显得更有排场。大家像讨论着婚礼上的嫁妆一样,讨论着那些纸扎的数量和种类。嫁妆和纸扎的东西之间,只有某种意义上的相似。当那些纸扎的东西,在坟地里化为灰烬,华丽与烦冗都快速消散。人们也从无尽的悲伤中,暂时平静下来,世界也回归朴素。
一些人开始讨论葬礼的简化。我们中的好些人,同样经历了昨日的那个葬礼。不同的葬礼,呈现给人的是完全不同的样子,一个被无限简化,另一个依然无比烦冗。纸扎艺人也在我们之中,他也在讨论葬礼该简化了。纸扎艺人在那一刻并未去想自己从事的民间艺术,会在简化中消亡。我看不出纸扎艺人有可能会因为自己的手艺失存而忧伤。或许只有真正消失之时,他才有可能会短时间里感伤和无奈。他不是象图河边最后的纸扎艺人。当我跟友人聊起那个唯一的纸扎艺人时,友人还说起了另外一个八十多岁的老人,他曾见过老人,也曾见过老人扎的东西,那些东西精致华丽,友人还说起了其他纸扎艺人,但年纪都已经不轻。
年轻的纸扎艺人,在象图河边很少见。我跟友人说着,他也觉得确实很难见到。我们也说不清楚,如果一个年轻的纸扎艺人出现在我们面前时,我们内心会产生怎样的震动。毕竟纸扎艺人在与葬礼联系得很紧密后,这样的身份也会让我们对世界的判断与认识产生影响。在澜沧江的那些支流边,每次见到一些年轻的民间艺人时,我们内心也会莫名高兴和激动。我曾在弥沙河边见到了年轻的布扎艺人,她前面展示的是她制作的十二生肖。同样也是弥沙河边,我见到了一个制作黑陶的民间艺人,我还在金龙河边见到了一些年轻的木雕艺人,在雪山河边见到了年轻的刺绣艺人,当看到年轻的他们时,我变得不再那么悲观。这与只是不断见到年老体衰的民间艺人,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
那些纸扎艺人是否都是神秘主义者,这是我好奇的,毕竟他们从事的艺术指向的是世界的另一个维度。在一场葬礼上,一切的不可信,似乎又都变得可信起来。许多人又开始成为神秘主义者,都在安葬好死者之后的那一晚,等着亡灵回家——一丝冰凉的风拂过身子,一条悲伤的狗在中堂前发出了既兴奋又悲伤的声音,还有第二天早上摆放在中堂前的烟斗,都在暗示亡灵回来过。当我们在谈论这些时,民间艺人也加入了谈论。
5
我无意间问起了有关那个戏台的种种。我最想了解的是唱戏的人。戏台的命运与唱戏的民间艺人,紧紧联系在一起。戏台的落寞与孤寂,往往是民间艺人赋予的。唱戏的人缺席的戏台,就是孤寂的舞台。我出现在那个戏台前时,戏台给我的感觉便是如此。我以为那个戏台上已经没有人唱戏了。许多传言称很多会唱戏的老人已经离开人世。一个村落的戏班子,无比依靠那些老人。纸扎艺人委婉地打断了我。他就是唱戏的人之一,民间的戏班子是他组织的。唱戏的日子,离我因为一场葬礼在这个村落待的那几天还很远。在春节,人们沉浸于过节的快乐之中。我在离那个古老戏台几座山的村落里,同样沉浸于快乐的过节氛围,没去想那个古老戏台上依然有一群人唱着戏。
我出现在那个古戏台时,太阳灼烧着我。我躲在了戏台之下的过道里,那是一条路。众人在一个戏台下往来。经过之时,我们都无法忽略那是戏台的事实。戏台之下,是阴凉之地。戏台之上,空落。只有在特殊的日子里,戏台上会变得喧闹起来。人们才会在戏台前看着人们表演唱戏。关于唱戏和业余的戏班子,都是他以讲述的方式呈现给我的。我本想让他唱几句。他似乎也看出了我内心的想法。他朝摆在中堂的棺木看了一眼,同时也把手中剪裁的绵纸在铁丝上快速地缠绕着,他以这样的方式暗示我在那时唱几句是很不妥当的。我也深知此理,只能继续听他讲述,也回忆着前不久出现在另外一些村落时,那些戏班子给我留下的印象。它们之间都有着很多相似的地方,它们唱的戏曲可能不一样,它们的戏服可能不一样,一样的是民间戏曲和民间艺人面临的困境。我们看到了那些无奈对于民间艺人的灼烧,他们倍感无奈,许多人外出打工,许多人从小便有意远离戏曲。眼前的老人没提到这些。老人说自己可以算是那个戏班子的头,他评价自己的唱腔时,用到了字正腔圆之类的字眼,对他和这个村落中的其他人而言,字正腔圆很难做到。这是一个白族村落,汉语在日常生活中往往是缺席的,这是一种没有被人们经常运用的语言。一门语言缺席,长时间缺席,它只是以很短暂又特殊的方式出现。
又是巧合的相遇,我在澜沧江的许多个村落里行走时,遇到的民间艺人唱戏的居多,有唱民间吹吹腔的,有唱滇戏的,他们的唱词不同。平日里藏身的语言,在特殊而重要的日子里,变得太重要了。出现在眼前的只有他。我没有多问。是我无意间提到古戏台时,他说自己也是其中唱戏的人。在那些参加葬礼的人群中,还有他们戏班子的人,这是我们都能想到的,也是一问便知的。我们都不问。现场一片喧闹,大家的注意力早就不在戏曲之上。只有我一个人对那些人感兴趣。此刻,最适合的是与人们谈论那些纸扎,那些纸扎出现在了该出现的地方,如果把它们放在别处,我们都无法想象将怎样面对它们。唱戏的人,暂时成了他一个人。
我们试着发挥想象,他一个人在戏台上表演,底下没有任何观众。他在唱给自己听,他也在练习。唱戏可以练习,吹奏伴乐的人也可以练习。唯独作为纸扎艺人时的他,无法进行任何练习。他从小就跟着父亲和爷爷奔走于象图河边的那些村落,参加一个又一个葬礼。在葬礼上,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才真正成为纸扎艺人。在葬礼上开始练习?年幼的心灵里开始意识到,从事纸扎就必然终生都要与悲伤为舞,就要努力适应人们因无尽的悲伤而号啕大哭。他明显感觉到了自己的颤抖。要把那种因无法做到无视别人忧伤的颤抖慢慢平复下来,需要太多的葬礼。纸扎艺人见到了很多种死亡的方式,自然死亡,患病死亡,意外身亡,甚而是轻生者。一个因癌症死亡的人,六十多岁,最后几天只能借助止痛药来缓解那种噬人的疼痛,肉身上已经基本没有肉了,他在苦熬着。众人在苦熬着。纸扎艺人,看到了他行将就木,就来到他家与他聊起了很多过往,过往有痛苦有欢乐,他们讲述的过程变得不再因为死亡的临近而忧伤。老人撑起身子感受着过往,也思考死亡临近之时对于死亡的理解。纸扎艺人跟老人说,那些需要做的纸扎都不会少。老人离开人世,纸扎艺人和自己的伴就来到了那里。还有因心血管疾病离世的,他们中的一些人会给人他们在慢慢恢复的错觉,突然之间,他们便离开了人世;还有年纪不是很大,也是因为疾病离世的,他们离开得很突然。
纸扎艺人有两个。一个负责扎那些葬礼上的东西,另一个负责在那些东西上面画上眼睛,画上嘴,画上鼻孔,画上眉毛,画上图案,写上文字,没有这个人的画笔,那些扎出来的东西身份模糊——这个人是在确定边界与维度,那些用绵纸做的东西都与亡灵有关。我们无法肯定艺术的恒久性问题。他们同样唯一的办法是像白石江边的泥塑艺人那样,把自己的作品拍摄下来。泥塑艺人的作品,会给人长久存在的错觉,不遭到人的破坏,那些作品就会存在很长时间,只有风吹雨噬慢慢破坏着那些泥塑。眼前的纸扎艺人,他们的作品只能存在几天。我本来想帮他们把其中的几种纸扎用手机拍摄记录下来。在面对着那些纸扎,同时想到纸扎背后的一些东西,便不再动念,我把原来拍摄的几张关于纸扎的照片悄悄删除了。他们一个依然在认真做着,另一个在确定身份。只有用毛笔在那些纸扎的东西上标注,我们才能看出是人是十二生肖,还是其他。
一切都是用来焚烧的。一切只是摆放在棺木前和抬着去往墓地的路上,人们才会看到的东西。许多人只是看数量和种类,他们已经太过熟悉纸扎艺人,在他们看来,纸扎艺人每一次的创作并未与上一次有什么不同。不同的只是数量。当我出现时,我告诉自己,一定不能像众人那样看数量和种类。我面对的是民间艺人和他们所创作的民间艺术。它们就是一种民间艺术,只是它们的特殊性,让我们在面对着它们时,很难做到纯粹地欣赏和品味。把目光放在上面时,莫名就会产生心理上的隔阂,我们要把那层厚厚的纸拨开,才能让自己真正面对一种民间艺术。我们从一场葬礼中抽身,那种民间艺术具象化的形态又很难被我们捕捉,它们早已被焚烧,我们不可能见到民间艺人扎一匹纸马摆放起来,只为了供人欣赏。绵纸已经注定了这种艺术的用途和最终的去处。在一场葬礼中,无论我怎么告诉自己,我都无法真正做到超脱于葬礼面对着那门艺术。当我从象图河边离开,我只能在记忆中寻找它们的影子,并尽力描述它们。它们已经很模糊,它们已经无法被我描述。
戏班子,是一个群体。当他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虽然有着各种各样的人,我们却只认识他。他也没有指给我们其他唱戏的人。他是个人,多与少,慢慢变少,直至无。这将是让人无比悲伤的过程。对一些人而言,他们未必会因此而感伤。在别处,那是在弥沙河边,我见到了一群人,他们在练习,他们开始化装,他们开始在那个古老的戏台上唱戏,戏台前坐满了观众,人们评价着那些人的表演。在这里,他依靠讲述。如果不是因为一场葬礼,关于他是一个纸扎艺人,同样只能借助各种讲述。沿着那些河流出现在那些村落时,我相信了众多的讲述,那些似真似幻的讲述。一些讲述进入的是世界神秘的部分,另一些讲述是现实与神秘的交互。
6
许多碎纸纸屑,五彩斑斓。风一吹,色彩飞离地面。我拿着扫把扫一下那些碎纸屑。老人阻止了我,在人下葬之前,这里的风俗是不能扫,只能用火钳捡。用火钳根本无法捡干净。我们姑且只能习惯那些碎片经风一吹,又在风中凌乱。许多人已经习惯那样的场景。我真是第一次面对这样的情景,竟多少还感到有些不习惯。当我离开之时,竟没有见到那个做纸扎的艺人的身影,本来我想跟他告别一声,并想与他约定找时间回来和他聊聊纸扎艺术。我真想了解一下这门我貌似熟悉,又根本不熟悉的民间艺术。他的不在场,似乎也在隐隐暗示着什么。他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他可能也意识到,葬礼结束那一刻,自己又将以另外的身份生活着,一个农民的身份,或者是其他的身份。
我沿着象图河往下。那些风中的五彩纸屑,有些飘落到象图河的某条支流里。随着地理空间的不断变化,象图河开始更名。更名为马渡登河,更名为大龙河,然后汇入沘江。河流一直陪伴着我。在那个行程里,没有人跟我说话,就我一个人,我听着河流撞击着河谷的声息,我看着河流清澈透蓝的样子。如果可以,那时我真有种冲动,在河流中清洗一下那几天身上沾染着的尘埃与污垢。真是一种希冀。我一直沿着河流往下,河流只消很短的时间就会离开我的视线。到云龙县城,沘江的水一直是浑黄的,河流继续往下朝澜沧江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