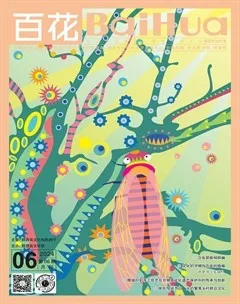戏曲本体下的解构与重构

摘 要:张彩香导演认为戏曲导排需要守正和继承,但继承不是因循守旧,不是原封不动照搬、照抄,而是在传统基础上转化与创新,既尊重传统,又不被传统束缚,就像梅兰芳先生说的“移步不换形”。她在排演每部秦腔剧目时,都坚持秦腔独有的音乐和唱腔,加之她深谙传统戏的舞台呈现,对传统舞台表现的手段信手拈来,但又不拘泥于传统,在守正与创新中不断提升艺术作品的整体性和生命力。
关键词:张彩香;导演艺术;秦腔
张彩香导演对秦腔艺术热爱一生,也奉献了一生。她七岁加入正艺社开始学艺,八岁即登台演出,启蒙老师是惠济民,先学青衣,后主攻刀马旦和花旦。张彩香导演是京剧四大名旦之一尚小云先生的亲传弟子,曾主演剧目《拾玉镯》《杀狗》《走南阳》《昭君出塞》《樊梨花》《失子惊疯》等。张导舞台上几十年的演出经验,让她熟知观众真正想要什么,加之导演理论的支撑,她熟练掌握了秦腔艺术的独特创作规律。她执导的《聂小倩》《白玉楼》《打神告庙》《金麒麟》《清风亭》等剧目不仅深受观众喜爱,而且屡获大奖。
一、深挖剧本,找准主题
在一出戏的整个创作过程中,导演所承担的创作任务是把文学剧本转化为舞台演出,即领导和组织整个创作集体,运用戏曲艺术手段,将剧本的语言、文字形象,转变成生动感人、鲜活具体的人物“立”在舞台上,使之成为舞台演出的艺术。导演二度创作的依据是剧本,排演前要先好好研究剧本。张导在开排前就会对故事的时代背景、人物关系进行纵向和横向的认识与了解,认真感受和理解剧作家笔下的生活和人物,准确把握剧作家的创作意图和剧本的艺术特点。她会在认真研读剧本及找到“戏核”后再进行舞台动作的设计,用戏曲程式去丰富人物,然后亲自示范并启发演员,在所有人的通力合作下将戏剧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立起来。
从事导演及表演教学六十余年的杨非教授曾说:“导演在分析剧本时就已经对剧本所要表现的主题进行了分析研究,并确定了未来演出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那么,这个被确定的主题和思想就成为导演进行艺术构思的一把标尺。”凡是有利于表现主题思想的地方,张导都会调动一切艺术手段去渲染、强调并深化;凡不利于表现甚至干扰主题思想的地方就要冲淡、削弱。她在进行艺术构思时,着力去表现确定的主题和思想,朝着确定的方向去渲染和强调。有的艺术家曾形容导演艺术是“强调与冲淡的艺术”,其道理就在于此。
1985年排演的《白玉楼》是张导排演的第一部戏,她下了很多功夫。张导在认真研读剧本的基础上,对剧本提出了修改意见。最终剧本由陕西省戏剧家协会李群芳老师改编,她将多条线索删减成了一条线索,将一出小生、小旦、武旦唱做并重的戏,改编为一台生旦戏,全剧更为简洁、紧凑,凸显主题。这出戏一经上演,反响热烈。1997年排演《葫芦峪》时,张导不满意原来剧本的唱词,让编剧汪浔进行了改编,大大提升了原剧本中诸葛亮的人物形象。如老剧本的唱词是“山丹丹碎窑窑……”,被编剧改为“三国鼎立不相让,西蜀岂肯束手亡。殚精竭虑托后事,鞠躬尽瘁保汉纲”,改编后的唱词押韵对仗,文采斐然,符合诸葛亮的身份。改编后剧中的“祭灯”“葬台”“托印”三大段均可单独作为折子戏演出,是很叫座的唱功戏。2015年在排演新编历史剧《金麒麟》时,张导对文本进行了逐字逐句的揣摩修改,力求让每个行当都有“戏”,每个角色都“出戏”。她认为秦腔很注重行当齐全,只有行当丰富了,搬上舞台“才有看头”。
二、合理编排,巧妙化用
导演不是只对文学作品进行完全客观的舞台解释,也不是只做简单的形象直译和图解,而是要根据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认知,运用与剧作家不同的艺术手段,对剧本中的文学形象进行再创造,使其成为具有新的审美价值的舞台艺术形象。张导认为各类戏曲剧种一直都有交集,一直都在交汇中相互碰撞、相互学习。张导能从不同艺术形式的表演中,汲取她需要的表现形式,以自然和谐为原则巧妙化用,丰富到秦腔表演当中。
人物形象是导演构思的中心任务之一。戏剧的主题思想、事件、冲突、情节等均要通过舞台上活生生的人物形象来体现,离开了人物形象的塑造,就不存在戏剧艺术了。导演对人物形象的构思直接关系到舞台演出的成败。演员是人物形象的创造者,导演要使众多演员扮演的角色融于一台,又各具个性,就必须在构思过程中对每一个角色进行艺术设计。张导告诫演员演戏一定要从人物出发,人物需要什么样的语言、动作、表情,需要演员根据自身舞台经验来准确把握。如果出现雷同,人物性格在声腔上就无法体现,饰演的角色也不能从声音上让观众分辨出来。
1986年,张导在给胡香串排《白玉楼》“上马”片段时,重新设计了一个动作,走一个单身旋子,上马童腿,一个后探身,完成一个身段造型。这种造型动作,在芭蕾舞表演中很常见。《白玉楼》原来的表演中,舞台上呈现的上马动作是马童把白玉楼背起来行走。张导借鉴了尚先生《昭君出塞》中的上马动作,加入了新的元素,给白玉楼编排了一个新的上马动作:白玉楼一个小圆场转身,上到马童腿上,然后一个向后探身造型亮相。整个动作一气呵成,毫不累赘,又符合现实生活。
剧目要有特色,观众喜欢看,离不开导演的调度。导演不仅要充分发挥地方戏的特长,而且要深挖演员身上的功夫,这就要求导演在二度创作时多费心思。张导认为只要这些功夫符合角色,符合这个戏的题材和体裁,就可以“化用”。2013年,张导把罗华演了多年的《辕门斩子》做了调整,她把降龙木从放在桌子后改为放在桌子前,把它作为一个贯穿始终的“线索”出现。在设计杨延昭(罗华饰演)出场时,借鉴了电影推镜头的手法,缩短与观众的距离,“啪”一转身演员出来了。在见到降龙木之前杨延昭经历了“三仗”:第一仗,被儿媳妇打下去了;第二仗,是与母亲的对手戏,他爱母亲孝顺母亲;第三仗,穆桂英拿着降龙木来了,之前的受辱,要斩儿子的一气之勇立马就站得住脚了。感情层层变化和推进,再从桌后调出杨六郎,一下就把节奏和情绪调动起来了。这时,杨延昭看见降龙木自然就很受震动,那种表演的激情超乎想象,立刻凸显出鲜明的人物形象。
戏曲表演离不开技巧程式,但表演运用要突破程式化。导演就是要把这些富有创造性变化的表演程式,在基于人物性格和剧情需要的基础上进行合理的创新,使每个动作程式都能找到传统的出处,又都能恰到好处地塑造剧中人物,从而推动剧情发展和主题深化。《金麒麟》第六场的绑子归案中,余安的母亲痛心不已,扭身掩面哭泣时一只水袖侧搭在肩膀上,这样细腻的动作来自昆曲,但用在这场戏这个人物身上极其恰当,表现出了她极度无助痛苦的内心活动。
三、保留唱腔,创新音乐
武汉大学郑传寅教授说过,戏曲趋同是没有出路的。俗话说“七分音乐三分戏”,戏曲音乐是戏曲的灵魂,也是一个戏曲剧种区别于其他剧种的关键所在。戏曲导演不单纯是和戏曲文学剧本打交道,其中还少不了音乐问题。这里所讲的音乐问题,不包括演唱、演奏等舞台创作中的音乐部分。戏曲剧本必然存在以下问题:一个剧本的戏剧结构与音乐结构统一与否,是否有该唱的地方不唱、不该唱的地方要唱的现象;诗的语言、音乐的语言与戏剧的语言动作有无矛盾;文学形象、音乐形象与戏曲舞台形象是否协调;唱与念白安排得是否恰当,是否适合于戏曲舞台演出。
张导对秦腔的音乐唱腔定位准确,有变化但不跑偏,她认为坚守不是保守,在坚守的前提下改变,是为了秦腔走得更远,而不是不懂秦腔音乐的灵魂就盲目创作。张导认为戏曲是个总称,戏曲就是互相借鉴,秦腔也可以有“优美”的表达,要学会“姊妹借鉴”,学会化用其他剧种的程式唱腔,丰富秦腔的舞台表演。秦腔唱腔中有的地方太刺激,让一些观众受不了,就需要请作曲加以调整和改进,但又不失秦腔激越的特点。秦腔的创新还要根据演员的演唱特点和人物设定来写音乐,改掉不太优美的地方,充分发挥演员的唱功,根据人物性格编排音乐,并且保持剧种音乐的特色。
导排《白玉楼》时,她希望用歌剧二部重唱的手法,渲染男女主角的爱情。著名琴师张满堂完成了音乐唱腔设计,歌舞剧院张长兴配器,这个唱段获得很好的反响。这场戏的服装、道具,还有演员的装饰,都经过重新构思设计,展现了一个全新的舞台样式,给人耳目一新的视觉享受。
四、服务演出,舞美写意
对舞台空间的构思是导演与舞台美术设计者合作的主要内容,它直接关系到演出样式的确定、演出风格的形成、演员在舞台上的行动。导演对舞台布景、服装、舞台灯光、影像等的处理,要尊重戏曲的美学原则。舞台空间布置要注意舞台构图的要求,要匀称、均衡、和谐;舞台空间要为剧中人物提供生活环境,要方便演员的表演,还要有利于导演进行舞台调度;在非幻觉的假定性的空间处理上,特别要注意安排好虚实关系、景与物之间的关系、景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等;舞美设计的整体风格要与剧种的气质相得益彰。
《白玉楼》的舞美多采用侧木条、绿木条、灰毯子、绿毯子等冷色调和较有质感的材质,和当下流行的“中性”舞美风格有些相似。戏曲的服、化、道是很有特点的,是分行当的,是很有规矩的,我们要尊重规矩,但不能死守规矩,要行当但不受行当限制,要程式但不要程式化。戏曲必须改革,不改革就没有生命力,但是改什么也不能改了“姓”。《白玉楼》的服饰设计去繁就简,整体比较飘逸,衣服上加了些许印花,增加了美感。其中有一场演出是观画,张导设计的舞美是把白绸缎从桌子上拉到舞台一角,大约就是从上场口到下场口舞台的一角这样的距离。然后又给张彦设计了拖腔、搓步、跪步等程式动作,一步一步往前移,一步一步调动情绪,把贫贱不能移的坚定的夫妻之情和悲怆无奈表现得淋漓尽致。
《聂小倩》的舞美打破了传统一桌二椅的舞台布景,将舞台幕布从后台一直延伸到台上。演员从后台的幕布中缓缓走出来,营造出一种跋山涉水的意境,有种时空穿梭之感。正是这种时空穿梭之感给演员留足了表演的空间,演员很容易就进入导演所创造的这种意境,这样的舞美设计对整体的舞台表演都有很大的助益。《葫芦峪》写意的舞美及飘逸的服装设计也是一个亮点,张导推翻秦腔原来的装扮,借鉴京剧马连良的《借东风》,设计了仿京剧服装,比较潇洒灵动。
五、全情投入,执着付出
导演排戏,也是一个创作的过程,如果没有情感投入,根本无法支撑这一过程,看似平淡甚至孤独的过程其实是对导演的一种磨炼。在经历了剧中人物的情感洗礼之后,一切的想法和努力最后都通过演员在舞台上呈现,这也就是导演的自我心灵与演员、与舞美等一切舞台表现形式相融的过程。
无论是在排练场还是在舞台上,张导都喜欢在细微处琢磨戏,在塑造不同的剧中人物时,反复推敲、反复演练。她觉得天赋固然重要,但是静下心琢磨戏更重要。她平时就很善于观察生活,对自己的几出拿手戏总是反复锤炼、精心打磨,从生活出发,在表现人物丰富的感情上下功夫。1978年,43岁的张彩香重返舞台排演《拾玉镯》,对剧中“三看傅朋”这段戏重新设计了一系列动作,把孙玉姣邂逅傅朋时羞怯爱慕的神态表现得细腻逼真而富有层次。观众无不为她能克服自身年龄与角色要求之间的矛盾,塑造出孙玉姣这个美丽多情的少女形象而赞叹。张彩香老师演戏如此认真鲜活,导戏亦是如此,她说:“我只要一看剧本,头脑中就会出现人物、场景,这个怎么演,那个怎么弄,脑子里有画面。”
“要想人前甩翠,就得背后受罪。”张导用一生践行着她的恩师尚小云先生的这句话。正如她所说:“其实,我每天都要对着镜子,反复练习舞台基本功,耸肩、抬肘、吸腹、夹屁股,把这全套的动作要练到一种自然状态,不能让观众看出来,身体各个部位要呈现出自然和谐的状态。”[1]1994年退休后,张导“退而不休”,坚持练功不懈,授艺不止。在2013年举行的陕西省文华奖专业秦腔电视大赛中,张彩香应邀担任评委,精彩独到、批评鼓励兼有的点评风格,深受行内外人士认可。
在张导身上没有一个“私”字,不管是自己上台演出还是后来当导演为团里排戏,她都倾囊相授,毫不保留。据罗华回忆,当时为了排戏,张彩香不仅给演员做饭,还在后台给演员们化妆、包大头、画眉毛画眼睛、贴水鬓、绑鞋带、提靴子,事无巨细。令罗华记忆深刻的是,秦腔《谢瑶环》搬上舞台时,张导场场到,场场守,还搭手贴片子、换场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演员演好,给观众呈现一场完美的演出。她还要求演员不要把后场的矛盾带到前场,要做到在搭戏时一丝不苟,这是对自己负责,对观众负责。有一件特别不可思议的事情被罗华津津乐道,1997年,她们凭着一腔热血用了六天时间就把《葫芦峪》搬上了舞台,从重新改编、排练、制作服装到上演仅仅用了六天时间,一部大戏就“横空出世”了。寒冬腊月,演员们就在张导自家院子排练,张导一边导着戏一边还为排戏的演员们做着饭。因爱戏而无条件付出,也只有张导。
张导能依据传统技法、传统套路和戏剧特征,因势利导、灵活运用在演员身上、剧中人物身上、戏剧情节之中。“张彩香老师自1985年转任导演,1990年逐渐淡出舞台,1994年退休,她一刻也没有停歇。从‘六十而耳顺’到‘耄耋’老人,一直在为秦腔艺术的传承发展贡献余热,并以这种方式怀念自己的前辈、老师。”[2]张彩香一辈子默默爱着秦腔,想着秦腔,念着秦腔,为秦腔无私奉献,秦腔也成就了她的艺术生命。
参考文献
[1] 张彩香,李光辉.艺涯回溯[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22:206.
[2] 同[1]:2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