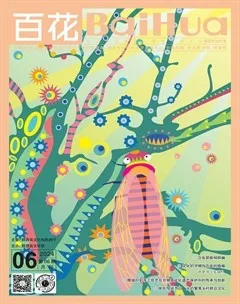从权力主题角度浅析弗兰茨·卡夫卡的小说《在流放地》

摘 要:权力可以作为《在流放地》主题研究的一个切入口。小说中,机器充当了权力的载体,执行处决的过程通过营造正义的幻象掩盖了背后的权力狂欢;在军官的不可靠叙述中,流放地正发生着一场权力斗争,小说通过戏剧性反讽揭示了传统专制权力的命运;作为旁观者,旅行者的权力审视使得小说再次走向了歧义。卡夫卡正是借助这篇具有荒诞色彩的小说,表达了对权力这一人类社会重大命题的关注与思考。本文以权力为切入口,结合叙事学理论,尝试为小说的主题研究提供一条新的阐释路径。
关键词:卡夫卡;《在流放地》;权力;主题研究
在《在流放地》这篇小说中,卡夫卡围绕着一个特殊的惩罚机器展开叙述。旅行者受邀观看一个士兵的处决,军官向他介绍处决的机器,对其设计和精密程度如数家珍。在判决执行前,旅行者得知被判决者的审判程序并不公正,产生了是否有权提出反对意见的纠结。军官企图说服他成为这项由老指挥官发明的刑罚的支持者,并与自己一同对抗新指挥官的革新措施。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军官自愿成为受刑者,不料机器运转出现问题,军官最终惨死于机器之中,并没有获得他所期许的解脱。综观全文,我们会发现人物和情节有着强烈的荒诞色彩:被判决者为何不知道自己的判决?程序不正当的审判何以成立?施虐者何以自愿成为受虐者?这些问题使得文本解读变得颇为困难。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种困难也带来了阐释的开放性,小说通过它的写作方法提供的是一种对事实的感觉,你可以自由解释它,自由创作它。[1]
目前国内关于《在流放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思想主旨的阐释上,代表观点如下:惩罚主题,宗教主题,异化主题。笔者则认为,小说中的象征意象和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视作权力的载体、符号或化身,权力也因此可以作为理解文本的一个切入口。
一、正义幻象背后的权力狂欢
关于权力,学者们在不同的理论语境中给出不同定义,其运用的广泛程度正如加尔布雷思在《权力的分析》一书中所言:“很少有什么词汇像‘权力’一词这样,几乎不需要考虑它的意义而又如此经常地被人们使用,像它这样存在于人类所有的时代。”[2]马克斯·韦伯认为:“权力是把一个人的意志强加在其他人的行为之上的能力。”[3]在卡夫卡的笔下,权力的这种压制性力量得到了充分展现。显而易见,小说描写的这场自始至终都没有遵循程序正义的审判,便是未加控制的权力的体现。军官所主导的法庭审判遵循的准则是“罪行总是毋庸置疑的”[4],这使得少尉的一面之词足以成为判决的依据。纯粹的权力形式存在于立法者的功能之中,权力的行为模式带有司法话语特征[5],军官一个人承担了立法者与司法者的双重角色,也就成为彻底的独裁者。而这种权力模式,恰如韦伯所言的传统型权威,是“被自古就有的遵从权威的影响和习惯性的观念神圣化的世俗的传统统治”[6]。
因为传统型权力模式对权力绝对性和不可侵犯性的要求,压制性力量往往通过暴力和惩罚得以实现。小说中那台独特的机器便是以暴力惩罚达到统治目的的最佳载体,甚至成为权力象征。而权力又通过一系列仪式显现自身,这样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军官对机器和判决形式的那种偏执狂式的痴迷,并从中窥视到他强烈的权力崇拜情结。小说中机器的处决形式,与福柯所描绘的古典时期的刑罚实践惊人相似,“刑罚是一种技术,它并非一种无法无天的极端狂暴表现”[7]。在卡夫卡笔下,机器的工作程序和操作过程有着精密特征,作为处决仪式的一部分,机器还会给被处决者打上所犯罪行的文字,并在受刑者辨认后刺穿他的身体,整个过程都有着精细的时间设定。在军官的叙述中,这种能被计算的、极端化的酷刑表演曾在数百双眼睛的注视下进行,情形如同狂欢节的盛况。
那么,这种权力展演的暴力性,又如何被流放地的人民接受的呢?汉娜·阿伦特在《暴力与文明》一书中谈道:“暴力从本质上讲是工具性的,像其他手段一样,它在达到目的的过程中总是需要指引和正当理由。”[8]我们会发现,流放地刑罚实践的正当性,就是小说中不断提及的“正义”。然而,就被判决者的审判程序来看,这里的正义话语显然带有虚假性质:权力生产了关于何谓“正义”的知识,而知识效命于生产它的权力,正义的实践过程实质上就是权力关系的符号化,由此两者形成了共谋关系。“权力通过语言,在创造法则的同时,也控制了对象。”[9]流放地的民众承认了这种不合理的权力话语,实质上就是承认了隐藏在后面的权力的合法性和正当性。在刑罚表演中,民众在“观看”与“被观看”的模式中进入了一种不对称的权力关系,“观看者”由于享受了虚假的权力下放,从而会感受到“正义得到了伸张”[10],而行刑结束后“正义的光辉”的消逝,则是这种权力幻觉的最终破灭。在一次次仪式中,宰制性的权力结构得到了不断再生产。由此可见,机器作为权力的载体,在营造正义幻象的同时也生产出了权力狂欢,不管是军官的语言狂欢还是民众观看时的狂欢盛况,权力狂欢的背后都潜藏着权力崇拜的影子。
二、不可靠叙述下的权力斗争
韦恩·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不可靠叙述”这一概念:“当叙述者为作品的思想规范辩护或接近这一准则行动时,我把这样的叙述者称之为可信(可靠)的,反之,我称之为不可信(不可靠)的。”[11]布斯从“事实轴”和“价值轴”两条轴线对不可靠叙述作了进一步解释:前者涉及故事事实,主要指叙述者在叙述事件时前后不一致或与事实不相符;后者涉及价值判断,主要指进行价值判断时出现偏差。在这里,隐含作者的代言人无疑可以视作最可靠的叙述者,而一旦作品中出现了在思维活动、精神状况、价值体系等方面不同寻常的叙述者,叙述的可靠与否便成为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在流放地》这一第三人称叙述的小说采用了不同人物的有限视角,从一个人物的有限感知转换到另一人物的有限感知,在整体上取代了全知叙述者的感知。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小说中不存在一个可靠的叙述者,卡夫卡巧妙地设置了一位外来者形象:“他一生经历甚丰,不可能在这件事上有任何动摇;他本质上是个诚实无畏的人。”[12]他对审判程序也有着自己的看法:“审判程序不公正,处决不人道,这都是毫无疑问的。”[13]而他最开始的中立态度又体现出了文化相对主义的思想。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军官对机器的痴迷,以及迫切想要维护审判程序的欲念,这些细节让我们不得不对这一人物的叙述产生怀疑,而读者也可以在两者话语的对照中看到军官对事实的扭曲和变形。除了上文谈到的军官回忆中的处决盛况,他对于流放地正在发生的权力斗争的叙述也呈现出类似的语言狂欢形式,其中充满了对未发生情景的想象和对他人想法的揣测。
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老指挥官还是新指挥官,他们也都是被人物叙述出来的,在文本中都是不在场的,我们无法看清他们真正的形象。因此总的来看,作为旧指挥官及其审判程序的非理性拥趸,军官传递了一种“变形了的信息”[14],而流放地上戏剧性的权力斗争更多是军官脑海中的想象。在这种想象性的对抗中,军官从老指挥官那里获得了假想的“精神支撑”,并不断争取旅行者的认同与支持,从而与新指挥官所代表的变革力量进行权力博弈。然而,当审判从“审判长的职责”变成了“随便哪个士兵都可以做的事”,当观看处决从曾经的人山人海变成了仅有五个人在场,当机器在运转过程中开始出现各种意外状况,这些情况的转变足以说明新旧力量对比的悬殊。更具讽刺性的是,军官虽然对这种情况有所感知,但依然义无反顾地成为这份遗产的唯一代理人。在这种境况下,军官是以自欺的方式延续了对权力的持有。
这种想象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张力,一方面揭示着军官及其推崇的审判程序终将被取代的事实,另一方面也在文本中创造了戏剧性的反讽,读者对作品中人物所处情境的认知与人物的认知存在本质上的差异。这种反讽形式的实现,离不开旅行者这一形象,这位故事内的人物叙述者所提供的可靠性话语,除了在事实轴层面帮助读者完成了军官虚假想象的纠偏,也在价值轴层面展开了对传统专制权力命运的深刻揭示:在启蒙主义和理性精神的审视下,独裁主义以及由专制权力所强加的统治终将走向崩溃。军官的死亡,便可视作这种传统型权威命运的象征。
三、旁观者的权力审视
正如格非在《卡夫卡的钟摆》中所说:“卡夫卡的故事是一个不发展的故事,从起点回到起点,或者说在被各种因素的纠缠中陷入了泥淖,剩下的就是一只秋千的摆动。”[15]我们将目光再次聚焦到旅行者身上,不由得发现他身上潜在的一种飘摇不定的态度,这使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再次产生歧义。如果说旅行者所表征的现代理性文化揭示了传统专制权力终将走向崩溃的命运,那么他对军官本身、对流放地的人民又秉持着什么样的态度呢?换句话说,这篇小说的结构可以单纯视作传统专制与现代文明的二元对立吗?军官与机器的毁灭,是否意味着流放地将走出权力的阴影?答案或许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
实际上,旅行者对机器和处决的态度是复杂的。一开始,他对这台机器的兴趣不大,但是在军官介绍的过程中,旅行者逐渐萌发了兴趣。在得知审判程序的不公正后,他虽然感到不满意,但采取了相对主义的态度,认为在流放地“特殊的惩处是必要的,彻底的军事化做法是必需的”[16]。而当军官自愿成为受刑者时,旅行者却又“一言不发”,“决心袖手旁观”[17]。在这里,否定性的态度被弱化了,旅行者的不作为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认同。而要理解旅行者这样做的深层原因,还需要联系他在流放地的所见所闻来看。
除了军官和新老指挥官,小说还塑造了流放地的人民形象。旅行者最开始时是同情,想弄清楚被判决者的处境。而被判决者对自己即将迎来的判决麻木而不自知的态度,让旅行者难以理解。放到现实来看,这种情形或许显得很荒谬,但卡夫卡在作品中正是通过建构观念的现实,将我们熟知的世界推向了极端,反而书写了人类生存境况的某种“真实”。笔者认为,小说的这一细节深刻揭示了被判决者和曾经的观刑者们在精神层面的共通性,即对于权力的绝对认同,这种认同既可以理解为潜意识层面的权力崇拜,也可以认为是人类永远无法逃脱的生存境况。
正如老指挥官墓碑上的预言“指挥官数载之后复活,由此屋率众追随者光复流放地”[18],权力并不会因为某个具体的人或政权的消失而消失,它始终以不同的形态如阴影般笼罩着人类社会。一方面,流放地人民的麻木和军官的殉道,揭示了权力崇拜这一精神传统的强大;另一方面,老指挥官墓碑上的预言,又暗示了权力形态的多样性以及权力追随者的众多。小说最后,旅行者拒绝让士兵和被判决者上船,独自一个人逃离了流放地,或许可以视作启蒙理性在权力面前的失效与无力。对权力的审视,让旅行者看到了它的根深蒂固性,也因此产生了对变革、启蒙和理性的深刻怀疑。卡夫卡正是借助这一形象,表达了对权力无始无终、无边无际的悲观体认。
参考文献
[1] 叶庭芳.论卡夫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
[2] 加尔布雷思.权力的分析[M].陶远华,苏世军,译.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8.
[3] 同[2].
[4] 卡夫卡.卡夫卡小说全集[M].韩瑞祥,仝保民,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
[5]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第一卷[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7.
[6] 韦伯.学术生涯与政治生涯:对大学生的两篇讲演[M].王容芬,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8.
[7] 福柯.规训与惩罚(修订译本)[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
[8] 阿伦特.暴力与文明[M].王晓娜,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3:19.
[9] 同[5].
[10] 同[4].
[11] 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宏,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12] 同[4].
[13] 同[4].
[14] 申丹,王丽亚.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15] 格非.卡夫卡的钟摆[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144.
[16] 同[4].
[17] 同[4].
[18] 同[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