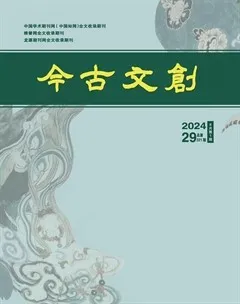雅安方言 “ 拢 ” 的语义分析
【摘要】四川省雅安地区是四川盆地和青藏高原的结合过渡地带,雅安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雅棉小片,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多种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因此,本文结合多种历史参考资料,试图通过探索雅安方言中“拢”的本义和今义,同时对比现代汉语普通话,对“拢”在词义上的历史继承和发展变化提供一个参考。
【关键词】雅安方言;拢;语义分析
【中图分类号】H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标号】2096-8264(2024)29-0129-04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38
泱泱华夏,自古以来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受语言系统外部、内部各种因素的相互影响,中国语言文字作为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发展,具有渐变和不平衡的演变特点。[1]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分化,地域方言(简称“方言”)作为同一语言的地域分支,在同一语言的心理认同下出现,语言社团的数量也有所增加。[1]在语言演变不平衡性的支配下,语言系统内部各要素也呈现出不同的变动速率,在语音、词汇、语法三个子系统中,除了变化最显著的语音,其次便是词汇。
四川雅安地区位于川藏、川滇公路交会处,距离成都120公里,是四川盆地与青藏高原、汉文化与民族文化、现代中心城市与原始自然生态区的结合过渡地带,是古南方丝绸之路的门户和必经之路。曾为西康省的省会,雅安位于四川盆地西缘,东靠成都、西连甘孜、南接凉山、北邻阿坝,素有“川西咽喉”“西藏门户”“民族走廊”之称。现共辖2区6县:雨城、名山两区和天全、芦山、宝兴、荥经、汉源、石棉六县。历史上,这里曾发生过多次移民活动,尤其是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大移民,在改变着雅安人口规模的同时也对雅安本土语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雅安方言属于西南官话灌赤片雅棉小片,是民族文化、地域文化等多种文化交流碰撞的结果,具有深刻的文化底蕴和历史价值。雅安方言中的词汇在历史的变迁中显示出浓厚的地域特色,反映出雅安本地人的文化心理状态以及本地文化的发展变化。本文以市政府所驻地雨城区方言作为考察对象,对雅安方言中的“拢”一词进行语义分析。
一、“拢”的本义
词的本义指词在文献中可考证的最初的意义,不一定等同于原始意义,本义是产生这个词的其他意义的基础。[2]
“拢”在汉字简化前写作“攏”,北宋陈彭年、丘雍所著的《广韵》一书中记载“攏”:“力董切,上董,来。”作动词,最早在东晋郭璞的名篇《江赋》中使用:“聿經始於洛沫,攏萬川乎巴梁。”意思是岷山引导的江河之水最先蜿蜒流经洛水和沫水,最后在古巴郡梁州收拢了无数条小河流。河流原先只有少数几条支流,最后这几条支流将周围的原本不同河道的流水合在一起。可见,“拢”最早的意义是“聚合”。
另外,唐代丁仙芝的《江南曲》之二:“知郎旧时意,且请拢船头。”当中的“拢”译为“靠拢”,使船靠岸,作动词,表趋向,与受事的移动方向有关。唐朝李延寿的《北史·卢诞传》:“于是率百骑,各拢一马,至大騩山。”中“拢”的意思是牵,指“人牵拉着马”,人和马原本在空间位置上有距离,人通过“拢”,使马和人聚合在一起,所以“拢”也是“聚合”的意思,这里“拢”与施事的动作有关。清代翟灏《通俗编·杂事》:“小理发曰拢。”意思是梳理头发被称作“拢”,“拢”在这里被理解为梳理、整理的一种动作,是将原本位置散的、乱的物体通过聚合变得整齐、有序,“拢”的词义也是“聚合”。
二、“拢”的今义
经过历史不断的演变,“拢”的词义到今天已经在本义基础上有了很多的发展和变化,在汉语普通话和雅安方言中都有体现。
(一)汉语普通话中“拢”的今义
根据《现代汉语词典》查找的结果,“拢”的今义有以下五个义项:
(1)合上:他笑得嘴都合不拢了。
(2)靠近;到达:拢岸;靠拢。
(3)总合:拢共;拢总;把账拢一拢。
(4)使不松散或不离开;收拢:拢音;用绳子把柴火拢住;把孩子拢在怀里;拢住他的心。
(5)梳(头发):她用梳子拢了拢头发。
第一个是“合上”。在这项词义里“拢”用作动词,表示使打开的东西贴合在一起,状态由开到闭,描述事物发展的一种结果。典型的例子就是“他笑得嘴都合不拢”,笑时上下嘴唇张开,难以闭合,故称“合不拢”。相反,“合拢”就是指合上,闭合,与本义“聚合”有关联。在清代李渔的《凰求凤·阻兵》中就已经可见:“这等说起来,神仙也讲不拢,劝你不要思量。”
第二个是“靠近、到达”。在“拢”的这个义项里,施事和受事同时出现,施事主体向中心靠近,发出带有趋向性的动作,使双方距离缩短。如“靠拢”,强调距离减小,着重突出位移的动作。而“拢岸”一般指的是未与陆地接触的船只、水生生物等渐渐缩小与陆地的距离直至距离为零的过程,有时也表示结果义。可见,“靠近、到达”这个意象也是由“拢”的本义“聚合”引申而来。如:“你靠拢炉子就热和了”或“我都走拢你说的这个地方了。”
第三个是“总合”。在这个义项里“拢”也是用作动词,表示一种可能义。“拢”既可以等同于“总”“总的”,如“拢共”“拢总”也可以表现出使动用法,指“使……归到一起”,如“把账拢一拢”指把账归到一起。可见,这个意义也与“聚合”有关联。例如:宋代李诫《营造法式·小木作制度四·佛道帐》:“造佛道帐之制,自坐龟脚至鸱尾,共高二丈九尺,内外拢深一丈二尺五寸。”中的“拢深”就已经表示“总深”的意义了。
第四个是“使不松散或不离开、收拢”。在这个词义里,“拢”也是作动词用,强调的是一种结果。如“拢音”表示使音波在一定范围内不分散,“用绳子把柴火拢住”意思是使柴火归拢,不使火焰熄灭。“把孩子拢在怀里”目的是让孩子不离开自己,缩短与自己的距离,由“拢”的意象“靠近”引申而来。这个用法在唐代白居易的《府西亭纳凉归》:“带宽衫解领,马稳人拢辔”中就有使用,“拢辔”就是“收拢辔头”的意思。唐末贯休《观李翰林真二首》:“天马难拢勒,仙房久闭扃”中的“拢勒”也是“收拢勒住缰绳”的意思。
第五个是“梳(头发)”。这个义项里“拢”还是作动词,表示梳理头发、毛发。如“她用梳子拢了拢头发”,自然状态下女性的头发是散乱的,当对头发实施[梳理]具体的动作后,头发方向会趋于一致。由此可见,这个意义也与“拢”的本义“聚合”有关。如唐代韩偓《信笔》诗:“睡髻休频拢,春眉忍更长”。前蜀李珣《南乡子》“拢云髻,背犀梳,焦红衫映绿罗裾”中也能体现。
(二)雅安方言“拢”的今义
楚国是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之一,作为延续最久、实力最强的诸侯国之一,在经历了上千年的发展后,楚语成了强势语言,伴随着楚国征服地区的不断扩大,这些地区的语言逐渐被楚语同化,楚语的生存土壤不断绵延。[3]曾作为战国时楚国都城所在地的湖北,深受楚语的影响。后来在少数民族向内地迁移的过程中,南方方言呈现流窜的现象,没有了强势语言,同化难以进行,所以楚语在湖北还保留着自己的方言特点。[3]明末清初,汉族往西南大规模迁移,在此次移民过程中,西南官话由于语言间的相互影响而逐步发展、定型。[4]在明末清初,长达三十年的战乱使得四川人口骤减,在清政府的政策鼓励下,“湖广填四川”运动作为一次人口大迁徙深刻影响着四川的文化生态,楚语便成了西南官话的起源。雅安市历来作为四川的重要地区,雅安方言同样是对西南官话的继承和发展,“拢”在今天的雅安方言中也展现出了丰富的意义。
1.词义继承
中国词汇系统经过几千年的发展,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新词不断产生,原有的词汇也在本义的基础上引申出了许多意义,反映出社会和人们心理的变化。因此,了解方言的引申义和本义之间的关系,认识词在共时层面不同地区的词义继承,有助于进一步认识和了解中国本土语言或方言的多样面貌。雅安方言中的“拢”就继承了其本义,同时也引申了一些地方口语。
(1)“拢”在雅安方言中的词类划分
词类即词在语法性质上的分类,主要根据与其他词组合,能够在一个句子中充当句法成分的能力,划分出一个词在语法上的分类。除了功能标准外,意义标准和形态标准(形态标准指汉语缺乏形态的改变以及充当不同成分时不会发生形态上的嬗变)也可作为划分词类的标准和依据。根据能否独立作句子成分,词可划分出实词和虚词两个大的组成部分,实词意义实在且能独立作句子成分,虚词意义空灵、抽象,不能独立充当句子成分。动词属于实词,表示动作、行为等,又可分为判断动词、能愿动词和趋向动词。
其中,趋向动词指的是表示实际动作位移的方向并能够后附于动词性词语充任补语的词。[5]“拢”在雅安方言中同时满足[+表示实际动作的位移][+方向性][+后附于动词性词语充任补语]三个属性,所以属于趋向动词的范畴。
(2)“拢”在雅安方言中的语义类型
现代汉语的句法结构中有八种句法成分,分别是主语、谓语、动语、宾语、定语、状语、补语和中心语,除此之外,还有句子独有的独立成分。其中,补语通常跟在谓词性短语里作为中心语的补充,例如:“写〈完了〉”是一个动词性的短语,动词“写”是短语的中心语,“完了”充当中心语的补语;“好看得〈很〉”是一个形容词性的短语,形容词“好看”是短语的中心语,“很”就充当着中心语的补语。补语作为一种句法成分,起着补充说明的作用,它可以用来说明结果、情态、趋向、数量、时间、地点和可能,还可以用来说明性质、状态的程度以及人、物的状态。补语可以分为结果补语、情态补语、趋向补语、数量补语、时地补语、可能补语以及程度补语。
在雅安方言中,“拢”可作趋向补语。表示事物随着动作的实施而移动的方向,都用趋向动词充当。刘月华通过对趋向动词作补语时的语法观察,得出趋向补语都具备的三种意义:趋向义、结果义和状态义。[6]雅安方言中的“拢”可以兼表趋向义和结果义。
①表示趋向义
作表示趋向义的趋向补语时,在雅安方言里,“拢”可以跟在动词后面,形成“V拢”结构,V是施事主体所实施的具体动作,“拢”是受事的位移方向。动词根据本身是否带有[闭合]的语义成分还可以分成两类:
A.V[+闭合],如“关、合、闭”等。
“你把门都关拢嘛。”(你把门关了吧。)
“我眼皮子都合拢哚。”(我眼睛都闭上了。)
“小娃娃些嘴巴闭拢罢。”(小孩子不要插话。)
这个意义在清代李海观的长篇小说《歧路灯》里就已经出现:“邓林摸着刀子来了,谢豹亦带着湿鞋袜合拢前来。”
B.V[-闭合],如“走、跑、拉”等。
“喇都走拢哚。”(他已经到达目的地了。)
“等你跑拢那儿,天都黑了。”(等你到的时候天都黑了。)
“你呚把窗子拉拢。”(你去关窗户。)
明末清初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中就有这个用法:“看了一本讲章,坐在上面,把那些学生,大的小的,通的不通的,都走拢一处,把那讲章上的说话,读一遍与他们听,不管人省得不省得,这便叫是讲过书了。”“走”表示实际动作,不含[闭合]的语义特征,“拢”表示受事随动作的实施不断向中心位移,“拢”跟在“走”后形成“走拢”结构,在这里表示走到学生附近讲课。
②表示结果义
作表示结果义的趋向补语时,雅安话里的“拢”表示物体从完全分离到不完全接触到完全接触直至闭合的结果,接触面积不断增大,距离逐渐减小最终为零。例如:
“我已经把笼笼儿关拢了。”(笼子已经关了。)
“你把杂本儿些都捡拢到一堆。”(你把杂物都收到同一个地方。)
元末明初小说《水浒传·第一百十回》:“却用油线缝拢,外用敷药贴了,内用长托之剂。”中“缝拢”的“拢”也作表示结果义的趋向补语使用,意思是通过油线使原本开裂的皮肉链接在一起,引申出“闭合”之义。可见“拢”的这个意义和作用在雅安方言中的词义继承。
(3)“拢”在雅安方言中的色彩义
词义可分为“词汇意义”和“语法意义”两个组成部分,其中词汇意义由概念义和色彩义组成,概念义又称“理性义”,是一个词的主要意义。色彩义以概念义为基础,又可以分为感情色彩义、形象色彩义、地域色彩义、时代色彩义、修辞色彩义及雅俗色彩义等多个种类。其中,语体色彩和日常生活中人际交往的得体与否有关,又称文体色彩,有口语体和书面语体之分。“拢”的语体色彩义在雅安方言中就尤为突出。
雅安方言里,“拢”常常用于本地人的日常交际,并在较亲密、私人的言语环境中作口语使用。而在正式场合,如上下级交流、发言演讲、文书写作等各个非私人的严肃场合,会使用同义并具有书面语色彩的词语来表达。
例如,同样传递“到达目的地”这一信息,在与家人、朋友传达时,雅安方言表达为:“我都拢说的那块旮旮哚。”传递出一种亲切感,能够迅速地拉近与听话者的距离。不会使用雅安方言的人则无法理解这句话的意思,而使用雅安话的语言社团则能迅速“解码”,一定程度上显示出雅安方言的“排他性”。在正式非私人言语环境如应上级要求出差前往某地,则表达为:“我已走到北京。”体现出对工作的重视和对上级的尊重,具有书面语色彩。可见,“拢”在雅安方言中具有浓厚的口语色彩。
“拢”的口语色彩义也体现了词义的继承关系。在我国古代,同样表达“整理毛发”这个意思,口语使用中会用“拢”,正式场合则用“梳”。《红楼梦·第四十二回》中宝钗和黛玉说笑,指着她说:“怪不得老太太疼你,众人爱你伶俐,今儿我也怪疼你的了。过来,我替你把头发拢一拢。”宝钗和黛玉关系亲密,且是姐妹间非私人的言语环境,故用体现口语色彩义的“拢”。同是《红楼梦》在第四十八回李纨、宝钗、探春、宝玉四人一起聊天时,宝钗说:“我就听见他起来了,忙忙碌碌梳了头就找颦儿去。”同样表达整理毛发的意思,动词随着言语环境的改变而发生色彩意义上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语体色彩以外,雅俗色彩义在雅安方言词语“拢”上也有着充分的体现,并且突出显示着时代发展和变迁的过程中雅安本土语言社团的文化心理状态。
“雅”原本指的是“文雅、高尚、优美”,“俗”本来指的是“粗俗、低俗、浅陋”。在雅安雨城方言的具体言语环境中,“雅”的词义有所弱化,通常就是指“得体、合适、适宜”,“俗”也有同样的情况,通常指的是“平俗”。
在雅安方言中,当处于气氛诙谐幽默、交谈随意随和、说话人和听话人关系不疏远、双方身份或社会地位差距小以及家庭聚会等场合,人们交谈时会使用“拢”,表达“靠近、接近”的意义。而当气氛庄严肃穆、交谈严肃认真、说话人与听话人关系陌生、双方身份或社会地位差距较大,比如向领导汇报工作、受害人向公安机关报案时,会使用同样表达接近义的词“到”或“近”来替代。与语体色彩不同,无论会或不会使用雅安方言,在交谈时,如果在意义表达过程中使用了“拢”来表达靠近、接近义,表示距离的缩小,听话人也能根据社会现实语境基本接收说话者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这正是因为利用了“拢”具有雅俗色彩义的特点,即当使用对象被固定化,听话人范围被相对锁定,以及说话人和听话人双方都掌握了“拢”的这一色彩义的情况下,说话者有意利用并显示雅安方言的“排他性”,听话者也明白说话人使用这一信息传递方式的目的,最终以获得“拢”[luŋ]的“言外之意”的方式对说话人的信息进行“接收”和“解码”。
雅俗色彩义不仅体现了雅安方言的“排他性”,同样也体现了其“包容性”,在不同的语言环境中,“拢”的雅俗色彩运用也适应和展现着语言运用中的“会话合作原则”。改革开放后,随着我国经济等各方面的飞速发展,雅安地区也搭上了发展的“顺风车”,人民生活发生着缓慢且翻天覆地的“巨变”。雅安本因地理位置因素,对外交通不便,与外界沟通少,方言呈现出较为“封闭”的特点,本地人长期难与外地人打交道,方言词十分活跃且使用频率极高。改革开放后,当地地理通道接连增多,四方的道路都被打通,语言因子也随着开放的不断进行更加活跃,表现为新词数量增多,词义也产生着新的变化,词的雅俗色彩义不断丰富,“拢”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2.词义发展
雅安方言中的“拢”除了继承本义,发挥重要语法功能外,在语义类型上也有一些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词义上。
可能补语由动词、形容词充当。在雅安方言里,“拢”还可以作表示可能义的可能补语。有学者针对普通话中可能补语表达的“可能义”根据语义进一步分类,总共分为四种不同情况,分别是:可能[条件]、可能[许可]、可能[能力]、可能[认识]。按照该学者的标准进行划分,雅安方言可能补语结构“V拢”表示的意义基本上可以归于“有生命的能动个体(以人类为典型)在主客观条件上是否具备实现某种行为或动作的能力”[7]。雅安方言“拢”表示施事主体所施加的实际动作是否可使受事闭合。
“这杆窗子关不拢尕。”(窗户怎么关不了?)
“这块木头片片抵得拢抵不拢哦!”(木片卡得上卡不上?)
三、结语
雅安地区是四川重要的行政区域,受特殊地理位置与历史影响,雅安方言与其他地域方言、民族语言有着密切的关系,具有明显的包容性,体现出中国语言文字背后中国文化海纳百川的博大胸怀。同时,雅安方言是西南官话的组成部分,其词汇系统的变化折射出历史变迁的痕迹,显示出劳动人民的智慧与创造力,因此对于雅安方言的研究显得尤为必要。比较雅安方言和现代汉语普通话的差异和联系,更是对于地域方言等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交流起着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我国幅员辽阔,民族众多,雅安方言研究对于丰富我国语言研究现有成果,繁荣民族文化,加强文化认同有着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1]叶蜚声,徐通锵.语言学纲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
[2]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3]崔展.对楚语和北方方言关系的探析[J].内江科技,2009,(30).
[4]牟成刚.西南官话的形成及其语源初探[J].学术探索,2016,(07).
[5]陈煌煌.温州方言趋向动词研究[D].上海交通大学,2020.
[6]刘月华.趋向补语通释[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8.
[7]骆莉萍.现代汉语的可能补语与“可能”意义[D].苏州大学,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