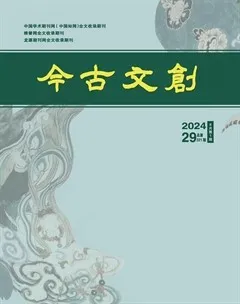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诗经 · 大雅》史诗音乐的社会功能
【摘要】上古社会,音乐已经成为先民祭祀活动、农业生活时歌功颂德、礼乐教化的重要表现形式。《诗经·大雅》中的史诗音乐不仅有利于人们研究西周开国史,并且其强大的社会功能,对培养个人道德情感、维系家族伦理观念以及稳定政治统治等都发挥着重要功能。
【关键词】《诗经·大雅》;史诗音乐;社会功能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84-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25
一、上古音乐的发展及社会功能
早在我国的原始社会,先民们就已经开始熟练地运用工具去创造和使用音乐了,虽然那时的人们无法解释音乐本身是什么,但却可以本能地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通过祭拜上帝和祖先的方式,保佑他们的生产生活,以确保生存环境的稳定和部落血脉的不断延续。因此,原始社会的音乐多服务于祭祀活动,而这一传统也在之后音乐的不断发展中得以保留下来。
随着夏朝的建立,氏族文化开始向奴隶制文化转型,音乐的功能也发生了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是更加关注对英雄人物功绩的讴歌。例如,为表现夏朝开国君主大禹的治水功绩,创作了《大夏》舞曲。《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此曲诞生之缘由:“禹立……降通漻水以导河,疏三江五湖……于是命皋陶作为《夏籥》九成,以昭其功。”[1]《大夏》舞曲以大禹的英雄功绩为主要内容,其目的在于“以昭其功”,即通过音乐表演来引起演奏者和表演者的情感共鸣,进而产生民众对英雄的崇拜,社会责任感也会应运而生。
再到殷商社会,“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先罚而后赏,尊而不亲”[2]。殷商王朝注重通过音乐将人与鬼神相通,达到一种“天人交互”的状态。这种“天人交互”的状态,不同于原始社会的图腾崇拜,主要是对先王、先妣的祭祀和崇拜,即“祖先崇拜”。
到周代,音乐则发展为一种与“礼”结合的“礼乐”共存状态,统治阶级将传统的祭祀性礼乐文化转换为一种政治性礼乐文化,即音乐不仅可以祭祀先祖和赞颂王者,而且可以体现出一种具有政治意义的德性文化。
二、《诗经·大雅》中的史诗音乐
《大雅》作为一种乐歌名,其音乐本体的功能在周代德治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政治伦理功能。《礼记·乐记》有言:“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儒家学者在研究《诗经》的过程中,认为诗作为音乐,本身就与政治具有一定的关系,且认为“乐者,通伦理也”,即音乐与伦理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从《大雅》的具体内容看,《诗经·大雅》共三十一篇,其中《文王》《大明》《绵》《皇矣》《生民》《公刘》六篇记载了周先祖开疆扩土之历史功绩,程俊英先生在《诗经译注》中将这六篇称为“周代史诗”[4]。这六篇史诗叙述了周始祖后稷开创农业,经公刘、古公亶父对建筑和交通等生存条件的开拓,并在两次迁徙中力克戎狄,创造出较为安稳的生存环境,再由季历转功业为德政,最后落脚于文王武王成就伟业德治天下。内容涉及我国古代农业、政治、战争以及祭祀等,为西周史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文献支持。因此,相较于前朝音乐,这六首史诗内容的丰富程度使其价值不再拘泥于祭祀和歌颂,转而表现出一种伦理规范和政治诉求。
《大雅》与《国风》虽同为乐调,但区别于《国风》中富于人民性的民歌,《大雅》史诗则更多地关注于道德教化,以及夹杂着具有部分真实性的历史记述和一定文学价值的古代神话,其作为乐调本身的传播性和感染性会对人自身的情感和伦理观念产生影响。《礼记·乐记》中记载:“故听其《雅》《颂》之声,志意得广焉。”[5]听《雅》声,会使人产生出一种自发的情感,这种情感不是《国风》中“风土之音”,而是类似于在演奏《大夏》时那种人与自然抗争搏斗,并付出巨大牺牲取得胜利后的一种深刻的社会情感,或者是《礼记·乐记》中记载地对《大武舞》的演奏:“是故先鼓以警戒,三步以见方,再始以著往,复乱以饬归,奋疾而不拔,极幽而不隐,独乐其志,不厌其道,备举其道,不私其欲。”[6]整个舞曲表现了武王对于伐纣的决心与信心,是一种由内而外的情感,而且这种情感来自个人却又不属于个人,是一种群体性的情绪与感受,这是《大雅》史诗与《国风》的最大区别,也是这种史诗音乐要达到目的的必要效果。
三、《诗经·大雅》史诗音乐的社会功能
对于大雅史诗的作用,《礼记·乐记》中提到:“……群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6]不论男女长幼,贵族百姓,都要经历礼乐的教化,这种教育中的美育作用远远小于道德作用,与其说是美育,不如说是一种德育,且这种德育通过血缘伦理进行规定,进而有益于政权的稳定。
(一)《诗经·大雅》史诗音乐的道德情感功能
《诗经·大雅》中的六首周代史诗都作于西周前期,作为史诗,其音乐本身对人的道德情感会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周代,音乐与道德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刘向说过:“凡从外入者,莫深于声音……故君子以礼正外,以乐正内。”[7]乐既是实现人的道德教化的最好的方式,也是调和礼所带来的差异性的合理方法。在礼所带来等级差异的同时,也会带来因差异而产生的不满,而乐就通过对人情感的调和与道德的培养,使人们心情舒缓并且接受这种差异性,这就是礼、乐、德的相互关系。
《礼记·乐记》中认为这种关系的根源在于人心对音乐的感知。《礼记·乐记》云:“乐者,音之所由生也,其本在人心之感于物也。”[8]儒家学者认为,“乐”由音所生,而究其根本在于人心之有感于外界事物。有了人心对外物的感知,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声音,才会有不同种类的音乐,而这些音乐也会表现出不同的情感,也就意味着会使人产生出不同的道德自觉。
在《诗经·大雅》的六篇史诗中,不同史诗的音乐韵律不同,所激发的人的道德情感也有所不同。在表现武王克商的战争场景时,多采用对战场环境的描写,且多用叠字。例如《诗经·大雅·大明》“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騵彭彭。”通过“洋洋”“煌煌”“彭彭”等叠字的用法,不仅从侧面描绘出了壮阔的战争场面,而且也可以通过乐调激发出人内心一种如临战争,奋勇杀敌的情感。《诗经·大雅·皇矣》“临卫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临卫茀茀,崇墉仡仡。”运用排比的叠词,真实地再现了商军在周武王所带领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土崩瓦解,彻底失败的情景。彰显了周“战必胜矣”的昂扬之气。在描绘文王之德行时,围绕天命与德业,再通过乐调舒缓展开,使人产生一种缓和、依附的心情,例如:《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升降,在帝左右。”乐调中时刻不离“上帝”与周的关系,这种感受在人的内心中形成一种对周的崇拜感与依附感,这种崇拜感和依附感是周“魅力型”权力——“克里斯玛”权威崇拜所必要的。
因此,《诗经·大雅》作为音乐在广泛传播的过程中,这种“作为音乐本体的道德作用”对于人内心主体的道德的教化与约束,符合周“德治”的要求。《诗经·大雅》的六首史诗音乐,既体现了周对《大雅》音乐本体功能的合理运用,也体现了在德治过程中对礼所产生的差异性的调和。
(二)《诗经·大雅》史诗音乐的伦理功能
《礼记·乐记》认为:“乐者,通伦理也。”[9]《诗经·大雅》史诗音乐会产生一种由内而外的社会情感,从而使人民产生出一种自觉的伦理规范,通过史诗音乐激发出人自身的伦理自觉。
西周之初,整个社会仍旧保存了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遗制,并逐渐发展为西周宗法等级制。刘大杰指出:“君主政治与父权的家族制度加强以后,于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的尊祖敬天的宗教观念更为进展……这两种观念互相结合推演,祖先也可以配天,于是形成一种上帝祖先的混合宗教,家族组织便成为政治上的主要元素,宗法精神遂成为国家政治上的主要精神了。”[10]而这种一脉相传的血缘宗法,在《诗经·大雅》六首史诗音乐中得以体现。从《生民》诗起始,“克禋克祀,以弗无子”是为周始祖后稷诞生所送出的祈福,也是强调周始祖的天命不凡。至《公刘》诗“笃公刘,匪居匪康。迺场迺疆,迺积迺仓。迺裹鍭粮,于橐于囊。思辑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和《绵》诗中极富内涵的“绵绵瓜瓞”,强调了周氏族子嗣的连绵不断,并将周氏族德行一以贯之。再至《皇矣》诗“既受帝祉,施于孙子”和《大明》诗对王季和太任、文王和太姒结婚的事件的述说,体现着对氏族继承的重视。最后落脚于《文王》“无念尔祖,聿修厥德”“世之不显,厥犹翼翼”,将周氏族血脉的延续性通过音乐史诗这一形式完美地表现出来。
朱贻庭提道:“所谓西周的道德,实际上就是宗法等级道德。”[11]这种对血缘等级的重视,根本在于生产资料(大部分为土地)归“王”,即奴隶主所有,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12],因此为了强调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以及巩固以血缘为纽带的氏族遗制,通过礼与乐相辅相成,“比经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其深’矣”[13],将伦理与音乐交融,通过音乐将统治阶级自身利益合理化,这不仅体现了周初政权统治的政治智慧,也体现了我国古代伦理道德中以家族为本位或个体必须服从于家族的等级秩序的整体意识。在《礼记·乐记》中也多次提到礼与乐的相互关系与秩序观念:“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14]
(三)《诗经·大雅》史诗音乐的政治功能
《礼记·乐记》又认为:“声音之道,与政通矣。”[3]周王朝以宗法制和分封制纲纪天下,为了达到宗亲和睦,君臣一体的政治效果,音乐所表现出的政治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首先,《诗经·大雅》中的六首史诗音乐作为先王赞歌,表达了克配上天、以德保民之意。王国维提道:“周人制度之大异于商者,一曰立子立嫡之制,由是而生宗法及丧服之制,并由是而有封建子弟之制、君天下臣诸侯之制;二曰庙数之制;三曰同姓不婚之制……周公制作之本意,实在于此。”[15]他认为周公所确立的宗法制、分封制等“礼制”,实则是以“德”为核心的等级制,一切的社会活动都归于“德”,而“德”又为政治所服务。因此,为了表现出周朝的以德配天,“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之意,《诗经·大雅》的六首史诗音乐通过对周历代先祖的赞颂,集中体现了君权神授、代天行治、维德之行的政权合法性。在《生民》诗中,通过神话对周始祖后稷进行神化:“牛羊腓字之”“会伐平林”“鸟覆翼之”等“神迹”使人确信后稷就是上天派来,代天行治的天命之主。到《公刘》“既庶既繁,既顺迺宣,而无咏叹”;《绵》“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皇矣》“万邦之方,下民之王”“比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孙子”中周几代人通过不断地耕耘努力与以德服人,从而不断赢得民心,为周朝基业的不断发展壮大攒下群众基础,在克配于天成为人君之后,修德修行,敬天保民。最后落脚于《大明》“厥德不回,以受六国”与《文王》“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夏传才评价道:“诗的第一章写一代兴亡系于天命,而天德合一,天命无常,唯德是从。这是西周统治者的天命论,说明他们之所以能够取代殷商奴隶主,是因为他们‘维德之行’而获天命。”[16]文王之所以能得“天命”,是祖先“维德之行”的结果,这个结果通过《诗经·大雅》六首史诗音乐得以彰显。
其次,《诗经·大雅》六首史诗音乐作为社会意识的载体,反映了周代政权对于稳定的需求。音乐和道德都来自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是一种社会意识,可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的一些具体情况。《礼记·乐记》中也记载了这种情况。例如对民生的反映“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其政散,其民流,诬上行私而不可止也”[17]。不同的音乐所反映出具体地方的民风不同,而音乐也可以反映出整个社会的人民整体情绪的变化:“是故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3]。因此,每个地方的道德可以通过音乐表现出来,而音乐又可以体现出政治的动荡与稳定。
周王室也注意到了这一点。在周初,周为了巩固新生政权,以“和”为目的,通过这种“和”来产生周人百姓自身的“归属感”以及臣服部落和商之百姓的“臣服感”,也就是“王者功成作乐”,其根本目的是为了巩固统治。周初国家撰写史诗并通过音乐去传播,是为了拉近人民与国家的距离,使人民产生出一种由内而外的臣服感以及归属感(土地)。而至于商的贵族,周武王没有过多的去对他们进行追责,只把罪归于纣一人,称之为“一夫”,也就是“独夫”,原因在于武王看到殷贵族人数众多,势力庞大,存在发生叛乱的情况,所以通过这种方法防止叛乱的发生。在《诗经·大雅》六首周代史诗音乐中,通过“天命”与“德行”所赋予“归属感”与“臣服感”,使周朝政权的稳定性得到保障。
总而言之,《诗经·大雅》史诗音乐所呈现出的不仅仅是文学价值与艺术价值,其所反映的伦理价值也不容忽视。在长期处于礼乐文明孕育的古代社会中,《诗经·大雅》史诗音乐的社会功能既可以对个人道德情感的培养具有教化作用,也为统治阶级的伦理道德以及政治教育带来一定的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蔡仲德.中国音乐美学史资料注译(增订版)[M].北京: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213.
[2]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728.
[3]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472.
[4]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165.
[5]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502.
[6]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488.
[7](汉)刘向撰,向宗鲁校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2000:508.
[8]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471-472.
[9]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473.
[10]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9.
[11]朱贻庭.中国传统伦理思想史(第五版)[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28.
[12]程俊英.诗经译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27.
[13]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485.
[14]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476, 477,478.
[15]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2.
[16]夏传才.诗经语言艺术[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5: 143.
[17]王文锦.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0:472-4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