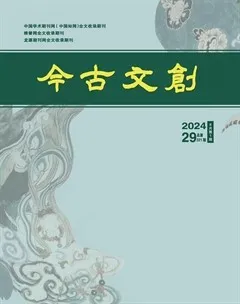从人性的角度分析儒家传统的 “ 孝 ” 文化
【摘要】中国传统孝道文化被延传几千年之久,“孝”也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美德的根据与源头,其中敬养父母、抚育后代、推己及人、忠孝两全、祭拜祖先等,这是一个由个体延展至整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完整流程。而被传承至今的孝道文化也绝不是凭空产生,它的出现与传承实际上与人性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人有性,性延情,情至孝,如此以来,孝道文化就依据人性而产生,跟随人情而发扬。然而,基于人性产生的“孝”却不仅仅是性情的外在表现,它还可以对人性进行超越,于是便有了修身养性,推己及人,个人操守的提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关键词】孝;人性;亲情之爱;推己及人
【中图分类号】B8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7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21
一、孝的内涵
“孝”是一个会意字,它是由两部分组成,上半部分是一个“老”字的一半,下半部分是一个“子”字,寓意子扶其父,老有所养。《说文解字》中对孝的解析:“善事父母者。从老省,从子,子承老也。” ①因此,爱老、敬老、尊老、养老、抚育子嗣、推己及人,敬长忠君便是孝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精神。
《论语·为政篇》中孔子对于“孝”也有自己的见解:“孟懿子问孝。子曰:‘无为’……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为孝乎?”孝可以有很多面,孝是不违背基本礼法;孝是对父母付出与子女同等之爱;孝不仅仅是对父母的“养”,更重要的是“敬”。“孝敬”从来不是只有养,若单养,那么犬马皆可养,而“敬”才是“孝”的精髓,“孝”发端于本能的爱,随后有了理性,有了礼的约束便成了“敬”,敬则需要“顺”,顺来源于敬,所以有敬、有顺、有养才是孝;孝中最不易的是对父母始终和颜悦色,对待双亲真心实意并非做表面文章,换言之,不惧不怨不悔的敬才是孝的最高境界。
《孝经》中表示:“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 ②也就是说,“孝”是产于人之天性,天地之法则,是天之地义的产物。而天地是中国古人信仰的对象,把“孝”推至天地的高度去理解和信奉,那必然是将其推崇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同时它也为对这种孝的行为寻找到了合理的依据,人本身具有天性,而“孝”既然是“天经地义”之事,那么人的天性中自然就蕴藏了孝的萌芽。《圣治章》也为此说法巩固了地位:“父子之道,天性也。”也就是说,父慈子孝,父子敬爱之心乃人之天性也。这也为中国古代的孝道文化的至高无上地位奠定了重要的哲学基础。《孝经·开宗明义章第一篇》:“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孝乃人伦之始,立人之本。因此道德修养与孝道之间也有着密切的关联,孝道是道德修养的根基,是道德修养的基础,以孝来修身养性,必将恶性养之端正,邪性养之良善。因此孝在社会伦理与道德修养过程中的作用不言而喻。
二、孝与性的关系
(一)“性”是“孝”的根本
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究竟因何而来?又是如何延续至今的?其实这与先哲们讨论的人性有着密切的联系,那么对于人性,先哲们对此也有着各自的理解。《说文解字》中表示,“性”形声字,从心,生声。③“性”从“心”即与个体情绪,心情和内心活动密切相连。《说文·心部》中提道:“性,人之阳气,性善者也。”本义是人之天性,人之本性。生来具有的本心即为“性”,而“心”则为内在,“生”则为表现。人性有善恶之分,物性有刚柔之别,性不仅是代人的品质,更是替物的性质,即物的外在形状与内在性能。但是无论是人性还是物性,皆是由内发而外现,性由心生,故“心”“生”为“性”。在孟子对性理解的基础上,他提出了性善论,但实质上,他认为人性并非生来就是善的,而仅仅只是人生之友善的倾向,即善端。《孟子·告子上》:“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 ④从人自身的资质上来看,人都是可以向善的,这便是孟子所说的性善。基于孟子的性善倾向,那么便从性中抒发出了情感,情有亲情、爱情、友情等等,有了情才是一个人格健全的完整个体。“情”是性的重要表现,人性中的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心都是情的抒发。那么“孝”以及孝道文化实际上就是在孟子性善的理论基础上,为了人自身情感的满足所表现出来的一种具象化的情感表达形式,这里的情感便是人的天性中所固有的“亲情”。换言之,如果从人性的角度上去看待性,“情”是“孝”的根本,“孝”才是人性的需要。
(二)“孝”是“性”的需要
自古以来,中华民族都十分看重传统文化,而孝道文化作为中国传统不可分割的思想文化之一被广泛流传,例如在传统丧葬文化中,有着丰富又十分规范的礼节与规定。实际上,无论是中国传统的丧葬文化还是古代流传的礼义法度都是依据人性的需要所创造出来的。《孝经·丧亲章》:“孝子之丧亲也,哭不偯,礼无容,言不文,服美不安,闻乐不乐,食旨不甘,此哀戚之情也。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 ⑤孔子认为,真正的孝子在父母逝世后是十分悲痛的,丧礼上哭得声嘶力竭,会失去了平时的端庄与优雅,连日常食“美味”,享“华服”都觉得亏欠,这一切都只是因为太悲伤的缘故。事实上,真正的儒家文化从不是为了刻板的规则而立,也绝非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而生。而所有的礼仪与规则,均是依“情”而定,依“性”而生,换言之,一切的礼仪法度皆是为了满足人性的要求提出的,情理相合。子孙在丧礼上的声嘶力竭是因对其亲不舍之情的抒发;失了端庄和优雅是因太过悲伤无暇顾及自身的仪容仪表;穿上华服便觉不安,是因内心不忍父母骨枯黄土。就连传统的丧葬文化中的“三年丧期”也有依从人自身情感的合理之处。《论语·阳货》中有明确记载孔子与宰我的论述:“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于其父母乎!” ⑥弟子宰我向孔子提出自己的想法说三年的守丧之期限太久了,会影响到社会的正常运行,礼乐规则也会遭到忽视。但是孔子认为,子女自出生三年才能脱离父母的怀抱,为感恩父母生育之情和养育之恩,自当在父母离世后为其守丧三年,才能使自己对父母的感恩之情找到一个合理的抒发之处,也是对自身内心的情感表达寻到了合适的期限。这实质上都是依从人性和人自身情感抒发的合理表达。
(三)孝的阶级化表现
孝不仅仅是人性的表现和需要,当然还会根据行孝之人身份的不同而产生阶级化的表现,这些表现实质上也是依据社会责任与分工而定,归根到底也是依礼而定,依人性而行。自西周以来,宗法制的确立使得中国古代的阶级特征在此后的任一朝代都十分的明确,阶级的分化就象征着责任的划分,不同的阶级都有着各自的责任与义务。在这其中,宗法制将人分为了五个等级即:天子、诸侯、卿大夫、士与庶人,由高至低各司其职,而且每层阶级对于孝的责任也有着不同的标准。
首先是“天子之孝”,一方面,天子乃各家之主,一国之首,所以定是不同于常人之孝,在治理国家层面,要爱惜国民,明德慎行。所以做到敬奉祖先,祭拜先人是首要的,然后要明德,慎行。作为一国之君,保全自身,然后扬名万世,始终都要伴随着自身的道德修养的提升,然后推己及人,做到真正的“仁”才能德教于百姓,保家,保天下。因此,西周的统治者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在明德的基础之上奉天命,保民生,以此来维护礼法,巩固自身的统治地位。另一方面,古人视天子为拥有天命之人,天为父,地为母,故凡事以天子作为榜样,天子如何行孝定会影响到百姓。所以天子的责任还要做好表率,把自身的孝敬之心推广到百姓的身上。《孝经·天子章第二》:“爱亲者,不敢恶于人;敬亲者,不敢慢于人……盖天子之孝也” ⑦孔子说如果连天子都能爱敬自己的父母,那就会给臣下做出榜样,那么四海之民都会像天子一样做到孝顺。
其次是“诸侯与卿大夫之孝”,《孝经》中提道:“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所以,在中国古代,孝与忠本为一体,是道德之本位,它是将血缘关系与忠君的政治意义融为一体。所以对于中国古代的中间阶级的诸侯、卿大夫来说,孝对于他们就是恪尽职守,尽职尽责。一方面,服从天子之命是作为臣子的本分,要“在上不骄”。另一方面,要节制财富流失,要“制节谨度”。《孝经·卿大夫章第四》:“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盖卿,大夫之孝也。” ⑧也就是说,只要行为符合法度礼义,依据天子行事,便达到诸侯与卿大夫的孝了。
再其次是“士人之孝”,士在先秦时期的含义非常之多,属贵族范畴,但实属贵族中最低等级的官员了。那么对士的行孝要求就相对不高了,对与士来说,首先要孝敬其双亲,繁衍子嗣以延续家庭血脉,然后服从君主,听从指令以保自身俸禄祖业。《孝经·士章第五篇》中对于士之孝有明确阐述:“资于事父以事母,而爱同;资于事父以事君……盖士之孝也。” ⑨以孝敬父母之心去侍奉君主,那么就达到了对君主的忠。以恭顺和遵从的态度去面对君主和上级,那么就可以保住作为士的身份和俸禄,也能够维持对于祖先的敬奉,这就是士人之孝了。
最后是“庶人之孝”,在先秦时期,庶人指拥有自由身份的平民百姓,而庶人是先秦社会的等级中最低的一级,因此《孝经·庶人章第六篇》中对于庶人的孝提道:“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谨身节用,以养父母,此庶人之孝也。” ⑩也就是说,只要了解天道地利,遵循自然天地之规律,做好基础生产工作,然后奉养父母,孝敬尊长就可以达到庶人之孝了。
所以在古代社会中,身份和等级的提升往往意味着责任与使命的范围也在拓展,孝道作为中华传统礼义,它的责任也随着身份的提升在逐步攀升,这本身就是作为人性形象化的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说,在先秦社会中,不同身份对于孝道文化的不同要求与阐释实际上都是对不同等级人性的满足。
三、“孝”对人性的超越
孝由人性而发,由人性产生的孝道文化延续至今有几千年之久,在未来也会被广泛流传。孝的内涵十分丰富,孝的实现要在“养”“敬”“顺”的基础上进一步去“爱”,去修身养性,去推己及人,然后实现“恕道”。也就是依靠礼去把孝中的“敬”推广,最终达到“仁”,这便是“孝”实现了对人性的超越,即由“亲情之爱”到“推己及人”。
(一)儒家的“亲情之爱”
在儒家思想中,“亲情之爱”始终被看得十分之重。例如孔子就把妻子和孩子的身份看得尤为重要,并且认为妻子是“亲之主”,而儿子是“亲之后”,一个是为其繁衍子嗣之人,一个是其家传宗接代之人,所以他十分敬重自己的妻儿。《论语·子路篇》:“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直在其中矣。” ⑪在孔子的眼中亲情是极为重要的。朱熹也曾表达,父子相隐是天理,是人情。所以只有爱亲,才能在这基础上推己及人。从人性的角度上来说,只有满足了人性,才会进一步实现对人性的超越。
(二)“推己及人”对“亲情之爱”的完善
首先推己及人实际上就是儒家所讲求的“恕道”。《孟子·梁惠王上》中表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也就是说,如果人们能够把爱父母之心推广出去,以爱父母之心爱他人,那么便是有了仁爱之心,如若人人对他人都有这种仁爱之心,那么天下便可尽在掌握之中了。所以儒家所说的这种推己及人实际上就是对“亲情之爱”以及孝道文化的超越与完善,而且它在儒家传统思想中的地位是十分之高的。从国家治理的角度上来说,孟子强调只有达到了对人性的超越进一步实现推己及人才可实现仁政,万民归心最后才能实现王道。
其次,这种推己及人不仅仅体现在“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上,还可以体现在更高的层次上,《论语·雍也》:“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也就是说如若个人想要立身,通达,那么就也要让他人立身,通达。这便是将推己及人达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无论是爱他人之亲如同爱双亲还是己欲立而立,人实际上都是超越了亲情之爱,都是在亲情之爱的基础上实现了人格的完善。如若说亲情之爱产生的“孝”是人性的本发,那么推己及人就是在基于人性的基础上对孝的超越,最终实现了对人性的超越。
四、结语
中华文明延续几千年之久,丰富的礼义文化也跟随流传下来,孝道文化就是其中之一。而“孝”的流传至今所依靠的并不是礼仪对人们的约束,而是更深层次的人情的共鸣,所以说孝是人性的表现,也是人性中情感抒发的需要,而人性才是孝的内在动力与本质。但是由本性所产生的孝却不仅仅止步在亲情之爱上,还体现在对人性的超越即推己及人。以爱父母之心去爱他人,才能做到真正的仁,平等的爱每一个人才能实现所谓的“一体之仁”。这便是实现从“亲情之爱”到“推己及人”,才是真正地实现了对孝的超越,对人性的超越。
注释: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592页。
②张景,张松辉译注:《孝经》,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62页。
③(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2057页。
④方勇译:《孟子》,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218页。
⑤张景,张松辉译注:《孝经》,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119页。
⑥(宋)朱熹注:《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76页。
⑦张景,张松辉译注:《孝经》,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36页。
⑧⑨⑩张景,张松辉译注:《孝经》,中华书局2022年版,第50页,第55页,第58页。
⑪钱穆:《论语新解》,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版。
参考文献:
[1](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钱穆.论语新解[M].北京:三联书店,2002.
[3](清)焦循.孟子正义[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4]北京大学《荀子》注释组.荀子新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张景,张松辉译注.孝经[M].北京:中华书局,2022.
[6]方勇.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7.
[7](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8]杜改仙.中国孝道文化研究[M].北京:中国时代经济出版社,2013.
作者简介:
姜雪,女,汉族,辽宁大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研究方向:中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