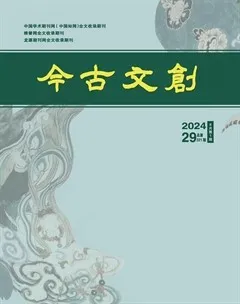梁晓声小说中的知青 “ 还乡 ” 书写研究
【摘要】“还乡”这一行为是梁晓声小说叙述的矛盾起点,在“还乡”书写中,知青们为了生存逐渐舍弃北大荒知青身份,以城市创业者的身份开始新生活。通过网状叙事结构展现知青完成群体分化的过程:以知青身份构建复杂的人物关系网,在倒叙和插叙、现实与回忆的交错叙事时间中逐渐分割过去与现在,不同叙事空间的个体选择呈现群体分化结局。梁晓声开辟了“还乡”书写新模式,以知青的“故乡错位”关注一代青年的奋斗经历,寄寓了作家对知青的深厚情谊。
【关键词】知青小说;“还乡”书写;梁晓声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60-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18
“还乡”是中国文学中一个具有古老渊源的母题,也是中国人情感表达和精神寄托的常见意象。对“还乡”母题的原型可以追溯到原始蒙昧时代的神话和早期文学文本《诗经》《楚辞》中。有学者关于中国文学“还乡”母题原型研究发现,从发生学的角度看,“还乡”的心理诉求来源于人们对生命的体验和思考——从对诞生到死亡的生命过程的惊颤,对肉体和灵魂分离、归栖的生命构成的想象。①知青群体在历史转型时期所经历的不仅是身份的转变,还有生存困境和内心惶惑导致故乡错位带来的精神重建。“还乡”行为背后承载着知青共同体意识逐渐削弱的结果,“还乡”的游子失去“游人”集体认同,也未能被城市完全接受,他们是在时代飞速进步中强行适应的一批人,既从心理上离开了城市,又在距离上离开了承载的理想的精神故乡。“还乡”后的“再离乡”不仅意味着知青群体的分化和再造,还体现了青年实现自我价值的认知变化和国家发展路线的转向。赵青曾从心理学角度剖析知青们生存的困境和人生的惶惑:“对于知青来讲,他们作为一个群体,被迫完成了两次生存空间的迁移……他们不仅在生存空间上有无法消除的焦虑感,甚至精神空间上,这种焦虑感变得更为沉重,因此‘家归何处’‘魂归何处’就成了知青作家群为完成自我构建而想要探讨的问题之一。” ②“还乡者”与故乡格格不入是中国现代文学文本中常见的话语模式,梁晓声书写了特定历史时期从乡村返回城市的一代青年人如何更换身份和理想的过程。通过叙事策略逐步实现知青集体的分化,在失去集体身份之后,这批还乡者们带着焦虑完成了物质和精神的双重离乡。
一、知青还乡后的身份变化
对知青们而言,回到故乡恰是与故乡疏离的开始zs4V8/qQl+loNO5tkcVqbw==,身在北大荒时城市是寄托温暖向往的避风港,回到城市却发现故乡残酷冷漠的一面。“家”这一最后堡垒对待业知青而言形同于无,甚至成为压力与尴尬的一种来源。③他们被迫以外来者的身份重新争夺城市生存的权利,而他们身上挥之不去的北大荒经历又成为知青在城市抱团立足的唯一凭借,青年们的挣扎与迷茫来源于身份重建过程中无序的探索。
(一)“还乡者”的窘迫处境
长期分别致使知青们回到家乡后还来不及修补薄弱的家庭关系,就要为摆在面前的现实问题发愁的困境。返城知青大都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生存所需的物质基础亟须满足。但是他们在北大荒的工作经验在城市一文不值,想要在城市找工作维持生活都要依靠父母的社会关系。《雪城》借铁路局领导之口说:“要接父母班的人很多啊……许多当父母的为了早点让返程待业的孩子有个工作,不到五十岁就打报告申请退休哇!” ④对大部分返城知青来说,对家人的歉疚和对城市的怨怼成为他们沉重的心理压力。“他们感到的不仅仅是物质上的匮乏带来的窘迫,而更多的是一种从高尚的身份跌落到卑微者的无所适从。巨大的反差让他们不得不在现实面前自惭形秽……他们可以忍受贫困,却难以忍受这种来自精神上的折磨。” ⑤少时热烈的理想精神被北大荒的风雪消磨,更深层的是对自我选择的怀疑。姚守义想要报考师范学院的师资进修班,可是他母亲道出了实情:“十来年你连念过的中学课本都没再摸过一次。”知青们当年是先进思想和知识文化的携带者,现在却是落后的弱势话语方,这种位置的倒转使他们萌生巨大的疏离感。
(二)“外来者”的强势融入
数十万返城知青在生存困境和精神压力的双重围堵之下,每个人都寻找机会宣泄着内心的悲愤与不满。他们因为知青身份被城市排斥,也以知青身份为号召,个体抗争最终形成集体抗争。《雪城》中返城知青们在音乐厅外为刘大文组织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引起歌唱家对刘大文的关注;师范学院招教事件内幕公开后知青们大闹考场,致使包括郭立强在内的多人入狱,郭立强狱中去世直接点燃了知青怒火,引发知青大游行。《返城年代》中林超然卖饺子被工商部门查抄,大量知青聚集到看守所门口静坐要求释放林超然。有学者认为:“巨大的心理情结与感情依恋使他总是难以割舍和否定集体强大温暖的怀抱,但梁晓声努力地从感情的控制下挣脱,去检视过度的集体观念潜在的危险性。” ⑥
(三)“创业者”的艰难困顿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正是社会主义现代化转型的关键时期,大多数知青的人生转折都与开放市场经济脱不开关系,返城知青们因人数众多无法加入城市原有的工作体制内,造成大批待业青年就业难问题。长期下乡导致知青们不熟悉城市规则,在创业中屡次受限。《返城年代》中林超然和张继红曾将旧自行车配件组装成新的“无牌自行车”售卖,但是遭到市场监管部门的阻拦。后来林超然又组织知青们在冬天卖水饺,经历风波后办下了营业执照,正式开始个体经营。《雪城》中严晓东抓住机遇,拉关系做个体户存下了十四万元,徐淑芳则经历了艰难的资本积累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女儿国”百花玩具工厂。知青在初返城市时,是一个被夹在城乡之间、工农之间的一个既独立又不稳定的特殊阶层 ⑦,他们在身份上是城市居民,但对于城市的规范和制度并不清晰,甚至多因误会而被粗暴对待。创业帮助知青们保留城市生存条件,但却进一步造成知青集体的分解,创业成功之后小家庭的建立也是致使知青群体分化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网状叙事策略去知青化
梁晓声的长篇小说擅长把握宏观历史事件下多人物的刻画,通过关注个人命运表现时代发展,两部以知青返城为主题的小说用高度相似的叙事策略书写了返城知青“去知青化”的全过程。知青群体在城市家庭生活中被分解成单独的个体,个人意志随着现实和记忆的插叙回溯逐渐确立新的方向,篇末人物的不同命运也暗示了改革开放背景下知青底色进一步消逝。
(一)复杂的人物关系
梁晓声在小说开篇以纵横交错的人物关系组建出一副紧密联结的知青关系网。《雪城》以姚玉慧展开,围绕在她身边的人物有同兵团的刘大文、徐淑芳,又在这二人之下引出刘大文的妻子袁梅,徐淑芳的男友王志松、现任丈夫郭志强以及严晓东、姚守义、吴茵、郭立伟、曲秀娟等人。《返城年代》则围绕知青夫妇林超然、何凝之,以及他们的家人林岚、何慧之、何静之与兵团知青杨一凡、罗一民等人展开叙述。知青身份构建的关系网络相互交错,甚至随着时间的延续增加或变换交点,使得故事矛盾集中发生在读者视野。由于知青经历遗留的社会关系也必然造就他们之间命运互通,然而随着个人选择不断分化,大多数人在摆脱知青群体影响后通过个人奋斗获得新的社会身份,知青关系网解体。
(二)交错的叙事时间
在“还乡”这一动作下的小说叙事离不开关于回忆的倒叙,以及补充人物命运的插叙。《返程年代》中林超然对弟弟林超越的回忆是分几次补充完整的,由一开始想起就会觉得痛苦,抱着深切怀念小心翼翼地隐瞒死讯,到后来与父亲说起弟弟生前好笑的事,甚至将弟弟与恋人的相处讲给家人。从林超然的变化上可以感受到北大荒记忆前后的分别,林超然接受了弟弟离去的事实,牢牢记住弟弟生前鲜活有趣的面貌,不再将生离死别看作和弟弟最深刻的记忆片段。闪回、闪前的运用丰富了人物形象,在《雪城》中徐淑芳经历了四次情感,性格也由一开始的柔弱犹豫变成后期的有胆有谋,小说通过写北大荒时期——返程初期——丈夫去世——创业成为厂长几个时期的前后事件,详细解释了徐淑芳性格形成的契机与原因。但在实际叙述中,作家并没有按照顺叙的时间顺序,而是穿插跳跃,增强了人物的陌生化。
(三)多重叙事空间
梁晓声构建了许多家庭空间,知青“返乡”前后最大的空间样态变化就是由北大荒的集体空间回归到城市故乡的个体空间。北大荒作为知青集体空间,在小说叙述中也存在着高度一致的倾向,尤其是荒原的广阔与城市的拥挤、北大荒人的淳朴和城市人的市侩、大展拳脚的理想主义高扬和处处受限无处施展的现实困境,在知青心里形成对立的两种空间印象。在小说的后半部分,知青群体完成分化建立起自己的小家庭,通过对不同知青家庭的叙写,更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壁垒。《雪城》在结尾徐淑芳的婚礼上对知青现状进行了总体观照,王志松和吴茵来之不易的婚姻已经名存实亡,曾经是知青中心的指导员姚玉慧找借口缺席,其余人也各怀心事,将婚礼当作社交场合扩大自己的社会关系。小说开篇因知青身份紧密联系的众人,在城市空间中已经因其各自的新身份失去了统一立场。
三、知青“还乡”的现代性错位
城市和乡村在文学中一直是常见的两种文化符号。朴婕关注到梁晓声作品中的城市意义:“城市的意义在此是多重的,它首先是知青生长和获得知识的土壤。” ⑧北大荒的意义也可以对应着进行定义,它是知青实现理想的载体,也是知青理想事业的见证;返城时期它是知青记忆中的精神故乡。现代小说还乡母题是基于游子身上他乡烙印造成回到故乡产生沧桑感和陌生感,在知青返城事件中具备这样的因素,知青群体是城市的“乡下人”,双重身份使他们对“故乡”认定产生错位。
(一)城市潜规则的掣肘与熟稔
在物理空间上,城市是不容置喙的故乡,也是知青们在远行归来后产生撕裂的痛苦的家园。而在价值观念的文化身份上,他们则更为熟悉北大荒的生存法则。有学者直言:“在人格形成的最关键时期,知青们接受了以理想主义和集体主义为主体的价值体系的熏陶和导向,十一年的北大荒生活后重返城市,时间与空间的双重变化背后是异质价值准则的交锋碰撞。” ⑨首先,知青在北大荒形成的集体意识是不便于在城市这种拥挤生存空间下以个人家庭为组成单位的空间生存的。在《返城年代》中林超然从搬运工变成路边工,因急需赚钱但工作机会少,没有联系一同失业的兵团工友,被人当面叱骂。另外,城市对于“托关系走后门”等灰色手段的运用也比北大荒更为直露。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雪城》中没下过乡的郭立伟为了哥哥回城的机会设局与区知青专管盖章的家伙认识,威逼利诱获得了盖过章的病返申请书。从北大荒回来的哥哥郭立强在监狱里隐忍着无端的挑衅,却被骗拿起铁锹,被当作暴动分子击毙。徐淑芳创业之初在厂房置换过程中艰难疏通关系,还为此卖掉了自己的城市户口,收到的钱却被公社扣留,最终拿到手的只是卖户口的两万元钱。而在成为玩具厂长之后,她深谙此中关窍,不仅将事业做得风生水起,还用自己的婚姻一举化解了被罗织的罪名。
(二)北大荒记忆的沉湎与扬弃
在传统归乡母题定义中,“故乡之‘乡’是生命出发之‘乡’,也是与都市相对的乡村之‘乡’,与异域文化相对之本土文化之‘乡’,与道德沦丧、人性衰退、精神荒芜相对的道德人伦醇美、人性自然、精神健康之‘乡’。” ⑩从这一意味上看,北大荒似乎是更为合格的理想故乡,大多数知识青年都在内心保留着北大荒精神家园的一席之地。从还乡者的角度来看,跨越千里接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特别是在这种体系中获得过极高荣誉和地位的人,猛然失去这种身份对于他们来说是不小的打击,一定程度上压抑着其对故乡的认同。极为明显地表现在《雪城》中姚玉慧的身上,她是所有人中最看重北大荒经历的人,她不断沉浸在北大荒记忆中,为躲避难以融入的现实生活频频向精神故乡求援。随着北大荒仓库管保员的“女儿”扯掉她美好回忆的最后一层遮羞布,对北大荒的回忆分裂成两种不同立场的讲述,姚玉慧主动斩断了与社会的联系,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与她形成鲜明对比的另一女性徐淑芳,从知青经历中汲取了吃苦耐劳的顽强精神,在城市生活中学会新的生存技巧,变成姚玉慧艳羡的对象。
无论是还乡和离乡,“此处”和“别处”的距离总是无法得到消弭。返城知青们遭到物理空间城市故乡的排挤和厌弃,心理上与现实故乡产生间隙;知青集体身份认同弱化和群体分化后,北大荒精神故乡也与他们渐行渐远。去知青化导致一代青年们曾寄托理想的精神家园落空,知青还乡后感受到的是与精神故乡的地理距离感和与物理故乡的文化距离感。梁晓声以饱含真情的笔触道出了知青返乡后的迷茫与蜕变,为“返乡”题材增添了新的写作范式。
注释:
①何平:《中国文学“还乡”母题原型研究》,《民族艺术研究》2004年第3期。
②赵青:《生存的困境与人生的惶惑》,河北大学2019年硕士学位论文。
③徐晓东:《〈雪城〉:徘/Sz0wpjK/OvozUamuY/K+jY3/7TGmMwtpXjl+6TDrj8=徊在理想与世俗之间的精神殉葬之作》,《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3期,第69-75页。
④梁晓声:《雪城》,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年版。
⑤黄昕:《艰难的回归之路——读梁晓声〈雪城〉》,《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8期,第62-67页。
⑥徐晓东:《〈雪城〉:徘徊在理想与世俗之间的精神殉葬之作》,《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3期,第69-75页。
⑦刘明明、盛昕:《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后知青时代的集体记忆》,《新疆社会科学》2019年第6期,第147-156+159页。
⑧朴婕:《论梁晓声的小说创作》,《小说评论》2019年第5期。
⑨徐晓东:《〈雪城〉:徘徊在理想与世俗之间的精神殉葬之作》,《理论与创作》2004年第3期,第69-75页。
⑩何平:《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江苏社会科学》2012年第6期。
参考文献:
[1]何平.中国文学“还乡”母题原型研究[J].民族艺术研究,2004,(03).
[2]赵青.生存的困境与人生的惶惑——知青文学的空间焦虑研究[D].河北大学,2019.
[3]徐晓东.《雪城》:徘徊在理想与世俗之间的精神殉葬之作[J].理论与创作,2004,(03):69-75.
[4]梁晓声.雪城[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9.
[5]黄昕.艰难的回归之路——读梁晓声《雪城》[J].广西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8(06):62-67.
[6]刘明明,盛昕.社会融入与身份认同:后知青时代的集体记忆[J].新疆社会科学,2019,(06).
[7]朴婕.论梁晓声的小说创作[J].小说评论,2019,(05).
[8]何平.现代中国小说还乡母题的“转换”和“安置”[J]. 江苏社会科学,2012,(06).
作者简介:
赵奇薇,女,汉族,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