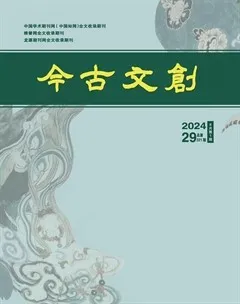小说《神死在尼罗河畔》的人物形象解读
【摘要】纳娃勒·萨阿达维是埃及最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一,本文通过对《神死在尼罗河畔》中人物形象的解读,描绘出埃及普通百姓在统治者的压迫下,负债累累,穷困潦倒。尤其是埃及妇女生活在父权制社会下,受到阶级、宗教以及家庭的三重压迫,逐渐沦为社会中的“他者”。纳娃勒通过这本小说反映出当时埃及社会的现实,同时呼吁人们关注和反思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和压迫问题。
【关键词】纳娃勒·萨阿达维;《神死在尼罗河畔》;父权制;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8264(2024)29-0035-03
【DOI】10.20024/j.cnki.CN42-1911/I.2024.29.010
一、引言
纳娃勒·萨阿达维是埃及最负盛名的作家之一,她也是一位医生、女性主义者、社会活动家。《神死在尼罗河畔》是纳娃勒的代表作品之一,小说描述了尼罗河畔的一座美丽村庄——卡弗埃尔特,但在美丽的表象之下,村长与卫队队长贪恋财富,抢夺、奴役村里的妇女,利用职权与民众信仰施以种种压迫,一切抵抗似乎都是徒劳。生活在这座村庄的女性扎克娅,本只能蹲在尘土飞扬的家门前静静接受自己的命运,可当她的侄女们也沦为村长手下的牺牲品时,她选择不再听任摆布,起身反抗。纳娃勒通过这部小说勾勒出当时的社会状况,萨达特正在推行“打开国门”政策,致使贫困、失业、女性掩面及遭受歧视等问题加重,埃及普通百姓受到统治者的压迫,基本的物质需求得不到满足,负债累累,生活贫困。特别是埃及的女性,她们除了受到殖民统治的压迫,在家里、社会上和街头受到男人的压迫,在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和两性关系中受到剥削,成为关系中的他者。
二、小说中人物形象解读
(一)村长:“一手遮天”的统治者形象
作为英埃混血的村长,铁门是其权力的标志。铁门外,他是卡弗埃尔特村最有权力的人,自视出身高贵,在村里的各种大小事情上凭借着自己村长的权威,一手遮天。先后通过自己的威名,以雇用内菲萨和宰娜卜为自家女佣为由,强迫她们与其发生性关系。铁门内,是母亲与哥哥眼中的失败者,是妻子眼中影响儿子价值观的罪魁祸首,紧闭的铁门因此成为其权力的保护伞。村长常在田间地头凝视辛勤劳作的年轻女性,在脑海中幻想着内菲萨、宰娜卜等女性的胴体,内菲萨等女性在这种“凝视”下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是一个为以村长为代表的男性提供欲望消遣的商品。[6]23假借他人之手,从卡夫拉维与扎克娅身边夺走了内菲萨和宰娜卜,占有并摧毁她们的贞洁从中获得某种欲望得到满足的快感。[6]26在内菲萨怀孕后,村长将其赶出铁门外,为后文宰娜卜的结局埋下伏笔。
村长作为上层阶级的代表者,他将自己凌驾于怀疑与法律之上,凌驾于规范通人的道德准则之上[5]147,身着昂贵的斗篷,住着装修奢华的房屋,与身穿粗布长袍、居住环境简陋的下层阶级——卡弗埃尔特村民们形成对比。在村长的治理下,村民的福祉以及权利并未得到保障,上层阶级利用自己职权剥削、压榨下层阶级[5]23,尤其是为上层阶级工作的贫困女性所遭受的性虐待困境。村长戴着“神”的面具,他是父权制下对女性的施暴者,同时也是对下层阶级的压迫者。纳娃勒通过塑造村长这一形象,不仅揭示了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公平和权力滥用,反映了其对社会正义和人性道德的深刻思考,表现出其对父权制的痛批和对埃及当权者的失望。
(二)哈扎维教长、哈吉·伊斯梅尔、扎赫兰队长等人:仗势欺人的帮凶形象
哈扎维教长、哈吉·伊斯梅尔、扎赫兰队长作为村长的追随者,他们对村长百依百顺、阿谀奉承,既是统治者的工具、助手,以及管理大小事务的手段[5]147,同样也是父权社会中凝视女性和压迫女性的参与者。
为了替村长隐瞒强奸妇女的行径,扎赫兰与哈吉·伊斯梅尔杀害邻村的埃尔瓦,并嫁祸于卡夫拉维,随后将盗窃罪栽赃于加拉尔,致使卡夫拉维与加拉尔遭受牢狱之灾。当面对内菲萨的苦苦哀求,扎赫兰队长非但没有同情心,反而对卡夫拉维加以威胁,并责令卡夫拉维:“揍她。难道你不知道吗,女孩和妇人不听话,除非挨揍。”[5]36
虔诚的老教长哈扎维经历过三次婚姻,没有一个儿子。年老、失去性能力的哈扎维在见到法提娅后,认定法提娅定能为自己生下儿子。他携哈吉·伊斯梅尔一起,前往马苏德家求娶法提娅。法提娅拒绝回应的举动惹怒了二人,哈扎维呵斥马苏德:“揍她,我的兄弟,揍她一下、两下、三下,难道你不知道吗,女孩和妇人只有被好好揍一揍,才会心服口服。”[5]51
在父权制社会中,女性被视作附属品、家庭财产,成为丈夫与父亲之间转手与买卖的一件商品。[7]当妻子未完成其生儿子的心愿,丈夫以此为由,与妻子离婚,并快速进入下一段婚姻,将期望寄托于新一任妻子。领域划分意识形态认为,公共领域专属于男性,而私人领域专属于女性,女性与生俱来的位置在家里,是以家庭这个私人世界为其主要活动领域的;而男人则以工作和政治这些公共世界为主。[4]哈扎维教长在与法提娅结婚后,认为法提娅应该生活在自己充满关切与尊重的家中,不得出现在别的地方。[5]49
奥姆·撒贝作为一个女性,村民则认为她既不是男性,又不是女性。她是父权制社会的坚定维护者。她是卡弗埃尔特每个家庭的一分子,为女性实施割礼,她会捍卫家庭的名声和年轻女子的贞洁,会帮忙掩饰任何可能象征不忠、玷污名誉、造成丑闻、招致灾难的事情。[5]110在阿拉伯文化中,贞洁对于妇女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贞洁被视为妇女的荣誉和尊严的象征,是社会道德和家庭价值观的核心之一。保持贞洁意味着妇女在性关系方面保持纯洁和节制,符合教义中的道德规范。违反贞洁观念可能导致严重的社会排斥和家庭失去荣誉,甚至可能导致被暴力对待。奥姆·撒贝在法提娅结婚当天打破她的童真,通过控制其女性的欲望,控制她本身,从而巩固自己的地位。正如福柯所提到的“权力的对象和目标就是要通过控制人的身体来进行”[6]42。哈扎维、哈吉·伊斯梅尔、扎赫兰等人的帮凶形象,进一步助长了统治者的暴虐行径,维护了阿拉伯原有的父权制对女性的压迫,加深了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的矛盾。
(三)阶级压迫、男性暴力下的受害者形象
社会性别是一种不对称的、不平等的两性社会关系。[9]纳瓦勒在小说中展示了女性在基于阶级和性别的父权社会中生活的困难。村长的妻子在儿子塔里克谈论女性不知羞耻时,她能够看到父权的虚伪,父权制下的男性忘却自己的行为,将此归于女性,将她们视为妓女,并抨击她们不知羞耻的行为如何污染了村庄的环境。塔里克与其父亲强奸女性,用自己的权力征服女性,特别是家境贫苦、教育程度低的女性。而他的母亲即村长的妻子来自富有的家庭,在这种源自家庭内部的“私人父权制”的压迫下[1],即使观察着这一切,却也总是保持沉默,承受着来自父权的心理压迫。
内菲萨与宰娜卜这对姐妹自小在田地里干活,自从堂弟加拉尔参军、姐姐内菲萨失踪、父亲卡夫拉维被抓,宰娜卜代替姑姑扎克娅承担起负担家庭的重任。三者受到来自阶级、宗教的“公共父权制”以及源自家庭内部“私人父权制”的双重压迫。[2]
内菲萨有时会伸出小手,想玩弄卡夫拉维的胡子。卡夫拉维张开嘴,轻轻咬住她光滑的小手指,作势要咬下去,内菲萨总是笑着迅速抽回自己的小手指。这种玩耍方式代表着性本能,而直到父亲真正地用牙齿咬住内菲萨的手指后[5]72,这种性本能转变为攻击性本能,将内菲萨置于性压迫的阴影下。宰娜卜来自下层阶级,她接受去村长家干活的原因并非是想得到村长的青睐,而是受到了一种更强大的力量的操控。这种力量并非来自村长的权威,来自一个更为神秘和难以理解的存在。她被告知要服从一切,以拯救她的姑姑扎克娅免受恶魔的侵扰。在她眼中,村长就是帮助姑姑驱除魔鬼的神。宰娜卜的行动不仅仅是为了谋求生存和温饱,更是为了追求一种超越自我的信仰和宗教敬畏。她愿意放下自己的尊严和自由,成为村长的仆人,只为了拯救她所爱的人,保护她的家人免受邪恶力量的侵害。在她心中,这不仅是一种牺牲,更是一种信仰的体现,一种对神圣力z580F4pNXBOc3Mp0NAxumSXsdMiPagLtnBOL8z69tuc=量的顺从和敬畏。在她所处的文化和宗教环境中,对于神秘力量和超自然现象的信仰是根深蒂固的。人们愿意为了寻求超自然的保护和祝福而付出一切,甚至是自己的尊严和自由。
扎克娅出生时,其父亲因为妻子未能生出儿子,而殴打她。[5]114结婚后,每当死了儿子,扎克娅的丈夫阿卜杜勒·穆纳姆就会抄起手里的任何东西,疯狂殴打扎克娅;每当生了女儿,亦是如此[5]106,而扎克娅总共生了四个儿子和六个女儿。在男权社会,女性的身体与思想通常受到男性的控制,女性被定义为生育的工具,她的价值仅仅是她能够生育的能力。而生育男孩更是被视为一种神圣的义务,一个对男性尊严的象征。当这个义务未能被实现时,男性们并不考虑理性和尊严,而是诉诸最野蛮的手段,以确保他们的权威不受动摇。在这种残酷的环境下,女性被迫选择沉默。她们的声音被压抑,她们的权利被剥夺,她们被迫陷入家庭内部的边缘,成为一个被遗忘的“他者”。
在小说中,纳娃勒在多处对女性佩戴头巾、身穿黑袍进行描写,尤其是描写法提娅与哈扎维教长结婚后,哈扎维认为,自己作为负责宣扬教诲,维护村庄道德与虔诚的教长,其妻子除了脸和手掌,身体不应该被其他人看见。面纱被视为保护妇女贞洁的标志,外出需要包裹严严实实的面纱。纳娃勒曾提到自己的外祖母一生只有结婚和去世两次出门[8],小说中的法提娅即代表了自己的祖母以及埃及生活在面纱下的女性。面纱背后,是女性被剥夺的自由和尊严,是她们在沉重的压力下挣扎求存的生活,因而纳娃勒又将面纱视为“压迫女性的工具”。
作为在埃及传统家庭中长大的法提娅,从小觉得自己不够纯洁,感到身上有一个部位肮脏堕落。在得知会有专人为自己切掉身上肮脏堕落的部位而沾沾自喜。相比较于开罗宽阔华丽的街道、宏伟的建筑、穿梭不停的轿车、叮叮作响的有轨电车和穿着时髦的女士与绅士,“割礼”在卡弗埃尔特这样的村庄依旧盛行,“割礼”是埃及家庭中父权制拥护者对女性的物化和奴役。而小说的作者纳娃勒同样是“割礼”这一野蛮仪式的受害者。
导致内菲萨、宰娜卜、扎克娅、法提娅等女性悲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周围人的凝视。首先是来自村长、哈扎维等人对内菲萨、宰娜卜等人的“凝视”,其次是来自村民的凝视。无论她们担任着什么样的角色,始终处于被凝视者的位置。纳娃勒笔下的法提娅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女性。面对内菲萨抛弃在自家门口的婴儿,法提娅收养他并像对待自己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他。然而自己的丈夫以及愚昧的村名视婴儿为灾星,认为婴儿是自己职业道路上的绊脚石,是不幸的携带者。当法提娅察觉到儿子有性命之忧时,她害怕孩子受到迫害,将孩子抱在胸前,裹紧头巾,悄悄带其离开,却受到了周围村民的凝视。周围村民的凝视以及言语与身体暴力,害死了无辜的法提娅与孩子。
村长压榨的并非只是柔弱的女性,村里的男性也同样陷入被村长压迫的境地。任何违背村长命令或被怀疑违抗村长的人都将被追捕并杀害。小说中的埃瓦尔在卡夫拉维所代表的普通村民眼中,是一位有教养的人,而在村长及其儿子眼中,他被描写为一个轻率的人,通过栽赃诬陷埃瓦尔,可以掩盖内菲萨失踪的真相,从而达到掩盖自己恶行的目的。随着物价的上涨,农民欠政府的税越来越多,村里的情况越来越糟糕。从前的百姓因害怕权威,选择躲避来自统治者的凝视。村民们对所有的警察、所有的官员,以及所有的权威和政府的代表充满仇恨。农民的脊背被无穷无尽的劳作压弯,他们的脚因日复一日地行走磨破。卫队队长说道:“人们变了。”从前人们都不敢看我的眼睛,现在他们竟然会直视我的脸,走过我身边时也不再低头看地面。农民越来越饿,他们的食物只剩下干面包和被虫蛀过的咸奶酪。[5]189
小说最后,扎克娅将自己惯用的锄头高高举到空中将村长的脑袋敲碎,化作卡夫埃尔特村庄里遭受压迫的农夫、农妇的代表,推翻压迫自己的“神”。小说深刻地揭示了统治者对普通百姓的残酷压迫和剥削,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在这个虚伪的统治体制下,都面临着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村长等统治阶级代表了权力和财富的集中,而农民则成了他们手中的牺牲品。他们的生活被税收的负担和无尽的劳作所笼罩,饱受着物质和精神上的双重折磨。然而,即便如此,他们仍然保持着对权利、自由和尊严的渴望,最终勇敢地站起来反抗压迫,为自己争取到应有的权利和尊严。
三、结语
纳娃勒·萨阿达维的小说《神死在尼罗河畔》通过塑造一系列人物角色,展现出当时埃及社会状况下,统治阶级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尖锐矛盾,女性除了受到殖民统治的压迫,还受到家庭、宗教、阶级的“公共以及私人父权制”的压迫。小说中对各种人物形象的描写是半个多世纪以前的写照,而时至今日,他们仍旧生活在贫困、新殖民主义愈演愈烈的社会中。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不同社会阶层和背景的人物,每个人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经历和社会压力。统治阶级的人物往往以权力、财富和特权为基础,而普通民众则被迫在贫困、压迫和不公平的环境下艰难生存。女性角色尤其凸显了这种不公,她们不仅要面对外部的殖民统治,还要应对家庭内部和社会结构带来的束缚和歧视。通过分析这部作品,有助于我们认清埃及普通百姓,特别是女性遭受压迫的根源。
参考文献:
[1]Akhter,S.,S.Shah,and S.Nazir.Exploitation of Women in Arab Patriarchal Society in Saadawi's God Dies by the Nile:A Marxist Feminist Analysis[J].Annals of Human and Social Sciences,vol.4,no.1,Jan,2023:93-103.
[2]Jaber,Nabila.BARGAINING WITH PATRIARCHY: GENDER,VOICE AND SPATIAL DEVELOPMENT IN THE MIDDLE EAST[J].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23,no.3,2001:101–06.
[3]Said-Foqahaa,Nader,and Marwa Maziad.Arab Women:Duality of Deprivation in Decision-making under Patriarchal Authority[J].Hawwa,vol.9,no.1-2,2011:234- 272.
[4]李银河.女性主义[M].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21.
[5]纳瓦勒·赛达维.神死在尼罗河畔[M].蒋慧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
[6]梁焕然.米切尔女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研究[D].吉林大学,2023.
[7]梁哲铭.福克纳小说的“凝视”叙事研究[D].湘潭大学,2022.
[8]牛子牧.纳娃勒·赛阿达维作品与思想研究[D].北京外国语大学,2015.
[9]范若兰.文明冲突中的面纱[J].世界经济与政治, 2006,(03):32-38+5.
[10]孙绍先.女权主义[J].外国文学,2004,(05):48-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