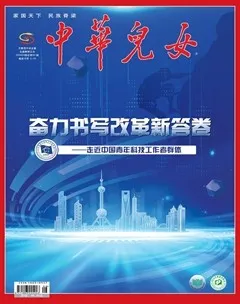杨光辉 探索生命的无限可能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杨光辉的古典文学功底很好,原典籍语信手拈来。他对人文主义的探索也打破了当前教育模式下形成的刻板印象——文理科泾渭分明的专业划分,极易形成各自知识领域的壁垒。某种程度上,他的生命状态也是蔡元培先生教育观的具体呈现:融通文理。或许,这也和他的专业有关,他研究基础生物学,生命的物质基础、运动与变化中蕴含着深刻的哲学视角。从最细微的肉眼看不见的细胞中得到生命规律的启示,这也是一种“尽精微见广大”了。
向内探索,向外追寻
1990年出生于河北容城的杨光辉,童年生活很快乐。放学回来,可以和小伙伴们一起在田野里疯跑,有时也会去田地里帮家人搭把手,但回想起来,并不觉得累,想到的都是一群孩子在野外的欢乐。此外,他还有大量的课余时间可以背原典古籍。家庭无形中构建了一个“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天然教育场景。大量的留白,意味着更多的自由。自由会生出自主,无需强调驱动力,自由成长的过程本身就蕴含着源源不绝的力量。
杨光辉高中学习成绩很好,尤其物理成绩,常常会拿到满分。最后一道大题,大部分同学都会“折戟”,他却能轻松做出来,而且越做越“上瘾”,一点点积累出来的“正反馈”让他认为自己有物理学方面的天分,一度,他想以物理学为专业。参加高考时,恰逢“21世纪是生命科学的世纪”最流行的时代,受到这句话影响的杨光辉,在次年高考时报了中国农业大学的生物学专业,当时,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会成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施一公的学生。
进入施一公院士的实验室做研究,对于生物专业的学生来说,无疑有着巨大吸引力,报名者众。杨光辉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给施老师发了一封邮件,介绍了自己的经历、学习成绩与感兴趣的领域。没想到,隔天就收到了施老师的回复,要他去参加20天后的面试。
“农大距离清华也近,也是抱着试试的心态去了。面试后,我感觉自己表现不太好。最后一个问题,施老师问:五年后你会做什么,有想过吗?我说想过,但也没接着往下说。施老师又追问了一下,我说,这五年,我会认真读书做科研,但是五年之后,不知道想法会不会变,可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杨光辉是那么想的也就那么说了,出来后,和其他参加面试的同学一聊,发现别人的回答都是继续做科研,成为科学家。他觉得自己“没戏了”,没想到的是,他顺利通过了面试,成为施一公院士的学生。
“回过头来想想,我觉得可能还是因为真实吧,那是我当时的想法,我就如实表达了。”或许也是因为这样实在、真诚的表达让他在众多的面试者中脱颖而出。
直到现在,杨光辉依然会像当年参加面试时那样,真实表达自己的想法。他尊重自己每时每刻当下的感受,并做出当时当下的应答,他的生活中最重要的时刻就是当下。“对未来最大的慷慨,是把一切献给现在。”法国作家阿尔贝·加缪的这句话,真正能落地到生活中需要有强大的行动力和清晰的自我认知,真实面对他人和自己。向内探索,向外追寻。简简单单,脚踏实地。
探索生物结构学的奥秘
在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硕博连读五年,即将毕业时,杨光辉的确如面试时所说,尚未确定以后是否做科研。有一度,他想过去企业工作,工作单位都已经联系好了。这时,导师施一公的人生建议就显得特别重要——继续在科研路上探一探吧,如果再给自己一段时间,还是觉得不是自己的预期,还可以去企业闯荡历练,可如果直接去了企业,想要回到科研似乎就难了。杨光辉很认可,2017年博士毕业后,他留在了清华大学结构生物学高精尖中心继续攻读博士后。

两年博士后的科研生活,是他科研工作颇有收获的一个阶段。他和团队在施一公老师的带领下,一起在顶级学术期刊《Nature》《Science》先后发表两篇论文:《人源γ-分泌酶识别底物Notch的结构机制》和《人源γ-分泌酶底物淀粉样前体蛋白的识别》的文章,两篇文章报道了人体γ-分泌酶结合底物Notch以及和淀粉样前体蛋白(APP)的高分辨率冷冻电镜结构,从分子层面为理解γ-分泌酶特异性识别和底物切割的机制提供了重要认知基础,为研究与阿尔兹海默症以及癌症相关的发病机制、特异性药物设计提供了重要的结构信息。
施一公实验室一直在做γ分泌酶相关的工作,杨光辉也一直在思考如何解析γ分泌酶与底物结合的结构,但初期各种蛋白质设计的方法并不能获得酶和底物稳定在一起的状态。“在读文献的过程中,我看到了酶与底物可能发生相互作用的部分位点,有了一些线索,从2017年初开始尝试使用交联的方法,然而也不知道哪几个氨基酸位点能交联在一起,于是就在有限线索下进行尝试,希望能够筛选出最优解。”
实验过程并不顺利。“有一阵子就很迷茫,不知道能不能出结果,不知道未来会怎样。这时候就找各种书来读,想缓解一下压力。”他遇到了刘慈欣的《三体》,拿起来就放不下了,晚上因实验中的问题而苦恼的时候就看这本书,大约读了两个星期,看完了三本。“我觉得科研很像面壁,在自己研究的领域里面,可能没有人会懂你,没有人知道你研究的细节是什么,你相当于做一个面壁者,你在不断奋斗,不断思考,在想怎样把研究的内容搞出来。”杨光辉说,作为面壁者,注定是孤独的,但内心经历的苦楚、寂寞,都是科研道路上必不可少的经历。
历经“山穷水尽”的挫败有多痛苦,迎来“柳暗花明”的那一瞬就有多兴奋。看完《三体》,领略过刘慈欣创造的磅礴世界与波诡云谲的星际穿行,在更漫长的时间线里,他的迷茫与焦虑也缓解了很多。定下心神,他开始回顾自己的实验设计,看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还有哪个环节可以修正,不论是否得到预期结果,定时复盘,这也是施一公老师教给他们的。就是在这次复盘中,他注意到了此前被自己忽略的部分。
“课题最难的点在于获得稳定的酶和底物的复合体,酶与底物的相互作用短短一瞬,就好像剪刀剪断绳子的刹那,我们要探知的是这个瞬间的结构和机理,”杨光辉说,“两种底物的研究过程是螺旋上升的,一直同时进行。在最初的对APP的尝试中,由于APP蛋白本身的性质,我们并没有获得很大突破。随后我们比较了Notch与APP的蛋白质序列,惊奇地发现尽管二者序列各不相同,但是二级结构相似性很大。这一规律的总结带给我们突破口。我们先获得了Notch与γ-分泌酶的稳定复合物,随后在解析结构后再次对比APP与Notch的序列,确定了针对APP的方案,真是有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
最终团队成功获得了解答,并且获得Notch与γ分泌酶在一起的状态。这时,也快到春节了。“我们立即收了一些数据,春节在家远程计算,大年初三早上我算出来一个初步结果,发现我们想要的底物确实存在。很兴奋!有一种迫不及待想把课题做出来的心情。于是我们很快回到实验室,准备样品,收集数据,最终把课题做了出来。”冲破关隘的兴奋无以言表。他也在这个实验中体验到了科研工作者的成就感。
在这个实验中,杨光辉深刻体会到了结构生物学巨大的魅力。“课题做出来后,我们从结构里发现了一个没有想象到的二级结构β-sheet的形成。如果没有结构生物学,是很难想象或者预测出来的。”这也坚定了他要在结构生物学领域深潜的决心。
为学贵在持之以恒
2019年,杨光辉以“杰出人才”身份引进中国农业大学,任生物学院教授。那一年,他29岁。他感谢学校给予的信任,也希望将自己的科研方向与农业做一些融合——生物学是一门基础学科,可以和很多学科交叉。以前促使他报考生物学专业的那句话:“21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如今他也有了更多理解。“很多话需要有一定的语境和时间。21世纪,生物科学固然非常重要,但学科交叉是科学发展的趋势,未来的科学一定是在不同学科通力合作基础上发展的。”
2023年,杨光辉和郭岩课题组合作解析植物抗盐胁迫关键蛋白SOS1的结构和功能调节机理的文章在《Nature Plants》发表。土地盐碱化在世界范围内影响着植物的生长和作物的生产,土壤的盐碱化使植物遭受盐胁迫。植物在适应盐胁迫的过程中进化出了一系列抗盐信号通路,弄明白其中蛋白质作用的机理,会有助于植物抗盐碱化,促进农作物更好生长。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基础生物学与农业相结合,空间广阔。
关注农业领域后,杨光辉也有了很多时间和农业专家们一起在田间研究的经历,去过大东北,走过大西北,看过黄淮海。他已经习惯了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在他看来,也不算什么高强度,这是科学工作者的常态。出差期间,恰逢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杨光辉关注到,全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他深有感触地说,自己从学生转变为青年高校教师后,要紧跟全会提出的“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做到和学生共同进步。既要敢于挑战研究领域的难题,也要充分和其他学科交叉,将研究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这离不开对重要研究领域的深耕,也离不开和老师同学们团结在一起努力,更离不开党和国家的引导。
“科研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之前掌握的知识,很可能多年后攻克其他重要课题时用到。”杨光辉一直记得施一公老师的指导,阅读大量文献,积累知识、独立思考,形成批判性思维,才能在遇到难题时,找到正确思路。
施一公老师对他的影响很大。“在方法论层面上,他教会了我们做科研的技能,这是当时在实验室里能够即时得到的。精神层面的影响,很多时候是离开实验室后慢慢悟到的。”杨光辉说,“有些感受是需要时间结合经历,慢慢沉淀才有体会。”比如施老师的勤奋,当年他们路过施老师的办公室时,不论多早,都能看到他的办公室已经开门了。很晚离开办公大楼时,施老师的灯还亮着。在施老师那里,他看到了科研工作者的勤奋。耳濡目染间,他也习惯了这样的作息时间,包括周末,也会去实验室坐一坐,哪怕就看一会文献,写一段工作总结,坐在办公室里,就会觉得内心很宁静。但是,他也不提倡无效勤奋,更不提倡无谓吃苦。不管干什么,还是要讲究方法和效率,毕竟时间宝贵。
如今他也开始带博士生,对于年轻一代的学子们,他说,有时也会应学校的要求给新生讲一些成长感言,但他每次都会先表达,这些经验与感受也仅代表他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特的,成长经历,家庭背景,性格禀赋等等都不同,所以没有一个人可以复制另外一个人的路径。他鼓励学生们去探索适合自己的路。
相比于人生经验,他更愿意分享的是在科研道路上的喜悦。“科学的魅力在于可以去发现未知领域,深潜其中,不被外物干扰时的专注也很迷人。”杨光辉说,“如果一定要给年轻人说一点个人感受的话,我觉得就是坚持,《劝学》中有说,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选择的路觉得是对的,就坚持走下去。”
他喜欢读一些人文哲学方面的书,也喜欢读名人传记,不论是《三体》中虚构的世界,还是那些越过沟壑险境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他都会从里面看到这些人身上所蕴含的勇气与力量。他会常常默念一些古诗词,比如李白的诗,那些在他很小的时候就熟背的句子,在他中年时会时不时以另一种方式回旋到他心里,引起一些波动与觉察,有时会顺着这些小小的窗口再往深处探,就会有一些对自己的新认识和发现,这也有些像他研究的蛋白分子,有很多路径可以抵达,他要做的就是一条一条把它们捋出来,说不定就有惊喜发现。
责任编辑 张惠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