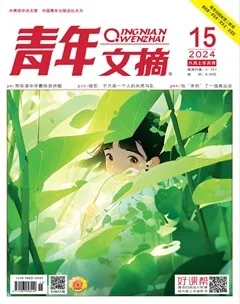不要赠人以虚空
朋友在“520”当天跟男友进行了书信版的真心话,约定在给彼此的信里列出一条希望对方改变的地方,她男友在信的结尾里写:我有时觉得你是个很难被取悦的人,无论我做什么你好像都不在意。
她当下面带笑容地跟男友说我想想,转头就委屈巴巴在微信群里跟我们吐槽:我难取悦?!我俩谈恋爱一年多,我从来没对他提过什么要求,不要求晨昏定省嘘寒问暖,不要求节假日纪念日送礼物,还有我这么好说话的女朋友吗?
几个朋友在群里七嘴八舌应和她的吐槽,我旁观几个回合还是没忍住——可恰恰就是没有要求的人才最难被讨好啊,你以为你给的是自由,可对方感知到的却是一片虚空。
无论哪种关系,这种摸不着底也看不到边的自由都最难熬,因为不知道什么是被鼓励的,什么又是被厌弃的,一切的努力似乎都像在跟空气过招,没有任何反馈。
我第一次见识到这种空虚感的杀伤力,其实是在跟同事聊起她小孩的时候,同事奉行的是“自由散养”策略,整天挂在嘴边的就是“你开心就好”。听上去这小孩的生活很自由很幸福吧,然而她却在小升初的当口崩溃了,大哭着跟她妈妈发了好大一通脾气——“你为什么从来都不对我提要求”“你为什么从来不告诉我该怎么做”“我一点也不开心,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开心”。
同事也很委屈,难道人偏得被制约着拘束着才满足?
很难承认,但的确如此。人口口声声向往自由,但对确定性的追求却高于一切,无论是物理空间还是心理空间,都需要一个边界明确的框才能感到安全。
这也是为什么心理学和社会学上都有“存在主义危机”这个词条,一旦一个人连自己的存在都无法感知,他生活中几乎所有的秩序都会崩溃。而人从何感知自己的存在呢?恰恰是靠被约束,被驱从,被需要,是所有的被动式构成了存在的基础,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有沟通,才有磨合,才有碰撞,才有拥抱。

在这些被动式1 到100 的刻度里选择最合适的度,才是最难也最有趣的试炼,但至少得从0 上走出第一步。
(偶然摘自“陶瓷兔子的悦读笔记”微信公众号,郭德鑫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