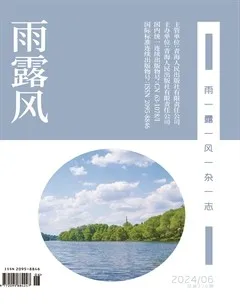从《诗经·国风》中探析中华传统美德
《国风》是《诗经》中的精华,是中国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涉及内容广泛,泛指一切美好的德行,由个人层面上升到国家层面,从小到大可归纳为“修身”“齐家”“治国”。文章通过交替使用归纳统计法与文本细读法,从修身、齐家、治国的层次探析《诗经·国风》中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
一、修身
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构建和谐社会、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资源。在《诗经·国风》中,个人层面的传统美德丰富多彩,主要包括对“礼”的重视,对“勇”的歌颂,以及对“劳”和“忠”的赞美。
(一)礼
孔子云:“不学礼,无以立。”《国风》中的很多篇目都体现了当时人们对传统美德“礼”的重视。如《鄘风·相鼠》是一篇劳动人民斥责卫国统治阶级苟且偷生、暗昧无耻的诗。毛序:“刺无礼也。”诗以“鼠”起兴,讽刺统治者“无仪”“无止”“无礼”。其中写道:“人而无礼,胡不遄死?”王先谦在《诗三家义集疏》中提道:“首二章皮、齿指一端,此举全体言之。”前两章的“仪”和“止”都是礼的一个方面,强调礼的重要性。
礼是互赠回馈之礼。有来有往,是人与人交往的基本礼仪。《礼记·曲礼上》中写道:“礼尚往来。往而不来,非礼也;来而不往,亦非礼也。”《国风》中对这一礼仪表现得较为明显的有《卫风·木瓜》,诗中的“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投我以木桃,报之以琼瑶。”“投我以木李,报之以琼玖。”反映了当时人们讲究礼尚往来,男主人公赠送了东西,女主人公也一定回赠。强调互赠回馈,此交际之礼也。
礼还是媒妁之礼。古时子女的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认为这是社会约定俗成的礼仪,每个人都要遵守。在《国风》中,《郑风·将仲子》《齐风·南山》都能体现这一思想。《将仲子》是一首女子被迫拒绝情人的诗,拒绝的理由是她与男子的行为不符合当时社会的礼仪。从诗的内容来看,这首诗的男女主人公是自由恋爱,但没有得到双方父母的认可。三章的首句都是“将仲子兮”,已是十分亲密。男主人公翻院墙、折树杞都要与女主人公见面。但女主人公坦言自己害怕“父母之言”“诸兄之言”“人之多言”,自己与情人自由恋爱不符合当时的礼仪。因此,纵使爱之深,也只能拒绝。一波三折,写尽女子爱与畏的矛盾心理。《南山》中的“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直接强调了当时人们对这一“礼”的重视。
(二)勇
《国风》中展现了古人对“勇”的歌颂,最突出的就是对猎人的赞美。古时,“狩猎”是人们谋生的手段,故对于勇猛、身手矫健的猎人颇为赞赏。《郑风·叔于田》就是一首典型的赞美青年猎手的诗。全篇详细地记录了打猎的过程,通过描写猎人驾车、射箭、打虎、烧火等场面,突显青年猎人勇武好胜的性格。《齐风·还》也是一首猎人之间互相赞美的诗,“子之还兮”“子之茂兮”“子之昌兮”,直接赞赏了猎人的勇敢。这种赞美在《周南·兔罝》《召南·驺虞》中同样有所体现。
此外,对“勇”的歌颂还体现在女子对心爱男子的夸赞中。《邶风·简兮》中的“硕人俣俣,公庭万舞。有力如虎,执辔如组。”虽然只是客观地描述舞狮的力大无比,但字里行间充满着女子对舞狮者的爱慕。可知,当时不管男子还是女子,都对“勇”大加称赞。
(三)劳
《诗经·国风》中对劳的称颂体现为对劳动的热爱以及对劳动者的赞美。《诗经》以其“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现实主义创作手法,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劳动场景和过程。在《国风》中尤其能看出人们对“劳”的赞美,如《周南·芣苢》《魏风·十亩之间》《豳风·七月》等。《芣苢》采用反复吟唱的形式,用一系列动词表示采摘的过程。不断的收获,伴随着不断的歌声,越采越多,越唱越高兴,表达了她们对劳动的热爱。《十亩之间》则写出了采桑女子劳动的欢快。《七月》充分展现了农民一年四季的劳动场面与生活图景,表达了对劳动者辛勤劳动的同情与赞美。
《国风》中有正面歌颂劳动者、表达对劳动人民的赞美的,也有从侧面对剥削者不劳而获进行讽刺的。如《魏风·伐檀》中反复强调:“不稼不穑,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猎,胡瞻尔庭有县貆兮?”以反问的语调表达对剥削者强烈的质问。农民们辛苦劳作的粮食和冒险打猎收获的野兽都被剥削者掠夺,在闲暇的时间里还要被剥削者奴役伐檀,为贵族造车,方便贵族出行。全诗将劳动人民与剥削者进行对比,突出了不劳而获与劳而不获的尖锐矛盾,反诘式的设问手法,毫不掩饰地表露出作者对剥削者的讽刺以及对劳动者被剥削被压迫的深切同情。
(四)忠
“忠”在辞典中解释为:尽心诚意待人处事的美德。《国风》中许多诗篇都表现了古人对这一美德的重视。其中的很多婚恋诗主要集中在对爱情和婚姻的描述上,能看出当时人们对爱情忠贞的赞美。
一方面是丈夫对妻子的忠贞。有男子不为外面如云如荼的女子心动,而始终坚持爱着自己贫贱的妻子,并借诗表达自己对妻子忠贞不贰的决心,如《郑风·出其东门》。用“有女如云”“有女如荼”喻街上的美女多若天上云,多若白茅花。但“匪我思存”,这些都不是“我”的心上人,“我”的心里只有自己的妻子。还有丈夫表达对亡妻的悼念,即使妻子已不在,但诗人并无再娶之意,借诗表达对妻子的忠贞。典型的就是《邶风·绿衣》,诗人睹物思人,看到亡妻之衣,触目伤怀。
另一方面是妻子对丈夫的忠贞。有妻子深爱丈夫,表示了愿意与丈夫生生死死在一起的决心,如《桧风·素冠》《唐风·葛生》。在《素冠》中,妻子看到丈夫体枯肌瘦,不由地“我心伤悲”“我心蕴结”,表达了“聊与子同归兮”“聊与子同一兮”的愿望,颇有“生同衾死同穴”的意味。可称为悼亡诗之祖的《葛生》,妻子愿百年之后与丈夫共归一处,也表达了对丈夫的忠贞。
二、齐家
先修身后齐家,好家风亦能治国。中华民族历来重视家庭,正所谓“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先有家再有国,“齐家”是“治国”和“平天下”的重要前提。《国风》中的很多篇目也展现了有关“家”的传统美德。从描写男女之情的诗篇中我们能够看到古人对结婚生子的渴望,即成家的追求。从对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夫妻和睦相处,婚姻美满的画面。此外,还渗透着对“孝”文化的重视和弘扬。
(一)结婚生子
“家”由人组成,自然就避不开“结婚”这一话题。《国风》中有很多诗篇能够看出人们对“结婚立家”的渴望。如《唐风·绸缪》是一首祝贺新婚的诗,全诗充满喜庆欢快的气氛。章头用“束薪”“束刍”“束楚”起兴,都用来象征结婚。“今夕何夕,见此良人(粲者)?子兮子兮,如此良人(粲者)何?”写出了两人的激动与急切,尽情享受这幸福的初婚的快乐。《国风》中还表达了对新娘的赞美,如《周南·桃夭》《召南·雀巢》;对新郎的祝贺,如《周南·樛木》;有待嫁女子等待未婚夫所唱的诗,如《邶风·匏有苦叶》。这些诗篇都能看出当时人们对爱情的渴望,对婚姻的向往。
此外,还有很多篇目表达了当时人们对“多子”的愿望。古时,生子是成年男子延续家族应尽的责任。《国风》中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借多子的动物或植物来兴人的多子。如《周南·麟之趾》中用麟趾喻子孙之盛,直接赞美统治者子孙繁荣。《周南·螽斯》中,诗人用蝗虫多子比喻人的多子。借“麟”“蝗虫”“椒”等意象,兴人的多子,进而表达人们多子多孙的愿望。
(二)夫妻和睦
《礼记·中庸》中写道:“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一个家庭要讲究“以和为贵”,才能“家和万事兴”,夫妻和睦则是最能体现“和”这一美德的标志。《国风》中有直接描写夫妻恩爱的场面,还有对夫妻间和睦相处的侧面描写,如妻子表达对丈夫的思念,以及夫妻重逢后的喜悦。
通过日常生活琐碎片段描写夫妻间的恩爱,直接表达夫妻间的和睦。如《郑风·女曰鸡鸣》中描写了三个镜头,第一个镜头:鸡鸣妻催。简单几个字为我们描绘了生活中常见的夫妻之间相处的画面。第二个镜头:女为夫祈愿。妻子对丈夫很满意,于是发出了一连串的祈愿:“弋言加之,与子宜之。宜言饮酒,与子偕老。”希望丈夫天天都能射下大雁,自己天天与丈夫佳肴共饮酒,两个人白头偕老永相爱。第三个镜头:男子赠佩。通过一系列的细节描写与直抒胸臆,我们能感受到其夫妻恩爱、如漆似胶的场面。
通过描写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和夫妻相见时的喜悦,间接表达夫妻间的和睦。春秋战国时期,战乱不断,男子要承担起保家卫国的责任,妻子则操劳家中事务。因此,《国风》中的许多篇目常常流露出妻子对丈夫的思念。如《王风·君子于役》《周南·汝坟》《卫风·伯兮》中都写到了女子思念远征的丈夫,担心丈夫的处境。思念有多浓,相见就有多喜。《国风》中有描写夫妻久别重逢的喜悦,侧面能看出其家庭的“和”、夫妻的恩爱,如《郑风·风雨》。三章都以风雨、鸡鸣起兴。“凄凄”“潇潇”“如晦”极力渲染风雨之大。但是与重逢相比,也不过如此。“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喜悦之情,难以掩饰。风雨越大,更衬重逢之喜,此所谓“以哀景写乐,倍增其乐”。
(三)孝顺父母
《说文解字》:“孝,善事父母者。”孝,作为中华传统美德之一,一直以来都被提倡。在《国风》中,孝的情感表达主要分为三类:出嫁女子对归宁的急切与激动、对父母的思念以及对父母辛劳的歌颂。这些情感交织在一起,能够看出人们对传统美德“孝”的赞美与弘扬。
一是出嫁女子对归宁的急切与激动。“归宁”一词解释为:回家省亲,多指已出嫁的女子回娘家看望父母。在《国风》中,有出嫁女子急切地期盼早点回家看望父母的描写,如《周南·葛覃》。诗歌用“葛藤”“黄鸟”起兴,皆用来兴自己念父母之急切。末章“害浣害否,归宁父母”一句才直接坦露自己思念父母、想要急切“归”的心情。整首诗的情感表达较为含蓄,前面描写“葛藤”“黄鸟”等事物,直到最后一句“归宁父母”才让人恍然大悟。
二是对父母的思念,这一情感在征战诗或行役诗中较为常见。在《国风》中,有很多诗篇都表达了人们对战争与徭役的控诉和不满。这类情感的表达往往与对父母的思念相结合,如《唐风·鸨羽》。全诗描写无休止的徭役给人带来的痛苦,但诗人不从自己切入,而是从自己不能赡养父母的角度出发,从而控诉战争徭役。诗人接连发出“父母何怙?”“父母何事?”“父母何尝?”的哀叹,担心父母的吃穿住行,将对父母的思念融入对君王徭役的怨愤。
三是对母亲辛劳的歌颂。《国风》中对父母的这种感恩之情表现得最为真切的莫过于《邶风·凯风》。诗序:“凯风,美孝子也。”全诗都在赞颂母亲的辛劳,自责自己做得还不够。前两章将兄弟七人比作“酸枣树”,酸枣树之所以能够健康成长,全靠母亲的辛勤哺育。后两章又以“寒泉”比母,以“黄鸟”比子。黄鸟之所以能够“载好其音”,都是因为寒泉在地下流淌,滋养浚人。一、二章末尾以“母氏劬劳”“母氏圣善”作结,赞美母亲的辛劳与美德。三、四章以“有子七人,母氏劳苦。”“有子七人,莫慰母心。”作结,自责不能侍奉,无法尽孝的处境。
三、治国
“国家”这一概念形成于春秋战国之际,在此之前,国与家是一体的,爱国情怀也伴随着国家的出现而出现。在国家层面,其传统美德主要是融入在人们的爱国精神中,《国风》中表现了当时人们保家卫国、勤劳勇敢、团结统一的优良传统。
(一)保家卫国
西周至春秋中叶几百年间,诸侯林立,外族入侵,征战不断,中原大地上经历过多次战争的洗礼。男子为了保家卫国,不得不舍小家、顾大家。《国风》中记录了多次民族之战和正义之战,闪耀着当时人们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如《邶风·击鼓》主题是卫国戍卒、思归不得,借此表达对战争的控诉。诗中的“击鼓其镗,踊跃用兵。”“从孙子仲,平陈与宋。”都是在描写战争,击鼓的声音震响耳旁,兵将奋勇操练,可见士兵们为保家卫国奋力操练的场面。
《国风》中不仅描写男子保家卫国的决心,还描写了妻子为丈夫保家卫国感到骄傲和对丈夫的支持。如《卫风·伯兮》中:“伯兮朅兮,邦兮桀兮。伯也执殳,为王前驱。”妻子夸赞丈夫执长殳真威猛,成为君王的前锋,真是邦国的英雄。可见当时社会不管男子还是女子,都以保家卫国为荣。尽管思念丈夫“甘心首疾”“使我心痗”,但还是以国为重,为丈夫感到骄傲。我们从这些描写战争的诗句中都能体会到中华儿女舍生忘死、保家卫国的民族精神和民族气节。
(二)勤劳勇敢
“勤劳”这一美德在国家层面则表现为当官者的勤政为民。“在其位,谋其职”,勤政为民当是每一位当官者所倡导的。《国风》中的诸多篇目就描写了当官者的“勤政为民”,突出对“勤”的赞美,如《齐风·东方未明》《唐风·蟋蟀》。《东方未明》中描写了一个小官吏忙于公事,早晚不得休息。《蟋蟀》中三次强调“好乐无荒”,即贤良之人不能荒废政事与正业,强调“勤”这一美德。此外,《国风》中还有反面讽刺为官者不为民的例子,进而突出“勤政为民”这一思想。如《郑风·清人》就是典型的讽刺诗。在外人眼中,高克带领的部队雄壮威武,但他们却只在河边逍遥闲逛,并没有为抵御外敌而认真备战。而身为将军的高克默许了士兵的闲散慵懒,自己也只是耍弄刀枪,消磨时光。诗人讽刺将军高克的这一做法,进而呼吁勤政为民。
“勇敢”这一美德在国家层面则表现在人民对国家的忠勇。在《国风》中,不仅有男子保家卫国的勇,还向我们展示了女子的英勇果敢。在听到自己的国家陷入危机时,女子也毫不退缩,为解救国家于水火而英勇奔驰,典型的就是《鄘风·载驰》。许穆夫人听到卫亡的消息后,没有一刻犹豫,立刻奔回卫国,并且提出“联齐抗荻”的主张。“载驰载驱”“驱马悠悠”为我们刻画了英姿飒爽、策马奔腾的女性形象。在“女子无德便是才”的时代,许穆夫人不顾大夫的阻拦,为救国家英勇奔驰,大有“花木兰替父从军”的气概,是对“勇”的完美诠释。
(三)团结统一
在《国风》中,团结统一主要体现在士兵之间的团结互助,士兵与将士之间高度一致,奋勇杀敌,如《秦风·无衣》。“与子同袍”“与子同仇”“与子同泽”“与子协作”“与子同裳”“与子偕行”写出了将士与士兵同衣同袍,同仇敌忾,奋勇杀敌。士兵还与君王保持一致,一听到“王于兴师”的号令,他们就一呼百诺,并肩作战,表现了秦国军民一心、共御外侮的高昂士气和爱国精神。
四、结语
作为现实主义诗歌的源头,《诗经·国风》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孔子曾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并且指出《诗经》的社会功能,即“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文章以《国风》为载体,探讨其中蕴含的中华传统美德,实现了“观”这一社会价值。《诗经·国风》中能够看出古人对“修身”“齐家”“治国”三方面美德的重视,对当下社会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作者简介:赖阳宁(2001—),女,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学科教学(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