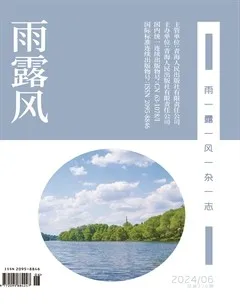身体·空间·时间

在刘亮程的叙述中,对于身体、空间和时间的探索是层层深入的。身体叙事是对于生命的存在状态的探索,也是一种对世界被建构的语言中反本体意义的要求。空间和时间则是生命所存在的场域,不刻意追求具体的意义,更多地表达成为一种象征性的延异。因而在他的笔下,空间不是纯粹的空间,而是一种时间化的空间。时间也不是纯粹的时间,是空间化的时间。生命所处的世界变成一种在现实和虚幻中的多维世界。
一、自反性的身体叙事
自柏拉图开始的对于生命状态的探讨,对于灵魂和身体,产生了二元对立的哲学关系传统。在这个关系传统中,身体总是受批判的对象,被视为处在被灵魂主宰的地位,同时灵魂被看作与理性和知识具有同一性。从启蒙哲学开始,对人的定义是理性的动物。根据海德格尔的看法,思想和理性是价值设定的基础和标准,动物性就变得无足轻重了,因此身体陷入了为哲学所排斥的漫长黑夜。
但尼采不这样认为,尼采认为由于权力意志构成了一切存在的基本属性,那么动物性当然就是人类存在的根本规定性。这样在对人的定义中,身体和动物性取代了形而上学中的理性的位置,身体就是权力意志。由于尼采身体哲学的出现,主体(意识)哲学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终于成为被审视的对象。如果将身体剔除在视野之外,那么就只有自我或者主体,就会导致绝对经验或者绝对理性的产生。但身体本体论认为身体可以自己做主,人首先是一个身体和动物性的存在,理性只是这个身体上的附着物。世界将总是从身体的角度获得它各种各样的解释性意义,世界是身体动态扬弃的产物。
刘亮程的作品中就体现出了这种对于身体叙事的扬弃过程,“从每个动物身上我找到一点自己。渐渐地,我变得很轻很轻,我不存在了,眼里唯有这一群动物,当他们分散到四处,我身上的某些部位也随他们去了”[1]。在刘亮程的笔触中,《一个人的村庄》是万物的生命生长之源,人与万物并没有高下之分,他曾扛着铁锹试图改变一只虫子的命运,或者追寻麻雀的足迹。刘亮程在《凿空》里描述各种生命的声音,鸡叫是白色,把天空照亮了。羊叫是绿色,使得青草能够生长,狗叫是黑色,属于夜晚的闯入者,驴叫是红色,直通天际的慷慨激昂。人的声音被描述为比黑夜更沉的黑,里面立满了高墙。[2]这时产生了轰鸣的机械声,没有颜色,也象征没有生命。可以看出在刘亮程的象征世界里,机械声象征着工业世界,或更深一层次作为现代理性的代表,是对于身体与生命的一种拒斥。
在刘亮程的身体叙事中动物性的表达有一个集中的象征代表——驴,小说《捎话》之中的主人公是人和驴,驴可以看作是人的动物化的身体象征。在人的生命尽头,引领着人即将死亡的破灭的肉体而继续前进的正是驴的目光。驴的叫声被视为照亮黑夜唯一的通道,通向神与人之间的桥梁,使人能够忠实地抵达自我的超越,在俗世的纷扰里支撑着人的本质而不至于倒塌。这里的驴叫具有知识的本质性和超越性,意味着人突破理性意识对主体的塑造,达成身体的复归。对于罗兰巴特等一大批的结构主义者来说,主体是语言结构的被动产物,并不是身体的直接控制者,也并不是一个绝对自主的东西,主体是被建构的产物,不具备本质性。在刘亮程的笔下,生命的终极只有慷慨激昂的驴叫可以传达沟通本质的声音,“驴叫把鸡鸣压在草垛下,把狗吠压在树荫下,把人声和牛哞压在屋檐下”[3]1。“驴叫像一根根柱子顶天立地,像一道道彩虹,拱起苍穹。”[3]274“驴叫从空中把诵经声盖住,传不到昆那里。”[4]6
然而人的身体叙事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动物性的复归,也应当包括理性意识与动物性争夺身体的过程。巴塔耶的人类学向人们解释了理性如何逐渐抑制动物性,尼采的身体哲学昭示着由动物性驱赶理性的历史。而在刘亮程的文学世界里,理性和动物性相生相长,此起彼伏地在不同的维度中占据主导地位。前文已经提到,在刘亮程的笔触里,自然界各式各样的声音是人的动物性象征,那么语言则是人的理性象征。刘亮程的文学世界里声音和语言分属于两个世界的维度。在世俗和现实的世界之中,语言来自现实世界,地位高于自然界的声音,语言显得更为清晰,所传达的信息也更为复杂,象征着理性主宰的世俗世界。但在灵魂的世界里,语言则比尘埃更加沉重,压得灵魂匍匐于地面,这时只有自然万物有形有色的声音,具备着神性,联通世界,能够使灵魂沟通上天,成为众生万物沟通的桥梁。
在世俗现实世界中,语言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在《本巴》中,语言有一个凝练的象征称为齐,齐并不是某一个固定的人,而是草原上连绵不断的人的总体生命力的象征。“洪古尔,赫兰、哈日王、江格尔,还有我策吉,都曾降生为齐,在那个世界里一出生,便会说唱所有的江格尔诗章。我们既在人世说唱史诗,又在史诗中被说唱出来,同时活在两个世界里。”[5]6语言在这里具有强大的力量,齐在《本巴》里可以沟通时间和空间、梦幻和现实,甚至可以用语言创造世界的角色,具有言出法随的强大言灵建构功能,混淆了真实与虚幻之间的界限。
这就进一步提出了命题,当语言和理性受到质疑的时候,刘亮程认为只有声音和身体原初的动物性能够承担起生命力的本质属性。相较于自然本真的声音,人类的语言与理性、主体与意识是一种建构的产物,带有矫饰的成分。《捎话》之中母驴带着“真言”到达天庭门口,天庭的守门人说:“上天从没给人什么经,都是人编的,你快扔回到人间去。”[4]214《捎话》讲述了毗沙国与黑勒国之间的捎话,这种捎话如同巴别塔,隐喻着语言所构建出来的虚假的圈套,给人类造成更多的伤痕和分歧,阐释拉开真理和真实之间的距离,语言和理性则为构建这种虚假的真实奠定基础。
在刘亮程的叙事中,现代的人就落入了这种圈套,能指和所指的分离,语言和阐释的分离,都导向了人的理性和动物性的分离,落入人的灵魂和身体对立的窠臼中不能自拔。语言和理性导致了二元对立,划分出主体与他者的生命价值的不对等,构建出作为主体存在的人,从而排斥不符合标准理性的一切存在。但这并不是本质性的,而是世俗现实社会对生命的一种规训,刘亮程的笔下呈现了这种反主体、非本质的历史叙事,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身体叙事的自反性。
二、象征化的空间叙事
刘亮程的身体叙事,在更大的场域上,进一步延伸成为空间叙事。身体就是一个最原生性、最小单元的空间母题,因此可以把身体也看作是空间叙事的一种象征性意象。这种象征性意象在刘亮程的书写之中俯拾皆是,比如在《本巴》之中,有关于母腹和乳汁的大段描写,这是一种对于原初生存家园的想象,洪古尔和赫兰、哈日王对于母腹的依恋是这种象征性意蕴的集中体现。母腹在这里不仅仅指向母亲的子宫、生命的诞生地乃至家园乐土等,甚至进一步延伸成为真实与虚幻的交集之处。
《本巴》所叙述的故事就是围绕着母腹所产生的三场游戏与梦,洪古尔、赫兰和哈日王一生不愿意离开母腹。赫兰在母腹中听到了大人在游牧转场的声音,于是自己也和洪古尔在母腹中玩起了搬家家的游戏。后来洪古尔为了守护本巴家园而不得不离开母腹,但他不愿长大,只肯做一个迷恋母乳的孩童。而留在母腹中的赫兰也照样感到一个人的孤独。母腹里和母腹外的世界,哪一个是真实的?明彦质疑拉玛国未出生的哈日王:“一个母腹中的人,他算是醒来的人呢,还是梦中的人?”[5]191最后一切回到原点,洪古尔回到母亲怀抱,赫兰回到母亲子宫,然后重新诞生,被取名为江格尔,赫兰本是江格尔齐所讲述的故事人物,最后又成了下一位江格尔齐。这使得母腹这一象征空间有多重意象场域的解读,能指指向另一个能指,从而形成德里达所说的延异,母腹这一空间就被重新解构了。
同时刘亮程笔下的空间书写十分具有特性,应当说它的空间叙事是着重表现象征意义的空间意象,而并非是现实的物质主义空间观。列菲伏尔的空间生产理论认为,土地、地底、空中、甚至光线都被纳入生产力和产物中。空间生产就如同任何的商品生产一样,是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生产出来的。这样空间就变成一种人化自然,而非自在自然。空间就不再是自然属性的,而是政治属性的。空间乃是各种利益角逐的产物,它是由各种历史性和自然性的元素共同组成的。空间从来不能够脱离社会生产和社会实践的过程,而保有一个自主的主体地位。
刘亮程的空间叙述既具有新疆本土地域广袤无垠的特点,又同时具有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过渡时期的特点。这使得刘亮程笔下的空间书写的历史性变得更加复杂,他的空间书写的象征主题主要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真实与虚幻,另一部分是交流与隔膜。很多时候他的空间书写同时具备这两种层面的象征主题,比如《本巴》中的母腹空间,或者《虚土》中的虚土庄空间,《凿空》中的地洞空间,以及在他的所有作品之中都不断重复书写的梦境空间。
虚土庄是被流沙所掩埋的荒芜一片的虚土,它不仅是刘亮程故乡的黄沙梁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精神世界的象征。虚土庄与周围的七个村庄的人都去往外地劳碌奔波,没有人的虚土庄和它周围被踩出一条一条的路,人去地空,只有静谧,沙漠吞噬的虚土庄是无限大又无限小的,是真实的,也是虚幻的,是开放的,也是封闭的。
《凿空》中的地洞也是如此,张旺才和玉素甫穷尽一生都在痴迷地挖地洞,地洞所掩埋的是他们真实的自我,作为逃避现实的心灵家园,现实中逐渐隐匿了他们的生存空间,所以他们在地洞中重新塑造虚幻的生存空间。时代飞速发展,工业社会侵蚀了被社会抛下的人们的心灵,于是张旺才和玉素甫作为这样被社会抛下的人的代表,开始了一种精神的返乡。这个地洞是他们对抗现实的一种武器和工具。作为深藏地下、不见光明的封闭空间,一方面地洞是与现实隔膜的体现,另一方面地洞给张旺才和玉素甫提供了与自己的精神交流的空间。“西部人之所以备尝离开故乡的流浪的痛楚,主要源于他们独特的生存方式和安放心灵的方式,这就是流寓的生活,以及对故乡和信仰彼岸的执着追寻。”[6]
在《本巴》里一切都是梦境空间的寄寓,本巴草原上的故事就是由梦境组成,本巴人的生活就是哈日王所造的一场梦,或者是江格尔齐口传的一个故事。现实和虚幻是没有界限的,一个人的真实生活是另一个人的梦境。洪古尔和赫兰在梦中做游戏,在梦中打仗。赫兰在作为江格尔重新出生前,在梦中消灭了莽古斯,又在梦中打仗营救父亲乌仲汉。梦中嵌套着梦,虚幻中描写虚幻,又与现实互相参照。《捎话》中的战争场景也是如此,毗沙国率领的无眠之师在白天打败仗后,会在夜晚敌人的梦境里打败敌军。“梦是我们经历的另一部分现实,人一生中一半时间在睡觉做梦,但我们不承认梦,主观地让梦变虚了。”[7]14刘亮程在访谈中说,文学就是做梦的艺术。梦境所建构的空间是一切象征性空间的母题。
三、后现代的时间叙事
在刘亮程的叙述中,时间是一个终极的尺度,他的书写把时间作为生命的本质和对象衡量。他着重表达的是生命与时间的关系。随着书写抵达的范围不同,在他的作品中生命的生存状态一定程度上体现为身体叙事,更进一步体现为空间叙事,最终是为了抵达时间叙事的深度。
在刘亮程的作品之中,生命与时间的关系可以总结为三个阶段:诞生、永恒、死亡。这一过程在《本巴》中展现得最为完整。《本巴》中还没有诞生的孩子洪古尔和赫兰在母腹中就已经开始做游戏,这寓示着他们已经具备了灵性和思想,但诞生是一个从灵性世界到现实世界的过渡,意味着生命真正的开始。从此人的理性和动物性开始斗争,现实和虚幻开始相生相长。这是一种胡塞尔所说的意识流的“内在时间”,而非经验世界的“客观时间”。
进一步地,进入永恒,本巴国的所有人都停留在年富力强的二十五岁,没有衰老也不会死亡,这是一个人类的童年最富有活力的时候,这是一个理想国,但是这样时间就失去了意义。“那里树不高长,河水不往两岸荡漾,太阳和月亮在人们的念想里发光。”[5]191洪古尔和江格尔由于长期沉迷于酒宴而失去了白日作战的能力。江格尔和其他英雄自始至终都沉醉在四十九天的青春酒宴之中,时间的永恒性在这里变成了一种“去英雄化”的手段。美人阿盖夫人的魅力也在时间的流逝之中褪去了,尽管她的肉体仍然年轻,但她的心灵衰老了,像落满了尘土。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认为“此在”是拥有时间性的生存结构,人只有在衰老、绝望、焦虑丰富的生命体验之中,才能够理解生的快乐、幸福和希望,存在是向死而生的,没有这样的时间性生存结构,永恒的二十五岁本巴家园只是一种对时间的乌托邦想象。
这最后达成了一种否定之否定的结局,本巴人厌倦了无穷无尽的青春。“人们开始渴望岁月流逝,向往三十岁、五十岁的自己。”阿盖夫人喝下那碗让人迅速老去的奶茶。从此天堂变成了幻影,乌托邦变成了一种反乌托邦。衰老的尽头导向了死亡。本巴人回避衰老,本质上是回避死亡。“时间也并不是无限的,所谓永恒,就是消磨一件事情的时间完了,但这件事还在,时间再没有时间。”[8]47“死亡教会我们的,永远是如何活着。”[9]17通过时间叙事,刘亮程探索出生命体验的内在张力,更深入地理解了生命的本真。
更深入地,刘亮程的时间叙述体现了一种后现代性的反思过程。诞生、永恒、死亡的阶段既对应着乌托邦、反乌托邦,以及重建乌托邦的过程,也对应着建构、解构与重构的过程。“后现代性正是这样,以一种反乌托邦的形式构想了乌托邦,以一种反希望的形式构想了希望,以一种反伦理的形式构想了伦理。以一种反上帝的形式构想了天堂。”[10]《本巴》中,对于本巴的乌托邦建构寄予着对于人类本真的探求,但是直到经历了永恒的二十五岁给本巴人所带来的生命的禁锢之后,这种禁锢实质上是理性的不变对身体变化的排斥,理性凌驾于身体之上变得绝对化,反而使得本真的探求变得越来越远。否定之否定之后的重构使得本巴人重新焕发生机,反而探求到了生命的本真。
在刘亮程的笔下,时间以生死为经纬,生命的过程是其中的某一个坐标。这种立体的结构模型使得时间和空间在人物的底下融合,成为一种多维层面螺旋式的叙事逻辑。在较低层面的叙事时间上,生死有时候表现为白天和黑夜。白天是现实和生,夜晚是梦境和死。《捎话》中形容:“更多的人在母腹中没有被分开,孤独地来到世上,但另一个自己却始终存在以精神分裂的形式存在。以梦中的我和醒来的我两种形态存在,我睡着时,另一个我在梦中醒来,那是我的孪生兄弟,我看见他在梦中过一种生活,他似乎也知道我在梦见他。”[4]320死连接着生,生走向死,生命延续如同莫比乌斯环。时间的叙述,在这种过程中抵达永恒。刘亮程在总结时谈道,他把时间作为一个本质而非手段去写,要写出时间的原貌。
四、结语
刘亮程书写中体现出的后现代性,更深层次表达在建构、解构、重构的过程中,也更进一步地契合了文学作品赋魅、祛魅,乃至复魅的过程。赋魅和祛魅的过程是一个诞生和死亡的过程,是QZIqvK9mvFtqlnX+3Tmb+Q==一个建构和解构现实世界理性传统的过程。在身体叙事中,呈现为对于理性排斥身体的动物性的历史传统,以及语言建构凌驾于自然声音之上的现实世界的解构过程。更进一步,在空间叙事中体现为对于现实和虚幻空间、交流和封闭空间的塑造,体现物质和精神两个维度的建构和解构。在这个过程中,理性和现实被赋魅和祛魅,而更深层次的复魅要从时间本质中寻求答案。
通过时间重构经验向天真的反归,达到返璞归真、否定之否定的境界。现代化是一个对世界的认知由多维化到被理性的科学和技术单维化的过程。在马克思韦伯的理论中,这样一种现代性的分化会导致过去的自足世界的破灭,然而,后现代性的理论中没有揭示如何创建一个新世界。刘亮程在《本巴》中通过对于时间叙事的探索,揭示了生命的自反性,由诞生、永恒到死亡是一个“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过程。
作者简介:侯雅妮(1998—),女,新疆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文艺学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民间文艺学。
注释:
〔1〕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2〕刘亮程.晒晒黄沙梁的太阳[M].乌鲁木齐:新疆青少年出版社,2007.
〔3〕刘亮程.凿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18.
〔4〕刘亮程.捎话[M].南京:译林出版,2018.
〔5〕刘亮程.本巴[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8.
〔6〕丁帆.中国西部新文学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
〔7〕刘亮程.文学是做梦的学问[J].文苑,2015(11):14.
〔8〕刘亮程.一个人的村庄(典藏本)[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13.
〔9〕刘亮程.让死活下去——读辛生散文《为褪色的时光涂一抹新绿》[J].绿洲,2020(3):15-17.
〔10〕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