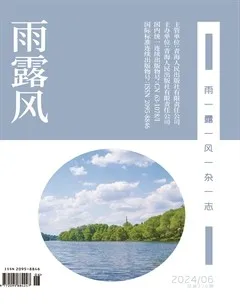刀郎《罗刹海市》的互文性分析
在当前网络媒介与大众文化盛行的境况之下,大部分歌曲呈现出单一化和同质化的特点,而刀郎的新专辑《山歌寥哉》无疑是一部别出心裁的作品。《罗刹海市》作为专辑中网络讨论度最高的歌曲,充满文学性的歌词让观众眼前一亮。作者借鉴并改写了《聊斋志异》中的同名故事,不仅赋予了其新的故事内核,同时将中国古典故事与民族音乐相结合,在传统民族文化如何与现代艺术形式融合的问题上,刀郎在《罗刹海市》中作出了创新性的尝试。
一、对《聊斋志异》的改写
(一)与《聊斋志异》的互文
“互文性”这个概念是由法国的女性主义批评家克里斯蒂娃提出来的。“互文性”也称“文本间性”,文本的英文“text”本身具有“编织”和“纤维”的意思。任何文本不可能独立存在,它是在一定社会文化、语言之上形成的产物。“任何文本都是对另一个文本的吸收和转换”,在一个文本之中可以看到其文本的痕迹,文本与文本之间相互渗透。“文本是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的产物,它至少是两个方向的交织品:从共时角度看,文本的所指又受到作者和接受者的主观性影响;从历时角度看,某一文本又与先前存在的文本有关系。”[1]某一文本可以是在对过去典故、引文、回忆等的改编和创造上形成。
刀郎的《罗刹海市》部分歌词来源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同名故事,同时也对其进行了改编,《聊斋志异》中的《罗刹海市》原文叙述的是一个叫马骥的美少年在海外经商途中误入罗刹国的故事,罗刹国中每个人都长相怪异,奇丑无比,但这个地方以丑为美,以丑的程度来划分权力等级,越丑的人越位高权重。刀郎的《罗刹海市》在其故事性的基础上增加了伊索寓言的色彩,在形式手法、意义主旨以及审美效果上,刀郎的《罗刹海市》都作出了创新。
(二)艺术手法的变化
不同于《聊斋志异》中原文的短篇小说的叙事体裁,刀郎的《罗刹海市》采用了散文诗的方式对这个故事进行继承和改写,并且在东北靠山调的基础上将歌词编得朗朗上口,并且在歌词中还使用了押韵和谐音的手法,增加了歌词的文学性,例如歌词中的“只为那有一条一丘河,河水流过苟苟营”,一丘河与苟苟营正是一丘之貉与蝇营狗苟的谐音。原文中,罗刹国的“相国”在歌词中变为了“马户”的形象,“马户”在歌词中又称为“叉杆儿”,“叉杆儿”在中国古代是对青楼老板的称呼,也是对奸诈之人的隐喻。除了运用谐音制造隐喻之外,歌词其他部分采用了押韵的手法,“哪来鞋拔作如意;它描红翅那个黑画皮,绿绣鸡冠金镶蹄”“西边的欧钢有老板,生儿维特根斯坦”两句歌词采用的押韵手法,让整个歌词读来朗朗上口,具有节奏感。从整首歌词的内容来看,大部分歌词都有很强烈的象征、讽刺意味,对文言文的使用,也产生了“陌生化”[2]的效果,让观众在接受过程中感受到阻隔性,增加了感受时延和感受难度,增加了整首歌词的可读性和含混性,歌词的背后还注入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聊斋志异》中的许多故事都取材于我国的古书《山海经》。文学艺术渗透着一个民族的精神意识,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简明富有节奏的形式,使整首歌词成为一个丰富的文学文本,将大雅与大俗融合,产生了一种雅俗共赏的审美效果,同时也引发了听众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关注。
(三)人物形象的改写
对“罗刹国”的改写还体现在人物角色的改变上,“马骥”在原文中在笔者看来是被作者加以讽刺的对象。关于“罗刹国”的描写,指向的是审美的雅俗之别。故事后半部分通过描写“马骥”借假面孔敛财的行为,塑造了一个虚伪、为财富迎合世俗的人物形象。而在刀郎的同名歌曲中,“马骥”不再是原文中曲意逢迎、为荣华富贵失去本心的形象,而只是一个经过罗刹国、窥见其中美丑颠倒的旁观者,其形象是关于作者理想的隐喻,表达的是对乌托邦的向往。“美丰姿,少倜傥,华夏的子弟”这几句歌词是对其理想的具体描述,其作为象征着真善美的符号,与“苟苟营”“又鸟”“马户”等形象形成鲜明的对比。马骥从原文中曲意逢迎、为荣华富贵失去本心的形象,变为作者借以表达美好愿望的载体。
蒲松龄《罗刹海市》由主人公“马骥”在“罗刹国”和“海市”两个地方发生的故事组成,前者在笔者看来指向的是审美的雅俗之分。原文中的“相国”虽外形丑陋,但作者并没有赋予其具体的讽刺意义,“相国”作为一个不符合“中华”审美标准的丑陋之人而存在,“双耳皆背生,鼻三孔”只是原文中对其外形的描述。歌曲《罗刹海市》中的“相国”是“苟苟营”的“叉杆儿”,叫“马户”,“叉杆儿”“马户”其词义中本身就具有贬义色彩。歌词中“两耳傍肩三鼻孔”是对讽刺对象的具象化,同时也是戴上假面具作威作福、拿鸡毛当令箭之人的象征。“又鸟”“马户”等在这里指涉的是社会中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之人,与原文中的马骥类似,这类人在人格面具的掩饰之下融入世俗,活在虚假的世界中洋洋得意。
二、叙述视角的转变
《罗刹海市》原文的叙事是以第三人称和第一人称交替进行的,全文以“马骥”游历“罗刹国”的所见所闻来展开,关于“罗刹国”的描写通过“内聚焦”[2]的方式呈现。尽管在“马骥”的视角下,“相国”“大夫”等人物外表丑陋而奇怪,但是针对其人物内核并没有具体的叙述,只是讲述了“罗刹国”中美丑颠倒这一反常现象。并且在“内聚焦”的基础上采用的是一种交换式人物有限视角的叙述方式[3]100。在“马骥”看来,“罗刹国”是一个神奇、陌生的国度,而从“罗刹国”子民的视角来看,“中华”也是如此。多视角叙事的手法,使故事具有一定的含混性,同时也给读者留下了解释和想象空间。“马骥”的视角与“罗刹国”子民的视角之间所产生的冲突性也让情节充满张力。
刀郎的《罗刹海市》从头到尾采用“全知视角”[3]100来进行叙事,全篇以一种说书人的口吻将说故事和评述结合在一起。其中的部分歌词展现了说书艺术的语言表达特色,“那马户不知道他是一头驴,那又鸟不知道他是一只鸡,勾栏从来扮高雅,自古公公好威名”“它红描翅那个黑画皮绿绣鸡冠金镶蹄,可是那从来煤蛋儿生来就黑,不管你咋样洗呀那也是个脏东西”等歌词都具有说书艺术的表演技巧,歌词抑扬顿挫,可以明显感受到歌词在声音、语调、语速上的变化。在说书表演中,说书人通过生动的语言和形象的描述,将故事中的人物、情节、场景等展现得淋漓尽致,让观众仿佛身临其境,感受到故事的魅力,产生情感的共鸣。
接下来从人物的视角叙述了主要的故事情节,叙述语言带有一定的讽刺意味,又充满了幽默气息。同时也对原文中的人物形象进行了扩展,中性的人物角色“相国”在歌曲中被塑造为反面人物,并对其人物行为、心理进行了描写,不同于原文中只对其进行了外貌描写,刀郎借用原文中形象怪异丑陋之人来隐喻现实生活中人心丑陋之人,并用俏皮的语言对其进行了讽刺。
《聊斋志异》是清朝小说家蒲松龄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其中充满了许多关于仙、神、鬼、妖等超自然题材的内容,还融入了中国民间传说中的诸多元素,独特的世界观和神秘色彩对读者产生浓厚的吸引力,是一部优秀的奇幻小说。在创作手法上也具有鲜明的特色,通过志怪手法、传奇手法描绘出奇特的超自然世界,映射出来现实世界的复杂性和矛盾性。刀郎的《罗刹海市》由于形式(歌曲)的特点,不同于传统的小说叙事手法,采用了评书的方式,全文也突出了“评”这一特点,“评书的艺术本质是‘第三人称代言体’的艺术门类”,并且评书也是以说书人的语言叙述为主,听众从说书人的口头描述中进入故事,感受人物形象。当评书中的主要人物第一次出现时,说书人会用最到位、最传神的语言对人物形象进行描述。歌词开篇用“她两耳傍肩三孔鼻”“未曾开言先转腚,每一日蹲窝里把蛋来卧”等都是对故事人物的具体描述,并且描述人物的用词非常形象,这几句歌词道出了“马户”和“又鸡”的外貌性格特点,作者的用词也具有鲜明的情感色彩,表达出创作者的观点和态度。
三、文本语境的互文性
刀郎《罗刹海市》中的第一句歌词是“罗刹国向东两万六千里”,原文是“马问其相骇之故,答曰:‘尝闻祖父言:西去两万六千里,有中国,其人民形象诡异。但耳识之,今始信’”[4]145,从歌词与原文的对比来看,这里存在着叙述视角的转变。在歌词的叙述视角中,马骥的国家是被观察的客体;原文中,关于罗刹国的经历,是通过马骥的视角来叙述的,歌曲《罗刹海市》颠倒了原文的叙述视角,原文中的转喻在这里变为一种隐喻,蒲松龄所描写的“罗刹国”是对当时环境和个人心境的替代;而在刀郎的《罗刹海市》中,被改写的第一句歌词和之后的内容采用的是一种隐喻的手法。
“问其何贫。曰:‘我国所重,不在文章,而在形貌。其美之极者,为上卿;次任民社;下焉者,亦邀贵人宠,故得鼎烹以养妻子。若我辈初生时,父母皆以为不详,往往弃置之;其不忍遽弃者,皆为宗嗣耳’,问:‘此名何国?’曰:‘大罗刹国’”[4]145,这是原文中对于罗刹国的描述,他们注重人的外貌多过人的内在,以美丑来划分等级,这其实是蒲松龄对于当时社会环境的一种讽刺,他撰写《聊斋志异》时,正是自己的人生不得志之时,面对黑暗的社会,作者的一腔抱负却难以施展。这一段文字不仅是对当时社会语境的描述,也交代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可以将其视为《罗刹海市》的文本语境。
原文中的相国两个耳朵倒过来生,鼻子有三个孔,睫毛遮住双眼,这是罗刹国认为的美,而在外乡人看来马骥是丑的,这里涉及两种视角的冲突,相国作为影射现实的一个符号,其背后所指向的是社会中权力颠倒、名不符实的现象,同时也指涉着审美的雅与俗之间的讨论。原文中的“罗刹国”象征着审美观念的颠倒,审美颠倒的预设是为讽刺马骥曲意逢迎行为作铺垫,作者的重心还是在讽刺马骥。在刀郎的《罗刹海市》中,蒲松龄笔下的“相国”变成歌词中所写的“苟苟营”的“马户”形象,随着时代环境的变迁,其背后的隐喻含义也有所变化。
首先,从作者的时代背景来看,“蒲松龄是科举制度之下落魄文人的典型,其并不完全否定科举制度本身,但却指出这一制度存在的两大缺陷:一是科举场上贪污、舞弊现象严重,二是考官素质低下,愚贤不辨”[5],在如此境遇之下,蒲松龄也希望通过科考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罗刹海市》中,主人公在龙宫受到的肯定和尊重,也是前者在现实中的期望。现实中的蒲松龄屡试未中,生活落魄,在家乡私塾以授课为生,与马骥受到的待遇相比简直是天壤之别。正因为蒲松龄在现实中的失意与怀才不遇,所以在小说中为马骥安排了一种理想的境遇,在虚幻的故事中表达对自身价值的肯定。
在现代社会的语境之下,刀郎作为艺术创作者,也有相似的经历。在大众文化主导艺术市场的背景下,刀郎的作品逐渐被淹没在流行音乐的浪潮中,逐渐被年轻一代遗忘,淡出了观众的视野。其艺术创作与现今大众的审美取向存在一定距离,刀郎虽多次获奖,但在流量当道的网络社会中并未完全取得大众的认可。其审美理想也在现实中受到否定,借用《罗刹海市》作为其创作的蓝本,实现了借古讽今的目的。当代大多数艺术作品呈现出一种无深度、快餐式、同质化的趋势,传统文化与流行艺术之间存在冲突,前者与后者的融合也是一大问题。“流行文化”这个舶来品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在流行文化对观众的审美取向的巨大影响下,传统文化的艺术创作如何突围,刀郎的《山歌寥哉》无疑是一次有效的尝试,将现代的艺术形式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在具有文学性的歌词之下传达了其本人的审美理想和对社会的批判,讽刺了黑白颠倒的现实。在网络上引起的热议,以及源源不断的解读和讨论也是对作品本身的肯定。《罗刹海市》以音乐的形式使听众获得一种审美享受,又在内涵丰厚的歌词之中传播着中国的传统文化知识,发挥着针砭时弊的功能,从以上方面来看,刀郎创作的这首歌无疑是对“兴、观、群、怨”理论的一次完美实践。《山歌寥哉》专辑中大部分歌词是具有悲剧性和现实性的,《罗刹海市》对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了讽刺,通过隐喻的方式反映了黑白颠倒的社会现实。并且借用大量的对比、反讽的手法对社会中存在的种种弊病进行剖析和批判,对虚实颠倒、真假难辨的“异托邦”极尽嘲讽。刀郎与蒲松龄虽所处的时代不同,但二者在实现理想的道路上都受到了现实的阻隔,现实与理想的背离也让他们试图在虚幻的艺术世界中追寻心目中的乌托邦,并且依旧怀有对人类文明的希冀,表达出向真、向善、向美这一永恒的艺术主题。
四、结语
《山歌寥哉》整张专辑的大部分歌曲都取材于《聊斋志异》中的故事,在原有的基础之上,前者用不同的艺术形式改写了中国传统神话故事,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作品。在被同质化审美裹挟的时代,《罗刹海市》的出现也让观众眼前一亮,传统故事与现代艺术形式的结合,不仅为听众带来独特的审美体验,也在歌词的叙述中直指社会的灵魂深处。
作者简介:李园娜(2000—),女,贵州贵阳人,文艺学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文艺美学。
注释:
〔1〕童明.互文性[J].北京:外国文学,2015(3):86-102,159.
〔2〕伊格尔顿.20世纪西方文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3〕朱立元,李均主编.20世纪西方文论选(下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4〕蒲松龄.聊斋志异[M].北京:中华书局,2009.
〔5〕栗亮.从《罗刹海市》看蒲松龄的人生理想[J].蒲松龄研究,2011(2):75-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