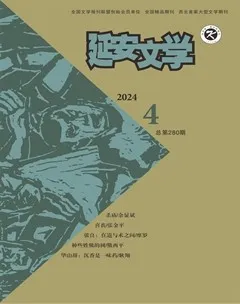被遗忘的生机终于走出我的视线
一只鸟的跌坠
猎人走在山路上,肩上的枪口对着身后的树林。鸟声远去,猎人的嘴微微地张开,呼出一股又一股热气,把松林走得躁动不安。山路在松林里左拐右拐,猎人的皮靴踩在凝结的霜花上,溅起的冰屑把寒冷的晨光撞得四处躲藏。松树上落下一滴一滴的油脂,里面折射着远处一只鸟在脚步声中惊慌飞起的翅影。飞鸟从一棵松树的枝头上飞起来,刚要到达另一棵松树枝头,猎人手里的枪发出震撼山谷的响声。几片羽毛从空中轻轻地飘落到山洼里。
飞鸟艰难地挣扎着,落到一个庞大的荆棘丛里。
一只鸟的一去不返,没有改变山谷里的一草一木。鸟的翅膀在寒霜里拍打着,在渐渐失去温暖的巢穴里拍打着,它的身后还有几个比它更幼小的鸟儿,那黄色的嘴角,还没有长成黑色的喙。一只幼鸟在巢的边沿叫唤着,一不小心就从高高的鸟巢失足跌落下来,那跌跌撞撞的样子,与它的母亲在枪口下的跌落极其相似。
迅速下坠使它在惊惶失措中张开了稚嫩的翅膀,拍打着不断向上涌来的气流。它的沉坠因此没有撞在坚硬的山坡上。当它斜斜地掠过一丛又一丛灌木,它发现了惊慕已久的姿势。也是这个不是很成熟的姿势,使它在扑倒的时候,没有被摔伤。黑夜很快到来,鸟儿再也没有了栖居的巢穴,横斜的枝条不断地遮住它向着鸟巢仰望的视线,只有天上的星星围拢在月亮的身边,倾听着大地上传来的歌声。寒霜很快打湿了它身上尚未出现的光泽的羽毛,它不敢大声呻吟,任凭严寒浪潮一样汹涌而来,敲打它,撕扯它,淹没它,把它冻僵,然后无情地将它推向死亡。
第二天的太阳在正午的时候发现草丛里冻僵了的鸟儿,惊奇地注视了很久,无意中的温暖让鸟儿苏醒过来。它睁开眼睛,艰难地伸长疲惫的脖子,寻找可以让它的生命在失去巢穴后的支撑与依靠。一只冻死在树枝上的蜻蜓,缘分一样悬挂在它身边,于是它艰难地站起来,一次又一次扑腾着,让虚弱的身子暖和起来,艰难地飞起来,把蜻蜓塞进空空的嘴巴,然后从空中再一次跌落下来。一只死亡的蜻蜓让鸟儿在阳光下站起来,在果实、草叶、蚯蚓、蟋蟀的残骸中,它度过了一个又一个没有让它冻僵的夜晚。又一个清晨,它在山坡上飞起来,从一棵树到达另一棵树,从低矮的枝头到达高高的枝头,过早地进入了属于它的天空。翅膀扇动着空中的气流,它终于看见了峡谷里绵长的山脊,看见了远处洁白的雪山。
它回到了它曾经跌落下来的鸟巢。几只小鸟,失去了生命的迹象。一群蚂蚁一路爬过来,带走了还没有被阳光灸烤过的羽毛。悲伤的童年躺在眼前,一个巢穴记载着一场经历,把鸟巢的残破呈现给飞翔的翅膀。鸟儿衔来树枝,铺在那些残存的羽毛上面,开始孤独地生活与飞翔。太阳一天天升起,雪山的反光把山崖照得一片光明,晨光与暮色把鸟儿托举着,赠送给它一个长满了松树的山坡。风声一手制造的浪涛推动着松枝不停地摇摆着,每一天的飞翔都给鸟儿带来新的喜悦,也许它已经在空中渐渐忘记了它在黄昏前的跌落。它每一天都准时回到它的巢穴,望着远处的雪山开始一个又一个的梦,对着充满了水声和风声的峡谷想象着它的爱情。
春天到来的时候,松树把头向着更高的天空欢快地伸展着。鸟儿展开宽大的翅膀一次次掠过低低的山脊,寻找曾经对它许下终身相爱诺言的鸟儿。它在天上高声地呼唤着,旋转着,把梦境中的誓言一遍又一遍地向着峡谷里所有的枝头宣读。两扇宽大的翅膀飞抵它的身边,围绕着它的轨迹,跟随着它回到山崖上的鸟巢,增添的鸣叫,让整个山崖充满浓浓的诗意。遥远的雪山收起了明亮的光芒,扯过一片云彩,隔离了对山崖的眺望。从此,山崖上的夜晚重新温暖起来,在一个古老的鸟巢里,一对生命鼓励着一只鸟把坚硬的喙伸向另一只鸟坚硬的喙。于是一窝新的生命又诞生了。
一窝新的生命如约而来,柔软的羽毛不断地在巢穴边沿生长着,张开了嘴巴迎接飞翔在外的鸟。秋天的峡谷里到处落满果实和种子,鸟的翅膀盘旋着一片繁忙。巢穴里的一群嘴巴,发出兴奋的鸣叫。黄昏到来的时候,鸟嘴里带来一些树叶和羽毛,把鸟巢铺得温暖如春,最后一次飞出去寻找食物,枪声在这时候响起了,几片羽毛从它的身上落下,它挣扎着无可奈何地扑向一片沼泽地。在坠地之前,它一直放心不下的是那山崖上的巢穴,以及巢穴中饥饿的嘴。
没有谁会想起猎人不断举起的枪口。
逃遁的叶子
核桃树在春天里开着一串串淡黄色的花,在金沙江的流水声中,核桃花慢慢地落下来,被一群猴子捡起来,放进嘴里,吃下去。峡谷里的一个山坡上森林正在消失,童话一样悄悄地消失。一群人在夜色里走进森林,把树木砍倒在山坡上,经过一个深深的山谷,把木头送进江里,让江水浮着巨大的木头,漂到遥远的不知名的地方去。猴群就在这时候到来,居住在村庄外面的核桃树林里。
猴群,它们在核桃林里跳动,一串淡黄色的核桃花在风中落下来,映在它们的瞳仁里,勾起了它们的饥饿。村庄里干燥的巷道,炎热的空气把它们一次次地拒绝在进村的石头丛中。两只猴子,以它们白色的长毛成为猴群中一个单独的群落,两只猴子不停地跳动着,寻找它们曾经失去的家园。春天正在过去,核桃花从树上落下来,落在树下一条浅浅的沟渠里,无声地向着不远处的金沙江流去。
猴群在路过村庄的时候,被一个耕地的村人发现,消息在村子里洪水一样沸腾着。白色,白色,白色,猴子的白色传遍了整个村庄。猴子的饥饿没有被人发现,它们在村庄附近的行走与逃窜,为了寻找到一片茂密的森林。
猴群所居住着的山坡,石头反射出太阳的炽热,荒草低下了头,山坡开始裸露出红色的土地和黑色的石头,只有对岸的森林,让猴群一次次越过村庄边的玉米地,在夜色降临的时候,站在江滩上,抬起头来发出一声声嘶叫。
春天正在过去,食物正在森林的消失中不断地消失着,饥饿感正在猴群的肚子里翻腾着。猴群的白色,被村庄里居住着的人时时惦记着,屋檐底下放着绳索与猎枪。一条路在江边的一块巨大的岩石上被断开,岩石高高地架着一座桥,粗重的铁链伸向对岸,铁链上铺着厚厚的木板。猴群每天晚上都对铁链桥充满了向往。向往着那江对岸的森林,向往着那森林中茂密的树枝,向往着弯曲的树枝上新鲜的嫩芽,向往着嫩芽旁边一天天成熟的野果。
金沙江水一直在流淌,对面山坡上茂密的树叶倒映在江水里,一片生机。逆流而上的江风吹过森林,绿色的树叶一轮一轮地在翻动着,如同绿色的江水漫上了山坡。猴群在光光的山坡上想象着对面森林里幸福的生活。深深的草丛里不停地生长着深黄色的蘑菇、疯狂歌唱着的雉菊、望着天空畅想的野葵花,一条背上长着暗红色斑痕的蛇从草丛里爬过来,吐着黑色的信子,悄悄地钻进另一片草丛,拨动了草尖上迷宫一样的蜂房,成群的蜜蜂飞起来,寻找贸然侵入的敌人。一棵橡树高高地笼罩着草丛边的土地,风吹过,往年落在树杈上的橡子随风而落,坠在树根上,发出轻微的响声。橡树旁边长着一片山茶树,冬天过去后,野茶树上长满了暗绿色的茶果,在椭圆形的叶子中间显得十分诱人。猴群空守在江边,村庄守在猴群与森林之间,森林里的一切,都与猴群无关。
猴群每天都守在江边不停地嘶叫着,它们从很远的地方跋涉而来,沉重的饥饿,使它们找到了一片茂密的森林,村庄的阻隔,使它们必须忍耐一天天强烈的渴望,人们对白色猴群的好奇,使它们一次次在相机闪光声中和枪声中逃窜。日子带来的饥饿给猴群的眼神抹上了一层失望,猴群等待着夜色的到来,等待着在月色中寻找另一片土地。一路上它们要路过多少荒坡,又要经过多少村庄,它们肯定不知道。
往事覆尘
火光冲天。牛角对着前面的旗帜,鼓起腮帮吹着。一个个身影纷纷跃出壕沟,手里举着火光四射的火把,把高高的门楼照得分毫毕现。手握牛角的人,身后是一片开着鲜艳花朵的罂粟地,一群少女站在他的身边,惊恐的眼神注视着前方那箭簇纷飞中不断倒下的汉子,她们把手指不知不觉地咬在嘴唇间,不敢对血泊中不停翻滚的人说一句话。牛角一直在吹响,冲锋的人,一个个死去,另一些人手里紧紧握着刀柄,高高地举起,砍在敌人的背上,血飞溅起来,染红了握刀的手和喷火的眼眶,踩倒了散发出浓烈香气的罂粟花。牛角号召着举着火把的人,赤身渡过漆黑的江流,穿过纷乱的礁石,掠取门楼紧闭的城池,赶走一群人,夺回了自己曾经失去的家园。
战火燃烧着结满时间的草绳,高山与峡谷屏声静气地倾听着。牛角在危崖上飞过叶子宽大的树林,呼唤着每一个坐在茅屋里围着火塘喝酒的人,用一根麻布在额头上挽一个粗大的结,拿起长枪就走出门外,接过一支火把,飞奔到寨门前高高的土墙上。雪亮的长枪靠在墙垛上,铁弓被搭上毒箭,拉成一轮满月,向着冲到墙下的人射击。酒气在火光中呼出来,弥漫到每一个人周围,激起无穷的力量,举起放在脚下的擂石,掷下去,让一些人在血肉横飞中魂飞魄散。月亮失去了往日的光芒,山影庞大无比,牛角的浑厚激励着的汉子,把生命挥舞成一面旗帜,死守一方疆土。
烟消云散。太阳炙烤着江边的土地,身背牛角的人走在江滩上,腾空而起的浪花,溅湿了他腰间的牛角,溅湿了他长满了厚厚老茧的脚掌。女人们身穿黑红相间的长裙,弯腰收割梯田里的罂粟,花香沐浴着她们的裙裾,蓓蕾贴近她们柔软的腰肢。女人们抬起头来,看见了走在江滩上的人,向他微笑着招手,从陶罐里倒出一碗水,送过去。递过去的木碗,水面上映照出一张羞涩的脸,江滩边畔的山路上,渐行渐远地响起山寨里世代相传的情歌:
啊妹妹,哥有情来不好说么,笨如牛角喽!
哥随马帮走远方么,再难见面喽!
啊妹妹,哥是一个赶马人么,四海为家喽!
今天回来一匹缎么,送到你家喽!
啊妹妹,你家阿妈莫收下么,赶我出门喽!
明天又要出远门么,想死妹妹喽!
啊妹妹,你如对哥也有意么,听我一句喽!
今天晚上凤凰树么,哥在等你喽!
身背牛角的人一步一回头地离去,水光照着他的背影。有人在目送他消失在竹林后面,潺潺的目光打湿了那些远去的脚印。夜色笼罩着整个村寨,凤凰树下有两人始终不愿离去,凤凰花无声地落下来,覆盖了温情脉脉的誓言。鸡鸣的时候,两行泪拴住了一颗心,开始默数一段山高水远的行程。
心爱的牛角被悬挂在屋檐下,马蹄声又将在村寨门口响起。战火熄灭了,一条路把一群人的脚步引向遥远的地方,带走茶叶、丝绸、食盐、药材,也带走了一个女人站在罂粟地里的思念。等到某一个谁也不曾意料到的日子,那一群人才会在深夜里赶着马群回到村寨,坐到茅屋里的火塘边喝上一碗酒,把心里的一团火浇了又浇,却总会有一种不能隔夜的想念在胸中跳跃着,使他不得不站起身来,向着一棵高大的凤凰树走去。没有了战火,牛角只能系在腰间。牛角贴近被酒气烧着的嘴唇,一股气流轻轻地从小小的孔隙里穿过去,没有战火纷飞时的激越,神圣的牛角,只有在维护村寨命运和荣辱的时候,才能被吹响。
凤凰树下的夜色,一只牛角陪伴着一个人,把孤独的夜晚守候着,无声无息。坐在凤凰树下的人,曾经手里握着寒光闪闪的长刀,背上背着坚韧不拔的铁弓,冲破许多围攻上来的敌阵,却不能把一个穿着黑红相间长裙的女人拥在怀里。
战火远去了,村寨门前的高墙在风吹雨打中渐渐地倒塌了。山坡上的一间茅屋里炊烟袅袅升起,一个老人坐在火塘前,脚下放着一杯酒。牛角悬挂在床头边的墙壁上,火塘里的烟雾一天天升起来,绕过牛角渐渐暗淡下去的光泽,仿佛要忘记一段历史,忘记一段无数次被唱起的情歌。酒意升腾,酒意沉浮,茅屋渐渐忘却了牛角曾经猝然响起的嘹亮与惊心动魄。黑红相间的长裙,自从最后一声情歌在江滩上唱起之后,离开了一扇低矮的土门,在遥远的地方为另一个人寂寞地绽放成一朵野花,被风吹雨打着,从此再没有回到凤凰树下的消息。老人在火塘里添了一根从山里砍来的柴禾,让火塘里的光芒更明亮地照耀着真实的世界。他走向一张窄窄的床,躺下去,进入一个让他年轻的梦境,让他微笑的世界。牛角无声。
路上饥寒
雪花飘荡着一句沉默的呓语,树林低着头注视着一个梦。溪水浮着冰块一路向山下流去。没有鸟的影子,一声树枝断裂的声音远远地传来,仿佛一声轻轻的叹息,把一间木屋紧紧地包围着,不放过缭绕在低矮的天空里的炊烟。
清晨到来,木屋从雪花的覆盖中醒来,紧闭着的窗口,关住所有的秘密,关住所有的脚印。水声隐隐约约,雪花隐隐约约,天堂的消息被隔断了,只有匍匐在石阶上的枯草,潮湿的叶片,洇湿了石阶暗绿色的纹路。木屋垂下自己的头,屋檐就成了一个迈进晚霞的老人,无奈地等待着一个结局的到来,进入另外一个世界。高高的山峰,默不做声地把雪花不停的压迫当成无法改变的命运,山坡上的木屋,守着它一直守望着的森林,倾听着树枝在雪花的重压下一次次断裂。
太阳把雪花的降临当作是与己无关的事件,高高地望着不敢说话的高山与峡谷,没有稍作停留,回到了它自己的地方,留下一个无声的世界。木屋在森林的边沿处,苦苦地等着雪花的压迫早些过去。走在雪地上的人,手里拿着一个被冻结了的饭团,慢慢地啃着,在雪花的围困下向着木屋行进。木屋从来不曾拒绝过任何一个路过森林的人,只是一条路在雪花的覆盖中展现出一种艰辛,拉长了一条路对脚步的考验与挑战。饭团从嘴唇抵达牙齿的时候,给牙齿带来了寒冷,到达肚腹的时候,给肚腹带来了寒冷。但是走在雪地里的人,他只能把仅有的一个从很远的地方带来的饭团作为能够给他的胃补充能量的食物,艰难地吃下去,虚弱地抵抗雪花在森林里给他带来的摧残,支撑他寻找到让他可以住进去取暖的木屋。
马尾巴在前面垂直地拖到雪地里去,沾上了雪花,一股一股的热气从马背上飘出来,刚要飘到跟在它身后的人面前,却被雪花带来的寒冷给阻隔开了。走在马匹后面的人很想拉住他前面艰难地行走在雪地里的马尾巴,但是,马背上驮着重重的货物,深深的雪地使它在山路上的行走,异常地辛苦,每走一步都会从鼻孔里呼出一股粗粗的白气,让走在它身后的人闻到一股青草和汗水相混合的气味。马蹄在山路上不止一次碰到坚硬的冰块上,发出沉闷的响声,还要一次次跨过那些横在路上的被雪花压断后落下来的树枝。走在森林里,不断有树枝被压断,带着覆盖着的雪花,轰然落在地上,发出惊心动魄的响声。
山岭一转,木屋就在眼前了,门前堆着厚厚的雪花。没有人愿意在鸟儿都停止飞翔的时候,走出屋子来接受雪花的凛冽与苍茫。马匹带着一个人在清晨到来,没有惊动任何人,连院里瘦瘦的桃枝都顶着雪花一动不动站在那里,没有因为一个人和一匹马的到来发出一丝轻微的颤动。卸下马背上的货物,人一侧身就进了屋,脸上堆满讨好的微笑,诉说一路上雪花对行程的阻挠,诉说木屋对筋疲力尽者的召唤。木屋里没有一个人说话,依旧围着房间中央燃起的火塘坐着,被火光映红了的脸上,面无表情的目光注视着在柴禾上不停舞蹈着的火焰。只有其中一个人往边上挪了挪,让出了一个位置,让他坐下去,围着火塘取暖。
雪花在眉毛上融化了,顺着眼眶流下来,流进他的嘴里,满是路途的汗水凝结的味道。空气中飘散着茶叶被火烘烤着的味道,一个黑色的陶罐里放上一撮茶叶,放在火塘边烤着,人间的气息在屋子里弥漫,让他忘记了雪地行走的寒冷与孤独。茶叶被烤黄了,被冻结了的猪油又放进陶罐,开始发出吱吱的响声。火塘里的一只被烟火烤成黑色的铜壶里的水缓缓注进陶罐,发出响亮的声音。人们依然没有做声,目光注视着那黑色的陶罐里沸腾的茶水,茶水被一只骨节粗大的手倒进火塘边散乱摆放着的瓷杯里。淡黄色的茶水,与原就盛着的茶水相混,味道特殊。一只只手伸向茶杯,慢慢品着苦味、辣味、咸味、香味。雪花带给森林的寒冷渐渐退到屋外,像幽灵一样悄无声息。所有的人都不说话,他们从来都是陌生的,在小屋里,粗粗的木头搭建起来的屋子,总会在一个不确定的日子接待着一群从不认识的人,从山路上到来,从山路上离开。不曾留下一句话,也不会有任何动人的故事情节。
马匹留在屋檐下,圆圆的眼睛一直往屋檐下小小的窗口里望。没有一个人出来对马匹给予一个小小的亲热的举动,它不停地刨着蹄子,打着响鼻,想要说些什么,只是没有人出来,只好在地上寻找可以裹腹的干草和落在地上的玉米秸。雪花一直在不停地飘落,树枝被雪压断时发出的声响不断地传来,依旧还很遥远的路程,使它感到非常地不安。坐在屋子里的人没有发现马匹的表情,他坐在火塘边,贪婪地喝着茶杯里有限的茶与酒混和的饮料,与小木屋的主人商量着买一些路上吃的食物。主人打开墙脚下的一个黑色的木箱,让他看里面仅有的一小袋玉米面,无神地望着递过来的钱票,把玉米面又放进了木箱里去。他叹了一口气,收起了自己仅有的几块钱,眼里充满了浓烈的失望。火塘边上的几个人看着两个人小声地讲话,都没有做声,各自喝着越来越少的茶水和烈酒,想着即将开始的山路,以及路上飘飞着的雪花。
一匹马,一个人,走在雪花纷飞的山路上。木屋渐渐消失在背后,让人对那淡淡升起的炊烟充满了怀念,前去的一群人和一群马给他留下了杂乱的脚印。太阳都跟他们去了,被雪花覆盖着的山路向峡谷伸进去,一双眼睛眯起眼睑,望着远远的山脊,心情沉重。一双手紧紧捂着胸前的布袋,里面装着从木屋捡来的土豆皮——火塘里烤焦后剥下来的土豆皮。
责任编辑:杨建
陈洪金,云南永胜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十月》《长城》《清明》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