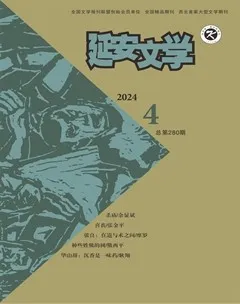母与子
立春过后,冰封的土地悄悄地开始解冻,一天天变成了深黄色。山峁上、圪梁上、沟渠里的树和草还没有绿,山下的河水还结着冰,站在山坡上可以模模糊糊望见对面半山腰上密集的窑洞和房屋。他家的院子就在对面的半山腰上。他总盼望着清明节,等到了清明,也许母亲就会来看他。
他不记得在何时才预感到死亡已经离他不远,他就要永远离开自己生活了五十年的人世间。他再也吃不到妻子烙的焦黄香脆的葱油饼,女儿做的红烧肉,还有母亲做的手擀面,或是偷偷留给他的一点儿外甥侄子侄女们为母亲从馆子里买回的好饭好菜。瞧瞧,他这么想就好像他活了五十年只是为了那一口吃的喝的。可不,庄稼人活了一辈子苦了一辈子,可不就是为了吃喝?可直到他被病痛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他才顾不上再去稀罕什么吃喝了。
清明节这天,天上下起了雨,风把雨水的气息吹得漫山遍野,一直吹进了他的墓穴。他闻到了新鲜的泥土和花草树木清新鲜活的味道。山坡上的树和草泛着清脆的绿,柳树上的山雀叽叽喳喳地叫,不远处有妇女领着孩子挎着柳条编织的筐子蹲在山坡上和荒草地里捡地软,就像小时候母亲领着他一样。
兄弟姊妹还有孩子们都来了,他们跪在他的坟前上香、烧纸、磕头,对他说了些话便拍拍裤腿站起身。他从人群中找了半天都没找到母亲,他突然想到,他走时母亲已痴呆并半身不遂,也许她至今不知道她的大儿子已故,又怎么可能来到山里看他?
最后一次看到母亲是在他去世前的那天中午。那天天气晴朗,太阳暖洋洋的。病痛使他蜷缩着身子侧躺在母亲屋外破旧的棉布沙发里晒太阳,他的肚子肿胀得像口大铁锅,癌细胞已经在他身上扩散。母亲就坐在他斜对面的轮椅上。她的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斑点和褶子,太阳照着他,他望着母亲,她头顶的太阳光让背后的屋檐遮挡了大半儿,只有双腿露在太阳光里。疼痛弄得他忍不住哼哼唧唧呲牙咧嘴。他瞪着母亲,喊她:“妈,妈,我疼。”他看到母亲只是呆头呆脑地望着他,不一会儿就把头转向一边儿了。他疼得满头是汗,额头的汗珠子流进眼窝里,他又尝试着喊叫道:“妈呀!妈呀!”就好像母亲明明可以救他,可她却偏偏稳稳当当地坐在轮椅上,只是睁大了眼睛看着他。他咬牙切齿,大声吼叫。他忽然明白母亲不再是以前的母亲了。要知道,他是母亲最疼爱的儿子。可是如今,母亲却像是不认得他了,自从她不久前在院子里跌了一跤后就变了。
他回到自己窑里,他的窑挨着母亲的窑,他跟母亲在这座院子里住了五十年,从他出生到他死的那天,他从没有离开过母亲。他没脱鞋就躺到炕上,窑里死气沉沉的,光线很暗,窗户纸旧得发黄,白色的墙壁早已被烟熏黄。他躺在炕上,觉得眼前越来越黑,呼吸越来越难,还总觉得眼前有黑影子飘来飘去。他最后一次在心里叫着,妈,妈。
不记得他在炕上挣扎了多长时间,后来他终于感觉不到疼,又像是从炕上飘了起来。不一会儿他看见儿子从门里进来,他叫了一声爸,并说:“睡觉又不盖被子。”儿子边说边走到炕沿儿边,从炕头拉了一块被子盖在他身上,儿子正打算为他脱鞋,忽而又抓起他的手腕摸了摸,顿时脸色惨白。接着又颤巍巍地把手指轻轻放在他鼻孔前停留了好一会儿,他便听见儿子趴在他身上大哭大叫,眼泪哗哗地流。不一会儿,他的妻子、女儿,还有弟弟妹妹们都从门里进来围在他身边又哭又嚎。这时他才知道自己死了。
几天后,他被埋在了河对面的后山上。村里人都说他的丧事让孩子们办风光了。柏木棺材,蓝红黄棕绸缎寿衣,被子、褥子、袍子、褂子、裤子一样不少。灵棚就搭在院子里,请了吹鼓手吹吹打打了好几天。他算是躺在棺材里风光了几天。那几天,母亲一直没露面,他想家里人一定都瞒着她。就像他们当初瞒着他跟母亲,说他患的是小病而不是肝癌一样。
就这么走他心里实在难受,总觉得他不能就这么离开母亲,他还没跟母亲好好告别呢。
清明过后的一个晚上,他悄悄地溜回家去,站在母亲的窑门口。他本想再往窑掌心的炕沿儿上走近一点儿,可没等他靠近便被母亲含糊不清的呓语惊得不敢再往前,他怕自己影响她,害她睡不安生,便只好远远地站在门口望着她。
母亲痴呆后,他的弟弟妹妹们轮流照顾她。母亲起初话也说不利索,上下嘴唇也不对称,下嘴唇斜歪到一边儿,嘴巴总也合不拢,像开了一道细口子。她一侧的胳膊和腿也不会动,意识一会儿清醒一会儿糊涂。他们每次来总会先问她,妈,认得我不?
这天轮到二弟来照顾母亲,二弟把头探到母亲面前问:“妈,认得我不?”
母亲呆呆地看上半宿,然后垂下眼帘嘴里哼哼唧唧了几声再没说话,老二摸了摸后脑勺嘀咕道:“糊涂着哩。”
轮到三弟来时,三弟也凑上来问:“妈,我是谁知道不?”母亲白了老三一眼没吱声,好像陷入了一种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朦胧意识里,她的目光呆滞了片刻便转向别处去了。
当三弟把买来的猪肉拿出来放在案板上打算切肉时,却听见母亲自顾自地嘟囔:“你爱吃肉就给我做肉吃。”
三弟回头问:“妈,我是谁?”
母亲撇撇嘴不屑一顾地说:“三娃儿!”
母亲这回认对了,小时候家里穷,平时根本吃不上肉,总要等到过年母亲才会杀猪宰鸡,把它们拿到集市上卖了,只给家里留下一点儿。三弟小时候身体瘦巴巴的,可脑子机灵,他总是趁着大伙儿出去干活,自己偷偷从碗里夹几片肉放在玉米窝头里一起蒸热了吃。
四妹脸红扑扑地走进院子,掀起门帘一屁股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她把鞋脱掉,一边揉着脚一边扭头看母亲,刚想张嘴问便被母亲拦住。
“小女娃。”母亲含含糊糊地说。
四妹瞪大了眼说:“咱妈一点儿也不糊涂!”
他记得四妹的脸从小就红扑扑的,那是小时候经常被他跟母亲背到地里让太阳晒红的。
有那么一阵子他总觉得母亲像是完全恢复了。
总算轮到他的妻子伺候母亲了,他想,看到妻子,母亲一定会想起他。要知道,他生前是母亲最疼爱的大儿子。
妻子五十三岁,大他三岁,母亲常说女大三抱金砖。妻子穿一件别人穿过的黑褐色翻领毛呢外套,头发盘在脑后,呆呆地站在母亲屋里的灶台边上,双手交叉拢在腹前,眼神呆滞。她总是看上去有点儿憨憨的,母亲总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因为别人也总说他是个半憨憨。妻子还是母亲当年托了远房亲戚介绍的。他们结婚前只见过一面,她就嫁过来了。妻子那会儿扎着两根粗辫子,穿一件绿格子布衫,高个子,大长脸,人也很壮硕,他一见她就喜欢上了。母亲也喜欢。他对母亲说,就要这个。母亲问了媒人要多少彩礼,人家说要二百。母亲犯了难,看他一心喜欢,就把当时家里的那头猪给卖了,又跟街坊四邻东挪西借才凑够了结婚的钱。
那时,父亲早已过世,母亲一个人拉扯着他们兄妹四个,他早早地就辍学回家跟着母亲下地干活儿。他个头儿高,力气大,背上扛一大包洋芋蛋子也不觉得累。他家的地好大一片,地里每年都种上谷子、糜子、麦子,只留一点儿种菜。母亲总说粮食就是他们的命。
妻子一早就开始和面,擀面。早上太阳照在窗户纸上时,她便在灶膛里生起了火,又把锅碗瓢盆弄得叮叮当当响。母亲一个人坐在门口的沙发上发呆,她的脖子上挂着一只手掌大的花布兜。快到中午时妻子的饭才做好。她从热气腾腾的锅里捞出面条,他生前也总是最爱吃面条。一大碗手擀面就着几颗大蒜,他几筷子就能吃完。有时弟弟妹妹也会从外头的馆子给母亲买回一碗肉丝炒面,或肝子盖面。母亲总会吃一半然后对他们说:“太多哩,吃不完,留着下顿吃。”然后他们看见她把面条挑出一半放进柜子里。其实他们都知道那是母亲留给大哥的。等他从外头捡破烂回来,母亲就会站在门口喊他:“留儿!你来。”等他进到母亲屋里,她便把放进柜里的半碗面拿到他面前让他吃。
对他和母亲来说,饭馆里买回的都是好饭好菜,因为他跟母亲一辈子都舍不得花钱下馆子。
母亲吃了半碗面条就不吃了。到了下午,她又拉进了裤子。妻子为母亲脱了屎裤子,把身上擦干净,又把脏裤子洗了,她总是一边干活儿一边抱怨。
“臭死了!脏死人哩!你儿子女儿在,你咋不往裤子里拉?”
窑里果真臭烘烘的。母亲像个犯了错的孩子,呆坐在沙发上噘着嘴一句话不敢说。妻子把一切收拾妥当,站起身时发现自己的衣角上也粘上了一点儿屎,她又抓起自己粘了屎的衣角,凑到母亲眼前,气鼓鼓地说:“你看看,你的屎都把我的衣服弄臭哩!”
母亲还是不说话,她低着头像一名学生在听老师训斥似的不出声。他猜想母亲此刻一定觉得有些委屈。看到妻子衣服上的屎,他想起自己第一天上学的事。
他只上了一天学就再也没去学校。那天中午吃过饭,他蹲在学校外头的茅房里拉屎,茅房搭在学校院子外的半山坡上。茅坑是一个嵌在土坑里的圆桶,桶上搭了两块窄木条,他的脚踩在木条上,撅着屁股,哼着酸曲左摇右晃地拉着屎。等他拉完屎出来,与他同班的一名满身屎尿味的同学告诉他,他的屎拉到他身上去了。同学拽着他,又喊自己父母一起去了他家。到家才发现母亲不在,他们便站在他家院门口等。他知道母亲一定在地里,正暗自高兴以为他们等等就会走,可没想到他看见母亲背上扛着一麻袋洋芋正从坡底往上走,一抬头就看见站在院门口的人。
“看看你儿子干的好事,把屎往我们孩子身上拉!”同学的母亲指着自己孩子身上臭烘烘的衣服对他母亲说。
母亲有些不知所措,她看了看他,他在一旁红着脸喘着气梗着脖子不说话。
“是不是你拉的?”母亲问他。
“不是。”他说。
“就是你拉的!”同学说。
“你拉屎了没?”母亲又问他。
“拉了。”他说。
“在哪儿拉的?”母亲问。
“在学校的茅房里。”他说。
母亲转身看了看同学那家人,微笑着说:“兴许是误会了。”母亲正要继续往下说,却被同学父亲打断了。
“别想抵赖,还不承认就找学校,找村委会!”
“就是,谁不知道你儿子脑子有问题,是个半憨憨?”
他看见母亲顿时脸色突变。
“你们不能这么说我儿子。”他看见母亲急得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他只觉得冤枉,实在想不明白自己明明蹲在茅房里怎么就惹上茅房外的事儿了。后来,母亲还是从柜子里挖出一碗豆面给了同学家,这才将他们打发走。从此以后他再也没去过学校。
妻子照顾母亲有一周了,母亲的病情在逐渐好转,她几乎可以自己吃饭,可以被人搀扶着下地走路,也可以认人了。可母亲从没有提到过他,他为此很难过,心想难道母亲已经忘了我?他总在想,如果他站在母亲面前,她能不能认出他。在母亲心里他究竟是怎样的人,难道也是个憨憨?
四年前他第一次在医院醒来,看见弟弟妹妹、儿子女儿、侄子侄女们一大家子人围着他,他们眼圈红红的,有的还在抹眼泪,有的因为哭得厉害在清鼻涕。他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哭得这么厉害,他看见自己身上插了两根管子,一根插在肚子上,还有一根插在撒尿的地方。看到管子他大概明白他们为什么哭得这么凶了。他想大概是因为他们生病时谁的身上都没插过管子。
他问自己得了什么病,他们说身上长了个囊肿给割了。可后来回到家他又听六岁的大孙子说他看见他的肝被切下来一大块,就放在病房地上的塑料袋里,深褐色的,一大块儿,泡在黄色的水里。家里好多人都看见了。他那时想,要是真的肝子被切下来,那人还能活吗?
他当然没有信大孙子的话,不然就不可能比医生估计的时间多活了几年。出了院,他照样天天上山下沟,走街串巷。早上两手空空地出门,等到晚上回来,他准能扛回一麻袋捡来的废品,有矿泉水瓶子、饮料瓶子、报纸、衣服、鞋,有时还有家用电器。有一次他就捡到过一台小型电冰箱。那冰箱拿回家来被他大儿子鼓捣了一会儿,插上电竟然可以用哩。
本来他也许还能多活几年,说不定更长。可偏偏半年前的那天早上,他送完大孙子上学,在返回的路上被疾驰而来的三轮车给撞了。他躺在地上满头满脸的血,血把他身上的深蓝色衣裳浸湿了一大片。他在医院输了两周的营养液,被三轮车撞伤的地方算是治好了,可没想到这两周的营养液却把他体内的癌细胞重新激活了。
这天,二弟顺路来看母亲,他又从馆子里买了一碗炖羊肉递给妻子,她端着碗喂给母亲吃。他老远就闻到了肉香味。记得有一回,他站在门外就听见二弟告诉母亲他给她买了炖羊肉,让母亲趁热吃。他就在自家的窑门前,等着母亲喊他:“留儿,快来吃羊肉!”可站了半天母亲窑里也没动静,他一直站在院子听着母亲把肉吃完,看着二弟把肉骨头端出来倒进垃圾桶里。他闷声闷气地回到自己屋里乱发脾气,心想母亲从来不这样,只要有口好吃的好喝的,一定会端一碗送到他门上,或者一定会叫他去吃。当天下午,他便把气撒在了儿子身上。
“你们吃香喝辣,让老子受着,白养了你们这些狼儿子!”他站在儿子家门口大喊大叫。
那会儿正值冬天,儿子没活儿干,天天窝在家,听见他叫嚷就出门拉他进屋。他当然不进去,他就要站在院子里,要让母亲听见他的叫喊声。
“滚,给老子滚出去,房子是老子盖的!”他叫骂着,让儿子把住的房子还给他,不让儿子在他的房子里住。
其实,那房子是儿子自己挣来的钱在院子里盖起来的。可他那会儿就是不讲理,站在儿子门前骂他,让他滚出去,让他赔为他结婚花掉的钱。母亲很快便出来劝他了,母亲那时已六十多岁,弯腰驼背,走起路来迈着小碎步,两边的肩膀一高一低摇摇晃晃的。
“这是咋了又寻事?”母亲抓着他的胳膊,语气近乎恳求道,“好端端的,咋又闹上了?”
他不看母亲,故意不理她,心想,他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跟她说话?
他的儿子在一边劝慰奶奶说:“奶,别理我爸,让他闹!”
其实他也不明白自己为什么又犯病。像这样莫名其妙犯病不是一次两次了。他一听儿子的话,愈发气急败坏,又自顾自地开始谩骂,骂儿子不孝顺,忘恩负义,吃里扒外。他每次都把能想到的最恶毒的词全都用上,他不管那些话对不对,反正怎么解气怎么骂。他儿子最终忍不住也开始对他吼叫,而他妻子每回都像那些外人一样站在一旁,两手交叉放在腹前看热闹。
母亲眼里噙着泪抬头看他,两只手还在拉着他的胳膊。
“留儿,你跟妈说,你这是哪里气又不顺了,你说呀。”母亲哭着问他。
他扭头看她,一股无名火直冲向她。“吃,吃你的羊肉去!”
他说着胳膊一甩从母亲手里挣脱出来,没想到母亲退了几步便倒在地上。儿子见状便向他猛扑上来,他跟儿子顿时在院子里抱成一团扭打起来。他只记得突然听到母亲嚎啕大哭,院子里围了几个孩子咯吱咯吱地在笑,脑畔上也有人在向院子里喊着什么。
他跟儿子在地上连着打了几个滚儿,他们扯衣服,拽头发,挥拳头,他看见儿子脸上、头上、衣服上全是黄土,颧骨那地方儿还有被他抓烂的血印子。后来他被儿子死死按在地上,心想,这小子力气真大,不愧是我儿子。
他还记得自己跟儿子的战斗是如何停下来的,因为母亲突然哭喊着跪在地上:“别打了!我给你们跪下,别打了!”
跟儿子打完架的当天,他便开始绝食,躺在炕上三天三夜不吃不喝,谁来劝他都没用。没有人知道他究竟为什么发疯发神经。还是母亲了解他,第三天夜里,母亲端着一碗羊肉递到他面前,红着眼眶问他:“留儿,你是不是嫌我没给你吃羊肉?这不,妈专门给你买的,你吃吧。”看到母亲又哭起来,还把肉夹起一块儿放在他嘴边儿,他终于又做回个人哩,他张开嘴就把那块儿肉给吃下去了。
他就是这副样子,一辈子都这样,总是三番五次地闹事,每回都为一丁点儿小事。有一次,他因为四妹答应帮他下地干活儿,可到那天人却没来,他便当晚跟她要前一天她才从他家借走的骡子,让她立马还他。还有一次他因为两个弟弟的空窑招到租户,他的空屋没招到,便气不顺要跟他们在院子里划地盘,不让他们从他窑门前过。自从羊肉事件后,他动不动就绝食相逼,一绝食,母亲就急了,每次都是她来劝他,也只有母亲来劝他。
每回他做了错事,母亲都要替他在弟妹跟前说好话:“他憨着哩,你们别跟他计较。”
其实母亲说的也是实话。
日子最好那几年,只有他家里还年年养猪、养鸡。到了年底杀猪宰鸡,他就把弟弟妹妹们都叫来,每家每户分一块儿猪肉又给一只鸡。这时母亲又急了,她把他拉到一边悄悄跟他说:“他们的光景都比你好,你少给一点儿,留着自己吃。”
他病重,最后一次住进医院时,突然就开始想过去这些年的事儿。似乎想明白一些什么。也许那时他已经模模糊糊感到自己快要死啦,他怕自己死在医院里,回去见不着母亲。因为他还有话要对母亲说呢。
等他出院回到家时,母亲已经痴呆了,她连他都不认得了。
他已经在母亲的门外徘徊了好一阵子,每次他来,院子里便会起风,圪崂里的柴火垛便会轻轻摇晃。他看见母亲手里总是拿着一根痒痒挠,那是他以前用过的。他看见母亲有时会把它捏在手里端详老半天。他在想,母亲会不会想起我了?
天蒙蒙亮时,又起风了,风把尘土刮起来,把窗户纸刮得哗哗响,把院子里的干树叶子、碎纸屑、塑料袋混合在尘土里一起从院子的这头刮到那头,从母亲的窑门前刮过。
母亲的窑里黑着灯,自从他过世,妻子便在晚上同母亲睡在一个炕上。黑暗中他听见母亲叹气,不一会儿又听见她在喊妻子的名字:“兰儿,兰儿。”
“咋哩?”
“我想尿尿。”
窗户亮起,妻子起身搀扶着母亲慢慢下了炕,把她扶坐在门圪崂的马桶上。
“你的劲儿不大。”母亲坐在马桶上边尿边幽幽地说,“兰儿,留儿呢?”
院子的风又大了些,喂鸡食的小碟子被风拉得哗啦啦地在地上移动,接着被又一股风打翻扣倒在地上。天黑洞洞的,鸡还没叫,只有狗吠声,起先是院子底下住的那户人家的狗,不一会儿,山上山下的好几条狗一起狂吠。
灯被关上,屋里重又响起妻子的鼾声,不一会儿听到母亲均匀平稳的呼吸。
早上吃过饭,母亲坐在炕上,妻子在灶台边刷碗。母亲又在问:“兰儿,留儿去哪儿啦?”
妻子手里拿着碗,站了半天隔了半晌才慢吞吞地说:“他死了!”
妻子说完便放下碗筷回自己窑里去了。不一会儿便听到她在窑里一遍一遍对她养的猫叫喊:“你大的,快出去,快出去,人还没吃哪有你吃的,出去!快出去!”
有人颤巍巍地从母亲窑门前经过,他走路的脚步声轻飘飘的,可步子还挺快,忽闪忽闪地跟阵风似的,边走边甩着他那两条大胳膊,两条细长的腿支着一副瘦巴巴的身子。那样子看起来真像他。母亲在屋里喊了一声:“留儿,是你不?”窗外没人应答。母亲又叫喊了两声。门帘被人掀起,来人问有啥事?母亲一看,原来是对门的邻居。
母亲总算想起他了,她总是逢人就问,留儿呢?没有人告诉她实话,他们先说他被孩子们带出去旅游了,又说他去外地打工了,后来他们总说,昨天不是刚来看过你,忘啦?母亲总是半歪着头,像是在思索又像是在怀疑。
院子里除了妻子跟母亲,白天都没什么人在。招来的租户白天都出去务工,晚上才回家。院子起先住着母亲跟他们兄妹四个。妹妹出嫁后,兄弟三人都跟母亲住在这里,院子里排着四面窑洞,母亲住一孔窑,兄弟三个每家一孔窑。后来,窑洞顶上又加盖了平房,窑洞对面也竖起了一排平房。加盖的平房里住着孙子们。院子里大大小小上上下下四代人,最多时居住过二十多口人。再往后,院子前边的几排破瓦房被拆迁,转眼立起了十几栋楼房。最终,只有他跟母亲仍然住在院子里。
弟弟妹妹们告诉母亲他们想把她接到自己家去住,一是方便他们照顾,二是想让母亲也住住楼房。
“妈,想不想住大楼房,带电梯的,就跟我二哥家的一样。”老三问。
母亲歪着头不说话。
“妈,我接你去楼房里住,你在这窑里住了一辈子,也该享享福哩,我们今天就带你住楼房。”老二说。
“楼房?谁的?”母亲问。
“妈,你在我们几个家里轮着住!一家住一个月!行不?”妹妹蹲在母亲脚前说。
母亲被他们接去了自家的楼房里。母亲不在,她的窑就空下了。他本想就此离开回到自己该去的地方,可没过几天,母亲又被送回了院子里。他们说母亲死活要回到院子来。
母亲才走了几天,可回来后看上去又衰老了许多。她瑟缩着身子侧躺在炕沿边儿上,额前的白头发遮住了半边的眼皮儿,她的头发有些长了,眼睛半睁着,一直盯着地上的火炉子。火炉子只有到了冬天才会用。一生火,窑里暖烘烘的,做完了饭母亲就会拿几个红薯放在炉膛里烤。还没烤熟,她就站在门口喊他:“留儿,过来吃红薯。”
“留儿,你来啦?”母亲自言自语着。他被惊得连连从炉子边上往门外退,只听她竟一个人呜呜地哭开了。眼泪从她深陷的眼窝里流出来,看起来就像是在干涸的黄土地上刚被凿开的井眼儿在慢慢地往外冒着水。
他突然想到,也许他不该盼着母亲想起他。他该让母亲忘记他!
院子里又响起风刮起地上的塑料瓶子、烂纸片和塑料袋吱啦吱啦的响声。母亲抹了抹眼泪,艰难地从炕上坐起,喊妻子:“兰儿,兰儿?”
妻子从自己窑里出来,站在门口问:“咋了?”
“你看看留儿捡回来的破烂是不是被风刮跑了,你赶紧拾掇拾掇。”
“麻烦死人了。”
妻子走到院子墙圪崂里的柴火垛下,白蓝相间的尿素袋子里装着他生前捡来的废品,一只袋子的口子大张,里头的饮料瓶、矿泉水瓶子散落一地。他不在了,母亲动弹不了了,捡来的废品也没有人去卖了,一直堆在柴垛底下。
“快拾掇拾掇,留儿回来又要骂了。”母亲在屋里喊道。
妻子蹲下身,撅着屁股,挪着步子,把周边散落的瓶子往袋子里捡,嘴上又开始唠唠叨叨个不停。
母亲一辈子勤俭持家,以前家里穷,缺衣少食,又要养活一家老小,她总是每天天不亮就去大修厂的院子里捡回一点儿人家烧得剩下的煤炭渣滓,或是在路上捡一点儿柴火,几块废纸片。后来生活越来越好了,她捡回的东西花样儿也多了,矿泉水瓶子,和新旧不一的衣服、鞋子。他总记得自己还在炕上迷迷糊糊睡觉时,就听见窗外窸窸窣窣的声音,抬头朝着窗户望出去,就看见头上戴着白布帽子的母亲正在整理破烂儿。她每次捡回东西总是习惯性地把它们堆在墙角的柴垛下,然后再把它们分类。母亲差不多到了七十岁时因为走不动路才不再出门捡破烂。他就从那时起接了母亲捡破烂儿的班。
后来,母亲不再跟任何人问起他。没过多久母亲便彻底病倒了,她白天黑夜昏睡不醒,他突然想到一定是他的逗留惊扰了她。他低着头站在母亲门口的炉子边上,他知道必须要和母亲做最后的告别了。他穿了生前最喜欢的那件旧得发白的深灰色中山装,来到母亲的梦里。
梦里母亲像以前那样坐在炕头上,她看到他从窗前经过便在屋里喊:“留儿,留儿!”
他掀起门帘就进来了。一进来像往常那样直端端地走到炕沿儿上坐上去。他总是喜欢坐在后炕,后炕对面的桌上放着电视,他是想离电视机近一点儿。开了电视回到炕上,支起一只胳膊肘侧身躺在炕上看电视。
“留儿,把鞋脱了上炕来。”母亲说。
他不说话,不看她,也不脱鞋,就盯着电视看。
“留儿,柜里有你妹拿来的早餐饼,你吃去。”母亲又说。
他一听,噌地起身走到门口的柜前,揭开柜盖埋头在里头翻出饼干。“妈,给你。”
他走到母亲身边把几片饼干递在她手里,重又躺在后炕盯着电视看。
“留儿,你这几天上哪儿去了?”
他吃着饼干盯着电视不看她,也没说话。
“留儿,你出去旅游了?”
他这时才像是反应过来,扭头看她。“噢,去医院转悠了几天。”
“去医院做啥?”
“我身上长了个囊肿,割了。”
母亲一听身体微微颠了一下。“你过来我看看。”
他挪到母亲跟前拉起衣裳,一层一层,穿了好几层,最后一层被揭开时,母亲用手轻轻地摸着他身上那道长长的口子。
“还疼不?”母亲又一层一层放下他的衣裳。
“疼哩,做了十来个小时手术,身上还插了管子,这儿,还有这儿!”他一边说一边在肚子上和下身比划。母亲没说话,隔了半晌才说:“妈下午擀面给你吃。”
窗外黑洞洞的,一股强劲的风从院子里刮过,狗吠声一声接一声地响起。他站在母亲的窑门口,母亲仍然坐在炕头上,眼睛睁得大大地望着他,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留儿,你回来啦?”
“妈,我该走了。”他不由得往前挪动了几步,院子的柴垛和窑顶脑畔上的杂草哗哗哗疯一样地抖动。
“妈知道,可妈舍不得你。”母亲此时又朝着炕沿上挪动着身子。
“妈,我得走了。你说过到了那边儿日子就会好。”
“噢,到了那边儿不会再遭罪,轮也该轮到咱享福哩!”
他想上前再靠近母亲一点儿,可还是走不到她跟前。他想,母亲总算是记着他,她永远是最疼他的母亲。他可以踏踏实实地走,回到他的山坡上去。直到有一天,母亲被人高高地抬起来,也抬到对面的山坡上,就在他停留的那座山坡上,到那时他就可以走近她。
责任编辑:魏建国
郝婷婷,女,陕西延安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四川文学》《黄河文学》《延安文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