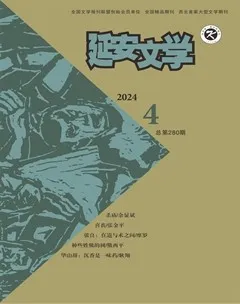乡村笔记
生长的村庄
夜幕未揭,月亮还在,星子还在,几声鸡鸣,像合唱时冒失地抢在伴奏之前,尴尬地闭嘴。接着几声狗叫,嘲笑着起哄着。人便惊醒了,迷迷糊糊地穿裤,摸几箱果袋,走进果园。
没有晨炊的村庄光净净的。万物都得晾着肚腹,省着气力,闭上嘴巴,辘辘之声也要摁住。最好的时辰是要挂在果树上的,大早趴在锅台上找吃食,有点浪费晨光。
初升的阳光迈过树梢、窑背,照出老人、狗、鸡和蝇虫荒落的影子。影子按住早行人潮湿的脚印,保持着蒸蒸的气息,怕他们在悠长的土路上走丢。白天的村庄是寂静的,人大都去了果园。老人们顶着帕帕左手搭着右手压住拐棍,立于硷畔,掏空了一辈子的话,只剩个骨架,再发出一点动静都会引发腐朽身体的轰倒。坐在墙根处打一会儿盹,像截枯寂的老树桩子,老弱的头磕一下又一下,还能证明是个活物。
院门虚掩或上锁,这不影响家在光阴中闲置。劳作或闲散,这也不影响人在光阴中一点点老化。只有土地在光阴中生生不息。
溏土开始招纳悬浮在半空的尘埃,树举着招魂的叶子揽收更大的风,墙皮嘣地一声开裂,揭露小虫子仓皇的一生,菜苗因一夜的拔节微微松塌了一下腰,鸟刚落到高挑的翘檐又摇摆不定地旋起。母鸡拖着肥重的身子跳上矮墙,它不愿独守寒窑,不惜把温热的蛋遗落他处,落得个吃里爬外的骂名。杂种的狗,生在村庄就得粗卑地活着,即便有着纯正血统。狗背上秃焦的一大块皮毛,露出坚厚的疤瘌,松弛的肚皮下吊几撮锈成黑疙瘩的毛,扫荡着浮土。没了狗模狗样为啥要屈辱地活着,连母鸡都表示困惑。可丑陋不碍忠诚。它狗视眈眈,扎上一副扑倒就是一嘴鸡毛的架势,暴烈地开足马力。母鸡惶恐,绝望地从矮墙又跳进院子,咯咯咯地叫骂,任谁都懂那鸡语:“狗日的,这狗日的!”一条称职的好狗,能守护母鸡肚子里的蛋。狗是知人事的。
刘四每天务果园前,总要把母鸡的屁股抠遍。他粗壮的中指轻易塞进母鸡滑润的肛肠,幽闭的狭道通往卵生的温热,心里会蹭出一层毛茸茸的绿,一些湿润细滑如珍珠般的蛋泡吮嘬着指尖,这一切使受到催化、刺激而蓬勃的绿也催化着另一个生命,他的喉管发痒,鼻息合鸣,肺叶鼓动如满风的帆,眼珠子向左一翻,嘴巴朝天翘翘,就能摸出满意的答案。沾了鸡屎的中指在满是垢痂的裤腿面上胡抹几下,没蛋的放养,有蛋的圈牢,绝不便宜旁处。守住母鸡肚子里的蛋便守住了家,这使他像公鸡一样高傲。对狗来说,虽没主人的技能,却有狗眼看鸡的本事,那大腹便便走路一摇三晃的一准是有货的母鸡。守住鸡肚子里的蛋便守住主人的颜面,获得蓄养的砝码,否则它的狗命也就不长了。这道理,狗懂。
一群大蚂蚁在狗的俯视下从土圪垯上列队而过。这个和恐龙差不多起源的古老物种,充满着智慧和力量,它们懂得利用信息源来纠正歧途,那它们会不会把温柔的狗眼当作天空来仰望呢?蚁群应该比人更熟悉土地的温度,就像风比人更熟悉土墙上的每一道细微的裂缝,炊烟比人更熟悉风的去向一样。果农只把苹果树当命。
九十点钟,溏土在前,人声在后,即便是突突的果果车也追不过沸扬的尘土。脚下的影子刚好合体,脚印也刚好重叠,像一渠水,咕咕涌动着朝各家流淌。又黑又密的炊烟像飘散的长发,这家和那家的缠抱着,那家和这家的又离散着。
各家各户荒野一样敞开。疲惫的人跌撞着把果锯插入大地,四仰八叉躺一阵。身体内的荒原等来了生机,喝饱水一样滋滋地向上蹿劲,腹腔内生出根系,错节相缠,四肢也长出枝条。不是无端生长,是被祖辈们的心力合围移植在这里了,绿,是囚禁多少年后的迸放,一种过欲的色彩,能搅动一潭的青翠。清淡的果香被风收藏,来不及在嗅觉中停留。躯体开始生根,向地下蔓延,心宅肺院被重重叠叠的青苹果蓄满,连灵魂都青涩生翠。
“掌柜的,别睡了,起来吃饭。”
把自己埋在果园,长出果树那样深的根茎,与它根根牵扯相连。弄清土地下的事情,弄清果树深藏不露的心事,即便埋得暗无天日,埋得骨朽肉腐。
农忙的每个白天都是短暂的。短暂到无法将一个人看清,一个动作做完,一件事情交代详尽,一口气吸进又吐出,得等第二天或者更多的日子再继续。村庄、人、草木、家禽、蝇虫,在短暂的一天里,在各自的轨道中安分,安命,生长而无所顾忌。只有到了夜晚,被裹在黑漆漆稠黏黏的暮帐里,看不清太多的眉眼,能感觉脚下都是路,阡陌纵横,一切都会走丢,一切都会迎来。人的魂梦会和万物私奔,万物和万物出逃,无论卑小或强大,熟悉或陌生,亲近而簇拥着朝一个叫未来的地方奔跑,而村庄生了根,迈不动步子,被远远地抛负。
果花还是冻了
春天从冬的怀抱挣脱,刚蹒跚着走进大塬,冷不丁栽个跟头,身上沾满冰屑霜痕。这惊醒了冬,又发起了洪威。雪,落在雪曾落过四指的地儿。冰,冻在冰曾冻过三尺的地儿。寒冷像尖刀一点一点划开夜的肌肤,并注入冷的浓液,蓄谋着更大的恶意。
春寒冷却灶台,比落雪冰冻更重要的事情开始降临村庄。乡政府下发的寒潮预警像根提线,把闲散一冬的果农扯动起来。家家地头拢起一堆堆枯枝烂叶,那些枝叶好像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郑重地聚集,紧密地码列并被赋予使命。他们把在炉火边烤得发烫发红的身体一层层裹紧,把那份温热隐藏在身体的死角,把跳动的火苗抵在寒埫的命门,便一头扎进夜幕。
通往果园的土路像冻僵的蛇蜷缩在狭促的手电筒光柱里,万条清冷的光线聚拢汇集,像一条充盈在天地间闪耀光芒的水流,渐渐有了跃动的暖意,有了方向和指引的能力。果农的一生搁置在这羊肠里磨损,岁岁年年,从一米七五磨到一米六五,从腰板挺拔磨成腰椎间盘突出,从净面小伙磨成槁木老汉。道路僻远而轻薄,再没有比一个家,一个人的一生更沉重的东西经过了。走得多了,心也会躁,任浮土没膝,扬天,风能轻易吹薄一条路,却改变不了方向。
远处,影影绰绰一大片黑影,摇摆而狰狞。仿佛只要挣脱出圈守它们的一堵土墙和栅栏,就能撕开风口,摆脱霜冻。那些黑影嚎叫着狂躁着,摧毁一株树的形象,会叫人疑惑,它们到底是白天伪装成果树,还是夜晚伪装成魔怪?若不是土路上的脚印还能叠合,树下的粪斑还能泛起灰白的光,真不知这些黑影就是自家的果树。
昨天还溺于果花隐隐的清馥,蹑足屏息,蕴在心底发酵。不急农事,每天都到果园溜达,吸鼻,嘬上两口。今天的清怡和昨天的淡雅混合在一起,昨天的淡雅和前天的幽香沉淀在一块。没几天工夫,心底捂得满满的,屯得实实的,能酿出蜜。“好我的二杆子,该疏花了。”婆娘这物种,最能轻易打破水中月镜中花,能让过分的美好撤换成虫吃鼠咬光板没毛的破皮烂袄一件,这,绝非虚说。
已有人立在地头,像筛子般抖动,他体内蓄藏的那份温热正一点点退守,身体内的器官抱成一团,抵御,无非是最后的消耗,最终裸露出陡峭的寒冷。西头的人大吼:“点火了。”风接过令旗,传达沉厚的声音,连同尘沙、冰粒和霜花悬在半空疾行,它们再往高往远走会惶恐不安,就摆脱风,落在东边地头上。东头的人打着冷战大吼:“点!”风调转逆行,刮走东地头的尘沙、冰粒和霜花,当然还捎带着东头人的残温。
点火只是熏烟。
黑夜把浓浓的烟全吃了进去。看不见它的声势,只闻到焦糊的味道,便清楚它的浩大。会迸出一丝火星,发出噼里啪啦的惊叫,别指望熬出热烈的火光,浓烟是赋予这场保卫战有力的武器。果园四周筑起黑色的巨大屏障,无数条黑龙喷出迷雾腾空而起。人仰着脸,像是一个通灵的夜盲者,把目光甩于浓烟之上,把法杖置于云层后的光亮。灰烬落在脸上,密密如针尖的暖电流向下传递,身体的哪个部位蓦地蹿出一股热意,消耗的温暖复生,闭上口鼻,屏住呼吸,捂严储存了一腔的冬果,并节俭地用于此后凉薄的某一天。
每个人的脑袋都灌满了烟尘,昏胀暗涌,感觉要飞升。脚陷在泥土里,如跋涉在大水之中,努力不让自己漂浮起来。抖下精神,半晌甩出一句酸曲,像冰冷的石片,打着水漂,轻飘而过。
东方终于跳出一线曙光。锅台回暖,老鼠出洞,羊狗煽情,蚂蚁搬家,和之前没两样。果园上空不知是青烟未散,还是被熏土了脸,灰塌塌的,竟没片云飘荡,没飞鸟掠过。上下眼皮终于合上,像合一本书,所有情绪、过渡、章节,只为结局铺垫。
果花还是被寒潮收割了,像是剪断脐带的胎儿,带着血红的绝望在光波中扭动着,痉挛着,落在坚硬的土地上,留下空荡荡的年景等人们熬过。
听说,刘四挖了几十棵绝收的老树。在机械猛兽般的咆哮声中,庞大的根系慢慢地从褐黑色的土壤里刨了出来,伴着强烈的痛苦、尖叫、撕裂和呻吟,一些腐旧的残体在翻滚的躯体里起伏跳跃,散发出霉潮的味道。被斩断的根系横截面露出茎的白骨,那是一种未见天日的白,是至暗的秘密。每一根根须都发出细微的、脆裂的声响,每一根都颤抖着与母体告别,每一根都牵扯着刘四的神经。他坐在地埂上七窍生烟,像点着了潮湿的柴火。抗寒那晚的烟在他脑袋里一直都未散去,他扛着沉重的头,不露声色地干活说话,生活在家人中间。只有在夜晚,一些梦从脑壳里生长,开始编织世界,把天空抬得高朗,把大地熨得辽阔。
又听说,刘四补种了几十棵幼树。新锃锃的树苗哗哗地抖落阳光,每棵果树是他最贵重的权杖,使他门庭鼎盛。
秋过果乡
大地的秋天从一片树叶的渐变开始,果乡的秋天从卸下果袋露出生怯的青白开始,而北谷的秋天从村长王大成了果园的守望者开始。
他的耳朵匿在谷物沉甸的喘息声中,眼睛藏在山林斑斓的层层递进中,鼻子躲在果木清醇的弥散中。从清晨到黄昏,从一个果子跳到另一个果子,果面光洁如釉,果面精致似瓷,眼睛守不住也站不稳。不急切,得有股貌似前清遗老奉来一盏茶水,揭开杯盖呷一口,缓缓地划过杯盖,发出清脆的碰击之声,再呷一口的悠闲。每天蹲在朽木墩上,像寄生出一株强大的植物,能感觉到蒸蒸的光合作用,感觉到打通全身经脉的耐心和希望。
能让六亩果园繁盛兴旺的黄土地,也一定会让一家人活得有模有样。王大这样想就兴奋不已,就热血上涌。秋天的太阳袒露敞亮,将每一颗青白的果子敷粉施朱,也将一副副面孔打磨成炙肤鸡皮。没有人为这种不公和偏心讨说法。
村长王大骑在墙头上变成粗砺的陶器,蹲在朽木上变成做旧的木雕,在金阳里卑微成一团。他怕自己强壮的影子能覆盖一棵树的光辉,这会让他羞愧不已。天地恩赐,草木生长,人恭谦侍候,永远不能抢占风头。他的思想可以恣意高远,眼睛可以顾盼流连。眉楞前,一枚苹果在阳光的暴雨中暗镀色彩,它从时光的指缝中凃染细细的一缕橘红的夕照,并缓慢、低浅地渗入肤底,这使它看起来羞怯而内敛,像待嫁的新娘静谧、灵动。一片树叶拍打着另一片树叶,一枚果子摇醒另一枚果子,欢快相告,接着又传递给远点的树,远点的树相簇相和,再向无边的远方传送,贯穿流畅。秋声不迭,秋声喧响,这一切就有了韵调、情绪平稳而充沛的前奏。
刘四的果园常年杂草不尽,和他的蓬头乱发也算呼应。还别说,这抠鸡屁眼的货真有绝活,苹果在手心颠两下,眼珠子向左一翻,嘴巴朝天翘翘,就能报出斤两,且误差不差毫厘,一筐苹果也精准无误。邪就邪在,他只对苹果情有独钟,像是通了灵犀,换成其它物件,肉身磅秤立马失灵。
李寡妇的果园规整得像棋盘,她把自己当作博弈的棋子,互为厮杀,也是在这样的时刻,才看到自己一直忽略的部分。去年送孩子读大学,火车带她走了最远的路,给了她最坚实的希望。她想象火车另一头的繁华和荣光,那将是她铺就给子女最大的幸福,而火车这头的沉苦凉寂隐入生命的地平线下。
秋,调重了颜料,人间斑驳又深了一层。
青幼的果子抱着一枚指纹跌入遥远的幽暗,无数个日月星辰的催生,已然暗合那枚指纹的基因,连同殷实的期望鼓涨涨地撑满整个果袋。从套袋到卸袋,像是揭开一段秘史,把所有暗藏的情绪、忧患、底气移交给秋天,仿佛一个至高境界的生命展示了它的一尘不染和高光时刻。反光膜一排排碎银般跳跃,集合阳光最深情的部分,折射出一个时节耀眼的光芒。果子一个个按条纹红、片红的品格上色,稳而有序,那般红艳可人。
风揭开新娘子的盖头,先是王一的果园,又揭王二家的,再去王三家闹腾,无数张粉嘟嘟的脸呼啦一下全亮相了,个个吹弹可破,梨涡蜜饯。风吹动太多事物,吹走的和吹来的无非是记事簿上或深或浅的一笔,面对果乡的浩瀚之秋,竟耗用了一顷笔墨。
王大跳下果梯,赶走了一只鬼祟的野鸡、两只偷情的雀儿,把一泡尿撒在自家果园,然后回家吃饭。远远望见稠密的炊烟,是每家每户朝天的素面,温和朴实,给迷路的人指引,王大一看就能认出自家的或他家的。世上万物都合时令。比如炊烟,春天过于招展,夏天多轻薄,冬天又浓厚,秋天的炊烟则像酒足饭饱的人,腆着肚子,身体摇摇晃晃地嚷着要腾飞。
人也逃不过时令的铁律。刚入十月,鼻子是放长的渔线,隔着数米把顺风飘来的果香钓到。先是住在村口的人闻见,纳鞋底的针线在空中顿了顿,爬上窑背,朝天空望望,朝自家果园的方向望望。村后的人闻着果香泱泱地涌到村口,把空气中成熟的果香搅动起来,招来了蜂,引来了蝶,蚂蚁都抖动着欢快的触角。村长王大骑着屁股冒着黑烟的摩托,快马加鞭传递起信息:“富能家的果子红了!”“明启家的果子红了!”“李寡妇家的果子红了!”……他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像飙起高昂的海豚音撞击着天空。身后的黑狗、母羊、公鸡也躁动起来,来来回回踱着步子,人踩起的尘土落在它们身上,它们扬起的尘土落在人身上,一层又一层,尘土、人、家畜和黏稠的果香在空气中搅动。
霜降之前,果子卸树。半个秋天被红透的苹果挥霍,另外半个被忙碌霸占。村庄显得空落落的,多余而孤零。从青到红,从涩到甜,对一个季节来说是一段光阴的转场,对一个人来说却隔山阻水千里迢迢,要用多少劳苦来遇见。
装果子的人坐上一天,会产生视觉质疑:是苹果吗?这是红色吗?同类的事物不断地累积、重复、拥沓,再加上时间的推手,慢慢失去对其真实的判断而产生一种虚幻,甚至否定了肉身——不过是一具黄土泥胎,在汗水的浸泡下开始瘫软、倒塌。
停下来望望天吧,缓一阵儿。大塬铺天盖地地奉上最隆重的秋礼,天空泼出湛蓝,大地掏出火红,劳作是这个季节最直白的抒情。而埋首在红和蓝之间的人,渺小而纯净。
责任编辑:魏建国
马静,女,河南周口人。作品散见于《延河》《延安文学》《散文·海外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