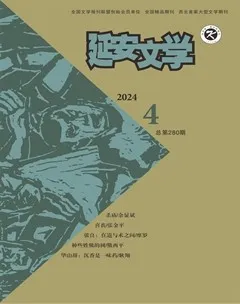少年电影
1
看一场电影要花四十块钱,这回村里连四十块钱都拿不出,可送到门上的电影怎舍得推掉?大队保管李世松眼瞅着他丈人卖了一头猪,就跑到丈人庄上从丈人手上借了四十块钱,留下了这场电影。电影叫《冰山上的来客》。
放映队到哪个村放电影并不事先通知,全镇六十多个村子轮流转,这村放完了到另一个村放。有时头午到,有时过午才到,田里干活的人们,有的天晚收工后才知道村里有电影,意外地惊喜,一天的劳累全没了。孩子们消息最灵通,放电影的一来,他们最先知道。电影队就两个人,一个推车一个拉车,一个放映,一个开电锅。一个胶皮轱辘独轮车,车上装满了大大小小扁形的铁皮箱子,生人和一群孩子迎上去,比亲爹亲娘还亲,前头引着,后头跟着,引进村来。妇女,老奶奶,沿街把着门观望,没有院墙的,或者是矮墙头的人家站在院子里就能看到电影来了,她们就要早做晚饭,耽误了看电影一家人会抱怨。
村子里有专门混大队差的闲人,迎头接着,安排放映场地。放映场地本没有悬念,就在村子中间一条十字路口的大街上,这地方出入方便,又宽敞。但有时也换地方,村东头的人主事就把场地安在村东头,村西头的人主事就把场地安在村西头。还有拍马屁的,支书马成法住在西南沟,便把场地安在西南沟马成法家的大门口,害得全村男女老少都要跑到西南沟去看电影。但多数时候是放在村子中间的十字路口。放电影的人卸下车便忙着刨坑竖杆挂银幕,银幕往往早早就挂上了,在两根大木头柱子上挂上银幕,银幕白底黑边,一挂上去,孩子们抢破头地占地方。十一二岁的小子,只有他们才有这闲工夫,再大一点的男孩子就没这闲工夫了。也有小丫头,小丫头要抢过这些男孩子必须在年龄上占优势,她们一般都在十三四岁。还有一些七八岁的孩子也跟着掺和,他们都是这些大孩子的弟弟妹妹。银幕下成了孩子的地盘,吵的闹的,也有打哭了的。他们在地上画杠,这杠就是法,谁画的杠就是谁的地盘,别人不能动。占的地盘要够全家人坐。有凳子的马上从家里往杠内搬凳子,如果没有那么多凳子就往杠内搬石头砖块,石头砖块也可以坐人,不坐也不要紧,先用它把地方占下,晚上家人带了小板凳来再把石头砖块换掉。他们都抢占最好的位置,不过放映机周围和放映机前都是好位置,这个地段看电影不能挡了后面人的视线,都必须坐矮凳子。看电影的人一层叠一层,前面是坐着的,后面是站着的,最后面的人站在凳子上。站在凳子上看电影的人都是一心一意看电影的,这一层像推不动挤不动的墙壁,搡不着挤不着。而那些大姑娘小伙子皆不带凳子,喜欢在场子中间挤,因能挤出甜头。一个大姑娘胸前的衣扣被人掏开了,一换片子一亮灯才被人发现,却不知是谁干的。
放映队配带小型发电机,村里人叫它电锅。电锅响了,好多人家还在吃晚饭,听到电锅响就急了,加速往嘴里扒饭,嘴里的饭囫囵咽了,一推碗筷就往外跑。从电锅到放映机扯一根长长的黑皮管线,有成人的小拇指粗,在人们的心目中管线越粗电流量越大,越粗越值得信赖。电锅放在场子外二百米远的草垛后或小树间。电锅没啥可看的,就是一个小型发电机,一盏马灯照明,电锅开起来,开电锅的人就倚在草垛下无事干,如果是冬天就裹着黄大衣倚在草垛下打盹。电锅一响,孩子们的热情陡涨,激动得心都要跳出来,大人小孩都知道电锅的重要,没有这电锅发电,再好的电影也演不成。电锅一响,街头便出现人流高潮,各条胡同里的男女都往场子涌。放映还没开始,挂在银幕一边杆子上的四方形黑匣子先响起来,响的是叫不出名的音乐。这音乐不是叫人听的,是催人的,听到黑匣子响很多人的脚步就乱了。每次放映之前都要调试一下镜头,从放映机放出一束光投到银幕上,是一个亮框,亮jy6SUrXTcB++VwGuX6ybNA==框在银幕正中不偏不斜。这束光极为强烈,是一通夸张的放倒的四棱光柱,无数只手伸到光柱里,投影到银幕上,有的手在银幕上舞蹈,有的手在银幕上变成鸭嘴兽头,还有人往光柱里扔帽子。银幕上上演着幻灯片,这是放映前奏,是让人无比兴奋的时刻。四棱光柱啪地灭了,银幕上忽然金花四溅,一个大大的几乎满了银幕的“八一”五星火花四射,像太阳放射光芒。全村人的幸福便全在这场电影上。
好事多磨,电影正放到关键处,银幕啪地灭了,电锅坏了。没有电,银幕下黑压压的人干着急。场子外安电锅的那个屋山头,一盏马灯亮着,围着一堆人,马灯的光不够用,好几只手电筒帮着照明,电锅却久久修不好。人们不想散,都想着下一刻就修好了。上次电锅坏了人就不想走,都在等,结果修到下半夜,修好了,电影没耽误看。这次人们也不想散,没有一个人动摇。忽然电锅响了,全场一阵欢腾,中间坐着的人刷地站起来一片,一个劲地鼓掌,接着,银幕突然亮了,有影了,出来一个真古兰丹姆,全场欢呼雀跃。
电锅修好了,天却变脸了,先前一直绷着没掉雨星,这会绷不住了,不怕扫大家的兴,下起来了。开始下得小,后来下大了,人还不散。没有人带雨具,在家门口放电影,有雨往家跑,哪用得着带雨具。可看起电影来就顾不得回家拿雨具了,总想着下一刻雨就变小了,雨就停了,这么好的电影哪舍得耽误。银幕上枪声正紧,战斗正打得激烈,谁还管它下雨,就是下刀子,也不散。外村来看电影的都不想走,本村的更不想,孩子们有这样的意志,大人们也有这样的意志。放映机上头挑起了一把伞,这就好了,人们放心了。雨越下越大,所有人都淋得像雨天的鸭子雨天的鸡,没有一个人吭声。人不散,放映就不能停,放电影的人也不想停,如果停了,就会在这个村子耽误一天一夜。银幕上突然没影了,放映机上方的大灯泡啪地亮了,这时所有的脸都扭向放映机,放映员两手迅速地倒着片子,把放完的片子摘下来,把下一个片子换上,电灯下那一张张雨脸没有一点沮丧,全是兴奋和期待。直到电影放完,银幕从雨中落下来了,放映员收拾放映机等一干设备,人们从这里往四下里退去,这一夜的精神享受才算圆满。
2
生人长成十四五岁的半大小子了。他本不叫这个名字,叫省力。他娘生他时在炕上啊哟啊哟肚子疼,他爹跑去叫接生婆,接生婆跑得满头大汗。到了,孩子却已经生出来了,所以取名叫“省力”。村里人发音不正,把省力叫成了“生人”,后来就叫生人了。生人最喜欢的三部电影是《南征北战》《地道战》《地雷战》,这三个片子放了无数遍看了无数遍,百看不厌,生人连电影中的台词都背得滚瓜烂熟。他一遍遍看得那个过瘾,那个激情,好像自己就是那个腰里别着驳壳枪的武工队长,那个手里抻着地雷拉线的民兵队长,一个少年的全部幻想,都在这几部电影里。
村子里最大的新闻是电影。当然不只是本村放电影,附近村子里有电影都是最大的新闻,三里五里,十里八里,不在话下。外村放电影同样是喜讯,有的是从半道上得到的消息,有的是亲戚专程来报信,一传十,十传百,马上传遍全村。下午地里的劳动就变成快乐的劳动,约好晚饭后几点出发,在谁家门前集合。不只是那些二十来岁的大姑娘小伙子振奋,那些成了家有了老婆孩子的爷们也不甘落后。最兴奋的是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子和十四五岁的丫头,像生人这个年龄,跑起来像弹簧,像野马,三里五里一口气跑到,十里八里半小时搞定。他们抄小道,甚至在野坡里穿插,地瓜沟,庄稼垅,下沟,上崖,冲锋陷阵一般。这些半大小子,有的是精力,地里的重活累活还轮不到他们,他们从来不知道疲乏,如果没有电影看,他们只能像大人一样吃了饭就睡。他们的野性只有在看电影时才得到释放。他们抄道从田野里奔跑,他们呼喊着,呜嗷着,变成电影中的角色。电影有时很长时间都看不到,本村没有,邻村也没有,有时又接二连三应接不暇,相邻好几个村子同时有电影,他们便幸福得不知所措。这消息下午在田里干活时就得知了,只是放什么片子没搞清。收工回到家匆匆忙忙吃饭。晚饭除了白水煮红薯便是南瓜汤,红薯也叫地瓜,上顿地瓜,下顿地瓜。夏天南瓜汤,秋冬地瓜蛋,大人孩子全是地瓜肚子南瓜肚子,这饭不好吃,可一有电影,就好吃啦。十五六岁的半大小子,正是装饭的年龄,南瓜汤能喝七八碗。喝得太饱,跑不起来,但脚步又不想慢下来,他们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肚子怎么能装那么多饭,而且装得再多也不会觉得撑。到了村头,他们为难了,往南三里唐家河村有电影,往北五里后村镇上有电影,到底往哪走,他们一时拿不定主意,两处都不知道放什么片,就怕错过了好电影,恨不得一个身子分成两个身子。有人选择往南,呼啦一群人往南去了,有人选择了往北,呼啦一群人往北去了。电影就是乡村的激情和兴奋剂。
有些新电影或者说好电影,都是城里放完才轮到乡下。村子里有在城里工作的,片子提前看过了,把片子内容传到村里,说片子如何如何感人,城里电影院里的人全看哭了。乡下人不轻信眼泪,眼泪确实吊人胃口。这个片子叫《卖花姑娘》,是外国片。《卖花姑娘》到了镇上,先从最西端的崖头村开始放映,崖头村离山西头村十八里地,但这不影响去看。生人吃过晚饭与伙伴们一同到崖头村去看电影,他们不走大道,从田野无路的地方抄近道,跑得像野马一般,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崖头村预计这场电影人会不少,所以就没在村子里放映,而是在村外的河滩上。生人到时,已开机放映了。河滩上银幕正面反面都是人,河滩成了人的板块,这个板块挤不动拥不动撼不动,像固定在河滩上。外围全是人墙,生人围着这个人墙转,插不进钻不进。银幕底下或许有空隙,可生人找不到进入的路,人挤成无缝无隙的一整块。生人只能在三层人外,远远地望银幕上的人影,只能听到那个吊在银幕一旁的黑匣子响,黑匣子里的响声与银幕上的人影对不上号,因为距离太远,人影看不清。但他不想放弃。这是生人看过的最挠心的一场电影,他实际上什么内容也没看到。
3
生人到茅房里拉了一泡屎,拉的时间过长。原因是中午娘做的南瓜的坏头没切干净,喝了八碗南瓜汤的生人就拉肚子了。他几次从茅房里提上裤子出来,都没拉净,又回去拉,三番五次,把时间耽误了。更糟糕的是,是哪村的电影他没弄清楚。待他提上裤子出了门,街上没遇到一个看电影的,他并不灰心,一口气跑到村东的大路。大路四通八达,人往哪个方向去他就跟着往哪个方向去,随大溜不会错。大路上没见人,只见一个十四五岁的半大丫头在彷徨,是虎牙。虎牙因为替娘刷了一摞碗耽误了,正在这路口不知往哪走。她也没拿准哪个村有电影。虎牙与生人虽然一个村,也经常照面,可从来没搭过话。虎牙先开的口:“哪村有电影?”生人说:“跟着人走。”前面五十步远有一群人走得急急火火,定是看电影的。既不往南也不往北,是往东,往东六里地有一个村子叫望海寺,肯定是望海寺有电影。望海寺在山里,被一层山又一层山包裹着,到望海寺村看电影要从两重山缝子里钻过去。哪里的电影都好看,不管它什么村,也不管它什么路,生人有了伴,虎牙也有了伴,有了伴心里就踏实了,只管跟着前面的人走,前面的人走得急,他们走得也急。天阴着,忽然打了一个闪,生人才发现天阴得没边没缝,但他不怕,就是大雨淋头也抵挡不住电影的诱惑。天阴,路黑,幸亏前面有一群人做向导,钻过一重山缝,又钻过一重山缝,脚底是一条大沟,能听到涧底的水声,夏季多雨,涧底水肥。一条小路自半山腰劈出,路沿上挂着松树,头顶上也挂着松树,路两边全是黑压压的松树。过了第二重山缝开始下坡,坡很大,像下井一般,坡下有一个村子,就是望海寺。村子是根据山起名的,有山叫望海寺,山上的寺庙早就砸了,不过还有一棵银杏树和一通石碑。村子就在望海寺山底,在山的阴面。村子四面的山很陡,树很厚,加上天阴,黑得无边无缝。先前还能影影绰绰看见前面那一群人影,偶尔还能听到他们清嗓子,可一下山一进村,前面的人忽然都不见了,只剩下一个村子,空空的街,连个人影都没有,连狗都不叫。村子里的房子都是依势而建,房子之上骑着房子,上户能踢着下户的房顶,从住户的院内窗子里漏出微弱的煤油灯光。两个人一下子不知所措,电影不在这个村子,他们跟错人啦。两个人都意识到错了,懊悔也无用,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两个人面对面,生人看不清虎牙的脸,虎牙看不清生人的脸,他们惶恐,他们不知所措,他们人生第一次遇到了这样的大麻烦。
虎牙愁得蹲下,哭了。忽然电光一闪,犹如白昼,接着一个焦雷,好像山崩了,焦雷炸出一股硫黄味,哗的一阵大雨从头上浇下来,两个人措手不及。天啊,这可怎么办?路边有一棵大树,生人拉起地上的虎牙,躲到大树下。大树下不是安全的地方,借着一个闪电,生人瞅准了一户人家的大门楼,拉着虎牙躲到门楼下。大雨暴跳,像剁了尾巴的狗,嗷嗷地尖叫。门楼前流成了河。整个村子像被山洪从头到脚浇下来。没办法,只有等,等雨小了或雨停了再走。不知过了多时,雨小了,事不宜迟,生人拉着虎牙就跑。他们沿着来路返回,路不熟,又不好走,他们跑不起来,就摸索着前行,有时借着闪电的光可以跑一阵,闪电过去,一团漆黑,比先前更黑,黑得让他们手足无措。摸过了一重山缝,又摸过了一重山缝,剩下的路就比较好走了。忽然一阵风起,吹得生人浑身打颤,吹得虎牙浑身打颤,他们的衣服早就淋湿了,贴在身上冰凉。六月北风当头雨,夏天一般不刮北风,刮北风就免不了下大暴雨。这会刮的正是北风,果然风声雷声一声比一声紧,天地更加黑暗,生人和虎牙像被扣在了一口大锅底下,暗无天日,见不到一点光明。忽然一道闪电,像龙爪,像树根,像燃烧的火信子,接着一个焦雷,劈头爆炸,好像天塌了,天漏了。虎牙一屁股坐在雨里,抱着头,大雨像水瓢从头顶往下浇,她走不动了,站不起来了。她哭了,不是累的,是吓的。
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生人也怕了。这条山路,暴雨来了也会流成山洪,石头都能冲得满地滚,冲走他们两个更不在话下。他们必须走,离开这里,雨再大也不能停。雨像瓢浇,像盆倒,生人头上脸上下巴上发了大水,他呛了一口水,又呛了一口水,像掉进河里,呛得鼻子里辣齁齁的。生人拉起虎牙顶着雨前进,两个人好像都成了大雨打击追赶的目标,衣服贴在身上,裤管裹在腿上,他们挣扎着往前迈,借着闪电,看清了路,跑起来。忽然又一个闪电,照得大地如同白昼。虎牙一屁股瘫在地上,再也起不来了,她哇哇地哭,可她的嘴被雨堵住了,雨的哭声更大。生人不知哪来的劲头,背起虎牙就跑,路边有一个打麦场,场边一溜草垛,苫蔽成丘,场头有一个场屋子,场屋子是那种瓜棚式的,门开在山墙上,这种场屋子是看场休息用的,无大用,不镶门,无论人,无论风,无论走兔,随便进。生人背着虎牙往场屋子里跑。这是个最好的避雨的地方,麦场是个平阔地段,相对安全,生人背着虎牙进了场屋子,一个闪电跟进来,一个焦雷跟进来,两个人瘫倒在场屋子里。场屋子很低矮,因为门在山墙上,成年人在里面能站起来,但一偏身就得弯腰,最矮的地方不到一尺高。场屋子里有麦穰,两个人倒在麦穰上。外面的风大雨急,像在向整个世界示威。雨在天地间嗷嗷嚎叫,风一阵赶着一阵,场屋子外大片庄稼无论玉米还是高粱,都在风雨里挣扎,倒了一片,再也爬不起来了,像找不到活人的战场。电光下,麦场成了一个湖泊。山洪下来了,麦场左右都是大沟,山上的洪水一滚一跌冲下来,像山崖崩塌。两个人缩在场屋子的麦穰堆里,颤成一块,寒气直往场屋子里钻。生人和虎牙两个人的衣服全是湿的,两个人都寒冷,两个人都打颤,尤其是虎牙,上牙与下牙直打架。一个焦雷,两个人一下抱紧了,抱紧了就再没有松开,这样的行为连他们自己都没有察觉。他们的世界如到了末日,末日让两个人变成一个人。两个人抱在一起就暖了,衣服渐渐干了,身子下面的麦穰也添暖,两个人像两条冻僵的蛇复活过来。生人的手开始知道动了,在虎牙的胸前动,一只手捂住了虎牙一只乳房,那只乳房正开始发育,像一个又硬又尖的窝头。虎牙用手挡了一下,便放弃了,不挡了,生人的手是小心的温柔的试探性的,这让虎牙觉得是安全的放心的友爱的。生人最后把一只手捂在虎牙的一只窝头一样的乳房上,他太疲乏了,他什么也做不成了。两个人都睡着了。
4
一夜雷雨电闪没停,虎牙一夜未归,虎牙的爹娘一夜没合眼。天明雨停了,太阳出来了,太阳出得比往日都好,仿佛什么事也没有,虎牙回来了。回家就要往她房里溜,被爹喊住了,就在堂屋当门,虎牙站住了,不敢移步。
“这一夜去哪啦?”爹问。
“没去哪。”虎牙说。
“呸!”爹逼近一步。
虎牙不想回答,说不出口,吞吞吐吐。她希望娘能帮她,娘站在爹的身后,怂恿爹,虎牙觉得躲不过去了,半天才回答:“看电影啦。”
“和谁,哪村看的?”爹紧逼不放。
虎牙依然吞吞吐吐。爹的巴掌要挥过来啦。
娘恨得跺脚:“还不快说实话!”
虎牙没法,只得把看电影跟错了帮,遇了大雨的事老实交代了。
爹气得直哼哼,问:“生人那小子怎么你啦?”
虎牙不说话。半天说:“没怎么,没……”
娘也生气了:“死丫头,什么时候啦,还掖着?”
爹的脸都气青了,虎牙害怕了,说:“他摸了我。”
“摸了哪?”娘问。
“胸。”虎牙低下了头。
“还摸了哪?”
“没摸哪。”
爹不信,娘也不信,继续逼问。
“没有,没有!”虎牙要炸了,双手捂着耳朵喊。她哭了,很委屈。看着那幼稚和憨真的样子,爹娘觉得没说假,但又不想轻易相信。
“丢不死人,还哭?早饭别吃啦。”
爹娘不给虎牙早饭吃了,把虎牙塞进西间里,按了锁。两口子到锅屋里计策,怎么办?坏了女儿名声,传出去还了得?场屋子里抱在一块睡了一夜,谁信只摸了胸?即使只摸了胸,那也犯法,大闺女的胸是随便摸的吗?村西头高老八家的小子摸了一头水牛还被派出所拿去审问。
“如果只摸了胸,无人知,也就罢了,就怕摸了别的。”娘说。
“没有不透风的墙,摸了胸也不行!找他爹娘。”爹说。
“你想要他们家钱?”
“钱是小事,我想让他们家赔我闺女!”
5
两口子找到生人家的门上,直接进了锅屋。生人的娘正在锅屋里准备早饭,生人的爹蹲在锅屋门口烧火,见虎牙爹娘上门,热情招呼,可虎牙爹娘一反常态,都唬着脸不说话。生人的娘放下手里的活,讪讪地不知出了什么事。
“生人呢?”虎牙的爹先声夺人,语气不善。
生人的爹娘一时不敢回答。
虎牙的娘说话了:“你们问生人吧,昨天夜里看电影,把我们家虎牙怎么啦?”生人爹娘立刻吓得两腿打颤。这可是坐大牢的事。
生人也刚到家,正在锅屋西间翻箱倒柜找裤头子准备换,裤头子就是半大小子的夏装。身上的裤头子虽然干了,但全是泥。他听到是虎牙的爹娘,裤头子没换成,就想溜。锅屋西间没有门,只有一个熏得像墙皮一样黑的布帘子,刚一露头,被爹上去一把薅住了头,拽到了虎牙爹娘面前:“说,你个畜生,昨天晚上对虎牙做了什么?”
生人不说话,不说话就是真的啦。生人的爹痛心疾首,“畜生畜生”地骂。一只脚飞起来,眼看着就要踢到生人的屁股上,虎牙的爹抢前一步挡住,说声“慢着”。他这会儿才好好地看了看生人这小子。两年前还是个鼻涕虫孩子头,在大街上玩得人仰马翻,转眼出息了,半大小子了,虽然才十五岁,却显露出一个健壮男子汉的苗头。他六个闺女没儿子,虎牙最大,到自己老了,连车粪都送不到地里去,有个女婿放在坐庄,这是他多年的算盘,没想到这小子撞上啦。想到这里,虎牙爹的态度平和了,说:“这事传出去,虎牙怎么嫁人?这么着,两家把亲订了……这可不是父母包办,是你们自己做下的。”生人的爹娘吃了一惊,太突然,太意外,但立刻应诺。虽然定亲早了点,可十七岁定亲的多的是,横竖只差两年。真是虚惊一场,生人爹娘好像一下子喘了一口阳气。
这个年龄定亲要吃点亏,那就是从现在起每年逢年过节都要到丈人门上送礼,也叫“上贡”。还要帮着丈人家干活,什么苦活累活脏活,都像牵牲口一样把女婿牵了去。
场屋子的事本来无人知晓,可两家一定亲,弄得全村老少皆知。村里的大人们无不掩口笑。生人再到外村看电影,找不到伴了,他一出门,街上一群半大小子拍打着屁股就跑了,声称不和有老婆的人一块看电影。
责任编辑:徐睿晗
李业成,山东日照人。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作品散见于《山东文学》《当代小说》《短篇小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