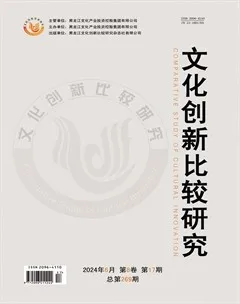探寻江户时代出版物背后的化妆文化
作者简介:粟瑶(1999-),女,四川达州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历史文化。
摘要:日本平安时代,以贵族为中心的国风文化诞生,独特的化妆文化开始萌芽,日本贵族们奠定了白红黑传统化妆三原色。至平安时代后期,这种独特化妆手法在男性间开始流行,男子打扮成女性模样之风渐及公卿。同时,化妆作为一种身份地位的表现与权力的象征随着政权的更替,由公家向武家扩散,并且渗透到庶民阶层。至江户时代,化妆文化在武家礼法与身份制度的双重规制下,逐渐在女性中普及并成为她们有限度展现个性的方式,这也是江户时代女性化妆文化的独特魅力所在。在化妆文化的发展历程中,“往来物”、美容指南书和浮世绘等出版物扮演了重要角色。该文深入分析这些出版物的具体内涵,重点关注它们如何塑造和影响了化妆观念,从而揭示其背后所蕴含的丰富化妆文化。
关键词:江户时代;化妆文化;出版物;女子用往来物;化妆书;浮世绘
中图分类号:K313.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4110(2024)06(b)-0069-05
Explore the Makeup Culture Behind Edo Period Publications
SU Yao
(College of Oriental Languages and Philosophy, Zhejiang Gongsh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During Japan's Heian period, centered around the aristocracy, a unique makeup culture began to emerge, with nobles establishing the traditional makeup colors of white, red, and black. By the late Heian period, this unique makeup technique began to gain popularity among men, leading to a trend of men dressing as women, even among the nobility. Simultaneously, makeup, as a symbol of social status and power, spread from the aristocracy to the warrior class with changes in political power, eventually permeating into the commoner class. In the Edo period, under the dual regulations of the warrior class etiquette and social hierarchy, makeup culture gradually became popular among women, serving as a limited means for them to express their individuality. This unique charm of Edo period women's makeup culture is examined in depth. Throughout the development of makeup culture, publications such as women's etiquette guides, beauty manuals, and ukiyo-e prints played significant roles. This paper will analyze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se publications, focusing on how they shaped and influenced makeup concepts, thereby revealing the rich makeup culture they embody.
Key words: Edo period; Makeup culture; Publications; Women's etiquette guides; Beauty manuals; Ukiyo-e prints
江户时代前期,武家礼法的完善促进了女性道德教育的兴起,如《女重宝记》等道德教科书强调女性应依循礼仪和习俗,选择适宜的服饰与妆容。此时,化妆不仅是美的展现,更是身份与婚姻状态的标识。随着经济的繁荣,化妆品逐渐普及至京都大阪的庶民之中,女性开始关注梳妆打扮。一系列美容指南书的出版,如《都风俗化妆传》《容颜美艳考》等,将化妆技巧传播给广大女性。同时,浮世绘美人画的风靡,使游女们成为时尚化妆的引领者,她们的妆容成为社会风尚的标杆,受到一般女性乃至上流贵族的追捧。
1 “往来物”中的规范与约束
随着近代出版业与教育的蓬勃发展,社会涌现出众多富含教育功能的往来物。“往来物”是初等教科书的总称,被广泛使用在平安时代末期至明治初期的庶民教育领域,早期的往来物是书信习作的范文集,江户时代演变为以传授历史、地理等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知识为目的的教材[1]。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时期也诞生了专门为女性编写的女子用往来物。这类书籍在中世纪前期,主要在贵族阶层内部流传,到近代它们逐渐走出了贵族的圈子,深入到普通百姓家中。在正式的化妆指南书出版之前,女性只能通过女子用往来物接触化妆。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为《女重宝记》与《和俗童子训》。
元禄5年(1692年)刊行的《女重宝记》全五卷,作者苗村丈伯。该书旨在启蒙教化妇女,并侧重于日常生活中的实用知识,所以其中的内容侧重于礼仪成规、妊娠生产、女子应该通晓的各种技艺、女性用语及文字汇编等。关于化妆的内容集中在一之卷的第六“女化妆之卷”中,其中关于头发的项目最多,有5项,可见头发的重要性。在《女化妆之卷》的开篇,作者引用了《徒然草》中的观点,强调了头发对于女性美丽的重要性。书中明确指出,一头亮丽的秀发足以让女性焕发出迷人的光彩。因此,女性在早晨起床时,应尤为注意自己的仪容,确保丈夫不会看到凌乱不堪的发丝。
关于白粉和红化妆的记载有“生而为女人,不可一日不涂白粉而素颜”。涂抹白粉不是为了美丽,而是为了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素颜。关于红粉的记载很少,只记载了“脸颊、嘴唇、指甲应薄涂”[2]。主张腮红、口红及爪红应淡饰,过红则宛若茶屋妓女般卑贱。因此,涂成浓红色并不符合礼仪,会被认为是向人献媚。唯一记载的浓妆的就是染黑齿,它要求女性每天早晨都要涂铁浆水。由此可见,染黑齿与梳头发和涂白粉一样,是每天的仪容整理中必不可少的环节。
《女重宝记》详尽地阐述了化妆的各个环节。从其所列的顺序和内容来看,该书对化妆的重视顺序依次为:头发、额头、眉毛、白粉、红、黑齿。特别是,书中对头发、额头和眉毛等部分还进行了详尽的插图说明,足见其对这些方面的重视。然而,对于眉墨、白粉、口红、腮红及爪红的运用,书中则建议采用淡雅自然的风格,不宜过分浓重。
另一部《和俗童子训》作者贝原益轩,他是日本著名的儒学家、本草学家,也是积极推动女子教育的教育家。该书系统地概括了他的教育思想,也是日本最早的教育论著,其中的卷之五《教女子法》对后世的女训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教女子法》记载了女子教育的方法和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分为18条进行了记述。
关于女性化妆的记载不多,主要集中在“7女性有四行”。其中提到的四行,即妇德、妇言、妇容、妇功。与容貌有关的妇容,益轩是这样说的:“所谓妇容,指的是外形。虽然没有刻意打扮,也能展现温柔之态。穿着干净利落,衣服也没有污渍痕迹,这就是妇容”。从这段记述中可以看出,妇容并非单指外貌之美,而是身心保持清洁。另外,在装束方面要求高雅,提倡身体和衣服上不要有污垢。在“13洁身自好,保持清洁”中,益轩进一步强调女性保持身体清洁的重要性。女子在家庭中侍奉父母,出嫁后则亲近侍奉公婆、丈夫,因此,她们需要时刻保持身体的清洁,不得有丝毫污秽。铃木则子指出,提倡保持身体清洁的言论仅限于往来物,清洁是特别严格要求的女子德行[3]。由此可见,清洁不仅是女性的一种外在表现,更是她们内在德行的重要体现,相较于涂抹白粉,往来物更重视清除身体污垢、保持肌肤清洁的护肤行为。
在“16父母应教导出嫁女儿的十三条训诫”中的第十一条中,益轩对于女性的穿着提出了明确的建议:“服饰的装饰、色彩与图案,皆应以低调朴素为宜,同时强调身体和衣物的整洁至关重要。内心是身体的主宰,衣物不过是外在的附属品,其重要性远不及内心的充实与行为的得体。穿着应以舒适合身为原则,而非过分追求华丽以炫耀于人”[4]。由此可见,益轩并不主张女性过分修饰外表,而是更看重其内在的修养。
女子用往来物对于化妆与服饰的篇幅相对有限,这或许是因为其核心观点认为女性的容貌乃天生,非化妆所能轻易改变。总体来看,女子用往来物中的化妆内容更多是在抑制化妆的过度发展,而非传授化妆技巧本身。
2 美容指南书中的化妆技巧
近代的女子用往来物中关于外貌的记述篇幅有限,并未深入探讨具体的化妆方法,仅提供了简约的化妆信息。直至19世纪,才逐渐涌现以平民女性为对象的化妆书,如佐山半七丸著的《都风俗化妆传》与并木正三著、浅野高造增补《容颜美艳考》。《都风俗化妆传》于1813年同时在京都、江户、大阪三个城市出版,至1922年为止的100多年间,共再版了6次;而《容颜美艳考》则自1814至1862年的50年间,再版了6次[5]。可见这两本书受欢迎程度。
《都风俗化妆传》上卷开头就提到了珍宝与女子的共性,作者认为女子与玉石一般,皆需经过精心修饰与打磨,方能绽放其独特之魅力。作者鼓励女性不仅要在外表上投入心力,更要注重内在修养的提升,以追求内外兼修之美。这种观念与女用往来物中常提到的“容貌天生,难以改变,内在修养更为重要”的观点有所不同,既强调了女性在外表上的重要性,又未忽视内在修养的价值。
《都风俗化妆传》上卷着重记载了能够使肤色白皙的各类药方,同时也详细阐述了针对脸部各种问题的处方。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口红的涂抹技巧,即避免口红过浓。因为口红涂抹太浓会显得嘴巴很大,而嘴巴的形状与大小在化妆中显得尤为重要,因为它们常常与个体的声音大小及自我主张的强弱相关联,所以在女性地位较为低下的封建社会,小嘴往往被视为女性美的标志。观察江户时代的浮世绘美人画,可以发现,画中的女性嘴巴被描绘得异常小巧,与脸部相比显得尤为突出。另一个避免口红过浓的理由是,浓重的口红会使得嘴巴在色彩上过于显眼,过分强调其存在,进而给人一种强烈自我主张的印象,甚至会被认为与当时女性应遵守的秩序相悖,因此并不受欢迎。
中卷则聚焦于手脚、头部等部位的美容的技巧,其中涵盖了使手脚肌肤白皙、头发乌黑亮丽的药方。关于手足部分,它明确指出:“美人之相,在于手脚纤细,姿态婀娜”。换言之,细腻柔软的手脚是构成美人形象的关键要素。此外,书中还提到了走路的姿态。它强调,即使拥有出众的容貌,若走路方式不当,整体形象也会大打折扣。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对于手足的呵护和行走姿态的重视,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女性美的全面追求,它不仅关注面部妆容,还注重身体的每一个细节。
下卷则主要探讨了根据脸型化妆的技巧,传授了如何通过化妆使短颈显得修长的方法。其中的“身嗜之部”强调女性全身清洁的重要性,这一点与《教女子法》中强调的清洁一致。具体而言,女性应时常清理耳垢,修剪鼻毛等无用之毛以维持身体的整洁。同时,对于口臭等问题,亦需时刻留意,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改善。例如:为减少出汗,可服用煎制药草或将米粉敷于全身;为消除口臭,可将药草磨成粉末,餐后服用。仔细观察每一卷的内容,可以发现《都风俗化妆传》全书贯穿了一个核心观点,即化妆能够改变容貌,且作为礼仪的一种,是展现女性仪容的重要手段。
另一部《容颜美艳考》由乾坤二卷构成。乾卷根据主要内容大致可以划分为4部分,化妆的大意、季节的化妆法、外出时的化妆法、不同身份的化妆法;坤卷根据主要内容也可以划分为4部分,改善脸部部位的化妆法、不同肤色的化妆法、简单的化妆法、化妆工具的使用。本书的序文对女性的华丽装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鼓励她们在化妆时展现独特的个人魅力。化妆的目的不仅在于维护仪容的整洁,更在于焕发女性迷人的光彩。
乾卷详尽地阐述了如何根据季节的更迭、目的的不同及生活状态的转变,灵活采用多样化的化妆方法。这与以往女子用往来物中那种笼统且泛泛而谈的化妆方法有着显著的差异。书中传授化妆技巧,其目的更在于帮助那些外出机会日益增多的女性在社交场合中展现最佳自我,而非单纯取悦丈夫。近世日本大量女性出游并留下游记,表明女性可不拘礼法,外出游玩、交友,在公开场合露面活动,也能与异性正常交往[6]。这与近世女子用往来物中描绘的单调生活状态形成鲜明对比,这些丰富多彩的休闲活动实际上拓宽了近世日本女性的生活空间,展示了她们真实而多元的生活面貌。
乾卷还根据不同身份的女性,如少女、主妇、侍女等,传授了适宜的化妆技巧。例如,对于忙于操持家务的主妇们,则传授了简洁而有效的化妆方式,以便她们在繁忙之中仍能维持优雅仪容;对于辛勤劳作的侍女,则教授了劳作之后如何通过热水浸泡等护理手段,呵护因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脚[7]。这些细致入微的化妆与美容技巧,不仅展现了平民女性对美的追求,也反映出在忙碌的日常生活中,她们对于自我形象和美容护肤的重视。
坤卷则重点讨论了如何通过化妆技巧改善脸部缺陷,如详细介绍了利用白粉、胭脂等化妆品来营造自然的阴影效果,突显面部轮廓。除了通过化妆技巧改善脸型及五官外,还可以利用白粉和胭脂来掩盖雀斑和麻子等皮肤瑕疵。此外,坤卷还详细阐述了化妆道具的使用,包括如何清洁脸部、存放口红及调整眉墨的颜色和浓度等。
相较于重视妇德妇容,不支持追逐流行的华美装扮,劝人淡妆的往来物,这两本化妆美容指南书为女性提供了更为详尽具体的化妆与美容技巧,对化妆给予积极的评价,书中的化妆技巧对于当时的女性具备更现实的意义。
3 浮世绘中的流行趋势
近代日本社会兴起的浮世绘这一艺术形式,以其独特的视角和表现方式,积极报道化妆潮流。浮世绘艺术题材主要分为4种,分别是美人画、役者画、风景画、春画[8]。其中,美人画尤为引人注目,其描绘的女性原形多来自社会最底层的游女。通过美人画,不仅可以欣赏到艺术家们精湛的技艺和独特的审美视角,更能窥见江户时期日本社会对女性相貌的审美标准,以及对妆容和服饰装扮的时尚追求。
17世纪中期,普通女性可以通过观赏歌舞伎和游女的画像,了解最新的化妆、服饰和发型趋势。例如,代表画师菱川师宣的作品《回眸美人图》便体现了元禄年间的流行风尚。画中女性身着红衣,驻足回望。其头上装饰着玳瑁制成的发梳,头发下垂,底端扎成圆圈“玉结”,这种发型在当时极为流行。服装为振袖样式,上面有菊花和樱花组成的“花环纹样”,是当时流行的图案。绿色腰带上系着发源于人气旦角演员上村吉弥的吉弥结。无论是发型还是服饰,都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当时的流行趋势。
随着江户时代木刻技术的精湛发展,大量经济实惠的美人画得以广泛流传于民间。特别是到了18世纪后半叶,多色印刷彩色版画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浮世绘作为时尚流行信息源的价值。这一时期,浮世绘领域涌现出众多杰出的画师。其中,喜多川歌磨通过大首绘和全身绘两种形式,将美人画的魅力发挥到了极致,他的《宽政三美人》就是典型的例子。画中的三位女子被誉为宽政时期(1789—1801年)的美人,她们共同的特征是嘴型小巧、鼻梁高挺、眼睛细长,具有女性的魅力,气质大方,这些特点在当时的审美观念中被视为美的象征[9]。
到了19世纪,这些流行的美人画像不仅将女性美的标准深入人心,同时也为现实中的女性提供了最新的化妆范本。例如,溪斋英泉的《浮世四十八手》,画中女性的下唇呈现绿色,这正是幕末时期颇为流行的笹色红妆容。到了文化时期(1804—1818年),下唇涂抹浓红的化妆法开始盛行,这种源自游女的风尚,被称为笹色红化妆法。仔细观察当时的浮世绘美人画,会发现许多画作中的女性下唇并非红色,而是绿色。这种妆容的特别之处在于,通过反复涂抹口红进而让嘴唇呈现出绿色的光泽。与现代口红材质和色彩截然不同,江户时代的口红是由红花精心制作而成。口红的价格非常昂贵,被称为“红一匁,金一匁”,能化笹色红妆容的多是富裕人家的女性以及游女。然而,买不起如此昂贵的口红的平民女性们又想追求潮流,就用墨和廉价的口红反复涂抹来表现玉虫色。这种化妆技巧在《都风俗化妆传》中也有记载,书中提到由于红粉价格昂贵,为了降低成本并达到相似效果,可先用墨或油烟作为底色,再涂抹口红,这一变通方法展现了平民在追求时尚过程中的创造力与智慧。
在《守贞漫稿》一书中,作者对笹色红化妆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探讨。据书中记载,作者幼年时期的大阪以及文化十年前的江户,女性唇妆普遍偏浓,流行一种带有荧光效果的玉虫色,这种风尚甚至影响到了婢女阶层。然而,到了天保时期以后,笹色红逐渐失去了人们的喜爱,转而以淡色为美。在江户地区,尽管近年来仍有浓妆的残余,但已远不如往昔盛行,这明显反映出近世末期笹色红化妆风尚的衰退与消逝。
除了笹色红化妆外,目红这一化妆特色也崭露头角。浮世绘描绘了大量的化妆风俗,但关于目红化妆的却非常少,歌川国贞的《当世美人合踊师匠》便是其中一例,画中女子以红猪口为工具,巧妙地用无名指在眼缘涂抹红色,形成独特的目红妆效,即现今所见的眼妆。在《都风俗化妆传》中,详细描述了目红化妆的步骤与效果,此法能突显面庞,赋予人一种俏皮之态。用手巾轻拭眼睑上的白粉,使其变薄,再以淡胭脂轻描其上,最后用带有残余白粉的刷毛均匀涂抹,若使用红粉需先稀释再涂抹,但频繁使用易使眼部略显暗沉[10]。关于目红化妆的文献较为罕见,在浮世绘作品中亦难觅其踪,似为当时女性间短暂的流行风尚[11]。
4 结束语
综上所述,文章从往来物、化妆书与浮世绘三个方面阐述了江户时代化妆文化的内涵。这一时期化妆文化的普及与确立,与出版媒体之间展现出了高度的关联。透过这些出版物可以窥见在武家礼法与身份制度的双重规范下,日本女性化妆成为一种有限度的个性化展示,她们在妆容的细微之处寻找自我表达的空间,既遵循了礼法规范,又巧妙地融入了流行风尚。这种在限制中寻找自由的表现方式,正是江户时代女性化妆文化的独特之处。文章简要就出版物背后的化妆文化进行探讨,期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全面地了解当时的文化、社会风貌和生活方式。
参考文献
[1] 沈霞.中日文化交流中往来物的研究价值[J].人民论坛,2016(11):244-246.
[2] 苗村丈伯,苗村常伯.女重宝記·男重宝記:元禄若者心得集[M].东京:社会思想社,1993.
[3] 鈴木則子.日本の化粧意識の近代化をめぐる比較史的考察―清潔習慣の展開をめぐって[J].コスメトロジー研究報告[R].2003(11):95-98.
[4] 貝原益軒.和俗童子訓[M].东京:目黒書店,1893.
[5] 铃木则子.镜中美女:从江户时代的化妆书看美容意识的变迁[J].黄秀敏,译.新史学,2000(11):41-73.
[6] 秦茵科.近世日本儒学思想影响下的江户城女性研究[D].武汉:湖北大学,2023.
[7] 並木正三,浅野高造.容顔美艶考[M].加賀屋善藏,1838.
[8] 孙悦怡.日本江户时代浮世绘美人画艺术的审美特征研究[D].大连:辽宁师范大学,2017.
[9] 白壁征夫.日本における美人の変遷—飛鳥時代から明治,大正,昭和期までの美人の基準について—[J].日本香粧品学会誌[S].2020(44):105-114.
[10]佐山半七丸.都風俗化粧伝[M].东京:平凡社,1982.
[11]村澤博人.顔の文化誌[M].东京:講談社,20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