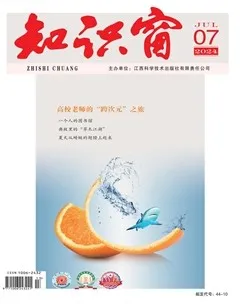稷下风铃入耳眠
此刻,我正坐在校内的稷下广场,风铃随风摇摆,风铃声好像童年时母亲哼唱着哄我入睡的安眠曲。
在每一个失眠的雨夜里,我都会执拗地听着稷下清音,就像是母亲在身旁哄我入眠。母亲的哼唱总能将我纷乱的思绪团团包裹,给我的心里送来一片宁静。
来大学的前一天晚上,也是一个雨夜,我早早收拾好行囊,却在床上翻来覆去,看着窗外柏油路反射的碎金,听着远处汽车的鸣笛,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即将到来的大学生活令我万分期待,但离乡的恋恋不舍也带来阵痛。我走后,少了我的叽叽喳喳,父亲母亲会孤单吗?以后母亲做饭的时候,还会烧很多我爱吃的菜吗?在起夜时,她还会习惯性地看一眼我的房间吗?我带着无尽的思念,将道不尽的感激诉诸笔端。
小时候,我不是一个安分的孩子,所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说的便是我。把我拉扯长大,本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还要把我照顾好,更是难上加难。初中三年,我是走读生,每天当我放学踏入家门的那一刻,家里的饭菜总是刚好出锅。要知道,我有时候要打扫教室卫生,有时候贪玩,流连路边的花花草草,每天到家的时间都不一样。可是每次踏进家门的那一刻,我总能听到母亲用锅铲盛菜的声音,不早不晚,分秒不差。为此,我一直感到困惑,难道母亲是预言家,能精准预料我踏入家门的时间?
直到2023年冬天,我放寒假回到家里,一切答案才悄然揭晓。那天晚上,我百无聊赖地等着母亲下班回来,一听到上楼的脚步声,我便迫不及待冲到门口。这时候,我才明白,原来母亲是听到我上楼急促的脚步声,才把菜从锅里盛起来的。所以,那时候的每一天晚上,她都在门前守候着,等着我上楼的脚步声,而且她总能精准辨别出我的脚步声。因为我的脚步声里有着独特的一个孩子放学回家的急切,也承载着一个母亲沉甸甸的盼望。
我早已不记得伏案学习的深夜,也不记得听过的成千上万节课,更不记得刷过的无数道数学题,可偏偏记得锅铲和锅底碰撞的声音,还有昏黄灯光下那冒着热气的一碗汆肉汤。我夹起一块肉,入口绵长而清醇。如今,我尝过很多美味佳肴,火锅、烤肉、日料、西餐,可偏偏最怀念南方飘着细雪时,母亲端上来的那一碗冒着热气的汆肉汤。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走过无数个季节,跨越年岁的转角,我一点点长大,第一次学会叫妈妈,第一次学会走路,第一次学会骑自行车,第一次念书,第一次读大学,第一次离开父母独自生活。可是,我常常忘记,母亲也曾是一个貌美如花的少女,也曾在呵护中长大,也曾骑着自行车在林间小路留下独一无二的青春印迹。只是,她选择了母亲这重身份,从此选择了柴米油盐。我不知道该用怎样的语言向母亲表达感激之情,因为任何赞美母亲的话语都在母亲对我细水长流的爱面前显得苍白。
我想起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一个女人的故事》中的一段话:“是她(母亲),以及她的语言、她的双手、她的姿势,她走路和微笑的习惯,把现在我所是的妇女和曾经我所是的女孩联系起来。”这是一种带着宿命论色彩的“脐带传承”,母亲把我们带到这个世界,也成为我们和这个世界的最后一根纽带。
落笔,我又闻稷下铃声起。
(作者系山东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2021级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