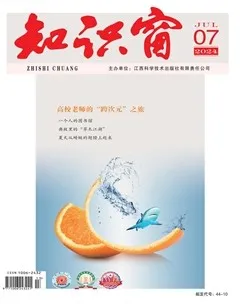怀民亦未寝
北宋元丰六年(公元1083
年)的一个冬天,一个被贬的官员来到黄州,寄居承天寺内。
他有一个很亲民的名字:张怀民,字偓佺。
张怀民谈不上是什么大人物,也没有过人之处。要说有,可能也就“偓佺”这个字很特别。
根据汉代刘向在《列仙传·偓佺》中的描述,偓佺是槐山上的采药人,喜欢吃松子,身体长毛,又厚又长,足有7寸(约23厘米),双眼可以朝不同的方向看,身体特别好,奔走如飞,跑得比马还要快。
张怀民给自己起这么个“仙儿”的字,可能是因为他心里很向往神仙般逍遥自由的生活。在现实中,张怀民却没有那么逍遥自由,甚至经常碰壁——就像这一次,他被贬黄州。好在黄州有一座承天寺,愿意接纳他疲惫的身躯与受伤的灵魂。
经过连日奔波,张怀民早已觉得有点疲惫,打算早点睡觉。僧人扫洒修行的声音早已被浓浓夜色淹没,四周寂静如死。可是躺下许久,张怀民丝毫没有睡意,他好像听到了飞鸟的一声哀鸣,于是坐起身来,隔窗望去——屋外有风,树影在月光下摇动。
张怀民挑起灯花,看着跳跃的孤灯烛光,微微叹息着,思索着,也等待着。突然,屋外响起了叩门声,他欣然起身开门,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苏轼。
说实话,此刻的张怀民太需要有人来陪自己说说话了。但苏轼仅微微一笑,并没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宽慰,只是拉起张怀民的手,邀他到院子里散步赏月。这夜的月亮又圆又亮,月光照在庭院里,像积满了清水一样澄澈透明,水藻、水草在水中纵横交错。哪里来的池子?张怀民以为自己看错了,待他挑眉细看才发现,原来是竹子和柏树的影子。
苏轼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对张怀民说:“哪一个夜晚没有月亮?又有哪个地方没有竹子和柏树呢?只是缺少像我们两个这样清闲的人罢了。”
苏轼并不知道,几百年后,有个叫张岱的人,也有过这样的幸运。那年冬夜,大雪茫茫,张岱想去湖心亭看雪。他乘上小舟,独自前行。他心想:除了自己,哪个人能有这样的闲情?但到了湖心亭,他发现有两个人在此煮酒赏雪……我想,张岱和他们也一定是这样清闲的人。
张怀民看着认识多年的苏轼,突然感到有些陌生。是的,他发现苏轼变了,不再是那个“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的大学士。张怀民哪里知道,经过4年的黄州生活,苏轼真的不再是苏轼,而是变成“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苏东坡。但张怀民知道的是,苏东坡和自己一样,都是被贬黄州,甚至连原因都是一样的。苏东坡的到来,并不是因为他与自己同病相怜,而是心有灵犀。
所以,没有慷慨激昂,也无侃侃而谈,没有抱怨,也无牢骚,苏轼和张怀民甚至什么都没说,只是散散步,赏赏月——或许最动人的,仅仅是平常。
苏东坡看着张怀民,想起四年前的自己;张怀民看着苏东坡,可能也会看到自己的未来吧。
不辜负月色优美的最好方式,只有写诗词了。苏东坡用短短的84字,把这一夜的月光记了下来——就是大名鼎鼎的《记承天寺夜游》。
其实对于张怀民来说,他不需要所谓的感同身受的安慰,或者诗词歌赋的鼓励,他需要的,只是一个能来陪自己的故人。“最难风雨故人来”,难的不是风,不是雨,而是故人能来,还揣着一颗懂自己的心。
所幸,苏东坡能“欣然起行”,而刚好,“怀民亦未寝”。